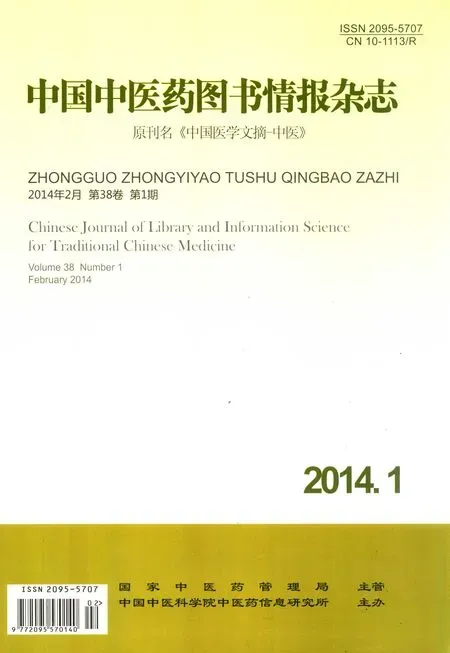对中医发展的哲学思辨
王松俊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北京 100850
对中医发展的哲学思辨
王松俊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究所,北京 100850
文章就中医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包括中医的“观念”能够被现代“转译”吗,“关系实在论”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吗,真能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吗,真能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吗,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的救命稻草吗,“分子中医药学”能救中医吗,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文章认为,中医发展的道路仍不清晰,还需继续求索。
中医;哲学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1]王松俊.辨证中医:对生命的哲学思考[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8.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TCM; philosophy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王松俊,研究员,研究方向:医药科技发展战略,科研管理,医学科技情报。E-mail: wangsjamms@sohu.com
2013-04-08,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