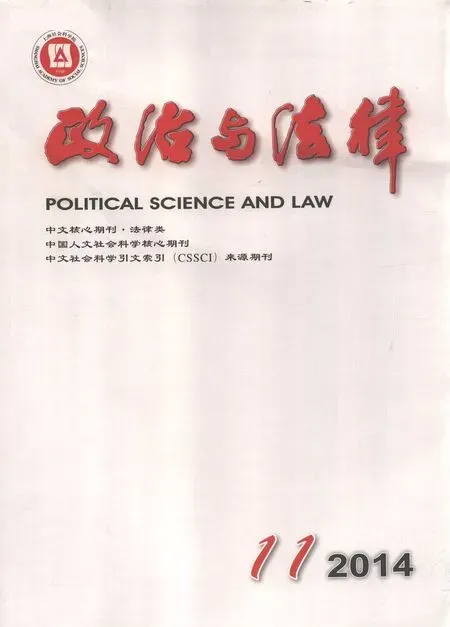美国“流动人口”的平等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牟效波
(北京行政学院法学部,北京100044)
美国的“流动人口”曾经受到各种歧视,他们不被称为“流动人口”,而通常被称为“新来者”(new comer)或者“州的新公民”(new state citizen)。有的州制定了一些法律,在福利援助、投票权、免费医疗服务等方面区别对待来自外州的新来者,通常使用的方法是要求申请者在申请或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已经在本州住满一年。这种“居住期间要求”(durational residency requirement)频频受到挑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也发展了丰富的判例。
一、基于平等保护条款的审查
可能是由于州法中的“居住期间要求”表面上直接表现为歧视新来人口,最高法院一开始援引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来推翻州法。①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各州不得在其管辖区域内,对任何人拒绝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
(一)“夏皮罗案”与平等保护的严格审查
“居住期间要求”系列案从“夏皮罗案”开始。②Shapiro v. Thompson, 394 U. S. 618 (1969).在1969年的“夏皮罗案”中,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相关法律拒绝向那些在本州或特区内居住不满一年的申请者提供福利援助,不满足条件的福利申请者在其申请遭到拒绝后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三个联邦地区法院都判决这样的法律规定违宪。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在平等保护条款之下使用了严格审查标准,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毫无疑问,在每一个案件中,等待期间要求的结果是在所有贫穷的居民家庭之中制造两个类型,而除了一类居民是那些在本辖区居住了一年或更多的时间,另一类居民在本辖区居住不满一年之外,他们之间却没有什么分别。基于这个唯一的区别,第一类居民得到福利援助,而另一类居民被拒绝福利援助。这些家庭依靠福利援助才能获得微薄的收入以生存下去——食物、居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即使在平等保护的传统标准之下,根据他们是否在本州居住满一年来区分这些福利申请者似乎也不合理并违宪。但是,传统标准当然不适用于这些案件。因为这里的划分触及到州际迁移这项基本权利,它的合宪与否必须用更严格的标准来判断,即它是否提升了一项‘迫切’(compelling)的政府利益。在这一标准之下,等待期间要求很明显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③Id., at 627, 638.
从上面的表述来看,最高法院在“夏皮罗案”中的审查方法是:由于州或特区的法律将贫穷的居民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辖区居住满一年的居民,另一类是在本辖区居住不满一年的居民,法院应当审查这里的立法归类是否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而且由于等待期间的要求侵犯了福利接受者州际迁徙这项“基本权利”,法院需要在平等保护条款之下对所主张的州的利益进行严格审查,即州的立法是否提升了一项“迫切”的政府利益。
就在平等保护条款的严格审查标准之下,最高法院审查了州所主张的各种利益。首先,州政府主张“等待期间要求”是一项保护性策略,以维持州的公共援助项目的财政完整性,因而是正当的。他们声称,在一州居住的第一年需要福利援助的人很可能成为州的福利项目的持续负担,因此,如果通过在第一年拒绝向他们提供福利来阻止这些人进入本辖区,州援助长期居民的项目就不会因穷人的大量涌入而受到削弱。最高法院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将需要或可能需要救济的穷人排除出本辖区是这些规定的特定目标,然后指出,“我们确信一年的等待期间设置非常适合用来阻碍需要援助的贫穷家庭的涌入,但禁止穷人迁入本州的目的本身在宪法上是不被允许的”,④Id., at 629.因而不能成为一年等待期间制造的归类的正当理由。
与此相关的一项主张是,即使一州试图阻止所有穷人是不被允许的,但这项归类可以阻碍那些进入本州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救济的穷人,因而是正当的。对此,最高法院指出,这一主张没有证据,而阻止新来者的归类是包括一切的,将怀着其他目的来本州的大多数人与那些来本州仅仅为了得到更高福利的人混在了一起。因此,这些法案实际上都假定,住在本州的第一年申请福利的每一个人来本辖区都仅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一州不能从总体上将穷人拦在州外,也同样不能将那些追求更高福利的穷人拦在州外。任何这类区分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与其他进入一州的穷人相比,进入一州希望获得更高福利的穷人因某种原因不值得帮助。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位为自己和她的孩子们追求新生活的母亲,因为她格外考虑了一州的公共援助水平就更加不值得帮助。无疑,这样一位母亲并不比一位迁入一州为了利用更好的教育质量的母亲更不值得获得援助。⑤Id., at 631-632.
州政府还主张,受到挑战的这种分类试图基于他们通过缴税对本共同体做出的贡献区分新老居民,因而应当获得维持。最高法院对此指出:“上诉人的推理将在逻辑上允许本州阻止新居民进入学校、公园和图书馆,或者剥夺他们获得警察和消防保护。平等保护条款禁止政府服务的这种分配。”⑥Id., at 632-633.
关于维持州的财政完整性(the fiscal integrity)的辩护,最高法院指出:“我们认可,一州在维持其项目的财政完整性上具有一种正当利益。它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努力限制开支,无论是在公共补助、公共教育,还是在任何其他项目上,但一州不能通过不公正的区分其公民的种类达到这一目的。”⑦Id., at 633.
州政府还提出某些行政和相关治理目的,据称可以借助“等待期间要求”来实现,从而为这项要求辩护。他们辩称,这项要求有如下好处:(1)便于制定福利预算计划;(2)提供一个居住的客观标准;(3)使欺骗性接受者从不只一个辖区得到福利的机会最小化;(4)鼓励新来的居民尽快进入劳动力行列。对此,最高法院首先指出:“在从一州迁移至另一州的过程中,被上诉人行使着一项宪法权利,除非是提升一项迫切的政府利益,任何惩罚这项权利行使的分类都是不合宪的。”⑧Id., at 634.然后其逐个回应了上述主张:“‘等待期间要求’便于预算的可控性(budget predictability)的主张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三项上诉案的记录中,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两州或哥伦比亚特区在事实上使用一年的期间要求作为一项手段,来预测在本预算年需要援助的人数。”⑨Id.“等待期间作为一项管理上有效率的经验法则可以用来确定居民身份同样经受不住审查。在同意审查之后,福利机构调查申请者的职业、住宅和家庭位置,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必然得知确定申请者是否是一位居民所依据的事实。”⑩Id., at 636.“一州没有必要使用一年的等待期间防止欺骗性的福利接受者,因为严厉程度更小的手段存在,并得到使用,使危害最小化。而且,各州福利部门之间的合作很普遍。一个类似程序可以有效防止双重付款的危险。因为双重付款可以借助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可以避免,拒绝向所有贫穷的新来者提供一整年的援助这种轻率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合理的。”⑪Id., at 637.“宾夕法尼亚州提出,一年的等待期间可以作为鼓励新居民迅速参与到劳动力行列的一种手段而受到辩护。但这一逻辑如果成立,也需要对本州的长期居民规定一个同样的等待期间。一州鼓励就业的目的不能为仅仅向新居民强加一年的等待期间提供合理根据。”⑫Id., at 637-638.基于以上分析,最高法院认为,在严格审查标准之下,“等待期间要求很明显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
在之后的相似案件中,最高法院沿用了“夏皮罗案”的审查思路。在1972年的“禁止投票案”中,⑬Dunn v. Blumstein, 405 U. S. 330 (1972).法院认为,田纳西州“法律将居民分为两类,老居民与新居民,并歧视后者到完全否定他们投票机会的程度。这里提出的宪法问题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否允许一州通过这种方式区别对待它的公民”。⑭Id., at 334-335.其最后的判决是,该州的“居住期间要求”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它们对于提升一项迫切利益——无论是避免非居民的欺骗性投票,还是促进获得有知识的投票者这一目标——是不必要的。
1974年的“拒绝提供免费医疗案”推翻了穷人享受免费医疗服务的居住期间要求,也同样延用了平等保护条款与“惩罚”理论支持的严格审查标准。⑮Memorial Hospital v. Maricopa County, 415 U. S. 250 (1974).上诉人亨利是一个穷人,患有慢性哮喘和支气管疾病。1971年6月,他从新墨西哥州移居到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Maricopa)。1971年6月8 日,他的呼吸病严重发作,并被送到同为本案上诉人的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即一家非营利性私人社区医院。根据亚利桑那州关于穷人医疗的法案,纪念医院通知马里科帕县管理委员会,本医院正在负责治疗一位穷人,他可能有资格获得县的照顾,并要求将亨利转移到该县的公共医疗机构。医院要求县政府为亨利获得的医疗服务偿付一千二百多美元的费用。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县政府负有向他们的穷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照顾的强制性义务。但法案要求一位穷人成为本县的居民十二个月后才有资格获得免费的非紧急医疗照顾。因此,马里科帕县仅仅因为亨利成为本县的居民还不到一年,拒绝接收亨利到公共医院治疗,并拒绝向纪念医院偿付医疗费。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开篇指出:“这里的宪法问题是,这项居住期间要求是否违反本院在‘夏皮罗案’中使用的平等保护条款。”⑯Id., at 251.接着,最高法院认为:“在决定受到挑战的居住期间规定是否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时,我们必须首先通过观察分类性质和受到影响的个体利益来确定这里的立法分类必须满足什么样的证明负担。”⑰Id., at 253.确定的结果是,“亚利桑那州对免费医疗的居住期间要求必须因一项迫切的州益才能获得辩护”。⑱Id., at 254.因为,“在‘夏皮罗案’中,我院认为拒绝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构成一种惩罚。……不管‘夏皮罗案’中的惩罚概念的边缘含义是什么,至少很明显,医疗照顾是和福利援助一样的‘一项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亚利桑那州被要求向亨利提供福利援助,使他免受住房不足造成的困苦或者饥饿的痛苦,却拒绝向他提供对减轻他的病痛必需的医疗照顾,这的确是非常荒谬的。”⑲Id., at 259-260.
(二)“佐贝尔案”与平等保护的“最小合理性”标准
在以上判例中,最高法院之所以使用平等保护的严格审查标准,是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州法阻碍或损害了州际迁徙权。而州法之所以对州际迁徙权构成损害,是因为州法拒绝向新来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如果一项州法既没有阻止州际迁徙,也没有因拒绝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惩罚新来居民,严格审查标准是否还能适用呢?
1982年“佐贝尔案”的案件事实就对“惩罚”理论的适用提出挑战。⑳Zobel v. Williams, 457 U. S. 55 (1982).1976年,阿拉斯加州通过宪法设立了一项永久基金,而且每年将该州矿产收入的25%存入这项基金。1980年,该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分红计划,每年向本州的成年居民分配一部分该基金的收益。在此计划之下,从阿拉斯加建州的第一年即1959年起,每一个成年居民按照他们在本州居住时间长短,每居住一年可以得到一个红利单位。该法案将1979年财政年度中的每个红利单位确定为50 美元,于是,一位居住了一年的居民可以得到1 个单位或者50 美元,而一位从1959年建州开始就是阿拉斯加居民的人可以得到21 个单位或1050 美元。佐贝尔夫妇从1978年开始成为了该州居民,于1980年提起诉讼,挑战这项红利分配计划,主张该计划侵犯了他们的平等权和他们的以下宪法权利:向阿拉斯加州迁徙的权利、在那里定居的权利以及之后享受本州公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虽然佐贝尔夫妇主张了这些权利,但最高法院的法院意见还是把问题确定为,阿拉斯加州基于公民居住时间长短分配红利的计划是否侵犯阿拉斯加州更新居民的平等保护权。㉑Id., at 56.
这里的问题是,红利并不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阿拉斯加州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可能已经通过各种福利、医疗保障等项目得到满足。因此,当案件上诉至阿拉斯加州最高法院时,法院认为阿拉斯加州的红利分配计划不会引发基于联邦宪法的严格审查,因为新居民没有被阻止迁移到阿拉斯加,而且没有拒绝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政府服务。于是,阿拉斯加州最高法院在本州宪法之下使用了中等审查标准,并判决阿拉斯加州的红利分配计划通过了审查。在最高法院,阿拉斯加州政府很自信地主张,分配非生活必需的利益时,基于居住时间长短的区分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合理”即可,并提出了这项计划如此分类的目的。第一,这项计划鼓励阿拉斯加州居民不会投票支持立即将这项永久基金全部分光。因为,如果所有的分配必须和将来的新来者平等分享,当前的居民就会希望通过要求当前更大的配给量而提高他们的所得份额。第二,因居住年限的递增而递增的收益可以鼓励阿拉斯加人留在本州,以收获增加的利益。第三,这项利益策略是对长期居民过去贡献的回报。
最高法院的法院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挑战阿拉斯加州关于其法律只需要满足最小合理性检验的主张,因为“这项策略连最小程度的检验都通不过”。㉒Id., at 60-61.阿拉斯加州前两项主张的问题在于,只要根据通过该法案“之后”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时间的长短决定分配红利的多少就足以达到这两项目标,没有必要再追溯到阿拉斯加建州的年份,并将过去居住的年限也计算进去。㉓Id., at 62-63.最后一项目标是回报过去的贡献,这很明显可以通过受到挑战的立法归类得到满足。但这项目标根本就是不合法的。㉔Id., at 63.
1985年的“退伍军人福利第一案”沿用了“佐贝尔案”的审查方法,推翻了新墨西哥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为越战退伍老兵免除交税义务,但只有在1976年5月8 日之前就居住在本州的才能享受这项待遇。法院意见认为,对符合条件与不符合条件的老兵的区分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因为“法案的策略不能通过最小合理性审查标准”。㉕Hooper v. Bernalillo, 472 U. S. 612 (1985).
在1986年的“退伍军人福利第二案”中,㉖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v. Soto-Lopez, 476 U. S. 898 (1986).推翻州法的法官意见在审查标准上出现分歧。该案中,法院推翻了纽约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将退伍军人获得公职的优先权限制在那些参军时就住在纽约的退伍军人。这意味着,参军时不在纽约州,但退伍后到纽约州居住的军人因这项优先权的设置而受到歧视。布伦南大法官撰写、其他三位大法官加入的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则基于1972年“禁止投票案”和1974年“拒绝提供免费医疗案”㉗Dunn v. Blumstein, 405 U. S. 330 (1972); Memorial Hospital v. Maricopa County, 415 U. S. 250 (1974).中的“惩罚”理论,认为“即使暂时剥夺非常重要的利益和权利也对惩罚移民起作用”,从而引发严格审查标准。㉘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v. Soto-Lopez, 476 U. S. 898 (1986), at 899-912.而伯格首席大法官和怀特大法官在赞同意见中遵循“佐贝尔案”和“退伍军人福利第一案”㉙Zobel v. Williams, 457 U. S. 55 (1982); Hooper v. Bernalillo, 472 U. S. 612 (1985).的判决方法和标准,认为拒绝向新居民提供退伍军人的优先权不能通过平等保护的合理性审查。㉚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v. Soto-Lopez, 476 U. S. 898 (1986), at 912-916.
二、平等保护条款的局限
从“夏皮罗案”开始,最高法院在绝大多数判例中都在平等保护条款之下审查区别对待新来人口的州法。但是,这些判决没有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州法为了提升一项“迫切”的利益,才能区别对待来自外州的新来人口,而防止那些追求更高福利的外州穷人来本州定居并分享本州财政、㉛Id., at 631-632.维持本州财政完整性的目的、㉜Id., at 633.用更多的分红回报老居民过去的贡献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呢?㉝Zobel v. Williams, 457 U. S. 55 (1982).为什么一州在分配政府服务时区别对待老居民和新来者就这么“难”呢?
这与司空见惯的情况似乎不一致,常见的情况是一州可以区别对待本州居民和外州居民。一州可以只向本州居民发放社会福利,不必向外州居民或在本州短期停留的外州居民发放;一州可以只向本州居民提供廉租房,不必向外州居民提供;一州可以只向本州居民减免公交车费用,如果区别对待本地原有居民与新来人口不被允许这一判断成立的话,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必定与那些合理的区别对待本州(省)人与外州(省)人的情形存在实质不同,而这种不同是平等权条款无法单独回答的。最高法院要使自己的判决有说服力,就不能仅仅依靠平等权条款,而是必须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和依据。
三、“萨恩斯案”:优惠与豁免权条款
早在1984年,科恩教授就针对“夏皮罗案”、“禁止投票案”、“拒绝提供免费医疗案”、“学费差异案”、“离婚限制案”和“佐贝尔案”发表评论,认为最高法院在这些案件中的判决结果没有问题,但使用的审查方法和标准没有说服力。㉞W illiam Cohen, Equal Treatment for New comers: The Core Meaning of National and State Citizenship, 1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9 (1984).因此,他认为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这项解释根植于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优惠与豁免权条款”。该条款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法律,来剥夺合众国公民的优惠与豁免权。㉟Se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ndment XIV, Section 1.科恩教授的以下论述值得认真研读:“一开始,我们确实需要记住,问题起源于以下背景:州可以将州的优惠和利益仅提供给它自己的公民。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这种区分是允许的,尽管乍看上去宪法第四条中的优惠与豁免权条款要求平等对待州的公民与其他州的公民。很明显的解释是,州之所以作为州而不是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府的部门存在的现实,需要一种观念的存在:州的公民拥有州有资源,而且一州并不需要与整个国家分享它的财政。但是,州将集体所有的资源仅仅分配给各自共同体成员的权力,受制于一项明显的推论。各州被否定全部主权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在这个共同体中,州不具有决定成员身份的权力。根据第十四修正案,所有合众国公民一旦在一州安顿下来,他们就立即成为这个州共同体的全权成员(full-fledged member)。(如果非要为这一观念寻找宪法条文依据,我会选择第十四修正案的优惠与豁免权条款。无论何种权利附着于合众国公民身份的概念,最少受到争论的应当是自由选择州的公民身份的权利。)各州老住户应得到州有资源更大份额的决定,与要求各州将新来居民作为本州共同体的全权成员来对待的宪政结构不相符。”㊱William Cohen, Equal Treatment for Newcomers: The Core Meaning of National and State Citizenship, 1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9 (1984), at 17.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科恩教授认为,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公民身份条款意味着州的公民身份取决于居住行为,一位合众国公民一旦选择居住在一州,即成为这个州的全权公民,必须受到该州的平等对待;这既是一项明确的宪法条款,也是一种观念;而在整个国家自由选择居住地(也就是选择州的公民身份)的权利受到优惠与豁免权条款的保护,各州无权否定;在一州安顿下来即成为该州全权成员的权利也受到优惠与豁免权条款的保护。
他在十年之后即1994年的一篇更新文章中说:“在这十年中,几乎没有发生变化。”㊲William Cohen, Discrim ination against New State Citizens: An Update, 11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73 (1994), at 75.最高法院在“退伍军人福利第一案”、“退伍军人福利第二案”中的判决仍然沿用平等保护条款之下的最小合理性标准,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有的案件中不能依靠区别对待新旧居民的办法实现财政的完整性,㊳Shapiro v. Thompson, 394 U. S. 618 (1969).但在有的案件中却可以依靠区别对待新旧居民来避免财政完整性受到破坏的一种特殊情形——“离婚工厂”;㊴Sosna v. Iowa, 419 U. S. 393 (1975).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有的案件中不允许政府回报老居民为本州做出的贡献,㊵Zobel v. W illiams, 457 U. S. 55 (1982).而在有的案件中却允许州立大学这样做。㊶Starns v. Malkerson, 326 F. Supp. 234, aff’d, 401 U. S. 985 (1971).因此,科恩教授在1994年的这篇文章中再次耐心地重申了他的解释:“合众国公民自然成为他们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没有等待期间。而且,就像否定这些新来者的公民身份会违反宪法一样,仅仅在名义上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而实际上仍然将他们当作其他州的公民对待也违反宪法。这意味着,拒绝向与其他公民处境类似的新来居民提供利益是违宪的——仅仅受制于合理地确保新居民的宣称是真诚的(bona fide)这样的情形。”㊷William Cohen, Discrim ination against New State Citizens: An Update, 11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73 (1994), at 79.
受科恩教授的影响,最高法院终于在科恩教授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十五年后即1999年的“萨恩斯案”中采纳了科恩教授的解释。㊸在史蒂文斯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中,脚注20 参考并引用了科恩教授于1994年发表这篇文章。Saenz v. Roe, 526 U. S. 489(1999), at 507, note 20.而且,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也接受了科恩教授的建议,在他提供的审查方法之下审查了加州的福利法案。
1992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项法案,限制新来居民可以获得的最高福利。这项计划将使得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居住不足十二个月的家庭的福利水平被限制在这个家庭原来居住的州发放的福利水平。三位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分别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科罗拉多州,为了逃避家庭暴力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在该项法案生效后的十二个月中,他们每月得到的福利大大少于该法案生效之前的数量。其中的前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和前俄克拉荷马州居民都是三口之家,他们将分别得到190 美元和341 美元,而加利福尼亚州三口之家的全部福利是641 美元;其中的前科罗拉多州居民是两口之家,每月只得到280 美元,而加利福尼亚州两口之家的全部福利是504 美元。于是他们于同年12月挑战了这项“居住期间要求”的合宪性。史蒂文斯大法官(Justice Stevens)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本案所涉及的是迁徙权的第三个方面——新来公民享有与本州其他公民同样的优惠与豁免权。那项权利不仅受到新来者作为一州公民的地位的保护,而且受到他作为合众国公民的地位的保护。尽管在第十四修正案的优惠与豁免权条款的含义范围上存在根本不同的观点,这在‘屠宰场系列案’的多数与反对意见中得到非常显著的表达,但以下含义一直是一个共同的底线:这项条款保护迁徙权的第三个方面。(米勒大法官在“屠宰场系列案”中撰写的多数意见认为:“这项条款赋予的其中一项特权‘是合众国的一位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真诚的定居而成为这个统一国家的任何一个州的公民,并和该州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答辩人及他们代表的这类成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这一点没有争议,他们对福利的需要与他们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间长短无关这一点也没有争议。如果他声称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公民的真诚性受到质疑,我们就不必继续考虑一位公民居住时间长短的不同价值。而且,因为无论他们得到什么福利,他们都会在加利福尼亚停留期间消费,认可他们的声称不会有以下危险:鼓励其他州的公民来加州定居,但居住的时间仅仅足以获得一些容易带走的福利,比如离婚或高等教育,然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享用。本案中受到挑战的分类不能因阻止福利申请者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目的而受到辩护。这一目的毫不含糊地受到禁止。加利福尼亚州否认任何将穷人挡在外面的企图,而是为其多层策略仅仅提出了一项财政上的辩护。这项策略的实施将为本州节省约每年1090 万美元。问题不在于这项节省是否是一项合法目的,而在于该州是否要以通过它选择的区别对待手段实现这一目的。平均每位受益者每月普遍减少72 美分的收入也将产生同样的结果。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明确将公民身份与居住行为划了等号:‘这一条款没有规定,也不允许基于居住时间长短规定公民身份的等级。’同样明显的是,这一条款不容许基于他们以前的居住地点将处境相同的公民划分为45 个类别。答辩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居住期间和他们过去的居住州的身份,都与他们对福利的需要无关。简言之,加利福尼亚州省钱的合法利益并没有为其区别对待具有平等资格的公民提供正当性。”㊹Saenz v. Roe, 526 U. S. 489 (1999), at 502-503, 504, 505, 506, 507.
不难看出,上述第一段是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判决的依据,即第十四修正案的“优惠与豁免权条款”以及以其为依据的“公民身份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明确将公民身份与居住行为划了等号”。只要真诚地居住在一州,合众国公民就自然成为这个州的公民。而“优惠与豁免权条款”则保障合众国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并保障合众国公民选择新的居住地因而成为该州公民后,享有与该州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因而各州不能“仅仅在名义上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而实际上仍然将他们当作其他州的公民对待”。因此,只要合众国的某个公民真诚地选择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既不能阻止他的选择,也不能在他定居后区别对待他。这与科恩教授的解释完全一致。
回到案件事实,按照上述前提,加利福尼亚州自然不能阻止外州居民移居本州。至于加利福尼亚州能否通过区别对待新来居民的手段实现省钱的目的,不用说可以通过每人每月减少72 美分来实现这一目的,即使需要救济的新来居民数量使加利福尼亚州无法承担这些福利项目,从而使加利福尼亚州的福利水平大大降低甚至取消,加利福尼亚州也不能依靠在本州制造特权等级来维持福利项目。
那么,这些居民是否真诚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呢?最高法院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福利项目不太可能吸引不真诚的居住行为。因为这些福利项目基本上都在加利福尼亚停留期间消费,不像“离婚”和“高等教育”一样可以带回原来的居住地享用。因此,如果加利福尼亚州仍然以“居住期间要求”作为确认居住行为真诚与否的手段,这项手段就是歧视新来居民的借口。
四、中国的同类问题分析
从“夏皮罗案”开始,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使用了平等保护条款的严格审查标准,在后来的“佐贝尔案”等一些案件中,由于州法并没有涉及“生活必需品”,最高法院转而使用了平等保护的“最小合理性”标准。但基于平等保护条款的审查思路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何区别对待老居民与新来居民和区别对待本州人与外州人两种情形不一样,因而缺乏说服力。在科恩教授的呼吁下,最高法院最终在“萨恩斯案”中采纳了“优惠与豁免权条款”作为审查这类案件的依据。“自由选择居住地”并且“在定居后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是“优惠与豁免权条款”的应有之义:合众国公民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一旦在某地区定居,自然成为这个地区的居民或公民,并且必须受到同该地区其他居民或公民一样的平等对待,除非某些情形导致不真诚的定居行为极有可能发生,但也不能受到过长等待期间的限制。基于优惠与豁免权对一国公民的重要性,笔者希望它所包含的观念应成为我国制定和改革“流动人口”政策与法律的出发点。
在中国,由于没有充分重视本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选择居住地点并且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人口流动面临障碍,最终导致国民迁徙自由及附带利益的损失。在一个国家内,如果人们跨地区迁徙不像跨国迁徙那样难,无需流入地的“签证”,到流入地后无需拿到“绿卡”或“国籍”就能永久居住,并且不会因为自己的迁徙行为而在迁入地面临子女入学难等种种重大不便,那么国民将有更大的自由度享受国内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在变换工作和生活方式时将减少顾虑。这是国家这种共同体应该给自己的国民提供的基本便利。有些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甚至人为划拨的资源优势获得良好发展,然后拒绝其他落后地区的民众前来定居分享,为新来定居的居民设置种种不便,是不妥当的。一个统一国家不仅意味着疆域的完整,还意味着内部尽可能的融合,至少包括国土共有、市场统一、道路共享、人口一体。“自由定居后受到平等对待”的公民权利之所谓可以成为我国制定和改革“流动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因为我国和美国一样,可能会面临某些极端的、需要对这项权利进行限制的情况。但既然这项权利是一国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便利,它就不能动辄受到限制,要限制它就必须基于更重要的利益考虑。
目前,在我国有一部分迁徙者,他们拿到迁入地的户籍比出国拿到绿卡或国籍都难,他们在迁入地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比在国外作为暂住者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都多,比如他们的子女在迁入地入读小学比在国外暂住期间入读小学都难,他们的子女都不能在迁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那么,在我国是否存在一些更重要的利益考虑,可以为限制迁徙人口的平等权提供正当辩护呢?我们不妨稍作分析。
其一,要考虑的是城市资源承载力难题。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学者经常被提及也是最可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是“城市资源的有限承载力”。这一难题似乎为控制人口规模提供了理由,而控制人口规模似乎又为限制落户提供了理由。但是,我们稍作推敲就会发现这个理由似是而非。
首先,城市资源的承载力的确不是无限的,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水资源就极端缺乏,但当资源缺乏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自然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或者坚持在本地受煎熬,或者移居外地。人们的头脑应该不会简单到面对资源缺乏时没有任何应对措施的程度,到时应该会去选择更好的居住环境,爱北京、上海、广州也不会爱到与这些城市共生死的地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事实上,正是人们的选择能力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源分配达至一种动态平衡,而不是在一个国家中,好的地方越来越好,差的地方越来越差。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来到特大城市生活、工作,还是因为这里的资源相对丰富,有某种更强的吸引力。
其次,目前的流动人口落户政策本身就使“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论调不攻自破。当前是否到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时候了呢?如果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饱和,为什么每年都允许大量具有高学历的毕业生在特大城市落户?为什么有的特大城市还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有人可能提出,目前虽然特大城市的人口尚未饱和,但已经到了饱和的边缘,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流入。笔者认为,且不说这种计划控制有无必要,即使必要,特大城市可以每年只允许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落户,以试探人口规模的上限,那也没有必要禁止已经在特大城市生活若干年的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更不应该选择性地批准“高学历”、“紧缺型”人才落户。事实上,如果人口规模的平衡不是主要依靠人们自己的理性选择来实现,而是任由当地政府和当地民众说了算,资源有限就很容易成为排外的借口。
其二,要考虑的是“捞一把就走”与应对之策。
诚然,为新来人口分享本地资源设置一定的等待时间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合理,有一种理由是正当的,即避免不真诚定居的外地人在本地获得一些容易带走的福利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享用,因为这将导致本地的资源被“洗劫一空”。但是,这个理由不能滥用。事实上,本地的大多数资源只要分配方式合理,都不适合“捞一把就走”。我们不妨拿北京的保障房福利政策作为一个例子稍作分析。人们通常会担心,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到北京,宣称自己真诚地定居在这里,但由于自己很穷,需要政府向他提供保障房,一旦政府给他安排了经济适用房,他有可能把该房出租,然后每个月拿着高额租金回到消费水平很低的老家享用,或者在满足一定年限条件后,按市场价把经济适用房卖掉,拿着赚取的差价房款回到老家享用。这种情况并不是允许外地人落户北京导致的,而是政府的保障房政策不合理且监管不力造成的。如果政府不提供这种具有所有权的经济适用房,而只提供没有产权的廉租房,或者严格禁止经济适用房转让,房主就不会卖掉房子,带着房款回老家享用;如果政府监管得力,就能及时制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转租行为,从而堵住本地资源流出的漏洞。并且,这样的福利政策不必专门为防止不真诚的迁徙定居行为而制定。事实上,如果政府的保障房政策不合理且监管不力,本地人也照样可以钻政策的漏洞,当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转时,也可能继续占有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转租给他人坐享租金,甚至有可能拿着租金到外地享用。因此,只要保障房政策合理,且监管得力,不真诚的定居者根本没有机会从中“捞一把就走”,换言之,在这项福利的分配中,不会引致“捞一把就走”的不真诚定居行为。
然而,的确有一些资源可能会吸引不真诚的定居者,目前许多省市的高校招生名额就是其中之一。还是以北京为例作简要分析。从全国来看,坐落于北京的部属高校数量最多,这些高校在每年的本科招生时,分配给北京的招生名额最多,与其他省市得到的名额不成比例。因此,在北京参加高考和招录的考生就更容易被大学录取。假如北京市允许没有北京户籍的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和高校招生,那么外地学生的家长就极有可能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参加高考。不来北京读一段时间高中,直接在北京报名参加高考自然不被允许,但是他们可以装作真诚的定居者,在离高考两三个月时来北京租房居住,宣称自己已经真诚地定居在北京,在自己的孩子高考结束并被大学录取后再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真诚定居的“高考移民”。
部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均衡可能导致“高考移民”的产生,而这种不均衡本身是不公平的。这里,暂且不论这种不公平因素,暂且承认这些招生配额是属于北京的资源。那么,北京市能否完全禁止没有北京市户籍的高中生在北京参加高考呢?它可以怎样避免上述不真诚的定居者分享北京的高校招生名额呢?有人可能会说,在巨大的吸引力面前,家长在高考前几个月在北京买房居住都无法证明他们是真诚的定居者,因为房子短期内可以再卖掉。思来想去,大概也只有美国的办法可以派上用场,即设立一段等待期间,规定外来定居者只有在北京居住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并分享北京的招生配额。在美国的有关判例中,这段等待期间是一年,北京市也可以选择一定的时间段,但这个期间不能太长。毕竟,这是一国公民受“优惠与豁免权”保障的迁徙自由原则做出的一种让步。在笔者看来,两年的等待期间就过长,毕竟有一大部分随迁子女的家长的确是真诚地定居在北京,在此他们做生意、打工,这样能比在老家干农活挣更多的钱。如果规定随迁子女在北京居住两年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假设他们的父母来北京居住时,他们刚刚开始读高二,那么为了不中断与高考命题方向一致的高中教育,他们就只能与父母分离近两年时间,这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合适的;或者,随迁子女的父母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户籍地完成高中学业,就会被迫将自己的迁徙谋生计划推迟近两年。这都是一国公民的“优惠与豁免权”受到侵犯的后果。且不说两年的等待期间过长还是不够长,总不能把等待期间设为无限长吧?事实上,一段等待期间的设立并不仅仅是(甚至并不是)对定居真诚度的考验,其更多含义是,如果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已经居住了一年,这已经是不需要再用其他事实证明的定居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