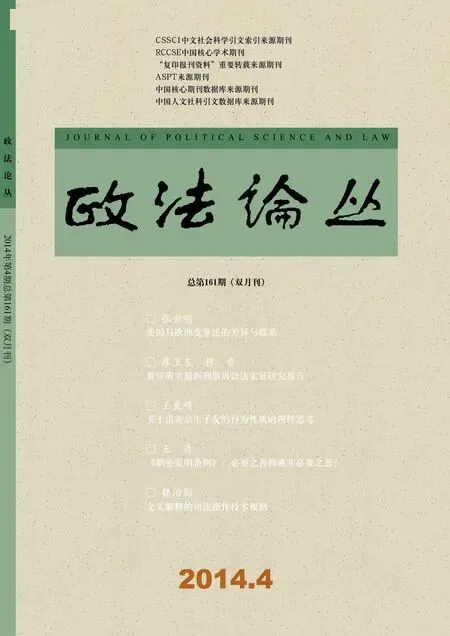美国与欧洲竞争法的差异与联系
张世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欧洲共同体条约》在起草的过程中受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取向的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影响,一些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法律人参与了竞争法条款的讨论和制定。但是,除了起源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所体现出的经济效率的观念之外,其他两个来源却是欧洲本土的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滥用控制方法和在战后时期凸现的德国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与流行的神话相反,欧洲的竞争法不是从美国输入的,或仅仅是行政管制向一个新领域的扩展。它首先是建立在欧洲思想家和决策者为回应欧洲的形势而提出的观念之上,从根本说是"欧洲的"。其传播是沿着本土的渠道,而不是通过模仿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在欧洲传播的。不可否认,美国是反托拉斯法的发源地,被称为美国“圣牛”的反托拉斯法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反垄断法不仅赢得了“宗教”般的地位,而且执法的经验丰富举世无双,成为研究反托拉斯执行变迁的极佳样本。即使在今天,学术界在研究中不提到美国的裁决,就不可能在细节上解决竞争问题,加之,美国在二战以后跃升为超级大国,睥睨一切,势不可遏,各国法律的美国化趋势有增无减,席卷全球。这已经成为美国权力的基盘,以至于有学者将当代法律的“美国时代”与“拉丁中世纪”相比拟。与此同时,美国的判例法伴随着一个优秀的学术话语系统,许多最重要的学术创新来自美国。在法理学方面,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几乎所有的战后的欧洲法律和对法律的理解的根本性的深远变化,均肇端于美国。至少在欧洲竞争法最初阶段,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鼻祖法律制度”。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20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经济的成功使得欧洲政策决策者颇为欣羡。这被欧盟的政策制定者视为一个挑战,力求赶上美国的竞争力。在此大化流行之中,各国无形之中“美美与共”。欧盟竞争法诞生的背景和目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更是统一的单一市场的形成。事实上,欧盟竞争法的方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竞争法作为一种工具来服务于实现统一的单一市场目标,然而,这种老式方法最近已经被抛弃,或至少被补充以更经济的方法。[1]P189从不同的传统出发,欧盟竞争法在某些方面已转向美国竞争法。有些人认为欧盟竞争法的现代化进程始于2004年,其特征就是接受美国反垄断思维,拥抱竞争法更经济的方法。走向美国式的欧盟竞争法的运动或者被明确地见诸法律,或者只是间接地被表现出来,反映了对美国经验的回应。例如,取消通报制度,即经常援引参照美国反托拉斯法工作相当有效而不需要通报系统的事实来证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欧洲的竞争法都是从相同的基本文化和法律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形成于大体上相同的时代,都是对工业化和民主化做出的回应;它们都承认竞争的价值和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的潜在危害。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比较研究能够成为对双方都有用的手段。[2]P7
一、反垄断法律渊源
在反垄断法渊源方面,美国的反垄断法称为反托拉斯法,并且不是一部独立的法律,而是由多部法律构成。1890年,美国颁布了标志现代竞争法产生的《谢尔曼法》。该法不仅是美国现代竞争立法的开端,而且也被全世界公认为现代竞争法的鼻祖和样板。由于该法产生的历史背景缘于反托拉斯运动,故美国反垄断法又称之为反托拉斯法。此后,美国以《谢尔曼法》为基础,针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竞争变化的实际情况,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创设了众多的判例及其法律原则,逐渐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美国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并在其后的100多年中极大地影响了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立法。从总体上看,美国竞争法的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本法律,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二是对基本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规则及相关法律;三是法院审理各种反竞争案件所形成的大量判例以及所确立的各项法律原则。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标志着美国反托拉斯法体系进一步形成。《谢尔曼法》如同“在马被偷之后才锁上马厩的门”[3]P20,且过于抽象和不确定,而这些缺陷在《克莱顿法》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克莱顿法》扩大反托拉斯法的调整范围,对垄断行为和必然导致垄断行为的垄断结构进行了规定和解释,以列举方式作出禁止性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最值得关注的是第5条,确立了概括性条款:“在商业中或者影响商业的各种不公正的竞争方法,均宣布为非法。”[4]此外,针对《谢尔曼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的缺陷,通过该法案在司法部之外另设立反垄断的专门机构,即联邦贸易委员会, 形成了美国的二元竞争执行机制。以上三部法律构成了美国现代竞争法律制度的基石。
尽管如此,《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美国竞争法的三项基本法律,总体来讲都是比较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特别是关于实体性问题的规定,往往不够详细、具体。这不仅给相关执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企业对此亦颇有微词。有鉴于此,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基本法律的修正案,其内容涉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的范围、价格歧视的表现、企业合并的形式以及竞争法例外适用的情况等诸多方面。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有:(1)1936年的《鲁宾逊-帕特曼法》修改了《克莱顿法》第2条关于价格歧视的规定,使之更为严格。作为侵略性竞争的阻止工具,《鲁宾逊-帕特曼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却存活下来,成为小商业者的保护伞。(2)1938年的《惠勒-李法》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做了进一步补充,可以视为美国反托拉斯法对20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回应。《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仅禁止“不公正的竞争方法”,《惠勒-李法》则加入“欺骗性的行为或活动”亦为禁止对象,尤其强调禁止企业登载虚假广告,使该法适用于直接对消费者产生有害影响的商业行为。(3)由于《克莱顿法》第7条仅禁止购买股票方式的反竞争性兼并,从而产生了法律上的漏洞,很多企业仍通过购买对方资产的方式规避法律而迂回到达兼并目的,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法》对这一条做了修正:禁止一切形式的减少竞争的合并,不论是通过购买股票还是收购资产。(4)1975年的《马格纳森-莫斯联邦贸易委员会改进法》强化联邦委员会的功能与权限,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内容进一步扩大到“商业中的或影响商业活动的”行为。(5)1976年的《哈特-斯各特-鲁迪南反托拉斯改进法》建立了联邦并购前通报程序,成为《克莱顿法》第7条A款。因为《克莱顿法》第7条尽管颁布颇有时日,但许多并购法律的实施都被所谓的“半夜并购”所阻碍。在这些案件中,政府的主要求偿权是在并购发生后在法院对其提出起诉,或如果起诉成功的话,试图通过“使鸡蛋复原”的方式剥夺其资产,而这常常发生在公司并购多年之后。1976年的《哈特-斯各特-鲁迪南反托拉斯改进法》的颁布旨在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要求欲进行股份或资产合并的当事方事前通知司法部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且须遵守主管机关所规定的等待期,俾使主管机关得有充分的时间审查该交易可能产生的竞争影响。除了国会立法外,美国由于是判例法国家,其判例法的特点决定了法院审理反竞争案件所形成的各种判例也是反托拉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大多比较笼统,所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确立的带有一般性的原则和规则更具有特别的意义。美国百余年的反托拉斯司法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判例,并依据这些判例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构成了美国竞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有关竞争的成文法规定和司法判例表现出一种互动关系,判例虽然多是在执行成文法过程中依据成文法的原则性规定做出的,但它们又大大丰富了成文法规定的内容。可以说,美国竞争法的适用“是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上的”,司法判例在美国竞争法律制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反垄断法上的两项判断违法行为的重要原则——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即是源自美国重要的案例。
欧洲竞争法的来源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罗马条约》自1957年签署以来,其中的竞争规则几乎一如其故。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被改为《欧洲共同体条约》,但竞争规则仍然无改于旧。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于1999年生效,其中的重要变化是,扩大了议会的立法权力,更改了《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条款序号,原来条约中第85条至第94条的规定被序列为第81条至89条,但其内容仍相沿不改。2009年12月1日生效的《里斯本条约》由修订后的《建立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共同体条约》构成。修订后的《欧洲共同体条约》改称为《关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成为欧盟基础条约。其虽然与先前的《欧洲共同体条约》不同,没有将自由竞争作为欧盟的目标加以规定,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欧洲共同体条约》中所有的实质性的欧共体竞争法规范,只是将原来的序号从第81条和第82条改为第101条和第102条。可以说,竞争法已成为欧盟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新兴的欧盟法律体系的“支柱”。欧盟竞争法作为欧盟经济一体化最终目标的战略手段之一,其主要是为了保护欧盟市场的完整统一与良好运转,保证企业间充分、有效竞争,维护自由、公平交易,努力建成一体化的欧洲内部大市场。它通常被作为打破贸易壁垒的利器,从而有助于建立积极的经济发展条件。与此相适应,欧盟竞争法在法律效力问题上突出了“影响成员国间贸易”的要求。在欧盟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之间的关系上,主要受到两项原则的支配:其一为欧盟法效力优先原则,即当成员国法与欧盟法不一致时,无论是成员国法院,还是欧盟两级法院,均应优先适用欧盟法;其二为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即欧盟法的执行,不仅是成员国政府的义务,也是全体在欧盟辖区活动的“经济实体”的直接义务。欧盟竞争法被赋予强大的实施力,个体可以直接据此主张其权利。在立法体例上,欧盟竞争法实现了两大法系特点的融合。虽然欧盟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在欧盟范围内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协调的努力几乎在欧共体成立伊始就发轫了。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竞争法体系之一的欧盟竞争法不是一部独立的法典。其法律渊源包括:(1)基础条约;(2)欧共体机构立法,其中包括欧共体各个组织机构分别制订的关于竞争法方面的诸如条例、指令、决定等形式的立法;(3)法院的判例法;(4)有关欧盟(欧共体)竞争法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协议。
欧盟竞争法的实体规范最集中地体现在经《欧盟条约》修改的《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原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即《罗马条约》,以下简称《欧洲共同体条约》)的第3条和第81条(原第85条)、第82条(原第86条)。其中,第3条是关于建立竞争保护机制、使之不受扭曲的原则规定。第81条是关于禁止和在一定条件下豁免反竞争性协议的规定。第82条是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并且未规定任何豁免情形。第84条规定了成员国主管机关适用条约规定对共同体市场上的协议、决议和协调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的管辖权。第86条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定。第87-89条涉及原则禁止国家援助问题。《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第1款规定,禁止与共同市场不相容的下列事项:企业之间订立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作出的决定和协同一致的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具有阻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目的或者效果的;尤其禁止下列事项:(a)直接或者间接地限定购买或销售价格或者任何其他贸易条件;(b)限制或者控制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或者投资;(c)瓜分市场或者供应来源;(d)对与其他贸易方的相同交易施以不同的条件,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e)要求对方当事人接受在性质或者商业惯例上与合同涉及的项目无关的附加义务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第81条第2款规定,依照本条规定而被禁止的协议或者决定自动无效。第81条第3款则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本来属于第1款规定的任何协议、决定和协同一致的行为或者任何类型的协议、决定和协同一致的行为,可以享受豁免请求权。这需要同时具备四个前提条件:(a)有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或者有利于促进技术或者经济的发展;(b)使消费者能够从由此获得的利益中分享公平的份额;(c)不对有关企业施加并非为达致上述目标所必不可或缺的限制;(d)没有排除有关商品或劳务的主要部分进行竞争的可能。第82条规定:一个或者多个在共同市场或者其主体部分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且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任何行为,则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应予禁止;尤其禁止下列滥用行为:(a)直接或者间接地施加不公平的购销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条件;(b)限制生产、销售或技术开发,损害消费者利益;(c)对与其他贸易方的相同交易施以不同的条件,从而使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d)要求对方当事人接受从性质或者商业惯例上与合同涉及的项目无关的附加义务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所谓“禁止搭配”)。《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与第82条之间的区别点在于:前者主要涉及两个独立企业之间的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其目的是防止通过订立协议来不合理地限制共同市场内的竞争;而后者主要涉及(但不限于)单个企业的市场行为,防止通过滥用其支配地位而不合理地限制共同市场内的竞争。
相对于作为欧共体存在法律基础的《欧洲共同体条约》而言,欧共体二级立法,现称欧盟二级立法,又称派生法,是由欧共体议会、欧共体理事会、欧共体委员会等共同体机构或相应的欧盟机构制定的法律规范,表现为条例、指令、决定、建议、意见等形式。基础条约中的竞争规范则在整个欧盟竞争法体系中起着母法的作用,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而大量二级立法的规定对于基础法简节疎目所留下的法律空间加以补充,构成欧盟(欧共体)竞争法律制度真正能够得以执行和落实的实体法基础。条例以其具有约束力而区别于没有约束力的建议和意见,以其普遍适用性区别于涉及个别主体和具体情形的决定,以其所有部分都具有约束力并在所有成员国直接适用无需转化而区别于不能直接适用于个人或企业组织的指令。[5]P449-456其中,最重要的条例是欧共体理事会1962年发布的《关于实施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第17/62号条例》和1989年发布的《关于控制企业合并的第4064/89号条例》。第17/62号条例是欧共体委员会执行欧共体竞争政策查处反竞争行为的程序性规范的重要法规,而第4064/89号条例是自1958年以来欧共体竞争法实体法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源而溯之,《欧洲共同体条约》并没有关于控制与共同市场相抵触的企业集中行为的明文规定,其第82条只能干预那些会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而对于那些会产生市场支配地位的合并则力所不逮。经过漫长的争论和谈判,欧共体理事会于1989年12月21日制定了一部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体的专门规定企业集中的第4064/89号条例,从而形成了与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所规定的两类反竞争行为规范鼎足而三的第三类反竞争行为规范,嗣后被《欧共体理事会1310/97号关于修改4064/89号条例的条例》所修改,这一条例后又在2004年被《关于企业集中控制的理事会第139/2004号条例》所取代。2002年欧盟理事会的《关于执行条约第81条、第82条中有关竞争规则的1/2003号条例》对欧盟竞争法的适用性以及成员国主管当局和欧盟委员会的权责范围做了新的规定。
欧共体竞争法除了成文法之外,欧共体委员会关于竞争案件的裁决、欧共体法院和1989年建立起来的欧共体初审法院关于欧共体竞争案件的判决,也都是欧共体竞争法的重要源渊。就竞争法领域而言,欧洲法院和欧洲初审法院首先负责判决由成员国、欧盟(欧共体)机构或者法人和自然人提起的竞争诉讼。其次,应成员国法院的申请对欧盟(欧共体)竞争法的解释或欧盟(欧共体)机构关于竞争法律和政策的立法和执法行为的有效性做出先行裁决。欧盟二级法院的总顾问在法院判决前呈递的意见书对于案件审理没有约束力,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学者认为,当法庭未采纳总顾问的意见而作出判决时,该意见书相当于异议判决,类似于欧洲初审法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在二审中被欧洲法院所撤销。[6]P498由欧洲司法系统对成员国法院提出的有关条约规定的解释、共同体机构通过的竞争法令的效力和解释等方面的问题统一作出裁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欧盟(欧共体)竞争法在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适用,而且为无权在欧洲司法机构直接起诉的当事人寻求欧洲层面的司法救济提供了间接通道。此外,作为基础条约的护法者,法院还负责宪法中规定的所有其他形式的司法监督。欧洲法院和欧洲初审法院通过其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和一系列现行裁定对条约和二级立法进行解释,并对欧共体机构的行为效力作出判断。其判决和先行裁决的结果不仅必须为欧共体各成员国所尊重,而且对欧共体其他机构也具有拘束力。由是言之,欧盟“判例法”的提法虽然存在不够谛当之处,法院在理论上并未被赋予创设法律的权力,但其重新解释和发展《欧洲共同体条约》的造法功能通过做出各方必须遵守的判决和先行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从以往的实践情况来看,在保证《欧洲共同体条约》目标实现方面,欧洲司法能动主义对以欧盟基础条约为核心的欧盟法的贯彻落实以及推进欧洲一体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举足轻重。欧洲法院和欧洲初审法院在法律解释和案件裁决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利用法律续造的活动空间积累了宝贵财富,殊堪重视。事实上,欧盟(欧共体)竞争法的很多适用原则及具体规定都是在欧洲法院判决中最终确立起来的。
二、法律实施:对抗制与法条主义
像英国一样,美国司法中也强调一种当事人抗辩的制度,即基于对法庭的信任,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律师以及刑事案件中公诉人(检察官)和被告律师(辩护人)在法庭上进行对抗,如提供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询问自己一方的证人或者盘问对方的证人等,起着主导法庭审理过程的作用。陪审员不主动进行庭前调查,在法庭上也不提问,其任务只是听取双方及其证人的发言,并在庭审后就案件事实作出裁决。法官也不主动进行调查,在主持开庭过程中甚至不参加提问,扮演着消极的仲裁人角色。其作用通常被限制在监督陪审团的选择、控制审判过程、决定对证据的质问、对陪审团进行指示以及决定是否将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等方面。换言之,在美国的司法审判中,出于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双方由律师作代理人,以最大的智慧和决心为各自的当事人辩护。法官的职能就是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知识,按照游戏规则,使这种抗辩游戏合法和公正地进行。法官不需要对争议事实进行认证和裁决,这是提出证据的律师和判决争议观点的陪审团成员的责任。此即所谓的“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甚至与英国的审判相比,尽管两者均属于对抗制,但美国的审判也显得更多受到当事人的影响而更少受到等级体制的控制[7],并且对当事人及其律师所提出的关于新的法律和政策主张,保持更高程度的开放性。
对抗制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让当事人双方相互对抗,才能澄清事实,体现正义与公平。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权力的普遍不信任,在美国历史上绵延不绝。和相对于政府其他机关而言更倚重法院的动机一样,美国对抗制诉讼模式背后同样隐藏着对于权威的一种怀疑主义。其基于控方证据可靠性的不信任,预设的前提是,允许证据在审判过程的控辩,才能最好地避免错误判决。[8]这种使一切天经地义的权威受到质疑本身具有天经地义的绝对性价值理念成为美国人信仰的支柱之一,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深刻而无微不至地浸润于美国法律教育和律师与法官的“法律文化”,表现为重视针对冲突的当事人和法律诉求做出反应,而不是尊崇等级制的法律权威和规范的一致性。法律不再被理解成返回某一理想的规则抽象总和,而被看做行动的工具箱。理想是有的,但它存在于诉讼程序中,而诉讼程序就是战斗。与许多国家相反,法律的不确定性在美国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损害,如同为保障个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那样。罗伯特·卡根使用“对抗制法条主义”(adversarial legalism)一词来概括美国的诉讼解决模式的总体特征,认为这种模式鼓励通过律师主导的诉讼实施政策和解决纠纷。在组织上,对抗制法条主义与对权威被分割的、等级控制程度相对较弱的裁决机构相关联。在诉讼和裁判层面,对抗制法条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诉讼能动主义:提出诉求、查找法律根据和搜集并提交证据这些事项,并非由法官或政府官员主导,而是主要由诉讼当事人、利益相关人或代理律师来完成。与对抗制法条主义不同,欧洲大陆法系的“科层制法条主义”是一种这样的决策和争议解决风格:法律权威和判决以等级制方式来运作,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9]P5-6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反映的“对垄断的仇恨”,被威廉·列特文称为“美国最古老的政治习惯之一”。[10]P59美国反托拉斯法律规范的特性特别值得予以关注,因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竞争法体系迥然不同。这种差异既影响了美国以外的人对该法的理解,也影响了美国人对国外竞争法的看法。美国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功能主义色彩,以结果为导向,从结果来“倒推”法律(应当)是什么,与建立在法律文本之上的欧洲传统法律文化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美国反托拉斯法通过判例形成的“理性规则”基于一个给定的协议企业之间的促进和阻碍竞争加以评价。通过这一点,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制度被称为“基于效果的”制度,相反,欧洲的竞争法制度被称为“基于规范的”制度。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即奉行规则怀疑主义,相信法律并无超验的性质,而是社会力量和诉讼活动中人们对社会力量作出反应的行为,不可能凭借一种不偏不倚的推理方式将规则适用于具体个案。在美国,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对判决鲜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实体法必须从通常并不具连续性、也不甚清晰的一堆判例法中得出,法院做判决时应依赖各自经验及先例所代表的集体经验。这种法律文化导致概念往往是“即兴”的而非系统性的概念。换言之,其在具体情形下为解决当事方的冲突而被创造出来。就实质而言,谢尔曼法的语言本身只不过是判例法的文字支撑点而已。与在其他国家的竞争法中的概念通常以抽象方式表述不同,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概念既不系统化,彼此也缺乏关联性。这意味着,一方面,美国反托拉斯法存在于非常抽象的概念中(如垄断化),而这些概念对判决者来说鲜有或者没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该法又体现在高度具体化的规范性判决中,代表着对具体情况的应对。[11]P126在美国,法院赋予反托拉斯法以内容,而立法机关在这方面事实上仅仅发挥了边缘性的作用。基于谢尔曼法作为“经济宪法”的形象和美国人对宪法作用的概念,美国法官长期以来致力于使其语言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美国反托拉斯法被大量私人诉讼所支配,这在欧盟比较少见。这导致了美国的制度发展基于逐案推进,而欧盟的法律主要由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得以发展。在程序方面,两个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只是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明显。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在美国所有的反托拉斯案件中,约75%是由私人执法方式提起(后续案件已经在这个数字中减去),而在欧洲,私人执法几乎不存在。这样做与美国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具有一定关系,这是在欧洲不存在和被广泛认为不必要的。美国竞争法模仿和引进了1623年英国垄断条例三倍赔偿规定。据此规定,原告在胜诉后将不仅能挽回他所受到的损失,还可以得到三倍于该损失的赔偿。这种三倍赔偿金制度具有推动私人诉讼的激励机制。此外,美国律师的风险代理收费也为致力于反托拉斯案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对于许多美国原告来说,胜诉可以获得赔偿金,败诉则不用承担任何费用,发动一场诉讼实质上是一个“不会失败的建议”。而在德国,这是违反公共政策的行为,德国律师被视为法律的司法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企业家。
美国模式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公共和私人诉讼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种实施手段的相互作用塑造每个判决。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实施中,私人诉讼和行政执法机制并行运作而双向影响,呈现出平行耦合与反向耦合。一方面,如果官方执法机构决定不对某一行为采取行动,就会减少人们对“该行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这种主张成功的可能性的预期或者对其重要性的看法。同时,它还会反过来减弱司法机构对这种指控的接受程度,并对此类私人诉讼产生阻却作用。反之,如果执法机构加强对某一类行为的执法力度,这便成为被告违法的强烈信号,私人诉讼的信心就会为之大振,私人诉讼的案件就会可以搭政府的便车而随之大增,直至法院否定相关指控为止。一个政府诉讼经常会衍生出很多的针对同一个被告的私人损害赔偿诉讼。私人当事人利用先前的有罪判决可以确定损害赔偿请求的基本构成要件,在不需要动用任何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即可以证明违法行为存在。这种模式因而被称为后继执行。另一方面,私人诉讼也会影响官方执法机构的执法。例如,私人诉讼削弱了公共机构控制反托拉斯法发展进程的能力。私人诉讼决策受到各种私人考量的推动,取决于私人对诉讼成本和价值的评估,并不直接受公共执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战略的影响。因此,在美国,当公共执法机构力图发展出某种观点或着力解决某类案件时,其影响往往弱于那些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行政机构实施其法律的国家。[11]P135美国利用司法的竞争机制发展竞争法,充分汲取配置性资源,使得竞争法领域在斗志昂扬的律师的推动下长期生机勃勃,而欧洲主要依赖于权威性资源。
在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中,律师作为法律竞技的角斗士大斗其法。而企业并购业务由于是块肥肉,在律师业务收入中属于来钱容易的金矿,所以无不攘臂而争,择肥而啖,这就是美国反垄断法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买卖企业的生意明显比企业的一般买卖生意等而上之,这种会下金蛋的鹅的买卖对于企业而言是挥金如土的大买卖,对于律师而言是大发利市的饕餮盛宴。对于美国高度企业化的法律职业及其阵容强大的律师事务所而言,金融、并购和诉讼这三块业务收入比较丰厚,而金融和并购业务又比诉讼更能财源广进。对美国律师来说,赚钱是第一位的,律师跟钱跑,哪里有客户,哪里就有律师战斗的身影,有客户就有钱。为了扩大业务,为了追随客户,律师事务所也往往展开兼并收购,而且经常是跨国兼并收购,以大团队的形式进行运作,逾越千山万水拓展法律服务市场,美国律师界的进攻性于此彰显无遗。
机构对反竞争行为采取的任何行动可以称之为公共执行。公共执行的特点是动用了公共财政和权力资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由私人发动的反垄断法执行简称为私人执行。私人实施的核心内容在于私人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推动竞争法的实施。其属于实施竞争法的私法性行为,是“直接司法”,不同于私人通过举报反垄断违法行为或者向行政主管机关提起反垄断申诉,在后两种途径中的私人参与仅仅是间接程序的启动。一般认为,私人执行模式有直接执行和“审决前置”执行之分,其中,直接执行模式是一种主流的私人执行模式。对于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影响”标准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诉讼是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主要途径,而损害赔偿和禁令则是私人反垄断法执行的主要救济方式。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通过消费者和企业直接主张权利实施竞争法则,可以为竞争法开启超越公共实施之外的广阔的实施空间。首先,作为公共实施的补充,促进私人诉讼可以加强竞争法的实施力度,提高实施水平,更好地维护以市场竞争秩序为代表的公益。其次,私人可以针对竞争主管机关未追究或没有足够资源追究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并且由违法者承担违法成本。建立在“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必须赔偿”的私法原理基础上的私人诉讼,与违法行为人可预见、可控制的损害确定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在公共实施的惩罚性功能之外的强有力的特别的遏制作用。这种私人诉讼的紧逼性和普遍性产生强有力的威慑效应,促使市场主体更好地、在更高层面上遵守竞争法。复次,与公共实施更强调事后制裁不同,私人实施更体现出事前防预的特性。美国学者们认为,在反托拉斯法执行体制中设置私人执行,可以大大增强反托拉斯法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同时也可以赔偿违法行为受害人的损失;私人诉讼不仅提高了反托拉斯执行的数量,而且部分承担了政府机关的执行成本,具有节约公共资源之效。由于私人执行是政府公共执行极为重要的补充,因此,其执行者在美国通常被称为“私人司法部长”。[12]在实践中,美国的私人反托拉斯救济方式主要是三倍损害赔偿,而在德国,虽然存在反竞争限制的私人诉讼机制,但当事人主要的救济方式是反竞争协议无效诉讼,又被称为防御性执行,与美国的差异歧别昭然若揭。
如果说美国的司法模式则主要是通过民事、刑事诉讼的形式来实施竞争法,那么,欧洲的行政主导模式强调由行政机关执行竞争政策,法院最多充当行政法院的角色,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盟竞争法的私人执行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基础和委员会享有垄断性的豁免审批权,长期以来颇为寂寥低迷。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整个欧洲的反托拉斯案件中,95%是通过公共执行形成的,仅有5%是由私人诉讼发动的。很多人将其中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仅将赔偿局限于恢复性赔偿而没有规定三倍赔偿或惩罚性赔偿。这种解释存在简单化的嫌疑。从欧盟的情况来看,其私人执行不发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盟法律并没有管制私人执行,而是将私人执行留给成员国法律加以调整,这种体制本身就造成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且大多数成员国法律在对待私人原告问题上又不像美国法律那样眷顾友善。一项研究报告还提到了阻碍欧盟竞争法私人执行发展的其他因素,包括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由于当事人证明违法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反垄断私人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一旦败诉,还要搭上不菲的诉讼费用,使当事人知难而退,望而却步。另外,由于欧盟国家的程序法通常都规定,一旦私人原告败诉,将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这种潜在的风险也被认为是私人原告为了稳妥起见不诉诸法院的主要原因之一。
竞争法的私人实施机制在欧洲历史上并不陌生,在19世纪初的奥地利法律中就有规定卡特尔协议无效的条款。但降及19世纪末,实践证明,这种私法机制在对付卡特尔问题上成效不彰,致使19世纪末奥地利人提出欧洲第一部竞争法案构想时,遂将行政对策作为制止卡特尔的唯一有效措施,明确提出竞争问题应当采取行政性的解决方案,批评美国竞争法过分依赖于常规的法院系统的私人实施模式,[13]P23这对后来欧洲竞争法形成独特的行政主导型实施模式影响甚巨。就此而言,肇始于欧洲第一部竞争法草案制定过程中的关于竞争法应当采用行政主导模式还是司法模式的争论,堪称欧洲竞争法现代化改革中被重新提起的加强竞争法私人实施大讨论的最初形态。构建有效的私人实施机制成为欧洲统一竞争法“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核心策略[14],这似乎是历史的发展又重新回到了原点。私人诉讼并非没有成本,但对于官僚硬化症具有纾解作用,打破一潭死水,荡漾出活泛的涟漪,是名副其实的贯彻和落实竞争文化的机制,使得竞争从思想文化、经济活动到法律实施一以贯之,从而呈现出机制上的耦合。
经济法不仅在实体法上强调公私结合,而且在程序法上也同样如此,即公共诉讼与私人诉讼的结合。欧洲竞争法的现代化便折射出这种取向。欧洲法律从压抑性法律向自反性法律发展,这本身即是现代性的表现。欧共体新的执行条例即l/2003号条例,是对《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实施制度的全面改革,旨在促进欧共体竞争法私人实施制度的建立。2005年12月,欧盟委员会鉴于私人实施机制受到冷落的现状,公布了《违反欧共体反托拉斯规则的损害赔偿诉讼绿皮书》及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文本。绿皮书强调,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规定的反托拉斯规则既可以通过公共来执行,也可以通过私人来执行,这两种执行殊途同归,共同服务于威慑反托拉斯法禁止的反竞争行为和保护公司和消费者不受反竞争行为的损害这一目标。绿皮书分析了欧盟竞争法私人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和问题,试探性提出引入两倍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希望进一步推动欧盟竞争法的私人执行,发展欧盟的竞争文化。综观绿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欧盟追慕于美国的模式,步其后尘,但又力图在含英咀华的同时剔除糟粕,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私人执行的康庄大道。欧盟的竞争法执行体制正从集中的、管制者处于支配地位的体制(即一元执行体制)向分权的、私人执行体制(即二元执行体制)转变。然而,应该承认,即便在欧盟委员会大力推动竞争法现代化改革和建立有效私人实施机制多年后的今天,欧盟通过损害赔偿之诉实施竞争法的水平仍然极其低下,根据成员国法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同样也非常有限,依旧处于欠发达状态。美国文化基础是移民社会,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四方杂沓,彼此傲然独立,争竞文化发达自然不难理解,而欧洲大陆在传统的约束下步履沉重凝滞。欧洲人更加含蓄,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不具备像美国那样蔚然成风的“争执文化”。较之美国,欧洲的诉讼文化不发达,加之反垄断争执中原告通常面对的又是强有力的垄断企业,取证困难重重,而且往往涉及对诸多经济信息的掌握和评价,胜诉把握小,但却会因为提起诉讼而导致正常经济关系破裂,所以欧洲竞争法私人实施的首要难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
三、垄断的衡量标准:滥用与禁止
中国学术界往往认为,欧盟竞争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法律目的上,以促进共同体市场的统一为最高目标,并不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唯一目的;在法律规制上,确立了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主轴的滥用型法律规制模式;在法律实施手段上,虽然也强调司法的作用,但更多地依靠行政机关的裁决。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竞争法态度、观点和行动表明,他们把战前这一阶段的德国经验看作为欧洲经验,塑造了“滥用模式”的欧洲竞争法模式,明显区别于美国的“禁止模式”。前者以对卡特尔等的“滥用模式”进行行政管制为主要法律内容,后者则直接禁止特定的行为类型如卡特尔等。虽然禁止模式的行为确定标准较高,但可以导致更好的辐射效果。中国学术界这种观点受到美国学者戴维·格伯尔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有关竞争法的一些基本观念开始在欧洲许多地区得到传播和支持,而且在欧洲的某些法律体系和某些重要的政治运动的纲领中扎下了根。这些观念也开始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竞争法“模式”,一种不同于美国反托斯法的欧洲替代方案。这个模式的核心思想是,法律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收到控制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的有害行为,而不是禁止特定的行为类型,从而保护竞争过程。这种模式被称为竞争法的“滥用模式”。[15]P164戴维·格伯尔把滥用问题视为欧盟法与美国法存在巨大差异的少数几个竞争法领域之一,认为在这种分歧中最突出的是,欧盟认为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有“特别的责任”不滥用其经济力量,由此受到一套比其他企业更严格的标准的审查。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的私有化经常导致私有化后的企业拥有支配地位的情形,滥用案件引人瞩目。[11]P186戴维·格伯尔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指出:德国人是把竞争法条款纳入《罗马条约》的主要支持者。《罗马条约》的竞争法条款(第85、86条)与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当时欧洲的另一些竞争法很少有相似之处。其中的禁止卡特尔协议的条款类似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但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一项重要的新发展,与秩序自由主义和德国竞争法的关系特别密切,非常不同于美国法律中的表述。[15]P264
在19世纪末叶,卡特尔和其他竞争约束尽管在德国引起讨论,但由于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和卡特尔数量不断增长,德国在1923年颁布的《卡特尔条例》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采取“滥用原则”而非禁止限制竞争(即“禁止原则”),对于卡特尔条例并未对卡特尔予以普遍禁止,而是将卡特尔的“不公正的”权力行使行为纳入法律控制之下,以防滥用权力,以强凌弱。竞争法中滥用权力的概念由此开始形成,在后来所有的欧洲竞争法中都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16]P5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对竞争限制法》是对竞争限制在德国第一次全面监管的法律。这样一个法律的内容在当时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尤其关于是遵循禁止原则还是滥用原则。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及其政治盟友(主要是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中)的目标是,制定一个以禁止滥用模式为基础的竞争法,类似于魏玛卡特尔法规。他们申辩指出,不必要禁止卡特尔,否则对德国工业具有潜在的危害。卡特尔已经长期以来被证明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经济发展的手段。一种禁止滥用法才是符合德国传统的。[15]P272然而,1954年,德国工业联合会的“阵营”出现分化,不妥协地坚持滥用型立法的立场遭到其阵营内部人士的批评。或许担心对其支持会被进一步侵蚀,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不久也转而接受禁止卡特尔的基本观念。作为交换,艾哈德同意接受了对禁止规定的额外豁免。虽然德国这部法律主要依赖行政机制来实施竞争法原则,但其新颖性无疑是昭然可见的,突破了战前欧洲竞争法的“滥用模式”。[11]P169最终通过的法律是基本禁止,但含有许多例外,故而,这只能说是禁止原则的胜利。换言之,二战以后德国竞争法思想和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发展。德国竞争法将保护自由竞争本身作为首要目标,与1923年《卡特尔条例》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以禁止滥用原则为核心的欧洲竞争法传统大相径庭,明确禁止卡特尔行为,旨在创建一个所有市场参与者自由竞争的经济社会秩序。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成立后的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卡特尔案件。在短短几年时间后,原来遍地开花的卡特尔数量趋于稀少,甚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这也充分说明了《反限制竞争法》禁止模式的效果。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反托拉斯法禁止公司故意获得(或试图获得)垄断力量,而《反对竞争限制法》谴责滥用市场主导力量。[17]
在《罗马条约》的谈判中,各国竞争立法模式上存在激烈的争论的问题。一派认为主张禁止原则,这主要是由德国代表所坚持,而另一派青睐滥用原则。最后达成的妥协是,适用第81条第(3)是依据禁止原则还是滥用原则暂时被留给了成员国自行决定。但是,欧共体竞争法中是存在禁止原则的。正如奥托·施莱西特所言,“没有对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争锋,就不会有欧洲共同体条约中的禁止卡特尔规定或滥用监管规定”[18]。由于卡特尔具有二重性,因此各国法律对卡特尔行为虽然在立法上原则持禁止态度,但实际上明令禁止的卡特尔类型寥寥无几。所谓明令禁止的卡特尔,也称本身违法的卡特尔,是指某一卡特尔行为无论其内容或环境如何,一经实施必然对竞争产生严重的危害,总是缺乏社会或经济的补偿价值,必须予以取缔。明令禁止的卡特尔一般包括价格卡特尔、限制数量卡特尔、市场划分卡特尔及联合抵制卡特尔。这些明令禁止的卡特尔行为是各法律体系经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发展而总结出来的类型,但事实上,目前真正在法律上明确予以揭示的只有匈牙利和欧盟的竞争法。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65、66条建立了具有申报义务的禁止制度,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86条禁止制度的蓝本。[19]P357《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在认为卡特尔行为应该予以禁止的同时,特别举例说明了应该予以禁止的行为。麦斯特梅克尔就将共同体卡特尔法分成四个规范群,即:可禁止的、被禁止的、可豁免的和被豁免的限制竞争行为。[20]P182其中,列为可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有已登记或免于登记的旧卡特尔(在1962年3月13日第17号条例生效前缔结的卡特尔),直到欧共体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欧洲法院的判例对这些卡特尔只作“临时有效”处理。属于被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有第85条第1款和第86条规定的情况,特别是新卡特尔和具有市场统治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地位的行为。如果这涉及到合同,禁止的特征源于第85条第2款对这类合同的无效规定。一般而言,反垄断法在行为禁止的调整模式下,主要是通过界定消极权利的途径规范竞争行为,维护竞争秩序,确立竞争过程不受超市场力量的阻碍、破坏和限制。1986年以后欧洲各国竞争法体系的演化堪称一个从建立在“滥用”原则上的体系向更加依靠禁止原则过渡的历程。在荷兰,早期禁令具有“滥用制度”的性质,而在基于“禁止制度”的1998年新竞争法出台后,其制度变迁就提供了这样性质的过渡例证。不仅如此,随着以过去相应的欧洲委员会实践为背景的欧盟竞争法第五次修正案的颁布,欧洲竞争法在银行领域已经从滥用原则过渡到禁止原则,银行的特殊地位被广泛取消。[21]P88
正是这样,一些中国学者就原则禁止模式和滥用规制模式这样阐述说:原则禁止模式认为卡特尔在本质上应是予以禁止的,但同时又规定了除外制度。当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法国、瑞士等国均采取此模式。滥用规制模式原则上允许设立卡特尔,但订立卡特尔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并接受审查。有关部门经审查认为有滥用优势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时,有权宣布该卡特尔无效。现在只有英国采用滥用规制模式。但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与原则禁止模式并无多大不同,两者均充分体现了卡特尔的二重性。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基于禁止原则,从而这样信念被共享:鉴于限制竞争基本上的不利影响,企业应使其获得例外许可。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区别是互相排斥的。任何立法机关都需要依据排中律作出决定。从本质上讲,需要决定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在新泽西州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案和美国烟草公司诉美国案中,英国的理性规则被引入了美国反托拉斯法,但并没有改变早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1条所确立的禁止原则。[19]P373费肯杰更是精辟地指出,人们可以将竞争限制置于“滥用控制”而不是禁止法规之下。这意味着竞争限制基本上是允许的,但国家或个人可以在个别情况下认定竞争限制基于特定的、法律规定的原因是不允许的并进而是滥用行为。滥用性法律的应用需要一被委托的应用机构。滥用性法律对于工业和商业是温和的措施,对于工业和商业主要是管理。而禁止法规典型地通过法院适用,对于经济采取司法措施。但在实践中,当卡特尔主管机关以彻底反对竞争限制为要务时,滥用原则趋向于禁止原则。但这一“理想”并不总是可达到的,此外也不符合“过错和责任相宜”。反之,在卡特尔主管机关倾向于权宜原则时,禁止原则趋向于滥用原则。[22]P246-253
尽管滥用这一概念在战前已经被纳入德国原来的反限制竞争法,在对立法内容的长期辩论中极少被注意到,并没有在德国战后反限制竞争法中得到定义。显然,其原因在于,它仅被假定该“似然”标准会提供充分指导以赋予其内容。[15]P307德国有关滥用概念的作用的讨论主要盛行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和学术界开始把滥用概念作为处理通货膨胀和经济集中的工具给予更密切的关注。欧盟竞争法深受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影响。特别是作为欧盟竞争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一般被认为是根植于德国法的传统,其以行政执法为主的执法模式也是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执法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解释和适用滥用支配地位的概念时,欧洲委员会和法院最初尤为谨慎。欧洲委员会不希望由于法院在这种迟疑而冒险的案件中失败,在1958年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很少运用第86条,使人们在20世纪六十年代担忧其会变成一纸空文。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委员会也试图建立解释滥用概念的理论框架,向有关法学专家进行咨询,希望为该项规定的适用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欧洲委员会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实施该法条。当时,欧洲委员会与欧洲法院戮力发展了一系列迄今仍具有权威性的案例,界定了“支配”和“滥用”等核心概念。可以说,欧盟竞争法中的核心理论就是“支配”理论,这是一种基于对经营者单独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即:为了维护市竞争,保持竞争机能,必须对经营者拥有的支配地位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滥用此经济地位。正是这样,欧盟竞争法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予以严厉规制。
为了使竞争限制的类型与按照法律后果的处理之间至少原则上一致,费肯杰提出通过措施的竞争限制和通过状态的竞争限制二分法的建议[23]P53。这种二分法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是以下述观察为基础,即:竞争可以是(sein)处于受限制的和变得(werden)受限制的[24]P231。如果竞争限制是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特征而存在,则禁止原则是原则上不合适的。人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市场上的一切竞争限制径予禁止。其毋宁是取决于为什么它在那里以及应如何处理它。因此,对于通过状态的竞争限制基本合适的法律反应是滥用原则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制:追问被发现的通过状态的竞争限制的事实构造是否有理由加以法律干预并命其承担适当的法律后果。而那些“被造成的”竞争限制、也可以说是通过措施的竞争限制,则是相关人可以取消的企业战略,也是原则上必须归入禁止之列的。这种二分法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它使得对所有竞争限制的一次性概略分类成为可能,并且提示了在此原则上适当的法律处理;其次,它与美国反托拉斯法划清了界限,后者原则上不认可对“通过状态的竞争限制”的禁止。从一开始,《谢尔曼法案》第2条所使用的“垄断行为”(monoplizing)的概念就涉及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这种行为旨在建立、维持市场支配地位或者类似的扩大了的市场影响的事实状态,或者利用这样的地位或状态。《谢尔曼法案》第2条在这里也是以禁止原则为依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反对竞争限制法》第22条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6条标示通过法律上反对滥用市场统治地位以保护消费者,这原则上与美国法大相异趣[25]。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中,面临这样的问题:基于“垄断化”而必须采取拆解,但在德国和欧洲共同体法律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反对竞争限制法》第22条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6条(《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66条第7款亦然)让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如此伤筋动骨。这些规章被限制于与致力于市场操纵的企业战略进行战斗。由于这种致力的“措施”性质,所以第86条的禁止原则与之更为一致。人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在通过状态的竞争限制中的禁止称之为具有消除后果的禁止法规(Verbotsgesetz mit Beseitigungsfolge),将在通过措施的竞争限制中的禁止称之为具有妨碍后果的禁止法规(Verbotsgesetz mit Verhinderungfolge)。
共体法律上的滥用行为分两大类:排他性滥用(亦称“妨碍型滥用”)和剥削性滥用。所谓“剥削性滥用”,主要针对消费者和经营者,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不受竞争的约束,自由地制定垄断,高价出售商品或者以低价购买商商品,或者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交易相对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或者榨取的行为。剥削性滥用主要围绕价格进行。由于相关市场上不存在替代性产品或者销售渠道,对垄断企业定价,消费者或者下游企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种剥削或榨取。所谓“排他性滥用”,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对手,利用其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实行掠夺性价格或者差别性价格,或者拒绝其使用其所拥有的关键设施等,最大限度地限制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或提高其经营成本的行为。与剥削性滥用相反,排他性滥用不是建立在一般的商业绩效基础上,而是主要表现为垄断企业通过价格或者非价格手段对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实施各种不利于其竞争的行为,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将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的目的。排他性滥用的典型代表为结构性滥用,即经营者通过合并或者收购的方式实施的排除竞争对手的行为。按照欧、美、日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如果实施合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那么将会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关注。因此,结构性滥用并不是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行为规制来对待的。在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这两种情形中,最终关切点在于对竞争过程的保护。不过,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划分成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划分,两者之间实则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例如,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附条件交易,既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滥用支配地位对消费者或者下游企业的盘剥,也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搭售这种形式,利用在主商品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去谋求在被搭售商品市场上的支配地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中就没有采纳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的划分方法。欧盟竞争法实施的最新动向也表明,欧盟委员会也正在逐步模糊对于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之间的区分,统一按照排他性效果的大小进行规制。[26]P385
欧盟竞争法的滥用规制深受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影晌,强调对于大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严格规制。这与美国反托拉斯法对私人追求垄断化的规制逐渐缓和的趋势不同。固然,欧盟委员会之所以重视滥用规制的实施,也是出于其在推动欧盟市场一体化过程中防止滥用行为的现实需求,而这在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中基本上不存在。欧盟竞争法中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不局限于经营者单独进行的排他性行为,也导入了对经营者共同支配地位的规制,并且这种支配理论还扩展适用于纵向协议以及经营者集中规制领域。这使得欧盟竞争法的滥用规制和协议规制在规制对象上的差别不再明显,增加了违法适用标准的不确定性。美国反托拉斯法明确拒绝采用共同支配地位的滥用规制,具有合理性。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滥用规制有关的指南或实施细则,对市场支配地位及其认定、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体现出成文法系的重要特征,这也与美国反托拉斯法在相关滥用规制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出台细则的情形构成鲜明的对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欧盟委员会大力加强滥用规制的运用,针对跨国企业的滥用行为作出了一系列违法裁决,显示了欧盟委员会对于滥用行为的强势规制立场。在诸如垄断高价或者低价、掠夺性价格以及拒绝使用关键设施行为的规制方面,很多原则或者理论都已经在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中提出,但这些原则或理论提出后在美国有的已经不再被恪守,反而在欧盟竞争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发扬光大。可以说,欧盟竞争法在滥用规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甚至超过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具有引领反垄断法滥用规制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欧洲,与美国不同的传统观念决定了受到人们抨击的是对绝对优势地位的滥用,而不是垄断本身。滥用者不一定拥有垄断企业,只要它有足够的优势条件可以使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定价权和营销权就够了。如果企业对这种地位的运用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它就会受到竞争法规的谴责。如果一个企业拥有某种天然的垄断权,例如,私有化的电信机构拒绝竞争者接入其线路,认定这样的企业是否有滥用优势的情况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但是,如果要论证诸如IBM这样的公司有没有滥用其在电脑制造方面的优势、微软公司有没有滥用其在电脑软件市场上的优势,则殊非易事。美国和欧盟对待合并和垄断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走越近,均承认垄断的存在,都谴责对垄断权的滥用。然而,美国对竞争的看法决定了其可能无法去界定何为“滥用”,对合并进行审查主要是为了考察其是否不适当地减少了竞争。如果合并导致了垄断,或者使企业获得了可能导致滥用的绝对优势的地位,也许一开始就禁止合并以免产生滥用权利的情况,才是更好的办法。但如今在欧洲和美国,对合并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通常来说,合并被认为是可以提高效益的办法,而并不会削弱竞争。在欧盟,那些会导致某一企业在某些成员国占据巨大市场份额的合并活动在以前可能会遭到禁止,但如今人们则会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从努力创建一个统一市场的角度对这些合并活动加以评判。此外,人们还越来越趋于从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的角度来判断这一问题,而由此作出的判定很可能具有某些产业政策的内容。[27]P314-315
余论
美国对于欧洲制定竞争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欧洲竞争法根植于欧洲本土的反垄断法律思想,体现着大陆法系法律发展的特有特征,是与美国反托拉斯法在本质上相互区别的另一种法律模式,并不是美国竞争法的翻版。两者之间从最初的立法目的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都存在迥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欧盟竞争法日益呈现出司法化的倾向,在对竞争评价以及限制竞争效果的评估方式上呈现出趋同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倾向,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面对共同竞争问题时必然出现的法律实用主义的趋同特征。欧盟竞争法在法律目的上,以促进共同体市场的统一为最高目标,并不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唯一目的,而是将竞争作为促进协调和平衡发展以及生活水平加速提高的一个工具。为了实现欧洲联邦的夙愿,欧盟所追寻的竞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干预主义的政策,包含了一切与市场统一化这个最根本、最广泛的目标的政策关怀。芝加哥学派的许多学者往往认为欧盟委员会对很低的掠夺定价对消费者有利的观点的坚决拒绝有些匪夷所思,但殊不知欧盟委员会更多地考虑的是贸易壁垒的产生和扩大及其可能对欧共体内部贸易产生的阻碍,对内部统一市场的分割和对自由开放的市场内部竞争的扭曲。诚然,法国统制经济影响下否定竞争之功效的竞争法与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下主张竞争是实现经济效率之有效途径的竞争思想,两者之间相去甚远,但前者恰恰在客观上推进了欧盟竞争法疏远弗莱堡学派的步伐。或许在否认竞争过程本身是目标、认为竞争仅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目标的手段这一点上,法国人正是借用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目前主导欧盟竞争法思想的布鲁塞尔学派更多地关注的是中小企业保护等平衡问题,笃信深植于《罗马条约》的前言之中的自由竞争的原则,将竞争、财政和社会政策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与美国反垄断主要针对私人力量后而逐渐开始针对政府的方式不同,“在欧洲,一些竞争规则是关于企业的,而另一些规则直接指向权力机构,这是欧洲所特有的”,而美国付诸阙如。这是由于二者传统不同所致。“欧洲的传统是国家总是积极发挥作用,而国家的作用可能会妨害竞争”。“欧洲竞争法干预的目的则是保证对市场参与者的同等待遇。这种平等的要求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制度上的。”[28]P190-191欧盟竞争法是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工具,为了实现这一法律目标,有必要借助于行政的甚至是政治的手段,由此决定了欧盟竞争法一开始就注重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和效力。在许多国家,法院通常仅仅审查行政决定是否符合行政程序,而在美国,普通法院在反托拉斯法的发展和运作中发挥着更大的核心作用。法院的作用不仅限于对竞争机构进行限制,而是这个体系的中心,是确立反托拉斯法的原则和规则的首要因素。在美国,由于法院决定了法律是什么,反托拉斯机构和私人律师就竞争法问题做决定时,主要参考的实为由法院所缔造的法律。[11]P136此外,反垄断在美国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私人行为者的问题,而在欧洲,竞争法迄今仍然是一个特定专家的用武之地,国家的作用不可避免被牵涉进来。行政官员已经有了“规制”产业的工具,并不需要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去履行同一职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竞争法被用于培养和扶持竞争的疆域,而不是政府的疆域。[11]P163这个体系在确立欧盟委员会在该领域的作用和发展竞争法时,均依赖于行政程序和机制,所遵循的是行政控制的模式。但是,受到德国竞争法的影响,欧盟已经将行政植入于司法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欧洲法院和后来的第一审法院发挥了核心作用。[11]P182美国反托拉斯法自始就包含刑事制裁,而欧洲竞争法迄今不提供这种救济。由于欧共体竞争法律制度相对于共同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滞后性日益彰显,特别是制约共同体竞争法有效实施的制度性缺陷日形凸显,欧共体在2002年将源于美国法的宽恕制度引入竞争法,拉开了欧共体竞争法改革的序幕。目前私人诉讼在欧洲竞争法中开始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施活动具有节约政府资源、制约执法机关以及赔偿受害者等多种功能。较诸美国,欧洲的诉讼文化不甚发达,加之反垄断争执中原告通常面对的又是强有力的垄断企业,取证困难,而且往往涉及对诸多经济信息的掌握和评价,胜诉把握较小,可能因为提起诉讼而导致正常经济关系破裂,所以,欧洲竞争法私人实施的首要难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欧洲竞争法私人实施机制既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来协调私益诉讼的形式与竞争法公益目标之间的关系,又不能听任私人因缺乏足够私益而怠于诉讼,使私人实施机制形同虚设,也必须制止私人因过分追逐私益而滥用私人实施机制,导致滥和阻碍竞争。
参考文献:
[1] Alison Jones & Brenda Sufrin,EU Competition Law,Text,Cases and Materials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 [美]戴维·J.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捍卫普罗米修斯[M]. 冯克利,魏志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John H. Shenefield & Irwin M. Stelzer,The Antitrust Laws:A Primer [M]. Washington DC:The AEI Press,2001.
[4]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lth_care/204694/appendixd.htm,2013-12-14访问.
[5] [德]费肯杰. 经济法(第一卷)[M].张世明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6] Henry G. Schermers,Denis F. Waelbroeck,Judicial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M]. The Hague,London,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2.
[7] Graham Hughes,English Criminal Justice:Is it Better Than Ours? [J]. Arizona Law Review,Volume26,Issue3,1984.
[8] Peter J. Henning,Lawyers,Truth,and Honesty in Representing Clients [J].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Ethics and Public Policy,Vol. 20,May 2006.
[9] Robert A. Kagan,American and European Ways of Law:Six Entrenched Differences,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and Society Faculty Working Papers [R].
[10] W. Lewtin,Law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merica:The Evolu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M]. New York:Random House,1965.
[11] David Gerber,Global Competition:Law,Markets,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2] Joseph P Bauer,Multiple Enforcers and Multiple Remedies:Reflections on the Manifold Means of Enforcing the Antitrust Laws:Too Much,Too Little,or Just Right [J].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Vol. 16,2004.
[13] Adolf Menzel,Die wirtschaftlichen Kartelle und die Rechtsordnung,Referat erstattet an di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Herbst 1894 [C],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LXI Verhandlungen von 1894,Leipzig,1895.
[14] Günter Hirsch,Private Enforcement of EC Competition Law -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J]. Competition Law Journal,vol.5,2006.
[15] David Gerber,Law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Protecting Prometheus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6] 方小敏.竞争法视野中的欧洲法律统一[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7] Hannah L. Buxbaum,German Legal Cultur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xpansion of 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J].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2005.
[18] Otto Schlecht,Macht und Ohnmacht der Ordnungspolitik -Eine Bilanz nach 40 Jahren Sozialer Marktwirtschaft [J]. ORDO,Bd. 40,1989.
[19] Mitsuo Matsushita,Clifford A. Jones,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M].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
[20] Ernst-Joachim Mestmäcker,Europäisches Wettbewerbsrecht [M]. München:C. H. Beck Verlag,1974.
[21] [德]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秩序政策论集[C].(何梦笔主编.)董靖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2] [德]费肯杰. 经济法(第二卷)[M].张世明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3] Wolfgang Fikentscher,Wettbewerb und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die Stellung des Rechts der Wettbewerbsbeschr?nkungen in der Rechtsordnung [M]. München:Beck,1958.
[24] Otto Sandrock,Grundbegriffe des Gesetzes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 [M]. München:Verlag C. H. Beck,1968.
[25] Wolfgang Fikentscher,United Nations Codes of Conduct:New Paths in International Law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 30,1982.
[26] See Lennart Ritter & W. David Braun,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A Practitioner’s Guide [M]. The Hague,London,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
[27] [英]布瑞恩·麦克唐纳. 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M]. 叶兴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8] [比]保罗·纽尔.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