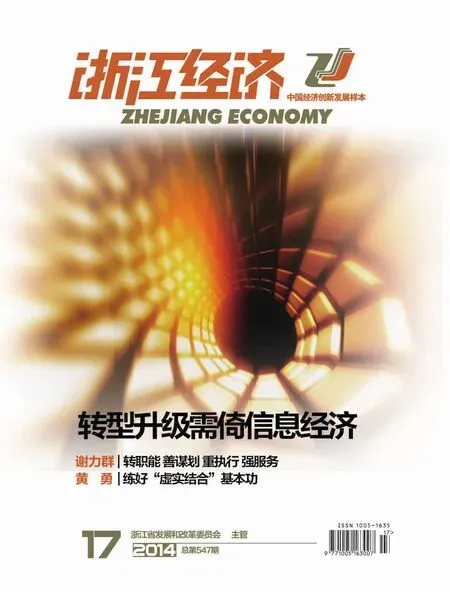邂逅云南返沪知青大军
30多年过去了,知青们那些说话内容、那些真切感情,那车厢内青春飞扬的气氛,仍在眼前
1979年初春时分,浙报老记者杨兴萱老师带我去金华采访。后独自一人,乘晚上八时多火车回杭,无意之中,相遇云南返沪知青大军。当时,我哪知道正进入一历史重大事件。甫入车厢,就觉得格外拥挤。坐席皆满,通道堵塞,车厢连接处亦满是人。我艰难穿过人群,来到一坐席旁,扶着靠背,这块地尚不拥挤,真心小幸福地安顿下来。
我打量车厢四周。当时正是首次记者实习,为培养职业素养,对任何事都有极大兴趣,总是努力仔细观察,专心听别人说话。这是沪昆特快,到金华已开了两天两夜多。车厢内基本都是二十七八岁年青人,男女夹杂,有几人蜷缩在坐席下,也有人卧在行李架上。很快我就发现他们是云南返沪的上海知青。我出生在上海,经常会在上海外婆等亲戚家呆上一段时间,当时能说一口毫无外地口音的上海话。听到柔和甜雅的上海腔调,十分亲切,暗里有一种车上遇知故感觉。
我有一个上海表姐,文革初期去了云南农场。当时,听说那地方与上海相比非常落后,反正上海人在那边是没法过日子的。我堂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姑婆,成天想念宝贝女儿,十分痛苦。后来,他们家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以生病和嫁人为由,回到老家镇海小港。表姐大我七八岁,初中时在上海遇见,已是小港人妻,前几年还电话联系过。那次上海姑妈家相遇印象十分深刻,我尚是十六七岁少年,表姐已然典型上海美女。我太太也有一位上海表姐在云南,不过际遇稍好。太太表姐在云南与一上海知青结婚,后进入云南外贸企业,继被派广州工作,全家在广州居住至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居然有二位云南知青,可见当年这事在上海涉及之广。
上海知青在列车上,正你一嘴我一舌说得非常热闹。有一个横卧在行李架上的男知青,探身俯首向他的同伴吹牛,他是如何多么巧妙地哄骗农场领导,又是何等艰难地搭上这列火车。听得出来,农场领导并不愿放行他们。他们为了能回上海,得编造种种理由,那位说话的知青,似乎是以生病名义返沪。通过关系开各种病情证明,也算是中国特色,至今盛行不衰。中国人出于无奈的造假,最后演变为全民受害,知青返城恐是原点。
车厢里不少知青大概是以顶替名义回沪。所谓顶替就是父母提前退休,然后其工作由子女来做。当时有些父母尚五十挂零,正是人生黄金时期,可是为了子女,他们不得不放下心爱的工作。其中一些技术工人,后来在乡镇企业发展中大显身手。我上世纪80年代初调查乡镇企业,宁绍甬一带工厂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
列车离上海越来越近。车过诸暨,按当时车速,起码还有5个多小时。然而,知青们的心已到了上海,回到了自己可爱的家。不少知青想象着家人如何迎接他们。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多半四五年没回家,有些甚至一次也没回来过。一位男知青:“阿拉姆妈晓得我顶喜欢吃油豆腐烤肉,伊呆板(肯定)烧好了等我。”一位女知青:“阿拉爷(父亲)已经没了,阿拉姆妈一介头(一个人),勿好(不能)来车站接我,反正我没啥物事(行李)。”一位男知青:“晓得我今朝回来,阿拉阿姐开心得不得了,伊拉(他们)呆板来车站来接我,侬迪眼(这些)物事,小事一桩。”一位男青年:“阿拉屋里房子老小咯,回起(去)勿晓得困(睡)啥地方起。”
我细心听着他们对话。30多年过去了,那些说话内容,那些他们的真切感情,那车厢内青春飞扬的气氛,仍在眼前。我当时遭受着知青们带给我的强烈感情冲击,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一人说及在云南的苦难,反而是满腔希望,期待着全新生活。这些青春期男男女女,开心地打情骂俏,欢畅的戏谑声此起彼落。不过,听到他们迫切想见家人时的那些话,我几乎是硬忍住自己眼泪。
车到杭州已近一时,夜班公交带我穿过深重的夜色。当时,我很是思绪万分,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总是不停地折腾,为什么非要让人骨肉分离远去他乡,为什么高层领导失误代价,却要我们一代年青人来承担。坦率地说,这些复杂的问题,当时并不是我这样的年青人能想明白的。
——献给知青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