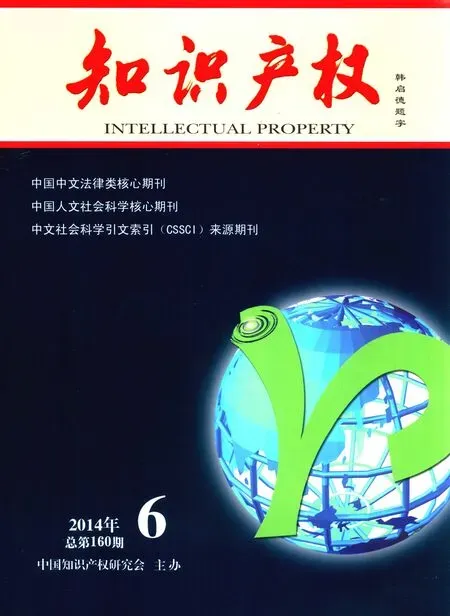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司法认定
霍文良 张天兴
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司法认定
霍文良 张天兴
侵犯商标权的一般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仅仅是数额的差异,在具体行为方式、行为内容、主观认知等方面也是有区别的。司法实践有忽视这种区别,泛犯罪化和刑罚化的趋势,准确地认定侵犯商标权的犯罪必须明确这些区别。首先,必须是直接在商品上使用假冒注册商标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服务商标不构成犯罪;其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必须坚持明知,要准确认定“应当知道”;第三,侵犯商标权共同犯罪的认定范围应当考虑犯罪的轻重。
商标权 应当知道 共同犯罪
关于侵犯注册商标权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三个罪名。从形式上看,这三个罪名与一般的侵犯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二者的区别并不只是量的差异,而是在具体的行为内容、对象范围、主观认知等多方面。当前司法实践有忽视这种差别,泛犯罪化和刑罚化的趋势。因此,准确认定侵犯商标权的犯罪,必须明确这些区别。
一、假冒行为的认定
《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明确规定,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才构成犯罪,而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并没有做出类似规定,那么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否应沿用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同一商品”、“相同的商标”这一标准?一般认为,刑法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三个罪名是一个复杂犯罪的阶段分工,刑法只是将通常由三个不同主体a当然也可以由一个主体独立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不需数罪并罚,只按假冒注册商标罪一罪处理。分阶段实施的犯罪进行了明确的分割,而区分成三个独立犯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这三个罪名看成是特殊的 “共同犯罪”,其指向了同一的被害人、同一的对象(注册商标)。假冒注册商标是以销售为目的的生产行为b不以销售为目的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原则上不构成犯罪,如基于炫耀目的假冒奢侈品商标自己使用,不应作为犯罪处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以假冒注册商标为前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又是为上述二者服务的,这三个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三个罪名应坚持统一标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也应适用“同一商品”、“相同的商标”这一标准。但对使用相同的商标”的认定采取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存在争议。所谓客观标准是指销售直接在商品上使用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主观标准则是强调主观上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故意,客观上有向他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但不强调必须在商品本身上直接使用假冒的注册商标,而包括使用其他方法使他人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假冒注册商标罪如果不直接涉及第三方,那么采用客观标准是理所当然的,而如果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涉及第三方(消费者)就会面临主观标准、客观标准的选择。司法实践中对此争议很大,导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如销售假冒“剪标”商品的行为,各地司法机关的处理就不同。
所谓“剪标”商品常见于服装领域,指品牌商将品牌标识剪掉,低价销售,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瑕疵商品剪标。因商品有小瑕疵而剪标低价销售;二是尾货剪标。为了避免尾货产品对正品造成价格冲击,剪标低价处理。这类剪标尾货质量与正品无差异,但价格往往只有正品的1/10;三是过季商品剪标。此类剪标产品与正品没有差别,因为款式过时而清仓处理。总之,不管基于哪一种理由的剪标,其剪标的目的就是要使被剪标的商品排除于注册商标的品牌之外,从而不影响品牌的声誉、质量标准、销售价格等品牌效应。正常情况下,剪标商品不能以原注册商标的名义宣传销售,但实践中商家往往以名牌剪标作为宣传、销售的噱头,因而形成了剪标服装的火爆市场。也因此产生了销售假冒名牌剪标商品的行为,此种行为是否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实践中某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关于剪牌、无吊牌、剪吊牌、无标款等问题,被告人其经营的网店,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以地素DAZZLE品牌专柜正品代购等名义销售与地素品牌款式一致的服装,既强调了地素DAZZLE品牌,又强调了专柜、正品、代购,事实上欺骗了购买者,足以产生误导,对地素公司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刑法规定的商标使用,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该案中,被告人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或许可,将地素商标或直接用于商品上,或用于网店的宣传及产品的介绍说明等商业活动中属于对地素商标的使用,这些行为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c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梅大军、朱某某假冒注册商标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sh/shsdyzjrmfy/ shsmxqrmfy/zscq/201402/t20140216_34698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3月21日。法院判决依据的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04解释》)。《04解释》第8条规定:《刑法》第213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本文认为,《04解释》对“使用”的界定不当,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属于扩大解释。这一解释直接引用国务院2002年《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02条例》),忽略了民事领域与刑事领域的区别。《02条例》规定的“使用”强调的是合法使用,而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合法使用与非法使用的范围是不同的,而构成刑事犯罪的“使用”则更是有其独特的范围。从刑法规定来看,“使用”被严格限制在商品本身上的应用,就是为了限制刑事打击的范围,是区分侵权的一般违法和犯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刑法意义上的“使用”,不应包含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强调的是由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与真实商品的不可区分性,而对商标权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刑法规定强调了必须是直接在商品上使用假冒注册商标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另外,如果没有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直接在商品上使用,仅是在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使用,其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是为欺诈行为服务的,该行为的实质不是混淆假冒商品与注册商标商品,因此不应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如在一些网络销售、电视销售中,宣传所售商品为知名品牌,但寄送的商品并非假冒知名品牌的商品,通常是其他品牌甚至无品牌的商品,这种行为是利用知名商标实施的欺诈行为,而非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既有假冒剪标商品,又有直接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判决未对两种行为加以区分,判定被告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文认为,单纯假冒剪标商品的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商标权人销售剪标商品本身表明其已在该商品上放弃了使用商标权,而冒充剪标商品实际上是冒充了商标权所有者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冒充商标本身,并不直接侵犯商标权,因此,销售假冒剪标商品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实践中,其他类似侵犯商标权而不构成犯罪的还有很多,如通过广告等宣传方式假冒著名商标的子品牌,因其利用的是消费者对商标权人所生产商品的信任,是对生产厂商的信任,而非商标本身,因此也不构成侵犯商标权的犯罪。
二、假冒服务商标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问题
关于假冒服务商标是否构成犯罪,当前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中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注册商品商标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对象,而注册服务商标不在其中,应不构成犯罪d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杨靖军、鲁统民 :《假冒服务性商标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8期,第56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同一服务项目上使用与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的商标,也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同样可以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e赵秉志:《侵犯知识产权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页;袁博:《假冒服务商标同样可以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载《中华商标》2013年第4期,第41~44页。。还有人认为,未来立法中应对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对服务商标作为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对象。f陈婵婷:《服务商标应成为商标犯罪的对象》,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1期,第64页。将假冒服务商标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包括现在和将来立法两种观点),其主要理由一般有以下两点:第一,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应同等保护。我国《商标法》第4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第二,依据国际义务和国际惯例。对于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都应该予以保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都将服务商标纳入了刑事保护体制,我国台湾地区也对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给予了同等的刑事保护。
本文认为,对于服务商标不应作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对象,基于服务商标的特点其并不需要进入刑事法律领域。首先,关于平等保护问题。商标法的规定代表了民事法律的平等保护,只能在民事领域适用,其并不能直接决定刑事法律的应用,必须注意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区别,刑事法律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即严格限定假冒商品的注册商标才构成犯罪。刑法的平等保护并非是同样一致的保护,而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需要来决定保护方式。如刑法中侵犯财产类犯罪最典型的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等,都明确其犯罪对象是动产及相类似的有价证券等,而不包含不动产。这并不能说明刑法上不动产不如动产重要、不加以平等保护,而是由于二者的不同特点导致不同的保护方式。盗窃、抢劫不动产的行为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由于不动产的不可移动性,使查处较为方便,挽回损失也更为容易,因此从刑法的谦抑性来说,如果其他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的保护与此相类似,服务商标无法像商品商标那样直接将商标缀附于商品或者服务本身,而是要通过广告、招牌等方式使用商标,因此假冒服务商标行为的公开性更强。不管是被侵犯商标权的受害人,还是执法者都容易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不管是证据的收集还是查处、打击都更容易实现。因此其他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刑法则保持谦抑。另外,服务商标与企业名称、商号等往往密不可分,许多时候是由相同文字构成,因此要证明行为人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故意很困难,行为人可能缺乏对服务商标的认识,只考虑商号或企业名称,通常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很难认定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故意。
其次,对于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问题,应当看到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我国对于商标权的保护既有司法保护,还有行政保护。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际上的刑事程序保护范围与我国不同,许多国家的刑法包含了轻罪与重罪,有的还包含了违警罪,在这些国家,一些轻罪和违警罪大约与我国的行政处罚相当,多以财产刑为主要惩罚措施g如法国《刑法》第131-12条至第131-18条规定违警罪的惩罚是罚金及附加刑而不包含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参见法国《新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而侵犯商标权的犯罪都是轻罪和违警罪,其规定的内容更是包含了我国《商标法》中绝大多数侵犯商标权的行为,甚至还更为广泛。如德国《标识法》除商标权外,还对名称权、装饰权等给予刑事法律保护h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39页。。这些国家刑事法律中有一部分的惩罚方式与我国的行政处罚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因此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处理方式,我国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双轨制并不违反国际公约。
三、主观“明知”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214条的规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销售的商品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是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因此,科学地认识“明知”是正确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重要前提。《04解释》第9条规定了四种情形的“明知”,在解释中前三项的明知是具体的,一般不会出现争议,关键是第四项规定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如何认定,特别是“应当知道”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常以各种理由辩解其不知销售的商品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给认定犯罪造成较大障碍。有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知道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很少见,因此运用证据推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为“应当知道”的情形更为普遍。但司法工作人员普遍反映推定的程度、推定的标准难以把握,推定程度过小可能放纵犯罪;推定程度过大可能将疏忽大意过失纳入明知范围,甚至导致明知要件虚设,造成客观归罪。
准确认定“应当知道”必须明确界定“应当知道”的内涵。“应当知道”在刑法理论上是具有很大争议的话题。张明楷教授认为,“应当知道”表明行为人事实上还不知道,而“明知”表明行为人事实上已经知道,故“应当知道”不属于“明知”。i张明楷:《如何理解和认定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第88页。陈兴良教授同样认为:“不能将应当知道解释为明知的表现形式,应当知道就是不知,不知岂能是明知”。j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解释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知道”是故意犯罪中关于主观明知状态的推定,并非过失犯的预见规定,而是故意明知认定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推定的故意,根基在于刑事推定,应当遵循推定的基本规则。k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53页。本文认为,“应当知道”从文字、语言的逻辑上,是指从客观来看知道是正常的状态,不知道通常是不可能的、不正常的,因此说是基于证据的逻辑推定,推定的前提是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的不知悉。至于以上学者所说的应当知道就是还不知道或不知的观点,其实是将“应当知道”与疏忽大意过失中的“应当预见”混淆。虽然二者都使用了应当,但二者有着明显区别,“应当预见”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认知,强调的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可能造成后果的认知,是一种逻辑判断认知,是法律基于当时客观状况、行为人的主体认知能力及相关职责等做出的事后判断。而“应当知道”是司法推定意义上的“应知”,强调的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行为对象的认知状况,这种认知是确定的,是通过行为表现表于外部的,并且这种行为通常是反复的、多次的,所以客观性更强。这里的应当强调的是证明方式、证明程度的特殊性,是证据意义上的“应知”。
事实上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犯罪故意中的明知,还是特殊犯罪中对行为对象的明知,作为行为人的主观活动都是需要证据来证明的。行为人内心的主观意识活动是无法直接阅读的,只能通过行为人外在行为来进行判断、认定。所以,《04解释》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都是指通过证据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认定或推定,行为人的所谓“真实认知状况”并不在法律考虑之中,主观状态的认定应当以客观证据的证明效果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方面都是推定的。如签字的效力,实践中一般只要行为人在相关书面材料上签字,就推定行为人知道,而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实知悉,是否真正地阅读并了解其内容。因此,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区分只是基于不同证明程度或证明方法而决定的,并不代表认知程度的差异。本文认为,明知的认定可以分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无需其他证据,客观事实行为本身就直接证明行为人主观事实的明知,如使用暴力违反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只需证明这一行为事实客观存在,行为人主观上的强奸故意(包括强奸故意中的明知)无需另行证明而自然成立,并且行为人通常不能以其他证据来否定其犯罪故意,只能通过否定犯罪行为事实本身来否定犯罪故意,二者是同时存在同时成立的。再如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故意没有强调明知,并不是说犯罪故意中不包含明知,而是其行为本身就证明了其故意,无需其他证据。第二种情形是通过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的明知,但行为人可以通过否定直接证据本身来否定自己明知,一般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来否定明知。这种情形是比较少见的,能直接证明行为人明知的直接证据的出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一旦出现则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第三种情形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而是通过间接证据推定行为人明知,行为人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否定自己明知。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但并不绝对,通常综合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行为人的明知。其中前两种明知就是所谓的知道,而最后一种证明方式就是“应当知道”。
因此“应当知道”实际是指通过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是知道的、是理所当然知道的,这种知道是正常状态、通常状态。而如果行为人主张确实不知来否定明知,则行为人应对此不正常状况、特殊情况进行举证,如能有充分证据则可以否定明知,否则推定行为人是明知的。所以,认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当知道”的标准就是,通过客观证据认定行为人的知道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不知道是不现实的、不正常的。事实上《04解释》第9条前三项的规定也是一种推定,属于应当知道。除司法解释之外“应当知道”的判定,应当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对间接证据进行综合判断。通常可包括:(1)行为人是否曾被告知所销售的商品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如能够证明有人曾明确告知其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则认定行为人明知。(2)销售商品进货价格和质量明显低于市场上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商品的进货价格和质量,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经验和知识,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这种不正常,推定行为人明知自己销售的可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l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04页。(3)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进货渠道、买卖及交接的时间、地点与方式、方法是否正常。m曲新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68页。如行为人采取隐蔽手段秘密售假;或者采用场内议价、场外交易的方式异地售假;或者在交易时更换或调换经销商品的商标,这些不正常行为充分说明行为人对商品的认知状况,就应认定行为人明知。(4)其他外在行为或者客观事实能推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四、共同犯罪人的认定
从司法实践来看,侵犯注册商标权的犯罪,通常是连续的犯罪,从生产到消费需要经过很多环节,必然涉及到市场链上的不同主体n,并且这些犯罪大多是人员众多的共同犯罪,且多为5人以上参与的共同犯罪。这就会涉及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04解释》第16条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储存、代理进出口等便利条件、帮助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尽管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哪些情形应认定为共犯,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是否认定为共犯及如何处理,并没有明规定,导致实践中认识不一。所谓辅助人员,主要指受雇于主要犯罪人的,具体侵权活动的直接实施者、参与者。对于这些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不同司法机关处理差别很大,有的未被纳入刑事程序;有的未被起诉;有的最终未被法院定罪判刑,也有的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在李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两名负责开车、搬运的辅助人员,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但检察机关认为情节轻微,审查后决定不起诉。而王某假冒注册商标案中,公安机关对参与制假的雇佣工人未作任何处理,检察机关亦未追诉。当前司法实践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犯罪情节较轻”、“情节显著轻微”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共同犯罪的犯罪人范围存在不同认识,从而导致对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是否认定为共犯及如何处理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应当如何认定共同犯罪人的范围呢?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但是不是在共同犯罪中发挥了作用的行为主体就都构成犯罪呢?就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呢?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追究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如将我国《刑法》总则中规定的犯罪预备,理解为适应刑法分则中每一个故意犯罪。从理论上说,犯罪预备应当只存在于严重犯罪,对于大多数较轻罪名的犯罪预备行为不应处罚。现代各国刑法原则上不处罚预备罪,只是处罚少数极为严重的犯罪的预备罪o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而且通常是在刑法分则罪刑条款中有明确规定才处罚。而共同犯罪的认定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对参与了犯罪、对犯罪发挥了作用的行为人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条文中一些罪名的规定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如在聚众犯罪中确定了不同的处罚范围,见下表:理,从而更好地把握好刑事法律尺度。即首先考虑罪名的法定刑轻重,侵犯商标权的三个罪名其基本犯罪的法定刑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即从刑罚角度来看都属于较轻的犯罪,因此原则上对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应采取谨慎态度,应当只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核心的犯罪人。对在犯罪活动中所起实际作用较小、参与时间较短、主观恶性不大的一般雇工,不宜作为共犯处理。对情节特别严重的侵犯商标权的共同犯罪人的认定,由于法定刑的提高,可以适当扩大范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综合考量对相关人员是否追究刑事责任:(1)行为人参与过生产和销售的数额、数量的大小;(2)行为人与主犯之间有无固定、稳定的雇佣关系,工作的时间长短,所起的作用大小;(3)行为人是否直接参与非法利益的分配;(4)行为动机、恶性程度等其他因素。
对于不作为共犯处理的情形,还可以直接依据《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进行处理。但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使用很少,主要是由于缺乏具体标准,担心受到质疑。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法律
从上图来看,我国刑法并非对参与犯罪的全部人员都追究刑事责任。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原则上罪名越重(体现在法定刑重)则共同犯罪人的范围越大,反之罪名越轻(体现在法定刑轻)则共同犯罪人的范围越小。这一结论应当同样适用于司法实践对共同犯罪的认定。
对侵犯注册商标权的犯罪,处于从属或者辅助地位的人员是否入罪,可以依据上述原则来处的适用有机械化倾向,缺乏灵活性、主动性,许多时候没有司法解释的明确具体标准,人民法院不敢判案。本文认为,对于法律的适用应灵活主动,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防止司法之“手”伸得太长或承载着非份之重,引起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p梁平:《语义与实践: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进路探究》,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3期,第59页。。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平衡好刑事司法政策与法律适用之间的关系。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eral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nd crim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is not just the numbers, their specifi c behavior, behavioral content and subjective cognition are different also. These differences are ignored in judicial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criminalization and punishmen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lear the differences to identify the crim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ccurately. Firstly, the crime of counterfeiting registered trademarks requires that the counterfeited registered trademarks must be directly used on the products, and counterfeiting the service trademarks does not constitute a crime. Secondly,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crime of selling commodities bearing counterfeit registered trademarks must be “clearly know” and we should also identify “should have know” accurately. Finally, when identifying the scope of the joint crime of trademark infringemen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severity of them.
trademark rights; should have know; joint crime
霍文良,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讲师,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张天兴,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教授,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实践(HB13FX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3MS120);河北省哲学社科研究基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