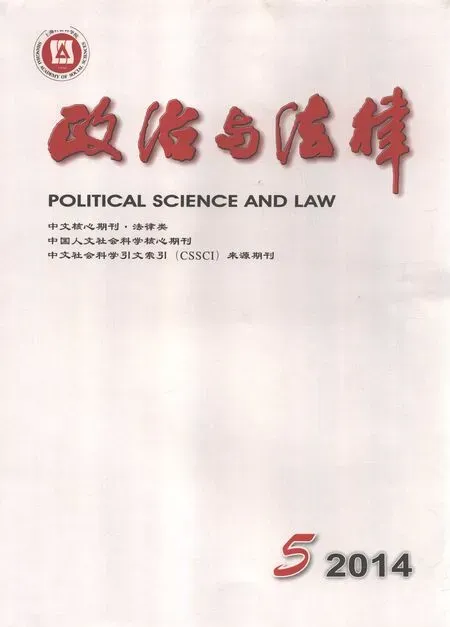民法中辅助占有状态的刑法解读*
马寅翔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1620)
民法中辅助占有状态的刑法解读*
马寅翔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1620)
虽然对于依他人占有意思在事实上控制、管领财物者与财物之间存在民法上的辅助占有状态,但不能以民法中的辅助占有理论为根据,否认此情形中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实际上已经普遍承认了刑法中占有的观念化,但较之于民法中的占有而言,刑法中的占有仍对支配事实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就辅助占有状态而言,由于支配事实的存在,辅助占有人对于财物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只不过需要根据支配领域判断其属于单独占有还是共同占有。单独占有者可能构成侵占,共同占有者则可能构成盗窃。是否具有处分权限与下位者是否占有财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通行的以处分权限的有无作为判断占有状态标准的做法值得商榷。
从属判断说;独立判断说;占有观念化;处分权限;支配领域
辅助占有制度原本是民法理论的塑造物,近些年来,这种民法上的主张逐渐为刑法学者所接受并运用于刑法问题的解决中,以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已出现在我国司法考试的标准答案里,影响可谓深远。就作为辅助占有上位概念的占有而言,刑法学者在讨论时,大多十分明确地主张其在刑法中的独特性,认为与民法中的占有相比,刑法中的占有更具有事实性,并否认为民法理论所承认的占有的观念化。但是,在判断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关系的有无时,学者们往往又不自觉地向民法中的占有概念靠拢,辅助占有的问题即为典型。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据通说地位的观点认为,在处理辅助占有问题时,应当遵循民法理论的主张,原则上否认下位者对于财物存在占有,只是例外地承认具有处分权限者的占有。根据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刑法中也可以存在观念化的占有。对于不具备处分权限的下位者彻底否认其对所握有的财物存在占有的做法,与刑法中强调支配事实的占有概念相抵牾,也与刑法理论对占有概念独立性的强调相悖逆。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支持的判例也表明,这种主张并未获得我国司法实践的认可。基于对这些矛盾现象的反思,本文试图在查明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可以逻辑自洽的答案,以期充分揭示刑法中的占有理应具备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分功能。
一、从属判断说与独立判断说之分歧
民法中的辅助占有,又称为占有辅助,系与自己占有相对的概念。“以实施占有者之从属关系为标准而区分,凡占有人亲自对于其物为事实上之管领者,谓之自己占有;反之,对于其物系基于特定之从属关系,受他人指示而为占有者,谓之辅助占有。”①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修订5版)(下册),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版,第1154页。例如,甲雇乙驾车时,甲为占有人,乙为辅助占有人。辅助占有人的概念源自德文Besitzdiener,为德国法学家贝克(Bekker)所创设。②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页。辅助占有现象古已有之,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工商社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将属于自己占有的财物交给他人以替代自己完成某种行为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这种情况导致所有人将财物交由受委托人后,在事实上无法再有效地对财物加以控制,如果按照传统民法理论对占有的理解,财物所有人就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而仅享有对受委托人的占有物返还请求权,这显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不符。为了解决传统占有理论的这一不合理之处,民法学者创设了辅助占有理论。根据该理论,辅助占有人并非真正的占有人,他与财物之间并不存在占有关系,处于上位者才属于真正的占有人。在存在辅助占有关系的情况下,民法中的“占有即所有”的通常理解被突破,在事实上管领财物的人不再被视为占有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辅助占有理论是对占有概念所作的限缩性的制度设计,属于占有的例外情形。③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为了避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相悖,民法理论并不承认辅助占有人对财物存在占有,但是作为对传统占有概念的限缩性解释,其实际上仍然承认的是,辅助占有人与财物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直接控制、支配关系,只不过不称这种关系为占有关系,而是称之为辅助占有关系。
虽然在民法理论中,并不承认辅助占有人对于其在事实上直接控制、支配的财物形成占有,但是在刑法理论中,对占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是重视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因而在辅助占有人将财物非法据为己有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围绕着是否要以民法理论的主张为根据,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存在着从属判断说与独立判断说之争。
从属判断说认为,在辅助占有人将辅助占有物据为己有时,应当以民法理论对辅助占有的理解作为判断标准。既然在民法上,辅助占有人不能获得民法意义上的对财物的占有,那么在刑法上,辅助占有人也不能获得刑法意义上的对财物的占有。也就是说,在存在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下,占有归于位于上级的占有者。因此可将这种观点称之为上位者占有说。根据上位者占有说,如果商店的工作人员在商店内销售商品时,取走了其所销售的商品,由于商品的占有归于店主,工作人员取走商品的行为构成盗窃。同样,仓库值班人员对仓库内的财物也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上位者占有说的这种处理方式是日本刑法理论及实务的通说。④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3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但是,也有日本学者对上位者占有说的主张进行了局部修正,可将其称为修正的从属判断说。该说认为,对于诸如掌柜、经理等下位者而言,由于其与属于上位者的主人、雇主之间存在高度的信赖关系,对其现实支配着的财物被赋予了一定的处分权限,应当承认这种情况的下位者对财物存在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占有归属的判断而言,信赖关系的程度、强弱属于实质的重要判断基准。⑤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述(各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日]大塚裕史:《刑法各论的思考方法》(第3版),早稻田经营出版2010年版,第47页。当然,信赖关系的程度、强弱等只是用来判断处分权限有无的因素,对于占有的判断而言,最为关键的仍是处分权限的有无本身。虽然修正的从属判断说同样以民法理论的见解为依据,在原则上否认辅助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但却例外地承认具有民法上的处分权限的辅助占有人的占有,如果这类辅助占有人将财物非法占据为己有,则构成侵占。
与日本的通说不同的是,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修正的从属判断说居于通说地位。详言之,我国的通说认为,当数人共同管理某种财物,而且存在上下主从关系时,刑法上的占有通常属于上位者,而不属于下位者。即使下位者事实上握有财物或者事实上支配财物,也只不过是单纯的监视者或者辅助占有者。因此,下位者基于非法占有目的取走财物的,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上位者与下位者具有高度的信赖关系,下位者被授予某种程度的处分权时,就应承认下位者的占有;下位者任意处分财物,就不构成盗窃罪,而构成其他犯罪。在判断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归属时,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的程度、强弱是重要的判断标准,根据信赖关系的程度、强弱,可以确定下位者是否对其所管理的财物具有一定的处分权限,不具有处分权限者的取得行为构成盗窃,具有处分权限者的取得行为构成侵占。⑥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6页;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魏海:《盗窃罪研究——以司法扩张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还有观点在承认财物通常由上位者占有的同时,认为当上位者基于信赖关系赋予下位者一定处分权限时,应当认为上位者与下位者共同占有财物,如果下位者避开上位者将财物取走,则可能构成盗窃;当上位者将具体某物委托给下位者时,则下位者成立专属占有,如果下位者将其非法据为己有,则可能构成侵占。⑦参见王玉珏:《刑法中的财产性质及财产控制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独立判断说认为,在辅助占有人对辅助占有物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问题上,应当以刑法对占有的理解作为判断标准。辅助占有人对辅助占有物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虽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但却不需要唯民法理论的主张马首是瞻。对于辅助占有人而言,尽管其对受其控制的财物并不存在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但却可能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独立判断说是德国的通说,在日本,也有牧野英一、植松正等学者持此观点。⑧同前注⑤,大塚仁书,第218页。在德国刑法理论界的多数学者及大部分司法实务部门看来,《德国民法典》关于辅助占有人的规定对于刑法而言并无意义。有德国学者认为,辅助占有人对财物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辅助占有人既可能和上位者一起对财物加以共同占有,也可能单独占有,或者根本不存在占有。⑨Vgl.Soltmann,Der Gewahrsamsbegriff in§242 StGB,Keip 1977,S.61.按照独立判断说的主张,如果民法上的辅助占有人将财物占为所有,在属于单独占有的情况下,则可能构成侵占罪;在属于共同占有的情况下,则可能构成盗窃罪。在德国,这一结论不仅为刑法学者所接受,也为实务部门所认可,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即认为,在主人外出期间受委托照看房屋的佣人,和屋主一起对房屋内的财物存在共同占有。⑩Vgl.BGHSt 10,400(400ff).此外,很多德国民法学者也承认民法中的占有与刑法中的占有存在如上述所说的区别。⑪⑪Vgl.Westermann,Sachenrecht,5.Aufl.,Verlag C.F.Müller Karlsruhe 1969,S.53.
然而,也有部分德国学者认为,关于在上下级关系中是否存在多重占有,或者上级是否属于排他性的占有人等问题的争论,在结论上并不存在什么不同之处。因为对于剥夺财物的行为而言,无论是下级实施的,还是第三人针对下级实施的,争论双方均会认为这种取走行为属于破坏占有,因此,“下级共同占有者”的法律形象在实践中是可有可无的。①Vgl.Schönke/Schröder/Eser/Bosch,28.Aufl.,Verlag C.H.Beck 2010,§242 Rn.32.更有学者甚至认为,既然只有下位者才能破坏上位者的占有,那么不妨根据社会—规范性的见解,认为下位者根本不存在支配,也就是说,上下级别的占有根本就不存在。②Vgl.Wessels/Hillenkamp,BT 2,34.Aufl.,C.F.Müller 2011,§2 Rn.96.这些观点实际上否认了辅助占有在刑法中的存在可能性。
尽管在如何看待刑法与民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从属判断说与独立判断说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是,对于刑法中的占有不同于民法中的占有,即刑法中的占有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点,持从属判断说的学者也同样持肯定态度。③同前注⑥,张明楷书,第873页;同前注⑥,黎宏文。既然如此,以民法中的辅助占有人对财物不构成占有为依据,来论证其在刑法上也同样不存在占有的作法,在逻辑上就难免自相矛盾,难以令人信服。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详细论述。此外,就结论而言,二者的差异的确并不悬殊,并且,无论是从属判断说还是独立判断说,在承认刑法中占有的观念化这一点上,也并无不同,因为两者都承认了上位者对于财物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并不是通过直接的事实上的支配力获得的。刑法中占有的观念化现象显然逸出了事实支配关系的范畴,而后者一直为刑法中的占有所强调,因而,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占有观念化在刑法中的逐步承认
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由于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具有后发型的特点,从德日引进的多为已经成熟定型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的发展脉络,除非专门研究,否则鲜为我国刑法学者所知晓。就占有的观念化而言,由于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刑法学界实际上已经普遍予以承认,这一点在辅助占有问题上已经清楚地得到体现。但是,由于这种承认属于理论的直接继受,其背后的原因被无意识地忽略了。应当说,对于深入把握占有的观念化而言,占有的观念化过程同样值得关注,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可以避免机械套用。为达到该目的,本文选取一度为日本所学习的德国刑法理论作为分析样本,试图忠实地勾勒出占有逐步观念化的发展过程。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占有的观念化是随着学者对占有概念内容认识的变化而逐步被接受的,它直接体现为占有状态认定标准的变化。就占有状态的认定标准而言,从最初的重视占有的事实要素的一面,到后来逐渐重视规范要素的一面,最终形成了强调占有的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并重的局面。上述演进过程的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标准的逐步提出。
(一)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最初的主流观点认为,占有是指人对财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关系,其承载着占有人的支配意思。④Vgl.Maurach,BT,Verlag C.F.Müller 1953,S.160.在认定某物的占有状态时,与该概念相一致,理论界采用的是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该标准以上述对占有概念的解释为基础,认为只要某人和财物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关系(客观—物理性要素),并反映着占有人的支配意思(主观—心理性要素),该占有人就对该物存在着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因而占有该物。但这一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适用,遗忘物便是其例。因为就遗忘物而言,作为主观—心理性要素的支配意思并不以支配者明确意识到该物的存在为必要,甚至在实际上支配者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意思。例如,对于乘客遗留在出租车内的手机,司机就未必意识到其存在,但根据社会文化观念,则认为司机对手机存在占有,这就证明了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寻求更为合适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德国司法实践中也鲜有判例彻底采纳这一主张。
(二)公众观念标准
为德国刑法理论提供转变契机的,是作为当时新兴现象的自助商店盗窃案。针对该类型案件所涉及的占有概念的问题,德国学者威尔哲尔(Welzel)教授指出,尽管所有权属于纯粹的法律关系,但占有却属于被纳入法律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控社会的手段,法律总是可以追溯至早已存在而非由其创设的社会结构,并为社会结构所包含。社会生活并无固定结构,而是通过风俗、传统、习惯、惯例等形成一定的结构与秩序,法律以各种形式将它们吸纳进来并加以保护。就占有而言,其映射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受社会尊重的人可以行使对物的支配的空间领域。物理支配中所含有的社会成分是占有概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①Vgl.Welzel,Der Gewahrsamsbegriff und die Diebstähle in Selbstbedienungsläden,GA 1960,264f.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赞同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尽管占有属于事实上的支配,在实体上靠近财物和能够施加物理上的力量,属于维持与财物关系的两个要素,但占有是否存在,却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两个要素的存否。对于财物的支配问题,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观点加以判断,占有的概念主要通过公众观念来认定。②Vgl.BGHSt 16,271(273).所谓公众观念标准反映的是一种考虑大多数公众观点的自然思考方式,实际上是社会文化观念在占有判断问题上的折射。根据这种思考方式,如果某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直接掌握某物时,就可以认为此人对该物存在事实上的支配。这种思考方式削弱了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的作用,导致不能再单独根据后者来判断是否对某物存在事实上的支配。③Vgl.Heinrich,in:Arzt/Mitarbeiter,BT,2.Aufl.,Verlag Ernst und Werner Gieseking 2009,§13 Rn.39.但是,这一判断标准被认为存在模糊性与恣意性,导致判决结论会根据判断者的好恶不同而变换。
(三)社会分配关系标准
在借鉴公众观念标准的主张的基础上,德国学者比特纳(Bittner)提出了更为激进也更为明确的主张,他认为占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表明的并非支配关系,也非尊重关系,而是一种社会分配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只能从与此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的角度加以考虑。比特纳认为,唯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有可能从客观上把握占有的概念,并摒弃传统占有概念所含有的主观要素。基于这种理解,比特纳将占有定义为:根据文化规范,在客观事实领域内产生的明显将某物归于某人的分配(Zuordnung)。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规范性质的占有概念。根据社会生活情况,比特纳将占有进一步划分为直接占有与一般占有。所谓的一般占有,是指虽然占有人并未直接占有某财物,但根据规制人类共同生活的法律规范以及社会文化规范,仍视为占有人占有该财物。例如停放在街道上的轿车,占有人对该轿车虽不存在直接占有,但却存在一般占有。④Vgl.Bittner,Der Gewahrsamsbegriff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Systematik der Vermögensdelikte,Südwestdeutscher Verlag für Hochschulschriften 2008,S.91 ff.比特纳的部分主张为某些德国学者所接受,他们在坚持支配关系的前提下,吸收了社会分配关系的合理内容,认为从社会规范性质的占有概念出发,对占有而言最为重要的支配关系,是根据社会规范将某物分配至某人的支配领域内而建立的。⑤Vgl.Wessels/Hillenkamp,BT 2,34.Aufl.,C.F.Müler 2011,§2 Rn.82,Fn.50.较之于公众观念标准的模糊性而言,社会分配关系标准已在很大程度上给出了较为客观、具体的可资利用的标准。而且,关于直接占有与一般占有的划分,对于规范要素在占有概念中的引入作了明确的说明,从而将人们的视线从先前的局限于直接占有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为更为明确地理解占有的规范属性奠定了基础。当然,就一般占有而言,由于其注重的是社会文化观念,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观念上的占有。在这一点上,占有的概念已经非常接近于民法中的占有,较之于直接占有而言,其在可把握性上开始变得模糊而困难。
(四)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
由于社会文化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像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那样容易把握,因此到目前为止,德国刑法理论通说仍认为,刑法中的占有是指某人和财物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关系(客观—物理性要素),其反映着人的支配意思(主观—心理性要素)。是否存在这两个要素,需要根据日常生活的朴素观念加以判断。如果对财物的意志影响能够不受阻碍地直接实现,则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关系。此时并不以法律上允许为标准,而是以事实上能够处分为依据,并且也不取决于占有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支配权。①Vgl.Schönke/Schröder/Eser/Bosch,a.a.O.Rn.24 ff.可见,尽管存在着前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主张,并且不乏倡导公众观念标准的学者,但德国刑法理论界总体上对占有概念的界定仍持保守态度,在认定占有状态时,并没有放弃对人的主观支配意思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抽象的概念应当满足法安定性的需求,并尽可能地保持对各种具体的占有问题作出一致的评价。但是,从上述表述不难看出,在德国刑法理论界,尽管还在继续沿用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理论,但对于占有的认定,事实上却常常需要考虑社会的评价。②Vgl.Heinrich,a.a.O.Rn.39.
由于较之于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现行的判断占有状态的标准已经指出了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影响,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这一标准实际上是对前述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与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的折中,认为只有当根据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无法对占有的认定给出明确的结论时,或者得出的结论显然与社会文化观念不符时,才需要考虑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从比特纳的主张来看,可以认为通说指的是只有当面临一般占有的情况时,才需要考虑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就此而言,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在直接占有的场合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仅是在判断是否存在一般占有的场合,即是否存在支配难以决断或者显然悖于常理时,才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根据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已经有了广为接受的明确结论时,例如农民对放置在离家几里甚至更远的田间农具仍存在占有,则排除纯粹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的适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虽然纯粹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因为自身的明确性而颇具优势,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公众观念标准/社会分配关系标准。③Vgl.Wessels/Hillenkamp,a.a.O.Rn.92.
(五)笔者的立场
由于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兼顾了公众观念标准以及社会分配关系标准的优点,加之公众观念标准与社会分配关系标准并非完全对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不予考虑,从这一点而言,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标准的融合,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因此其成为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也不足为奇。笔者同样赞同以该标准作为判断占有状态的总体依据,只是认为需要视具体情况侧重强调为其所包含的其他标准。这种综合性的判断标准所对应的占有概念不仅涉及对某物所具有的事实上的支配力,同时也涉及社会观念对于该支配力的承认,即所谓的观念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在本质上属于规范上的占有。这表明占有实际上具有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属性。当然,这种标准使得刑法中的占有概念放宽了对事实上的直接支配性的要求,将观念上的占有也涵盖在内。从这一点上来看,刑法中的占有与民法中的占有的区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但两者在出发点及范围上并不一致,例如民法中的占有就不承认幼儿或者精神病人对于财物的占有,刑法则仍加以承认。因而,即使在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下,仍然无法以民法中的占有概念来替代刑法中的占有概念。
对于占有的双重属性,不应认为它们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两者实际上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存在只具有事实的占有和只具有规范上的占有。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支配力和社会观念对于该支配力的承认成为占有这一概念的两个可区分等级的选言式要素,也就是说,占有的产生与存续并不需要事实上的支配与观念上的支配必须同时具备。此处所谓的可区分等级,指的是支配强度的强弱,如握在手中、摆在触手可得之处、置于当时并不处于但却能够自由进出的空间、放在明确知道具体位置的公共空间内,就事实上的支配力而言,这四种情形中的支配强度呈逐级减弱的趋势,而就社会观念对于该支配力的承认而言,则呈相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就占有的实现而言,事实上对某物的支配力(拿取可能性)越强,“社会上对此支配的承认”这个要求就可以越弱;反之,社会上对于某人之于某物的支配承认度越高,事实上拿取该物的可能性就可以越弱。当这两个可分级的占有属性其中之一强烈地显示时,即便另一个只有微弱的显示,也仍能够清楚地肯定占有的存在,只有当两个属性都很微弱地显现时,对于占有是否存在的判断才会产生困难。①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7页。在当今德国刑法理论中,单方面地以事实意义上的支配力或者规范意义上的支配可能性作为认定标准的主张并非通行做法,将两种属性相结合的做法才属于通说。同时,事实与规范的结合也并不是将二者简单拼凑在一起,实际上,两者属于互相补强的关系。
在这里,如果引入比特纳关于一般占有与直接占有的划分,那么直接占有与一般占有是否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则需要从以下两种情况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况为单独占有。在这一场合中,如果承认了一般占有的存在,则排除了直接占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一般占有的承认是以不存在直接占有为前提的。本文前面的讨论即是以单独占有为前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占有具有排他性的特征。
第二种情况为共同占有。占有的排他性并不等于说占有的主体只能为单数,除了单独占有以外,还存在着共同占有的情形。在这种场合中,既可能是共同的直接占有,也可能是直接占有与一般占有共存,还可能是共同的一般占有。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占有都是存在的,其程度的消长与事实属性和规范属性的强弱对比直接相关。这三种共同占有的情况表明,在存在一般占有的场合,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直接占有。
三、辅助占有状态在刑法中的多重意义
上文对于占有的观念化是如何被逐步承认的过程所作的梳理,虽然起因在于厘清其发展脉络,但落脚点却在于藉此来解决民法中的辅助占有现象。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普遍承认占有观念化的德国刑法理论中,也并未完全放弃占有的事实属性,当一个人对于财物存在直接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时,尤其是当他直接握有财物时,他对于财物就存在着刑法意义上占有。就辅助占有的现象而言,实际上涉及上文提及的共同占有的判断问题。
在厘清辅助占有现象中的共同占有应当如何判断之前,首先需要阐明的是,以民法为依据的从属判断说的做法并不具有合理性,即便是修正的从属判断说,也同样如此。
首先,与民法中的占有概念不同,刑法中的占有强调的是对财物的事实上的实际管理、支配可能性。虽然按照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这种对财物的事实上的管理、支配可能性不再限于直接占有,即存在着观念上的占有或者说一般占有,但即便是观念上的占有者也可能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从而不能成为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适格主体。因此,观念上的占有是否存在,并不以民法中的占有是否存在为前提。
其次,下位者对其所管理的财物是否具有一定的处分权限,也并非判断取得行为是构成盗窃罪还是构成侵占罪的恰当标准。从论者的表述来看,此处所谓的处分权限,指的应当是民法中属于所有权四大积极权能之一的处分权能。根据民法的相关理论,所谓的处分权能,是指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从而决定物的命运的权能,它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权能与法律上的处分权能。事实上的处分权能,是指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者毁损等物理上的事实行为;法律上的处分权能,是指将标的物的所有权加以转让、限制或者消灭,从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①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由于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引起财物形体的变更或消灭,显然其并非作为侵害所有权犯罪的盗窃罪与侵占罪所能涵盖的范畴,因此论者所说的处分权限,应指法律上的处分权能。但是,将财物交由他人保管与他人获得该财物的法律上的处分权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因为,从民法角度而言,将财物交由他人代为保管所涉及的仅仅是占有权能的转移,除委托人明确授权外,受委托人并不会获得对所托财物的处分权能。从刑法角度而言,作为侵犯所有权犯罪的侵占罪,其取得行为的本质特征即在于行为人将自己置于类似所有人的地位而僭用所有人的所有权,从而违法地将所有人的财物纳入自己的财产,实际上即为违法地行使处分权能。在这一点上,不论所有人与行为人是平级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均无不同。就此而言,正是因为对于所代为保管的财物,行为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处分权能但却违法地加以行使,才构成侵占。即便在辅助占有关系中,下位者根据授权对于财物享有一定的处分权(例如出售其代为保管的财物),但在他违反授权,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该财物的情况中,他同样不享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与原本并无处分权限的辅助占有人相比,具有一定处分权限的辅助占有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此处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对是否存在占有的判断,显然,此时依据处分权限的有无来判断是否存在占有的做法并不合适。
再次,从词源角度来看,以处分权的存否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观点,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不当理解,原因在于对处分权一词的理解存在偏颇之处。就刑法中的占有而言,其所涉及的处分权,指的是主体对于财物所具有的一种处置权力,德文为Verfügungsgewalt,即事实上的力量,凭借该力量,占有人可以按照自由意愿处置财物,例如供自己或他人使用,或者毁损等。这种处分权通常通过与财物的紧密空间关系来获得——要么财物必须处于占有人的支配空间范围之内,要么占有人必须具备随时不受障碍地掌握财物的可能性。②Vgl.Mitsch,BT 2/1,2.Aufl.,Springer 2003,§1 Rn.42 f.由此可见,刑法中的占有所指的处分权,涉及的是主体对于财物所存在的事实上的处置物品的实力,它与民法意义上的处分权存在着重大区别,它虽表现为具备事实上的处分实力,但目的却不在于像民法中的事实上的处分权能那样,对财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者毁损等物理上的事实行为,而是像民法上的权能那样,直指财物的所有权。其虽不能够在法律上引起民法中的所有权的变更,但却足以影响所有权的行使。因而,刑法中占有所说的事实上的处分权,同时兼具了民法占有中两种处分权能的特性,但却不以合法存在为必要,而是始终强调事实上的处置可能性。上述论者的观点实际上混淆了民法中的处分权与刑法中的处分权,因此,以是否具备民法中的处分权限来判断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并进而判断是构成盗窃还是侵占的判断思路,从一开始就不可取。
最后,认为辅助占有人对其所实际践行着支配的财物不存在占有的看法,不禁会使人想起受时代制约的等级观念,例如,对于企业交给高级雇员的工作设备或者货物,通常认定为单独持有或者与上位者的共同持有,而普通雇员对于这些物品,充其量也就存在共同占有。①Vgl.Vogel,in:LK-StGB,12.Aufl.,Walter de Gruyter 2010,§242 Rn.7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观念逐步发生着变化,社会从属关系即为适例。例如,先前的观点认为,对于生产工具的占有,一般分配给上位者,即便下位者随身携带也概莫能外。如今,几乎没有人再如此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尽管占有领域这一概念仍发挥着作用,但现在人们也开始考虑作为雇员的下位者的个人权利。如此一来,成为问题的就是,当上位者强行将生产工具从下位者处拿走时,是否也同样违反了下位者的意志?对此,正确的做法是,至少应当承认共同占有的存在。此时,不能简单地套用辅助占有制度,而是应当在个案中检验,谁能够在不违背社会主流观念的前提下接触物品。②Vgl.Schmitz,in:MK-StGB,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03,§242 Rn.65.
实际上,从刑法角度而言,对于民法理论中所说的辅助占有的情况,需要考虑的并非是否存在处分权限,而是如何处理直接占有与一般占有的关系。如前所述,直接占有表现的是占有的事实属性,一般占有表现的是占有的规范属性,在辅助占有的情况中,需要根据这两种属性在相关财物上所显示出的强弱程度判断谁属于占有人。详言之,在存在上下级辅助占有关系的情况下,当上位者对财物仍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可能性即存在事实上的直接占有时,则排除辅助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在这种情况下,辅助占有人如果取得该财物,则必然破坏上位者的占有,应构成盗窃。当上位者的占有为观念上的一般占有时,则直接握有财物的辅助占有人可以获得与上位者一起的共同占有。仍承认上位者存在这种形式的占有,是对日常生活观念的考虑,从而不至于因完全否认上位者的占有而丧失了结论的现实合理性。此种情况下,辅助占有人的占有属于事实上的占有,其实际支配力虽然并不一定弱于平级关系情况中的保管人,但同样是出于对公众观念的考虑,因而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只承认其与上位者一起对财物存在共同占有。在共同占有的情况下,如果辅助占有人取得了该财物,则其同样会破坏上位者对财物的占有,并建立起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单独占有,因而仍构成盗窃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认存在共同占有的前提下,对于下位者避开上位者取走财物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侵占,理由为:一是缺乏夺取占有,因为下位者本来就已经占有;二是这种情况同他人委托单独占有之后予以侵吞,并无实质差别。③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德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部门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在具有上下从属关系的占有中,下位者可以破坏上位者的占有,反之则不成立。原因在于,盗窃罪是侵犯他人所有权的犯罪,破坏下位者的占有并不会损害所有权,因而不构成盗窃。④Vgl.Eser/Bosch,a.a.O.Rn.32.应当说,既然承认共同占有的存在,当下位者将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时,势必会破坏上位者的占有,尽管这种占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观念上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存在,就此而言,以盗窃罪论处更具有合理性。
此外,为了避免不合理的结论,在判断辅助占有人是否存在共同占有时,还应当考虑财物所处的位置。具体来说,如果财物始终处于所有人的支配领域内,例如处于其所拥有的房屋、仓库、店铺、私家车内等,在此领域内将财物交由辅助占有人保管,则属于共同占有。如果财物所处位置发生变化,例如由所有人的支配领域转至公共支配领域,则此时辅助占有人的占有即属于单独占有,与平级关系的代为保管人无异。因此,在存在辅助占有关系的情况下,判断辅助占有人的占有状态时,需要参考的标准除了上下级关系以外,还需要对财物所处的支配领域加以考虑。因此,上述德国学者所谓的“下级共同占有者”的法律形象在实践中是可有可无的说法值得商榷。只有当下级占有的财物仍处于上级所有人的支配领域范围内时,这种说法才可以成立,在处于所有人的支配领域之外时,这种说法就变得不再妥当。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下位者被委托对财物行使处分权,具有直接的管理支配力,则上位者与下位者的主从关系随之消除,也就不存在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区分。因此,只要支配财物的数人之间具有上下主从关系,下位者就不可能单独占有财物。①参见张红昌:《财产罪中的占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对于主从关系的界定,该观点以下位者是否具备独立的处分权为标准,这显然与主从关系的本义相悖,以之否认下位者对财物的单独占有可能性,自然难言妥当。
为了不造成空洞言说的印象,此处以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曾出过的一道选择题(卷二第15题)作为分析样本:甲路过某自行车修理店,见有一辆名牌电动自行车(价值1万元)停在门口,欲据为己有。甲见店内货架上无自行车锁便谎称要购买,催促店主去50米之外的库房拿货。店主临走时对甲说:“我去拿锁,你帮我看一下店。”店主离店后,甲骑走电动自行车。
该题的答案认为,甲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为:“理论上一般认为,这种情况下财产的占有状态并没有发生转移,修理店仍然在店主的占有之下,甲只不过是一个辅助占有人,临时帮忙看管一下。所以,甲的行为构成盗窃而非侵占。”②陈兴良、陈子平:《两岸刑法案例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这是一个运用民法中的辅助占有概念来解决刑法问题的典型例子。认为甲属于辅助占有人的观点,显然是采纳了(修正的)从属判断说的立场。对于(修正的)从属判断说,暂且抛开上文所列的不合理性不谈,单就辅助占有的成立条件而言,案例中甲的情况也并不符合。民法理论一般认为,辅助占有的成立,以受他人指示而对于物有管领力为要件。所谓受他人指示,系指命令与服从的社会从属关系。该关系也被称之为命令服从关系,指的是雇佣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基于其他受他人的指示而为占有的类似关系。所谓他人,又称“主人”,是指处于上级地位而享有指示权的人。在其他类似关系中,受委托关系并不包括在内。③同前注②,王泽鉴书,第438页;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按照这种理解,案例中店主与甲之间并不存在社会从属关系,店主对于甲而言并不处于上级地位,因而也不享有指示权。因此,甲并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辅助占有人,而是受委托人。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甲由于受店主的委托而对电动自行车存在占有,其行为只可能构成侵占罪。原因在于,根据社会观念,案发地点处于店主的分配领域之内,其对于电动自行车仍存在为刑法所承认的观念上的占有。甲将车骑走,必然会破坏店主的占有,因而构成盗窃罪。因此,从行为定性上来说,司法考试的答案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见,对于辅助占有的概念,刑法学者虽然加以承认,但却作了比民法理论更为宽泛的理解,将并不具备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也纳入其中。这种理解实际上缺乏民法理论的支撑,同时也模糊了辅助占有与普通委托保管的界限。因此可以认为,对于辅助占有的成立条件,我国刑法理论通说的理解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基于这种理解所下的结论,会因为不区分具体情况而导致定性错误。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雇员利用职务之便将个体工商户的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应当以侵占罪论处,而不构成盗窃罪。例如张建忠侵占案中,被告人张建忠利用其任某个体加工厂司机的职务之便,趁该厂厂长朱某某安排其独自开车将一批价值87840.2元的不锈钢卷带送往某市某钢制品有限公司之际,将该批货物擅自变卖给他人,并弃车携变卖所得款40000元逃匿,后被抓获。⑤详细案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4年第5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对于该案,如果根据修正的从属判断说,当张建忠受指派将不锈钢卷带送往同城的指定地点时,作为辅助占有人,他对于该批货物不存在占有,如此一来,擅自变卖的行为势必会破坏雇主的占有,因而构成盗窃。但是判决理由认为,被告人张建忠并非通过秘密窃取的方式将他人占有下的财物占为所有,其行为的实质是将自己临时代为保管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拒不退还。实践中,能够就他人财物形成刑法意义上的代为保管关系的情形很多,而不仅限于根据正式的保管合同所产生的代为保管关系。本案被告人张建忠作为个体工商户朱某某所雇用的司机,受委托负责将户主所有的货物运交他人,这种雇用委托关系,使双方就所交运的货物已经形成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代为保管关系。①同前注㉟,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书,第39页。很显然,该案的判决理由肯定了民法中的辅助占有人在刑法意义上可以单独占有雇主所委托运输的财物,实际上也否定了根据辅助占有理论解决该案的主张。
就该案而言,判决的说理还是较为粗疏的,并未提及理论界所倡导的修正的从属判断说。根据笔者所主张的观点,尽管个体工商户朱某某与张建忠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是当朱某某安排张建忠独自一人开车将不锈钢卷带送往他处时,汽车及不锈钢卷带已经由朱某某的个人支配领域转移至公共支配领域,因此对于这些财物,朱某某已经丧失了刑法意义上的占有,而转由张建忠单独占有。在这种状态下,张建忠将该批货物擅自变卖给他人的行为并不存在破坏他人占有的情况,因此就缺乏成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不破坏占有状态的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法院以侵占罪定性的判决结论是正确的。那种根据是否指定运输路线以及运送路线长短来判断占有归属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上位者的支配领域做了不适当的延伸,而且,对于究竟多远的距离才算足够长,以致于财物转由下位者占有,也难以给出确切的数字,最终只能流于模糊的感觉,因而并不可取。
四、小结
从上述分析可见,基于对社会公众观念的考量,我们需要承认刑法中占有的观念化,但是并不能因此彻底否认刑法中的占有对于事实支配力的重视。具体到辅助占有现象而言,既然辅助占有人在客观上践行着对于财物的支配,主观上也意图这么做,就没有理由否认其对于财物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在此基础上,应当根据行为时财物所处的支配领域,来判断这种占有属于单独占有还是共同占有,从而最终确定是构成侵占还是盗窃。
虽然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借助处分权限这一要素,部分地承认了辅助占有人对财物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但是,处分权限并不属于占有的构成要素,因而将其作为判断占有有无标准的做法,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此外,对于支配领域这一判断占有的核心要素,这种做法也缺乏一以贯之的重视。这反映出理论界对于刑民交叉问题的研究仍流于表面,往往生搬硬套民法中的概念直接得出结论,存在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建立有效的刑法学者与民法学者的对话机制,对于刑法问题尤其是刑民交叉问题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25
A
1005-9512(2014)05-0037-11
马寅翔,华东政法大学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财产罪中规范性的占有概念及其展开”(项目编号:2014M 5513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