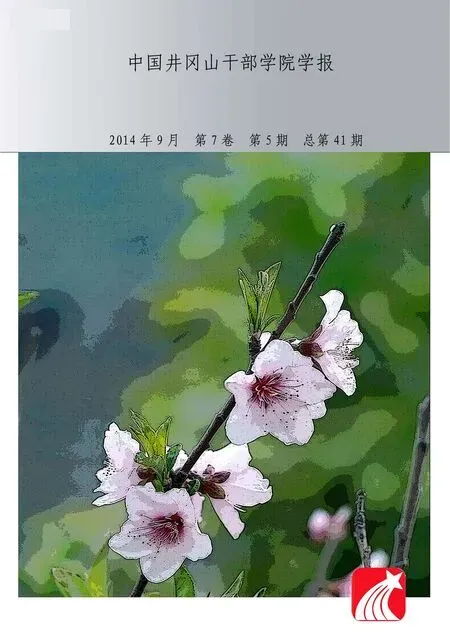对有关秋收起义几个争议问题的管见
□涂开荣
(九江市委史志办,江西 九江 332000)
秋收起义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创建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举起了第一面军旗,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三个第一”彪炳史册;秋收起义开启了湘鄂赣苏区创建的历史,是湘鄂赣苏区的前奏。特别是起义过程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所以,加大对秋收起义的研究和宣传非常必要。但史学界对秋收起义研究见仁见智,很多历史史实有待厘清。笔者对秋收起义若干史实进行了考证,以就教于秋收起义研究专家。
一、关于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的使命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所肩负的真正使命是什么?笔者认为:
一是领导湘南暴动。这是中央赋予毛泽东的重要使命。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彭公达被派回到湖南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和领导湖南全省秋收暴动。“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1]P96回到长沙后,中共中央多次来信指示:“(湖南)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1]P53“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1]P54中共中央指示湘南是湖南秋收暴动的重点地区之一,所以,中共中央多次要毛泽东到湘南,任命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领导湘南秋收暴动。无论是“八七”会议前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还是“八七”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1927年8月8日)》和《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都指示毛泽东任湘南特委书记,比如,《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1927年8月8日)》指出:“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1]P46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是派毛泽东往湘南,并非有的史书上所说的往湘赣边。尽管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湖南省委不赞同中央的这一决定,毛泽东也没有到任湘南特委书记一职,但中共中央赋予了他这一使命却是事实。
二是领导湘中暴动。这是湖南省委赋予毛泽东的新使命。湖南省委根据湖南的实际,改变了中共中央要求湖南全省暴动的决定,决定举行湘中七县暴动,“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1]P101于是,湖南省委改变了中共中央赋予毛泽东任湘南特委书记使命,又赋予毛泽东以新的使命,“当在决定湘中暴动的区域的时候是八月三十日,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挥湖[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1]P101毛泽东去安源,何资琛去岳州,毛泽东负责湘中七县暴动军事工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毛泽东去安源应视同在湖南开展活动。安源路矿工人多系湖南人,且安源到湖南有株萍铁路,交通便捷,安源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即于1922年由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帮助建立,当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毛泽东,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书记是李立三。此后,安源党组织一直归属湖南省委管辖,毛泽东很多次亲临安源进行指导,所以安源成为湘中七县暴动地域之一已是情理之中。2.“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当师长”,并不代表是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并不能说明湖南省委有意图把毛泽东派往江西的修水、铜鼓去。湖南省委此时对平浏农军仍然是知之甚少,并没有确切地知道平浏农军就在修铜。从历史文件中可知,起义在即的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给有关各县发布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紧急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长沙各区委、安源行委、岳阳行委、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宁乡、衡阳各县委,株洲部委,各县县委、各特支及各同志——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一九二七年.九.八晚”。[1]P64-65
安源是湘中七县之一的暴动地区,毛泽东对安源情况很熟悉,安源具有暴动的工运基础。9月初,毛泽东奉命来到湘中七县之一的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会上,潘心源详细汇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平浏农军驻扎修水和铜鼓的情况,毛泽东得知修水和铜鼓有我党所掌握的武装,非常兴奋,“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1]P77,亲赴铜鼓县领导秋收起义,联合警卫团等驻修水铜鼓的部队共襄盛举。这样,毛泽东就从湖南省委赋予的湘中七县暴动的军事负责人,转变为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实际负责人。
由此可知,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的使命首先是湘南暴动的主要领导,负责领导湘南秋收暴动;后湖南省委取消了全省暴动的初衷,决定举行湘中七县暴动,毛泽东又成为湘中七县暴动领导人。但当毛泽东亲临起义第一线后,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又进行了临机改变,将湘中七县暴动扩大为湘赣边秋收暴动。如前所分析,毛泽东的这一临机改变,并未得到湖南省委的认可,或者湖南省委并不知情。毛泽东之使命与其行动相异,说明毛泽东能够实事求是,不拘泥于上级的指示。这也就解释了此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中共中央的指示,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引兵井冈,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城市中心论”转而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是适应当时革命的实际情况应运而生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领导人。
二、关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地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昌起义时部队番号仍是沿用国民党左派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一开始,“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2]P7,这些名称贴切地体现了共产党的特点,表明了共产党公开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那么这第一支体现我党军队特色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到底在什么地方组建的,笔者认为:
(一)安源会议并未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之《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记载“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任总指挥……”[1]P121很多党史著作都持安源编师的观点。
历史留给我们关于安源会议的史料很少,《潘心源报告》是其中最重要的文件,让我们重温潘心源对安源会议的介绍:“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1]P121分析此一段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安源会议编师没有历史依据。《潘心源报告》中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介绍,只有将起义部队分为几路的说明。若此时毛泽东已将各路秋收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亲历者潘心源应该会在其《报告》中将部队番号写出来,而不只是写“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二是安源会议无法编师。《潘心源报告》介绍,毛泽东等“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但最了解情况的潘心源对平江工农义勇队已一分为二,编制不复存在竟然也一无所知。这一点从安源会议的军事部署可知。所以此时编师则是无从下手。三是安源会议不可能编师。从安源会议的参加对象看,既然是军事会议,却并没有师部和一、三团的主要领导参加。再者,如前所述,不同于余洒度在修水,毛泽东在安源是来去匆匆,时间很短,情况不熟悉,也没有酝酿过程,只凭潘心源单方面介绍就将这几支部队进行整编,不合情理。
故笔者认为,安源会议编师说是在没有确切史料证实的情况下,后来的研究者凭推测而出的,安源会议并没有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二)铜鼓没有建军编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写到:“接着,毛泽东又赶到铜鼓,召集位于修水、铜鼓各部负责人或代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任命余洒度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该部编为2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第3团”[3]P22。
这一表述是缺乏依据的。我们首先考证一下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时间,《苏先俊报告》明确说明:“10日毛泽东来到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1]P77即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时间是9月10日。此时召集驻修水的卢德铭、余洒度等开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的余洒度等“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1]P113第一师师部及所属一团已于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的前一天离开了修水县城,举行了起义,10日卢德铭、余洒度正率领一师及一团在渣津进攻平江的路上,无法来铜鼓参加会议。遍找秋收起义的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也没有毛泽东在铜鼓“召集位于修水、铜鼓各部负责人或代表开会……”之说。同时,此时编师,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已于9月9日在镰刀斧头旗帜上展示出来了。事实上,卢德铭、余洒度与毛泽东首次会面只是在秋收起义爆发若干天后的湖南浏阳孙家段,正如铁心在其《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中所描述的“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1]P212而此前却并没有毛泽东与卢德铭、余洒度见面的记录。
(三)修水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地
笔者认为,真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应在修水山口的建军编师大会上。
何长工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参加这次会议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4]P182
陈树华的回忆说得更清楚:“到修水后,我们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把余贲民部从武宁招来,编为特务营(卫队营)。我们知道苏先俊部在铜鼓,因为都是同学,决定让他做第三团团长……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还造具全师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以迷惑他。”[1]P156-157
再仔细研究《余洒度报告》和《苏先俊报告》可知,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无疑问。
《余洒度报告》中说:“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余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每人平均约百发。”[1]P112-113这进一步说明在山口会议上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师委会”,只是因为白色恐怖,只能采取“内红外白”的办法以保存自己,“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
《苏先俊报告》则是山口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更为有力的证据。《苏先俊报告》中称:“第三期,一、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实力:步枪一千三百枝,机关枪二艇(挺),驳壳枪二十枝。三、作战经过:……十一日修水第一团及新编第四团向平江进发,第三团向浏阳前进,安源、醴陵部队向老关进攻。”[1]P77苏先俊所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实力,与《余洒度报告》中所述枪枝数量惊人吻合,正好是修水和铜鼓部队的实力,不包含安源的部队。《苏先俊报告》中还有一个细节,修水和铜鼓的部队分别称为“第一团”、“第四团”、“第三团”,而“安源、醴陵的部队”并未有番号。这是苏先俊的漏记,还是此时安源的部队尚未纳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体系中,尚未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进一步说明,修水与铜鼓的部队已自成体系,安源部队编入前,就已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退一步说,假设山口会议只是组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是掩人耳目的编师,只是打出灰色旗号,反而是不合常理的:如果是组建一个“灰色”的省防军,则可大张旗鼓地进行,没有必要躲到偏远的山口老街去举行;只是造造册子,形式上的编师,也没有必要将平江工农义勇队一分为二,更没有必要把伍中豪、何坚等派到铜鼓去;只是组建省防军,没有必要将组建省防军这件事郑重其事地“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正因为这是组建我党自己的军队,是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所以才躲到偏远的山口去进行,并将编师结果郑重地向党汇报。所以山口会议不只是组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真正的目的是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那么,如此重大的事件,是谁领导实施的。笔者认为这一重大事件却与湖南省委无关,湖南省委对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南昌暴动后的去向不甚了解,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筹划湘中七县暴动,直到暴动在即,毛泽东才与师部接上关系。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在这里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湖北省委的作用不容低估。由于修水离鄂中不远,与鄂南三县通城、崇阳、通山山水相连,且素有往来,便于联络。特别是警卫团刚从湖北武汉开来,进驻修水,且卢德铭和韩浚等人过去同湖北省委与向警予同志熟悉,易于沟通关系。
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和有关资料,为我们证实了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在建军编师中所发挥的作用。
《江西省委给寿昌信》中说:“六、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专人前往指导……”[4]P17-18
《关于江西准备秋暴情形致金山》信中说:“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时曾派人来此接洽,此间亦召人前去报告现在军政情况,并提议以后进行以及一切联络事宜,派去之人尚未回来。”[4]P23
《余洒度报告》中说:“不久得通城刘××(注:即刘基宋)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1]P113
易礼容给苏先俊信中说:“……闻洒度已向中央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4]P251
刘基宋在其《加入共产党与脱节后工作经过》中写道:“我们既无法与大军会集,乃共商将全部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师,推余洒度为师长,我为参谋长,暂驻现地。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其主旨为中共决定在武汉来一个暴动,令我们作外应。”[5]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秋收暴动,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通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江西省委的渠道传达到驻修水、铜鼓的部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促使他们在山口召开了建军编师大会,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三、关于第一面军旗及诞生经过
我党第一面军旗的诞生,是党史和军史上均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笔者认为:
(一)“红布”说完全错误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军旗”条目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初创时以红旗为标志,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样式统一为长方形,红底上缀金黄色的镰刀、锤子和五角星。”[6]P552按照这一说法,我军1931年才有了带图案的军旗,1931年以前只是一块红布,自然也就否定了秋收起义打出过镰刀、斧头图案军旗的说法。同样,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著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只字未提秋收起义诞生了第一面军旗。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对秋收起义诞生第一面军旗的否定。这一观点是不尊重史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许多在修水参加秋收起义的亲历者,明确提到在修水设计制作和打出了第一面军旗。
陈士榘回忆:“秋收暴动前,发给每人一条红布,系在脖子上,作为起义的标志。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改为镰刀斧头红旗。”[4]P174
赖毅回忆:“师部还根据上级指示,设计制作了军旗,师、团、营、连都有,只是大小有别。中间是一个黄五角星,五角星上是黑色镰刀斧头,旗杆旁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营×连’字样。每面旗子还有一个油布套子。”[4]P187
张宗逊等其他亲历者也有类似的回忆,不一一列出。
其次,军事博物馆陈列的军旗复制品就是权威的说明。军事博物馆展出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这是一面带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据2007年赴修水参加秋收起义80周年研讨会专家樊昊介绍,他请教过军博有关专家,军博专家回答说:这面军旗是复制品,但不是随意复制的,这是建馆时根据许多老将军的回忆制作,并经过他们认可,又经过老帅和军委领导审查批准的。军博1959年7月落成,当年10月1日开始预展。周恩来、朱德、陈毅、罗荣桓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同志多次前来审查。建馆近半个世纪,期间经过多次审查和修改,这面军旗一直展出,一直列入军博的馆藏文物清单保存着、展览着。军事博物馆,是国家级博物馆,是搜集、鉴定、研究、展览军事革命文物的权威机关,他们对秋收起义打出这面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所持的肯定态度,就是有力的证明。
再次,毛泽东诗词是重要的原始依据。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期间留下了史诗般诗作《西江月.秋收暴动》,毛泽东看到起义之初的喜人局面,挥毫写下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这是秋收起义时诞生了第一面军旗的最有价值的原始史料,是不容置疑的证据。由于秋收起义打出了镰刀斧头旗,所以一年后的平江起义就依照秋收起义也打出了镰刀斧头旗。如李光的《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诞生——彭德怀同志组织红军第五军的经过》介绍:“参加武装起义的部队……撕毁了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旗子和帽徽,换上了斧头镰刀的大红旗和五角星帽徽。”[7]P34平江起义打的是镰刀斧头军旗,但亲历者和史学界并没有将平江起义制作的镰刀斧头军旗说成是第一面军旗。
综上所述,“红布”说是站不住脚的,在修水诞生了第一面军旗是没有疑问的。
(二)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不准确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编著的《毛泽东传》一书中写道:“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8]P这段文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与此类似的观点很多,理由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1]P50所以,很多研究者依此认为是毛泽东指示制作了我党第一面军旗。
从目前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原始资料《潘心源报告》来看,安源会议除部署了起义路线外,既没有编师的记载,更没有决定制作军旗的介绍。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报告或回忆文章也均未见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驻修水的警卫团9月8日收到了驻铜鼓的三团团长苏先俊转来的毛泽东关于举行起义的信件,苏先俊在信中强调“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1]P113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与警卫团联系的最早信件,尽管其详细内容已无从得知,但从《余洒度报告》中可知,这封信中主要是部署了起义和起义的路线,并未发现有制作军旗的指示。即使这封9月8日收到的信件中,有制作军旗的指示,起义在即,设计制作的时间也是不允许的!
假使毛泽东策划起义之时就有制作军旗的决定,在起义准备非常紧迫和交通通讯条件极不便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也不至于将制作军旗的决定送至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的江西修水来实施,只能就地安排在长沙或者当时党组织属湖南管辖的安源等地制作。何况,毛泽东上文中所论述的“旗子”问题,并非旗帜实物,而是象征意义的旗帜,是指政党的主张、路线及其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意即国民党的主张和形象已不得人心,共产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树立自己的形象。
总之,迄今为止没有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可以佐证,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提出过制作起义的实物旗帜。所以笔者认为由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证据是不准确的。
(三)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示制作军旗证据不充分
何长工回忆:“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4]P181
如前所述,警卫团直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开来,必然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和湖北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留下的原始材料也充分地印证了这些联系。《余洒度报告》记录了中共中央对警卫团的指示:“……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1]P113但是,中共中央由于考虑到我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时一直有借助国民党左派名义的考虑,希望借助左派的力量汇聚军队和民心,以有利于起义的顺利进行。所以,中共中央在8月23日回复湖南省委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1]P55-56李立三在总结“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时,就对南昌起义前后借助国民党这块招牌进行了反思:“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9]P338所以,秋收起义前夕的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与国民党决裂的打算,没有完全抛弃国民党旗帜的决心。既然国民党的招牌不愿丢,象征意义的旗帜也还举着,自然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也不会有打镰刀斧头军旗的想法。
所以,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指令制作军旗也不可信。
(四)第一面军旗的设计制作是由师委会决定且在修水完成的
警卫团在修水的一个月,秣马厉兵,积极作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和“七、……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1]P62后,警卫团即于九月初邀集平浏农军召开了山口会议,组建了秋收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策略地“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并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内部负责为师委会”。此时,因部队名称变了,“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警卫团群贤毕至,从武汉“七·一五”政变中走出来的这批年轻共产党人,经过一个多月所见、所思、所感,同样会对国民党旗帜有一个理性思考,也会有反对再打国民党旗号的主张,会毅然抛去国民党无形的和有形的旗帜。
亲历者陈树华的回忆正好印证了笔者这一推理:“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拼右拼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1]P157陈树华的多次回忆口径都是一致的,特别是陈树华分别于1988年10月22日、1988年11月3日和1989年1月31日三次就军旗等问题以书信形式给铜鼓县党史办进行了回复,详细回忆了军旗制作经过,并就军旗如何从修水带到铜鼓进行了回忆,其中在第二封回信中提到“二、军旗图案件八月初旬(应为农历。笔者注)一个下午决定后,我即当夜设计绘制,翌日即交街上裁缝制作,并没有中央的统一布置。这个图案,当然是由何坚、伍中豪带到铜鼓去了。是成为一致的原因。”[10]当时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由于属师领导,其回忆应是比较准确的。铁心的文章也佐证了我们的推测,“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1]P209
综上所述,第一面军旗是在中共中央命令军队名称改为”工农革命军”背景下,由师委会指示杨立三、何长工、陈树华在修水设计制作完成的。秋收起义在修水诞生第一面军旗是肯定的。
四、关于秋收起义的首发时间
秋收起义最早于什么时间爆发的?在什么地方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党史界本有定论,即9月9日于修水首先爆发了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综述中介绍:“9月9日,师部在修水宣布起义以后,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向平江长寿街进军,先师部一天到达渣津,镇压了从修水带来的八个大恶霸。”[1]P11
但近年来,随着秋收起义研究的“深入”,党史界特别是军史界提出了不少质疑的观点,很多新编的党史、军史资料否定了9月9日于修水首先爆发秋收起义这一史实,较多地提出了9月11日各地同时爆发起义说。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9月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3]P23《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也如是说“9月11日,在毛泽东、卢德铭、潘心源领导下,举行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1]P16
之所以这么多军史专家提出11日齐起发动说,其理由是:秋收起义前夕,《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强调:“……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1]P65既然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中共湖南省委命令各地“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自然秋收起义就应该是9月11日爆发,不会提前到9月9日起义。甚至有专家认为,尽管“9月9日说”有亲历者的详细回忆,那只能认定是亲历者回忆有误,是事隔多年后的误记。
对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正是上面这一则历史材料,给我们解释了修水9月9日首先暴动的原因。这份文件发送对象主要是湘中七县,修铜未收到文件。湖南省委尽管要求11日齐起发动,但并不影响修水9日发动,修水并非湘中七县之一,文件并未发至修水。特别是同前所述,由于修水与鄂南山水相依,驻修水的警卫团又是由湖北辗转到达修水的,所以驻修水的秋收起义部队更多受到湖北省委的影响,通过湖北省委“并得军部通告”,听取中共中央的指示。同时,警卫团主动与湖北党组织发生联系,将在修水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向鄂报告一切”,听取鄂传达中央的指示;鄂南的一部分军队崇通农民自卫军也在罗荣桓率领下来到了修水,加入了驻修水的警卫团,自然也会带来“鄂南决于九日发动”的消息。所以既然“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修水师部,在知道鄂南这一举动决定后,修水也会统一行动。适值毛泽东又从安源发出了指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起义自然早于安源、铜鼓爆发了。
许多原始材料和回忆文章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多次提到了9月9日爆发了秋收起义,修水率先举行起义。
《余洒度的报告》中记载:“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1]P113
何长工回忆:“九月九日,部队从修水出发。当时,准备打长沙,是在平江龙门过的中秋节。”[4]P183
陈士榘回忆:“九月九日,第一团向湖南开进,去攻打平江。”[4]P174
陈树华等亲历者也有类似的回忆,不一一列出。
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并镇压了“二打曹家”时捕获的几个恶霸,继而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由于受到邱国轩部偷袭,金坪失利,起义宣告失败,最后被迫改变作战计划,转兵文家市。
故9月9日在修水首先爆发了起义是不容否定的,确定9月9日作为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是符合史实的。
五、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谁领导了秋收起义,过去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事实上这是不全面的。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但不是唯一领导人,彭公达、易礼容、卢德铭等同样是重要领导人,为秋收起义的爆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
湘赣边秋收起义中,湖南省委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1]P107-108事实上,彭公达作了很多工作。“八七”会议后,他立即回到了湖南,主持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改组了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积极部署湖南秋收起义。此后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秋收暴动工作,特别是在8月30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组建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并将省委领导分别派驻各县指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就是此时被派往安源的。准备就绪后,又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此后,主持召开了9月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积极策应起义部队会攻长沙。9月8日,以湖南省委书记的名义发布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组编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P65彭公达在秋收起义中所作出的贡献应该铭记。
(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上组成了两个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一个是以易礼容为书记的由地方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过去在秋收起义研究和宣传中,只突出前敌委员会的作用,而忽视行动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这是有失公允的。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1]P142故行动委员会的作用不可小视,易礼容自然就是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此外,湖南省委在研究秋收暴动的有关工作时,作为省委常委的易礼容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比如讨论湖南省秋收暴动的区域,当毛泽东主张缩小暴动范围时,“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1]P101所以易礼容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也不容否定。
(三)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率领警卫团从武汉出发,巧妙躲过了张发奎的缴械,辗转到达奉新,再指示余洒度将部队带到“三不管”的修水。卢德铭在部队去向上的这一系列英明决策,为保存我党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支部队后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同时,卢德铭与韩浚、辛涣文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新的指示,在听取了向警予的指示后,“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P181起义即将爆发,卢德铭及时赶回修水掌握部队,就任总指挥。在金坪失利后,卢德铭非常理智地否决了余洒度的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向毛泽东靠拢,实行了第一次战略退却,顺利与第三团进行了会师。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全力支持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转兵南下的计划,又一次为保存我党这支重要军事力量,开辟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卢德铭在萍乡市芦溪县山口岩英勇牺牲,毛泽东为失去这一臂膀悲愤不已,喊出了“还我卢德铭”。卢德铭在秋收起义中的贡献彪炳史册。
[1]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2]田园东,廖国良.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4]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秋收起义在江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5]刘基宋.加入共产党与脱节后工作经过[R].1951年,原件存湖南省桂阳县公安局.
[6]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军事》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7]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0]陈树华.给铜鼓县党史办的回信[R].1988年11月3日,原件存铜鼓县党史办.
[11]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