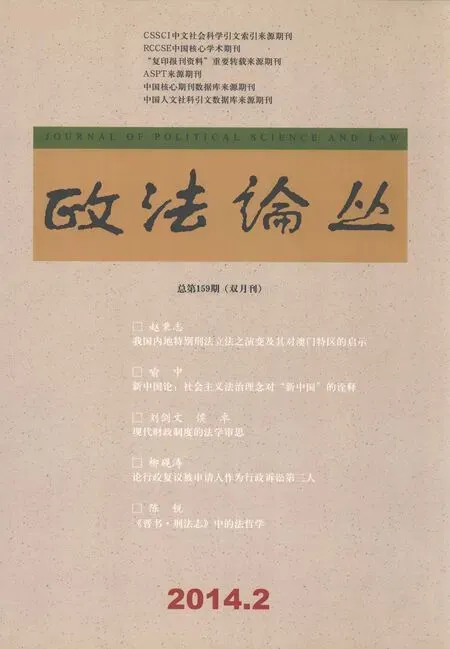《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
陈 锐
(西南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70)
无论是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还是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晋书·刑法志》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但有关《晋书·刑法志》的专门研究却非常少;并且,在如此稀少的研究成果中,人们的注意力又大多集中在张斐的“注律表”上,而忽视了对《晋书·刑法志》所包含的法哲学做全面阐发。虽说张斐的“注律表”是《晋书·刑法志》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至多只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非唯一内容,并且,与贯穿《晋书·刑法志》始终的法哲学相比,其重要性应当略低,因此,研究《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一种转折性、混合型法哲学
在探讨《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之前,有必要弄清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一是《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二是晋代的法哲学,这两者有一定区别。《晋书·刑法志》收录了不少晋代官员的上书或奏章,特别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张斐的“注律表”,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见晋代法哲学之一斑。此外,由于《晋书·刑法志》是唐代官方负责编修的,是为了从法律角度总结前代兴衰的历史教训,故在选裁汉以来的法律史料时带有明显倾向性,反映了唐代官方对待法律的态度,因此,毋宁说,这类法哲学是唐代官方推崇的法哲学。由于这两个层次的法哲学完美地叠加在一起,以至我们难以精确地区分它们,故我们只好笼统地称之为《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
《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有何特色呢?笔者认为,《晋书·刑法志》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混合型法哲学,其显性的一面是儒家法哲学,隐性的一面是法家、道家等学派的法哲学,并且,这一时期的法哲学又带有转折性特点,即由法家为主导的法哲学转向以儒家为主导的法哲学。
按照瞿同祖先生的说法,我国“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1]P357亦即秦汉时期,法家法哲学在法律中居主导性地位。但自汉武帝时起,董仲舒及其弟子运用“春秋大义”决狱,法律开始儒家化,与之相一致,儒家法哲学也随之走向前台,开始逐步替代法家法哲学。这一转变过程是通过儒家学者大规模参与修律活动而实现的。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魏律的主要制定者陈群、刘劭之辈皆为儒家学者,多习儒家经典,因此,“魏律出自此辈儒者手中,自难怪其儒家化程度之深”。[1]P360晋律的制定者除贾充外全都为当时有名的儒者,特别是郑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2]P646杜预“耽思经籍……备成一家之学”,[3]P673由他们担纲起草《晋律》,儒家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是完全可以料想的。陈寅恪先生有感于此,特别说到:“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4]P73
《晋书·刑法志》还记载了一些具体的儒家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情形,使我们大致可以领略从曹魏到晋代儒家法哲学是如何进入法律之中、并在内容上逐渐取代法家思想的。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曹魏定律时即依据儒家经义对以李悝、商鞅为宗的、带有法家精神的汉律进行了修改:“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驱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5]P602晋律在汉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新规定,如“重奸伯叔母之令”,[5]P603“子孙违背教令,敬恭有亏,父母告子不孝,欲杀者皆许之”。[5]P603除了上述具体内容以外,晋律还确立了“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5]P603的立法原则,将“八议”制度明确引入晋律之中,使儒家思想在精神层面上主宰着晋律,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晋律儒家化的程度。据英国汉学学者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考证,在晋律中,带有儒家化倾向的法律规定已经非常普遍,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有关财产继承、婚姻、犯罪的处罚等诸多法律规定之中。[6]
以上论述说明了自汉代以来(特别是晋代)我国古代法律哲学发生的重大变化与转折,揭示了《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具有“转折性”特点。
虽说儒家法哲学在晋代已居主导性地位,但并不表明,法家法哲学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晋代,法家思想仍有很大影响。在《晋书·刑法志》中,法家法哲学仍时时露出头来,成为一种略能与儒家法哲学分庭抗礼的思想,尤其是在《晋书·刑法志》的后半部分,某些晋代官员的奏议就带有明显的法家特点。如晋代一些官员动辄引用儒家信条作为反对恢复肉刑的理由,刘颂对这些信条做了法家式的引申,即“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5]P609并且,刘颂认为,一些带有儒家特色的观点“听言则美,论言则违”,[5]P609因为天下太大、事情太复杂,因此,人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故他建议说:“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5]P609“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5]P610刘颂的这些主张已迹近于商、韩。《商君书》中有类似的话语:“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者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序,使数日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7]P210《管子》亦有“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8]P2之语。《晋书·刑法志》还有“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5]P610“不能以私意而害法”、[5]P610“不能为尽善而伤法”[5]P610之类的说法,这些说法也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杨鸿烈先生将刘颂等人的思想归入了法家范畴:“晋代法家辈出,而最值得称道的即是刘颂、葛洪等人。”[9]P152
除法家思想以外,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想在《晋书·刑法志》中也隐约可见,其主要出现在张斐的“注律表”中。如在讨论“理”、“情”、“法”三者的辩证关系时,张斐借用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想对之进行了抽象化的解释:“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5]P605张斐还将“理”、“律”关系比拟为“道”、“器”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5]P605在界定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时,张斐用到了玄学家们惯用的“辨名析理”方法,使得法律概念变得明确起来,刘笃才先生对张斐引入玄学方法研究法律、带来方法论上的创新评价很高:“张斐引易说律……把律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使律学摆脱了汉代经学方法的束缚,并借助易学研究中的方法更新,开出了律学研究的新生面。”[10]P112
综上所述,《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是一种带有转折性、混合型特点的法哲学,其中,儒家法哲学为主导,法家、道家等法哲学思想居于辅助性地位。这种转折性、混合型特点表现在《晋书·刑法志》中的每一个侧面。
二、礼、刑、经为表,理、情、时为里:辩证统一的本体论立场
一般地,人们往往认为,哲学是由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重要部分组成,其中,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探讨《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必须从本体论(张岱年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与“本体”相对应的概念是“本根”这样一个概念[11]P167)开始。
(一)法律是什么?
一般地,人们习惯于将“是什么”的问题看成是本体论问题。对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晋书·刑法志》做了大量论述。这一问题又可分解为几个相互联系的小问题:(1)法律的起源是什么?(2)法律的功用是什么?(3)法律的形式有哪些?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论域都局限于“实然”范围,都是为了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的。
法律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法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同法系、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人们对此问题有着迥异的解释,因之形成了不同的法哲学。《晋书·刑法志》给出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政失礼微,狱成刑起”,[5]P595“祖述生成,宪章尧舜”,[5]P595“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奸宄弘多,乱离斯永,则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者也’”。[5]P595
上述论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法律是一种人造物,而非上帝或者其他诸神为人制定的。第二,法律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即为了适应“治乱”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三,法律的作者是古代的圣人们,他们通过观察自然、社会,发现了某些自然(或社会)规律,并结合人情、人性而制定了法律。以上解释突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特色,即不以神道设教,没有将法律的起源与宗教必然地联系起来。梅因在研究古代法时,即发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这一特点,[12]P23当代学者D·布迪与C·莫里斯也持大致类似的观点:“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起源于神的旨意。”[13]P7
与法律的起源问题紧密联系的是法律功用问题。由于对法律的起源问题做了一种世俗化解释,特别突出了法律的“对症下药”功效:“除残去乱”,[5]P596“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5]P606“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乃去其为恶之具……止奸绝本,理之尽也”。[5]P607
在《晋书·刑法志》看来,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保障社会秩序、惩罚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因此,晋代的法律是以刑事法律规范为主体、以义务为本位的,少了一些超越性目的。这与西方古代的法哲学相比,少了一分浪漫主义精神,多了几分实用主义色彩,这也使得中国古代法哲学带有朴素的实用主义特征。从《晋书·刑法志》关于法律功用的论述之中,我们还可以读出其中既有儒家的味道,如“礼以崇善,法以闲非”之类的说法几近于儒家的观点;又有法家的意蕴,如“去奸之本”、“以刑去刑”之类的说法在《商君书》中就很常见。
与以上两点紧密相关,《晋书·刑法志》论及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刑”,除此以外,“礼”是另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晋书·刑法志》花了大量篇幅论述礼与刑的关系。除了“礼”与“刑”以外,《晋书·刑法志》还多次提到法律“应合经义”。在晋代,“儒家经义”不只是充当法律正当性的根据,甚至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用瞿同祖先生的话说,“当时承认经传的法律效力与律令相等”,[1]P351这与晋代的法律儒家化程度已经很深有很大关系。
以上所论大致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它们属《晋书·刑法志》展现的法律本体论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由于“本体论”最原初的含义是探究事物背后根据的学问,因此,我们还将探讨《晋书·刑法志》所传达的中国传统法哲学对实在法背后根据的思索。
(二)法律应当怎样?
实在法背后的根据是什么?这是法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照中国传统法哲学,人们通常认为,实在法背后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情”与“理”,因此,人们经常将“情理法”并称,并认为,法只有上合乎“理”、下顺乎“情”才能取得“法律”资格。《晋书·刑法志》赞成这种观点。
在《晋书·刑法志》中,论及“理”的地方很多,从“理”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情况看,它无非有以下两种类型:(1)自然之“理”,亦即自然规律之意;如“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5]P595(2)社会之“理”,亦即社会规律之意,它包括“为人的道理”、“为政的道理”。《晋书·刑法志》在字里行间向我们灌输着儒家“为人的道理”,即人与人之间有尊卑贵贱、远近亲疏之别,因此,要叙尊卑,别亲疏,正名分;人人都爱其亲,故而应当允许“亲亲相与为隐”;人在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因之都畏惧刑罚,等等。《晋书·刑法志》还介绍了大量“为政的道理”:“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5]P605“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5]P604等等。在《晋书·刑法志》的作者看来,这些道理都是客观的,是不能违背的。
由于“理”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并且,“理”这一范畴本身又蕴涵有“客观”、“至当”之意,因此,法(或律、刑)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否则,其有效性与正当性就值得怀疑。《晋书·刑法志》就是如此强调“理”“法”关系的:“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5]P604“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止奸绝本,理之尽也”,[5]P607“夫法者,故以尽理为法”。[5]P607亦即“律”要合乎“理”,“法”是“尽理”的结果。因此,“理”是中国传统法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法律的内在根据之一。
按照中国传统法哲学的说法,“法”还必须合乎“情”,“情”是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另一个核心范畴。在《晋书·刑法志》中,“情”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比“理”要多,这一方面突出了“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揭示了“情”的复杂性。综观整个《晋书·刑法志》,不同的论者都经常诉诸“情”这一概念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但在“情”之具体所指上又往往不同。具体说来,“情”大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1)人之常情;既包括一般人都具有的正常道德情感(马伯良曾说到,“我在别处直接将‘情’译为‘人道道德情感’”[14]P226-258),又包括人们日常养成的习惯。(2)物之情形,即“情实”;《晋书·刑法志》有言:“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5]P605(3)偏私之情,即“私情”;这也是《晋书·刑法志》批判得最多的“情”之情形。
在“情”与“法”的关系上,《晋书·刑法志》表达了下述立场:其一,承认“情”与“法”之间有一定联系,但认为那主要在立法阶段,即立法时要考虑各种情实,要结合“人情”因素。刘颂说到:“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5]P609“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5]P609其二,反对在司法阶段仍“缘情定罪”,主张法吏应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定罪量刑。对于司法阶段“缘情定罪”的坏处,以刘颂、裴頠为代表的晋代官员进行了多方论证:第一,如果“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5]P609如果“上安于曲当,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顺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深浅,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5]P609第二,“情”会因人不同而不同,因时不同而有别,无法保证司法的一致性与公正性。正如裴頠所言:“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即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5]P608第三,“缘情定罪”从长远看弊大于利。刘颂断言:“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5]P610正是由于认识到“缘情定罪”的坏处,刘颂、裴頠等提出了掷地有声的主张:“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5]P610“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5]P610这些主张非常有见地,是对长期困扰人们的“情”“法”之争做一个系统总结,惜乎没有引起后来者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晋书·刑法志》肯定那些无偏私的、客观的人类情感在法律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极力否定“私情”,反对以“私情”扰法、坏法。
论及实在法背后的根据,除了上述“情”与“理”两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范畴,那就是“时”,即好的法律除了“上合天理,下顺人情”以外,还应“合乎时宜”。《晋书·刑法志》对此范畴做了比较完善而全面的论述。《晋书·刑法志》从三个侧面阐述“法”与“时”的关系。首先是从一般角度来说的,即法律的具体内容以及轻重缓急要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晋书·刑法志》非常推崇“周人以三典刑邦国”,多次运用这一理念为自己的理论佐证。其次是从立法的角度说的,强调立法应合乎时宜。如《晋书·刑法志》有“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5]P613“刑法轻重,随时而做”,[5]P613“事有时宜”之类的说法。再次是从司法角度说的。《晋书·刑法志》不赞成法吏们“因时断罪”,因为如此会导致法令不一,罪同罚异,最终会伤害法律的权威,故曰:“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证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5]P610但《晋书·刑法志》并不反对君主按照时宜而权断,即“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5]P610《晋书·刑法志》有关“时”的论述非常新颖,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代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之,《晋书·刑法志》在探讨实在法背后的根据时,注意到了“理”、“情”、“时”这三个重要的法哲学范畴,强调法律应上合天理,下顺人情,中随时宜,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理”是稳定不变的,“时”则相反,变动不居;“情”处于两者之间,其中既有恒久不变的要素,又有变易不居的要素,并因此而媒介两者。由上观之,中国古代法哲学强调法律的内在根据有三,其中既有变者,又有不变者;既有形而上的“理”,又有形而下的“情”;既有抽象,又有具象;既有超验性因素,又有经验性因素,因此,远比西方的自然法观念更为高明。
通过对“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考察,我们可大致总结出中国传统的法概念,并理解中国传统法律的权威问题。中国传统的法概念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带有整体性特点的概念,除了包括统治者明确发布、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律、令以外,还包括不以法律形式出现、但比法律更为严格的“礼”以及记载于儒家典籍中、作为法律原则存在的儒家经义,三者呈“三位一体”结构。这种整体性的法律权威何在?以《晋书·刑法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律典籍同样提供了一种“复合型权威”,即法律的权威依靠圣人的权威、皇帝的强权以及自然与社会规律的约束性力量(即“理”),同时还需要诉诸人类共有的道德情感乃至习俗的力量(即“情”),这五者结合,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共同保障法律的权威。这种整体性法律观的优点在于:它将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整合为一个整体,更易于约束人的行为;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它导致法律与道德、政治、伦理不分,一方面妨碍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获得发展,另一方面编织了一个细密的社会罗网,将大众网罗其中,个人权利难以伸张。
三、繁简相宜,轻重适当:追求“法律科学化”的认识论趣向
“科学”或“科学化”是中国现代方从西方引入的一个术语,如果用来表述晋代律学家们的追求,肯定会有很多人不赞成,故一些学者只好含蓄地称这种追求为“体系化”的追求。但如果不从特别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科学”这一术语,而将之理解为与“合理”、“体系”相若的术语,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从《晋书·刑法志》记载的情况看,当时的律学家在促使法律变得科学、合理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与努力。
(一)法律科学化的路径之一:删繁就简,使得晋律体系更为科学
如何使得法律体系科学合理、繁简适当,一直是困扰汉晋之时律学家们的难题。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看,汉以后,为了使得法律体系科学、合理,人们曾进行过两次重要的努力:一是曹魏制定《新律》,另一是晋代制定《泰始律》。两者都是在《汉律》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并且,从内容上看,后者肯定借鉴了前者的一些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将魏晋的两次修律看成是法律体系化过程中的连续性事件。
如何使得一部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晋书·刑法志》引用的《魏律序》对此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第一,将《汉律》中排在第六篇的“具律”移至篇首,并更名为《刑名》,使之起着统领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第二,对《汉律》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调整,“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5]P602最终删定为 18篇。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到“九章律”的每一篇章,而且涉及到“科”、“令”这两种汉代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从其趣向看,当时的立法者似乎有以一部法律囊括社会生活所有重要方面、尽量减少“科”、“令”使用之企图。从最终结果看,虽然难称十全十美,但毕竟向法律规定体系化、科学化这一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第三,对于建构科学的刑罚体系,曹魏的立法者们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更依古义制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5]P602亦即曹魏《新律》的制定者们对刑罚的使用进行了规范,使之体系更加科学。
到了晋代,晋文帝令郑冲等十四人在汉律基础上编订《泰始律》。《泰始律》在法律科学化方面取得了更大进步。首先,为消除汉代法律“本注烦杂”、“科网本密”的问题,晋代在立法时即确立了“简明立法”的原则,并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删繁就简的措施,从而使得《泰始律》得以可靠的“消肿”。杜预对此做过专门论述:“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3]P696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人们在制定晋律时还采取了下列具体措施:(一)将军事、田农、酤酒等事项“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从以令……违令有罪则入律”,[5]P603将一些“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5]P603(二)对条文及内容做了大量删减,如“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锢相告之条,除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5]P603从而使得晋律的条文与旧律相比大为精简,只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5]P603,因而博得了“实曰轻平,称为简易”[15]P160的名声。其次,人们在制定晋律时,还吸取了曹魏《新律》的经验,对《九章律》的内容结构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就九章律,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就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5]P603这二十篇内容“相须而成,若一体焉”,最终取得了张斐称赞的“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5]P604的效果。第三,减轻了汉律中一些刑罚较重的罪刑,同时“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将儒家礼教思想整合进了晋律之中。第四,在刑罚的科学化、体系化方面,晋律也取得了比曹魏《新律》更大的进步。张斐在“注律表”中洋洋自得地总结道:“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5]P604
经过魏晋两代的努力,中国古代的法律在体系结构方面日趋合理,基本上达到了“繁简相宜”的地步,这是法律科学化的表现之一。
(二)法律科学化的路径之二:明晰概念,使得法律体系能“纲举目张”
概念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是人们用以表达认识的重要形式。只有到了认识的最高阶段,才能产生概念。在概念产生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前概念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只是认识自己身边的一些个别事物与现象,之后,发现了某两种事物或现象属性上的相似性,于是,通过“类比”方法建构起了两种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形成了有关局部事物的知识;接着,通过举一反三,发现了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更为复杂的联系,将这些联系系统化,就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知识。在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尚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层面,因此,还只能通过“类型化方法”来认识世界,并建构起关于世界的“类型化”知识。随着认识的深入,发现了事物内部更为稳定的性质与关系,人的认识才进入到“概念”阶段。
人们的法律认识同样经历了上述发展过程,即从“类比”到“类型”进而深入到“概念”这一过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也符合这一规律。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由于立法水平低,经常出现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因此,需要借用“比”这种方法来解决法律问题,故而“比”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这表明,当时人们的法律认识水平尚处于较低阶段。随着汉代以来律学家们对法律现象进行日渐深入的探究,人们的法律认识逐渐走向成熟。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借助“类型化方法”建构法律概念体系,并抽象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概念。
由于《泰始律》的文本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其庐山真面目难以尽窥,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类型化方法”在晋律中得以应用的蛛丝马迹。如《晋书·刑法志》在描述《泰始律》的制定过程时说到:“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5]P603这等于说,晋律在明确具体罪名过程中运用到了“类型化方法”。至于如何运用“类型化方法”,《晋书·刑法志》也略有交待。如《盗律》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核心内容,其内容特别庞杂,以至许多差异巨大的行为都被纳入了《盗律》的调整范围之内,这使得法律规定显得不合理。直到曹魏制定《新律》才将一些不合理的内容排除出去,另用新的罪名加以调整。“《盗律》有劫略、恐吓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5]P602晋律做了进一步区分:“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5]P603也就是说,晋律的制定者将那些不属于“盗”这一罪名的内涵从《盗律》中剔除。在张斐的“注律表”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型化方法”在晋律中得以运用的蛛丝马迹。张斐说到:“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5]P604张斐觉得,将这四种情况归入“贼杀伤人”这一类型下比较合适。在论及“以威势取财”的诸多情形该如何归罪时,张斐同样使用了“类型化方法”。这表明,在晋律中,人们已经开始学会运用“类型化方法”来建构法律体系。这是立法水平显著提高的一种标志。
到了晋代,为了使得法律规定变得科学、合理,人们还对一些重要法律概念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探究,总结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法律概念,并对之进行了定义。张斐称这些概念为“较名”: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5]P604
这些“较名”就是带有普遍性、贯穿整个法律之中的概念,而非拘于某一篇。如“故意”、“过失”这对概念几乎与每一个罪名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在具体定罪时,都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并且,每个行为人所受到的惩罚也与此直接相关。这些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有何意义?它们类似于一个巨大网络上的“纲”,众多的具体规定类似于“节点”,邻近的“节点”组成“目”,正是凭依着这些“纲”,人们才能将纷繁复杂的具体罪名串起来,最终做到“纲举目张”。晋律能够实现“以简御繁”的效果全凭于此。因此,抽象法律概念的出现是法律科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王绍棠先生对此予以了很高评价:“张斐对封建刑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下的定义,揭示了这些概念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16]P160
总之,抽象法律概念的出现以及定义是法律认识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法律科学化过程中的一大飞跃。
(三)法律科学化的路径之三:“刑贵得中”,使得刑罚体系科学、合理
《晋书·刑法志》的主要内容之一为“是否应当恢复肉刑”,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这是有关肉刑存废之争,但内里却关乎“刑罚适当性”这一核心问题,进而与“法律科学化”这一问题挂上了钩。
晋代的一些官员对于“刑罚的适当性”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当时刑罚不适当的问题较前代尤甚,以刘颂为代表的一些主管法律的人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第一,由于晋律缺乏有关肉刑的规定,因此,对于那些累犯不得不多次处罚,其结果是“以徒生徒”,“以刑生刑”,这使得犯人永无出头之日,监狱人满为患;后又被迫通过多次赦免的方式减少监狱里犯人的人数,其结果是:使得一些人不畏惧法律,法律形同虚设,以至“刑不制罪,法不胜奸”。第二,在晋律中,仍存在着“事轻责重,有违于常”的情况。如元康五年二月,忽起大风,主管太常寺的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5]P608这反过来折射出晋律规定的罪刑不相适应。第三,在晋代,还大量存在着刑事处罚非常随意的情况。如裴頠指出,元康八年,周龙的奴才受人教唆,诬陷周龙曾焚烧皇家陵园中的草木,结果廷尉很草率地将其灭族,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特大冤案,虽予以了平反,但逝者已逝,死者如何复活?
针对上述问题,刘颂、裴頠首先指出,“刑罚不苟务轻重,务其中也”,[5]P608这一见解非常有见地,这表明,在晋代,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看到了刑罚科学、合理的重要性,提出了类似于今天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虽然这些有远见的思想并未变为现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努力。
综上所述,由于《晋书·刑法志》记载了晋代人们在追求法律体系化、法律概念明晰化、刑罚轻重合理化等方面的努力与尝试,因此,晋代的人们在追求“法律科学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从而使得晋律成为“中古时期法典大备的开始”,[17]P153并造就了晋初的“太康繁荣”。据《晋纪总论》记载:“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棲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18]P3521以至唐太宗都不禁赞叹:“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通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19]P53
四、奉法循理,一赏一罚:一种较多法家意味的法律方法论
现代西方法理学厌倦了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转而致力于研究司法领域出现的法律问题,有人称这种倾向为“司法中心主义”,这导致“法律方法论”成为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显学”。殊不知,早在千余年前,我国晋代的人们就非常重视法律方法论问题。
在《晋书·刑法志》中,人们对具体的法律方法论述得并不多,但在司法哲学方面却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如果细细品味这些司法哲学,就会发现,它们带有较多的法家意味,因为其中不时透露出“刑无等差”、“法不阿贵”、“一赏一罚”、“反对释法而任私议”等典型的法家思想。对于法家法哲学在晋代的司法领域仍有很大影响,一些史书就有所揭示。《晋书·阮籍传》中有阮籍从孙孚“避乱渡江……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20]P902之语,《晋书·庾亮传》中又有“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太子”[21]P1273的记载。在《晋书·刑法志》中,卫展在上书里就提到了晋元帝时法家手段在司法领域泛滥的情形:“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5]P611并直斥这种法家手段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伤顺破教,如此之众!”[5]P611从卫展的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司法领域儒法之争仍非常激烈,法家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应用,并得到了普元帝政治上的支持,但已经丧失了理论与道德上的制高点,以至作为大臣的卫展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斥其非。
正是在儒法两种司法哲学的直接碰撞之下,产生了一些非常高明的司法理念,这些司法理念同样带有转折性、混合型特点。《晋书·刑法志》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详细地记载下了这些有价值的司法理念。
(一)司法应专门化,忌层级分工不清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色是“中央集权”,皇帝总揽一切大权,皇权至高无上,故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少讲“分权”与“限制皇权”,很少敢于谈及皇帝、大臣、法吏在职权上的“分工”问题,《晋书·刑法志》这一官修的史书对上述问题却有所论述。
首先,《晋书·刑法志》不太赞成皇帝亲自过问一般案件。虽然《晋书·刑法志》在谈到周公告诫成王应留心庶狱时,持一种赞赏的态度,但对汉晋以来的皇帝亲自过问案件多持一种贬抑的态度,对于魏明帝亲自过问案件时,经常出现“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的情况,更是持一种否定态度。
其次,《晋书·刑法志》借一些大臣之口,表达了“皇帝、大臣与法吏之间应有所分工”的思想。如《晋书·刑法志》里明确地说到:“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是以辩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5]P608对于皇帝、大臣与法吏之间应当如何分工,《晋书·刑法志》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5]P609
第三,《晋书·刑法志》还强调皇帝不能随便改变已经颁布的法律。因为那样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5]P610
以上就是《晋书·刑法志》提出的一些重要司法理念,它突出了维护法律统一性与权威性的重要性,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强调皇帝也应当信守法律,皇帝不能随便干涉审判。在帝制时代,提出这些见解是需要勇气与胆识的。刘颂等人提出的这些主张毫不逊色于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反对詹姆士一世亲自断案时的论断。
(二)法律应严格适用,不能“尽善曲法”
是应当严格地适用法律,还是应当宽松地适用法律?这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各家观点差异巨大。大抵而言,儒家主张宽松地适用法律,法家主张严格地适用法律。不同时期的人们看法也各异。一般而言,承平之世法律适用比较宽松,动荡末世法律适用比较严格。自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法律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乃至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在此之时,严格适用法律显得尤为可贵。因此,在《晋书·刑法志》中,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提出应严格适用法律。
曾任廷尉、三公尚书的刘颂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刘颂明确地指出了“尽善曲法”的害处:“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顺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5]P609在上述论证基础上,刘颂提出应严格适用法律:“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5]P609因为“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5]P609刘颂还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中国法制史上非常重要的论断:“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行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5]P610这一论断近似于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比西方近代的相关理论要早几个世纪。这一理念在《唐律》中正式落实为一种法律制度,这比西方相关制度的确立也要早很多。因此,这一论断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有着重大意义。
刘颂主张严格适用法律,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与支持。如汝南王亮也持类似观点:“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5]P611门下省的官员们也认为:“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5]P611东晋时的熊远又重申了刘颂的观点:“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不得任情而破法……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5]P611
非常可惜的是,刘颂等人的观点并没有为统治者采纳,“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5]P611咸康之世更为不堪,以至“后益矫违,复从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5]P613后世的沈家本先生看到晋代虽有好的法律却废弛不用、且所用非人,不禁叹道:“晋之法岂宽弛之弊哉,亦用法者非其人耳,苟非其人,徒法而已。”[22]P20虽然刘颂等人的观点在当时的实践中并没有被采纳,那也不妨碍它们成为一种先进的司法哲学。
(三)法律推理应具有客观性,反对罪行擅断
《晋书·刑法志》还向我们推销一种客观的法律推理方法,它包括以下一系列内容:
首先,应保证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客观性。《晋书·刑法志》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其一,法律应先公布,广泛地周知老百姓,然后才能以之为标准,惩罚那些犯罪者。这实际上是力图通过“公开性”来保障“客观性”。在这一点上,儒家与法家不谋而合。其二,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解释法律,反对故意地曲解法律含义。在《晋书·刑法志》中,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其次,应保证作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晋书·刑法志》非常重视案件事实的客观性。为了弄清案件事实,《晋书·刑法志》非常推崇周人发明的“五听”、“三刺”之法,同时还有所发明。这主要表现在张斐提出的弄清客观情实的具体方法。张斐认为,可以通过察言观色的方式弄清情实,因为“心动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肢,发于事业”,[5]P606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5]P606另外还可通过一些外在行为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如“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侯在视息”。[5]P606对于张斐发明的这套方法,杨鸿烈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发明了审判心理学……它与现今德国格鲁士所著的《犯罪心理学》第一部分的话极为相似,在中国书里除前此有刘歆伪造《周官》里有‘五听’之说外,就要算张斐最懂得心理学在司法上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了。”[9]P154
再次,应保证法律审判过程的客观性,这是具体实现前两种客观性的程序保证。为了保障前两种客观性得以实现,《晋书·刑法志》提出,应公开审判,让民众充分了解犯罪者的罪行。如在“王肃抗疏”这一故事中,王肃就认为,只有先揭露犯罪者的罪行,然后惩罚,才能“不污宫掖,不为缙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5]P596
综上,到了晋代,虽然我国古代的司法状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罪行擅断、徇私情乱法律的情形仍大量存在,但无法否认,我国古代的司法哲学至此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
五、简短的结论
《晋书·刑法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国传统法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几乎全都囊括其中,因此,它可谓一部全面记载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宝典”,虽然距今年代已久远,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一些深邃法哲学思想尚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今天的人们一谈到古代的法哲学,马上就会如数家珍般地搬出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法哲学,而很少关注中国传统的法哲学,似乎中国传统法哲学难以与西方法哲学相提并论。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习惯,创造出了独特的法律文明,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法哲学思想,它们是我国人民实践智慧的结晶,与西方的法哲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有义务对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加以发掘,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对之进行新的诠释,赋予其新的生命。在对之进行诠释时,我们既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突出中国传统法文化独特性的一面;当然也可以采用现代西方的一些新方法,将之与西方的法律文明进行比较,发掘其与西方法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只有交互使用这两种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中国传统法文化,并正确地评价其价值。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房玄龄等.晋书·郑冲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房玄龄等.晋书·杜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5]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Geoffrey MacCormack:"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Westport,Connecticut:Hyperion,1980.
[7]商鞅.商君书·定分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管仲.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0]刘笃才.论张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A].何勤华.律学考[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12]Henry Sumner Maine:"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Routledge ,1910.
[13][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4]Brian E.Maknight.法律与道德:对于宋代司法的几点思考[A].江玮平等译.中国法制史学会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主编.法制史研究[C].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出版,2004,(6).
[15]魏征.隋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6]王召棠.王召棠法学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7]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8]萧统·文选全译[M].张启成徐达等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9]房玄龄等.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0]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1]房玄龄等.晋书·庾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2]徐世虹.沈家本全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