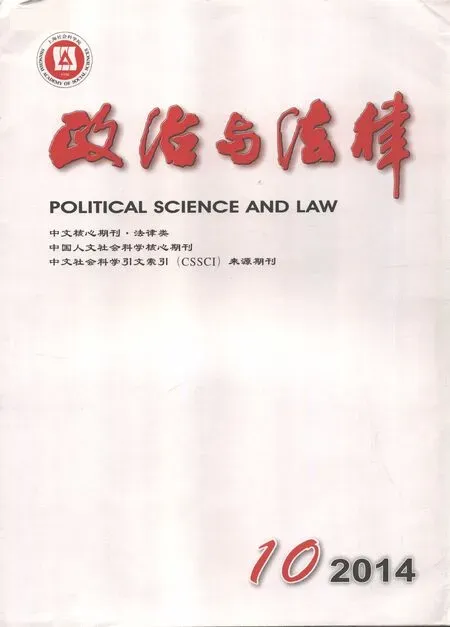临终会见:究竟是谁的权利*——死刑临行会见权的归属及保障探寻
何成兵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在死刑依然存在于中国刑法典的现时期,国家通过司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合法性问题,而死刑犯会如何被临终对待则是一个正当性问题。曾成杰案件将死刑犯的临终告别权引入了自媒体时代公众的视线,死刑犯是否有临终告别权引起热议。①湖南商人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于2013年7月12日突然被执行死刑,家属并未得到通知,也未见上最后一面。其女儿微博抗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回应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3 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死刑临终告别如此被漠视?疑问尚未消散,时隔仅仅两个多月,沈阳小贩夏俊峰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一案又激起了更大的疑问:死刑的临行会见权,是死刑犯的权利,还是其家属的权利?②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隐蔽携带的切肠刀多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后又重伤一人。2011年5月9日上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沈阳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的一审判决。2013年9月25日,夏俊峰被法院核准死刑,其家人被通知去见夏俊峰最后一面,在半个小时的会见结束后,夏俊峰当天被执行死刑。规定在司法解释中的死刑临刑会见权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一、死刑临终告别应当成为法定权利
死刑的临终告别,该称谓并不因曾成杰案件而起。早在2006年,陕西邱兴华恶性杀人案引起全社会极度的震惊与轰动,在邱兴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交付执行后,他的妻子何冉凤才从记者口中得知丈夫的死讯,最终也没能和丈夫见上最后一面。这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北京《法制晚报》于2006年12月29日刊登了《专家观点:家属应享临终告别权》一文,文中援用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张平的观点:“其实这种临终会面应该被称为临终告别权。这种权利是双方面的,从理论上讲,不管是死囚还是死囚家属都是应该享有临终告别权的。”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还没有兴起的2006年,“临终告别权”犹如昙花一现,转瞬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外。直至2013年曾成杰女儿微博上的抗议,又将这一概念拉回公众激烈论辩的话题,并持续发酵至今。毋庸置疑的是,死刑犯临终告别符合大众道德价值判断,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国人民传承至今的“死者为大”的观念。所以每每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临终告别的权利纳入全民热议话题时,支持者总是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临终告别如若作为一种权利,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它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吗?如果这两点可以得以证实,那么,探讨死刑犯临终告别的权利才具备初始的意义。
(一)合法性
1.死刑临终告别符合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此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人权入宪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一切法律的制定及修改指明了方向,开启了我国法制史上关于人权保障问题的先河,权利意识也将深入人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的再一次大修。其间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对于此次修法,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个修法过程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其中,“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最大亮点,被视为是继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通过法律修订释放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刑事法制捍卫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飞跃。
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而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
2.死刑临终告别在国外的合法性
公元前399年,以哲学成就闻名世界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不信神和败坏青年思想。苏格拉底在死刑执行前会见了亲朋好友。著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描述的正是苏格拉底临终告别的场景。画面中苏格拉底和弟子及朋友们共处一室,在牢房里完成了生离死别。弟子朋友们依偎在苏格拉底身旁,传达出浓烈的不舍和哀伤。有关资料也记载了苏格拉底临终会见的场景:“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就要在雅典监狱中被处决了。他虽然衣衫不整,披头散发,但面容却镇定自若、目光如炬。家属走后,他与几个朋友侃侃而谈,似乎忘记即将到来的处决。直至狱卒送进来一杯毒药,他才收住话题,一饮而尽。”③[美]霍普梅:《苏格拉底:最伟大的思想家》,瞿旭彤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3 页。很显然,当时的雅典法律,对于死刑犯的临终告别,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西方国家对死刑犯的临终告别历史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7 条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的大多数在立法中赋予了罪犯临刑会见权。
在美国,死刑的存废因州而异。多数州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州,死刑犯一般也会被允许与亲朋好友及其辩护律师通话通信,定期会见。同时,律师有权随时会见死刑犯。部分监狱甚至实行“接触探视”,死刑犯可以不被约束地与亲友交谈和接触,可以一起进餐、玩乐。死刑犯自接到处决命令后会被转移到死刑犯牢房,在那里可以与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处决前的最后一餐将会允许死刑犯的近亲属、律师及监狱局同意的其他人与死刑犯共进。有的监狱死刑犯甚至有与配偶临终同居的权利。
3.死刑犯的临终关怀在我国历史上的传统
在儒家文化浸染下,古代的中国是特殊的“家国合一”的模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支撑的伦理规范成了事实上统治社会的普适规则。“循天理,顺人情”,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适用原则。“死者为大”的传统文化心理造就了死囚临终前法律的特别恩惠。唐《狱官令》就有明确的规定:“诸决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宣告犯状,仍日未后乃行刑。”④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 页。在宋代,文学家宋祁任常州司法掾时,“每有重辟,必持案谂,囚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相见”。公元1086年4月,殿中侍御史林旦上言中提到《元丰令》令文:“决大辟时,仍先给酒食,听亲戚辞决,示以犯状,不得掩塞其口”。显然这一规定的落实并不理想,因此林旦上言:“罪人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亲戚辈亦何缘与囚辞决。”⑤同上注,朱勇主编书,第123 页。可以看出,死刑犯与亲戚的“辞决”,除彰显司法人性化之外,给予了犯人一个最后申诉的机会,如若确有冤情,亲属日后可助其昭雪。可见,临终告别权在我国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虽然这种临终告别的出发点并非来自于权利意识,而是统治者悲天悯人的一种姿态,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同样照顾到了人之将死时的尊重与亲情的需求。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十年来,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执行死刑前,常会让等待执行的死刑犯吃一顿“断头饭”,会提供尽可能好的伙食套餐,配备香烟等牢房里的“奢侈品”,为的是“一路好走”。甚至有的法警会拥抱下死刑犯以示最后的告别。这些做法既体现了司法人道主义,又稳定了死刑犯的情绪。
(二)合理性
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史中,道德标准在相当长的时期远远优先于法律标准。很多道德性的权利和利益成为大家共同自觉维护的天然存在。在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评价体系里,一个将死之人与家属见“最后一面”,具有同吃饭睡觉一样的天然正当性。在公民与国家的法律契约中,即便死刑的合法化意味着公民将生命权托付给了共同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有尊严地走向死亡的道德权利。
1.权利的天然性
对于即将被行刑的死刑犯而言,临刑前见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代一下后事,乃是他们及其亲属感情上的最后需要,也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从权利保障来看,死刑只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并未剥夺罪犯的其他权利。虽然最终罪犯的绝大部分权利都将会随着死亡而灰飞烟灭,但死亡之前未被剥夺的权利,仍当然合理的存在着。
对于死刑犯的家属而言,临行前会见意味着最后的告别。从古至今,无数的故事及事实述说着这样一种境遇:在至亲的家属临终时没有在场,不能送别,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无法言喻的苦楚和折磨。很多人因此抱憾终身。诚然,被判死刑的罪犯是给这个社会和他人造成了不可饶恕的创伤,对于亲属而言,没有基于法律求情的权利,但其仍有基于伦理送别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使死者安心,生者释然。
从尊重人的尊严来看,有必要保障临终告别权。因为罪犯及其近亲属作为社会中的人,除去自然属性之外,更多的是社会属性,无论多么罪大恶极,都不能割裂罪犯与其亲友之间的情感联络,情感交流是罪犯及其近亲属的最基本的诉求。特别是在死刑执行之前,罪犯与其亲友见面交流的愿望会更加迫切。无论对罪犯还是对其亲友来讲,在罪犯临死之前见上最后一面,都是一种莫大的情感慰藉,也能满足罪犯对身后事务做出安排的心理需求。正如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所言,“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保障罪犯及其亲属的临终告别权,是人性与道德的体现。
2.司法的人性化
死刑是剥夺生命权的最严厉的刑罚,亦被称作极刑。如何让罪犯“走”的口服心服,“走”的无怨无悔,除了要在审判中保障判决的公平、公正外,行刑的人性化处理也是有其极大的意义的。依法安排临刑前会见其家属可以使死刑犯在生命最后关头得到精神慰藉,有效缓解死刑犯的心理压力,还可以减少发生意外的概率,也能确保死刑能够正常执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性化的临终告别,在情感方面,使曾经冷漠的罪犯能唤醒良知,使其灵魂得到净化。在法律感召方面,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这是其他做法都无法比拟的。
临刑会见,给了法律一丝温暖,在惩治罪恶的同时,感召生者:生命珍贵,守法珍惜。
3.亲属伦理的法治关怀
亲属权是身份权的一种。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特定身份而依法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身份权包括亲权、亲属权等。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的管教、保护的权利。亲属权是亲属之间的权利。亲属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亲属。广义的亲属包括血缘、配偶和姻亲,狭义的亲属不包括配偶关系。亲属权的内容规定在民法中,主要有以下具体权利。(1)抚养、扶养权。《婚姻法》第22 条、第23 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外)祖父母对于(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义务。扶养与抚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资助,同时包括精神上的扶助、身体上的照顾。(2)赡养权。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婚姻法》第22 条还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外)孙子女对(外)祖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3)代理权。《民法通则》第13 条、第14 条规定,有监护权的亲属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代理权。《民事诉讼法》第58 条规定了近亲属的诉讼代理权利。(4)申请宣告失踪、死亡、申请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权。这些是民法中规定的主要的民事权利。这些基本的亲属权,笔者暂且称为一般亲属权,指亲属之间享有的,概括体现亲属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为全部内容的一般亲属权益,并由此产生规定具体亲属权的基本权利,其功能类似于一般人格权,对具体权利起到补充和完善亲属权不足的作用。
在罪犯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与家属的身份和身份权利依然存在,不受法律剥夺。所以,死刑前的临终告别,是死刑犯及其家属基于身份所享有的伦理权利。这种基于身份产生的伦理权利便具备当然性和现实性。符合中国人民的传统文化。如若将这种伦理权利加以法制化表达,由作为公法的刑事诉讼法将其上升为死刑临行会见权,并同时赋予身份关系的双方——死刑犯和家属,那么,法治将更容易因具备民意得到弘扬,因符合伦理得到支持。
4.制约权力的权利表达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认为“人们互相依仗而又互为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这在实际上对各人都属有利。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19 页。这话固然有一定的武断性,但避开人性善恶的争执,其道出了人依据社会属性进行活动时,必须有所收敛,不能为所欲为的道理。“绝对权力易生绝对腐败”的道理是共通的,因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⑦[美]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8 页。
在被最终行刑之前,死刑犯要在羁押场所度过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对死刑犯的关押成为一种极其隐蔽的权力。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羁押合法性的职责,但这种监督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这使得这种羁押权力成为一种实质上的绝对权力,于是极有可能发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虐待折磨、非人道待遇等非法行为。对死刑犯的人权保障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和隐患。而赋予并保障死刑犯及其近亲属的临终告别权,家属可以在会见时清楚地看到死刑犯是否受到身心伤害,通过倾听死刑犯的诉说了解看不到的隐情和细节,这犹如一丝阳光洒进黑暗的角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死刑犯多了一个管道向外界展示自己在羁押场所的待遇,司法便多了一层对公平正义的守护。
综上所述,死刑临终告别既具备合法性,又具备合理性,理应以立法的形式确认并保障这一伦理性的权利,如若纳入立法保障,为区别于死刑犯之外的民间的临终告别,并且更为严谨准确地界定这一权利,宜把死刑犯的临终告别的权利确定为“死刑临行会见权”。
二、死刑临行会见权的内涵及现状
如前所述,死刑临终告别是一种伦理权利,将之赋予法治保障后便成为一种法律权利——死刑临行会见权。
(一)死刑临行会见权的内涵
探讨死刑临行会见权的内涵,必须明确两个方面:一是权利归谁?二是权利的内容包括哪些?1.权利归属
死刑临行会见权在民法上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身份关系中的双方都享有这一权利,是题中应有之意。
(1)死刑犯有临刑会见权
死刑犯应当享有临行会见权,是基于人格权的考量。
在刑事司法中,死刑案件涉及人权保护、涉及民意、涉及社会综合治理、涉及国际形象等方方面面,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尺,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死刑犯之所以当死,是因为他对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但在其被执行死刑之前,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个体,这种个体的社会属性不能被漠视或限制,否则便是对社会规则的一种践踏。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人性在任何时候都看作目的,不能只视为手段”⑧[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 页。;“法院的惩罚决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无论是对犯罪者本人还是对公民社会”。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3 页。生死离别,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无论死刑犯如何罪大恶极,其作为人表达亲情的权利不容剥夺。准予死刑犯与亲属作最后的会见,既可以满足他们表达亲情的欲望,也有利于罪犯认罪服法,还可使其亲属感念国家的仁慈之举,接受刻骨铭心的法制教育,并能让死刑犯对身后之事做些交待和安排。因而,死刑临刑前允许死刑犯和近亲属做最后的告别,是司法人性化的必然要求和司法理性的发展趋势。
(2)近亲属有临刑会见权
死刑犯的近亲属应当享有临行会见权,是基于作为公法的刑事诉讼落实宪法确定的基本人权以及确认和规制身份权的考量而要求的。
身份权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亲属权,是存在于一定身份关系上的权利。王利明教授在其《人格权新论》一书中对身份权的定义是:“身份权是存在于一定身份关系上的权利,主要存在于亲属的身份关系之上,故亦称亲属权。”⑩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 页,第201 页,第204 页。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一些论述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数学者认为传统民法意义上的身份权一般限于亲属法的范围之内,基本上不存在亲属法之外的身份权。史尚宽先生即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生之权利,广义的包括亲属法上及继承法上之权利。最基本的身份为父母、为丈夫、为亲属,可称为根本的身份权,然通常此等地位仅称为身份。身份权系指由此根本的身份权分出之具体的权限或此等权限的集合。”⑪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 页。现代民法意义上的身份权的独立涵义是: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或身份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和非亲属法上的身份权;亲属法上的身份权主要包括配偶权、亲权以及亲属权,非亲属法上的身份权主要包括监护权、著作人身权、荣誉权、社员权和成员权等权利。
死刑近亲属的临刑会见权,虽然不是民事权利,应当规定刑事诉讼中,但是其所承认和规制的乃是公民的亲属身份关系和亲情自然属性。就死刑犯近亲属的临刑会见权而言,也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身份亲属权的肯定、保护和规制。
2.权利内容
死刑临刑会见权具有公法上的请求权特性。死刑临行会见权是由公法确认、保护和规制的人身权,其没有财产性利益,而有精神性利益;同时,死刑临行会见的实现,需要相对人的配合,对权利客体不能直接支配;其权利实现所请求的相对人理应是执行死刑判决的司法机关及其确定的关押机关。作为相对方的司法机关既有配合权利方的死刑犯及其近亲属实现临刑会见的义务,也有职责履行这一义务。相对方司法机关不履行这一义务和职责的,应依法承担公法上的责任。
同时,死刑临行会见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包括有获悉死刑复核结果的知情权、获悉死刑行刑时间及方式的知情权、会见权等权利。
(二)死刑临行会见权的现状
全国范围而言,关于死刑临终告别权利的规定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死刑犯及其近亲属在死刑执行前可以提出会见申请,司法机关可以准许。此后司法实践并不乐观,多数法院处于观望状态。2007年,“两高两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将1998年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规定对于死刑犯及其近亲属提出的会见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从“可以”到“应当”,死刑临终告别权完成了质的转变。但是,司法现状却并未因此有大的改善。不少法院仍然对死刑临终告别持回避态度。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3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而各地相关规定与落实情况并不一致。2003年9月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出台地方细则,确保临终告别得以落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仅在2004年就批准了7 次临终告别。2005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会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死刑犯与家属会见的实施意见》,细化了死刑临终告别制度。这一年,广东省佛山市对所有提出临终告别的申请都予以了批准,并作出了安排。之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会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了《死刑罪犯会见近亲属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推进死刑临终告别在江苏省的落实。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大部分省份和地区对于死刑临行会见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响应姿态。
我国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临行会见权”做出了规定。有人指出,“这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死刑犯会见亲属做出规定还不够,有必要将死刑犯会见亲属的提起、批准、实施等相关规定明确写入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使尊重人权、人道主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能进一步得到体现。”⑫宇文:《明确“临刑见面权”具有积极意义》,《方圆与法治》2007年第3 期。对此,笔者非常赞同,理由下文会有所论及,于此不再赘述。
三、死刑临行会见权的现实路径
如前所述,死刑临行会见权并非没有相关规定,但却很难落到实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规定(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过低;二是权利内容不明晰,主体不确定;三是执行机关的担心和焦虑对死刑临行会见权的落实形成了巨大障碍;四是死刑犯所在的监管部门不配合、经费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据笔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死刑执行法院通常的心态在于:如果通知了家属,死刑犯在临刑前见到了家属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死刑犯的情绪波动,给执行工作带来不可预料的危险和麻烦。如果家属不能控制好情绪,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也会威胁到执行工作的安全进行。因此,死刑执行法院都会以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态对待死刑临行会见权的落实。笔者认为,对此,应当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制度构造来保障死刑临行会见权的落实。
(一)权利定位:把死刑临行会见权上升到法律高度
根据《立法法》,权利的赋予必须通过法律设定,而通行于全国的司法解释,则因其尴尬的法律地位不能很好地保障临刑会见权的落实。
首先,司法解释并不具备宪法依据。迄今为止,我国《宪法》、《立法法》中没有“司法解释”这样的法律术语。目前与“司法解释”相关的法律文件最早来源于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第2 项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上述规定一般被解读为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进行“检察解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法律文件认定“司法解释”的概念,或者是认为“司法解释”仅包含“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解释”的主体被进一步扩大,公安部、司法部、国安部等也会参与制定相应的法律适用解释,这种解释也被统归于“司法解释”的门下。这些解释因为政出多门,不少条文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客观上反而导致了法律适用中的混乱,影响了法治权威。较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通过的法律,不具备宪法依据的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中被尊重和服从的程度较弱。
其次,司法解释不能创设新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的法治框架内,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其制定的法律在效力上具有普遍性,是每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日常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是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依据,同时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裁判标准。所以只有立法才能赋予某种权利,创设一种规则,然后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护这种权利和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立法解释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所以也可以创设权利和规则。而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做出的“审判解释”、“检察解释”、“联合解释”,只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实施活动,不属于立法范畴。因此,“审判解释”、“检察解释”、“联合解释”没有权力创设权利,而只能明确或解释法律适用中存在的程序性问题。死刑临行会见权在法律没有规定之前,属于伦理道德权利,基于司法人性化的考量,执行机关应当予以保障;其在法律规定之后,成为一种具体化的实在权利,执行机关也应当更加细致地加以落实。但是,死刑临行会见权却不能由司法解释加以创设,虽然这种创设较之没有相关规定之前有较大进步,也推动了死刑临终告别实践的发展,但因其固有的“名分”问题,导致实践中会出现“愿者遵从,违者没事”的不良状态,这反而会从另一个方面损害司法权威。
所以,为解决死刑临行会见权的“名正言顺”问题,必须改由《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死刑犯及其家属在死刑执行前享有会见权。”该权利具体的落实可由司法解释加以细化落实。但鉴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刚实施一年有余,修改频繁将影响法律的稳定性,更可行的方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立法解释,赋予死刑犯及其近亲属死刑临行会见权。
(二)权利主体:死刑犯及其近亲属
如前所述,死刑临行会见权既归属于死刑犯又归属于死刑近亲属,对此,当该权利落实之际,必须准确界定死刑犯及死刑近亲属的范畴。
1.死刑犯
死刑犯顾名思义是即将被依法剥夺生命的罪犯。这本不应该产生歧义,但是,由于死刑临行会见权具备双向性,必须考量关系另一方合法合理利益,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安排死刑犯的临刑会见。对此,以下情况死刑犯的临刑会见权将受到剥夺或限制:(1)死刑犯故意杀害近亲属的;(2)死刑犯对近亲属具有严重虐待、遗弃等行为的,近亲属同意会见的除外;(3)死刑犯自己不同意会见的;(4)死刑犯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可在保证双方安全的前提下安排隔离会见。
2.死刑犯近亲属
死刑犯的近亲属享有死刑临行会见权,在这一前提下需要界定的是,近亲属的范围有多大。在立法上,近亲属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在民事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 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刑事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106 条第6款,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行政法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 条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从上述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法领域中的“近亲属”范围最广,民法领域次之,而刑法领域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最窄。
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与严肃性,死刑犯的近亲属范围宜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界定:配偶、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同时,考虑到临终告别的特殊性,此范围适宜做扩大解释,上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对于生离死别的最后一次权利而言,更具备人文关怀。如此一来,《刑事诉讼法》便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对近亲属范围作如此的扩大解释,则《刑事诉讼法》有关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代理的近亲属规定便失去了应有的立法考量。但是死刑临行会见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近亲属范围,则不能彰显司法人性化。对此,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或立法解释时,在确定死刑临行会见权的相关条款之内,专作一款规定:“本条所指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由于近亲属人员较多,且与死刑犯亲疏远近关系不同,双方期望最后一次相见的迫切程度不同,可仿照监护权的设置,给予近亲属临刑会见权的不同待遇。在民法领域,监护权包括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和精神病人的监护权,由于现行法框架内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对死刑犯的司法临终关怀适宜参照民法上精神病人的监护权的设置。换言之,可以把近亲属划分为不同的顺位:(1)配偶;(2)父母;子女;(3)其他近亲属;(4)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经死刑犯和死刑执行法院同意的。对于这五类主体,理论上共享死刑临行会见权,但优先等级不同。对于第一、第二顺位的近亲属,法院必须通知,经申请符合条件必须安排会见。对于第三、第四顺位的近亲属,法院可以不必通知,但其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申请并符合条件的,法院也应当安排会见。
(三)权利内容:时间、地点、方式
死刑临行会见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若欲使该权利得以实现,权利的内容必须明确。
死刑临行会见权的时间有三种确定方法,其一是法院通知会见权的时间;其二是死刑犯及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时间;其三是安排会见的时间。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死刑执行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执行。“七日”这一期间是考量了死刑执行的影响及行刑风险等因素不宜因为死刑临行会见权而延长。那么,临行会见权的落实必须在7日内在以上三种方式内确定会见时间。其一,法院通知会见权的时间,宜由原审法院自接到死刑执行命令后2日内通知死刑犯及近亲属。其二,死刑犯及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时间,自接到死刑执行法院通知后24 小时内提出。其三,安排会见的时间,则死刑执行法院在收到临刑会见申请后至行刑前一天安排会见。会见时间一旦确定,执法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安排。具体会见的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最短不得低于1 个小时。
为安全起见,死刑临行会见应当安排在原羁押场所。对此,实务中应做好死刑犯羁押机关的沟通协调工作,同时在立法上给羁押机关设定相应的配合义务。
有些看守所已经设立专门的死刑临行会见室来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有条件的羁押机关可以参照。另外,为体现司法人性化,除非会见双方有人患有传染病或有暴力倾向等,原则上应当安排无隔离式会见。在严格安检的前提下,会见双方可以肢体接触,可以拍照合影。对于患有传染病和具有暴力倾向的情形发生时,应当安排隔离式会见。
(四)权利救济:纳入检察监督
在现代法治国家,权利救济的渠道通常存在于司法中。只有通过司法裁决,才能分清是非曲直,还原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的真相,依法确定救济的方法和程度。这样的救济才能使权利真正达成。
死刑临行会见权既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对于其程序性权利内容遭受侵害时的救济,宜以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进行,正如检察院具有死刑临场监督权一样,在死刑临行会见权遭受侵害时,死刑犯或其近亲属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为避免申诉不被漠视,应当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接到死刑临行会见权申诉时通知人民法院七日期间暂停计算,待申诉处理完毕时继续计算。对其实体性权利的救济,可通过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律责任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