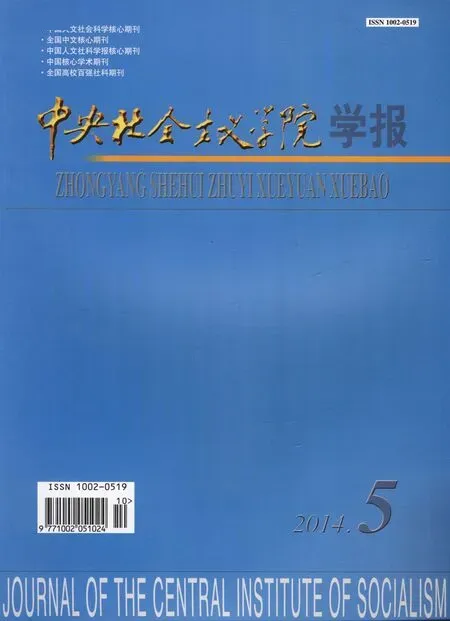从中华文化价值看中国发展道路
刘鲁会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中华文化研究·
从中华文化价值看中国发展道路
刘鲁会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文化代代相传、得来不易,有其价值所在。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绵延不绝,有其鲜明特色。文化决定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证明,模式不能照搬,文化无法背离,道路只能探索。这是我们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根据所在。
文化价值;中华文化;道路选择
文化决定道路,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选择发展道路,文化更为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发展而来,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坚持“中国实际”,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习近平强调“自觉自信”、“底线定力”,其根本都是从中华文化价值特色出发,走自己的路。
一、文化的价值
(一)文化价值与物质价值不同,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
文化由人创造、为人所需,供人所用、理家治国,很是值钱。物质的价值好说,看得见摸得着,视劳动和市场而论;文化的价值,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沁人心脾,值多少钱,就很难说。
有些文化在东方值钱,在西方就不行。咱们的《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以礼相待、互相谦让,不要相争。然而,拿到美国小学的课堂上讨论,结果大不一样。人家孩子说,这事大错特错。一是怎么能让四岁的孩子分梨,大人干什么去了?二是孔融分梨的原则也不公平,凭什么大人吃大梨,小人吃小梨;三是为了分配公平,应该制定《分梨法》,交公民讨论,还可以民主竞争。
就算是中国人,也有文化差异。拿一部《红楼梦》来说,鲁迅曾指出:“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当然也有例外,像毛泽东那样,把一部《红楼梦》看做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书中价值就难以估量。据说毛泽东的一生,光《红楼梦》就至少读了二十遍,如此重视学习传统文化,他该是从中汲取了多少丰富的精神营养?
(二)文化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精神财富
物质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物质财富,满足人的吃穿用行;文化财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有句话说得好:“文化暖心,艺术化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我们的祖先,挑几块石头磨磨,刻刻画画,整些形状符号动静,这就告别了动物,站立成人。后来,就一发而不可收,越整越美,有了文字书画音乐戏剧舞蹈,又有了报纸书籍电影电视网络大片,这就是文化。总之,文化财富和物质财富,犹如阳光、空气、清泉,都是人类的基本需要,离了谁都不行。
去年我去成都考察金沙遗址,发现它有“两多两少”:玉器和象牙多,粮食和农具少。玉器多达万件,象牙层层堆积。这说明什么?第一,说明那时成都平原物产丰富、生活富足,人们闲着没事,都在那儿打磨玉石,或用作祭祀礼品,或穿戴打扮在身,美化心灵。第二,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蜀国,人们已经告别打磨石头用作劳动工具和狩猎武器的旧石器时代,将其升华为文化艺术的追求。第三,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人类社会要发展,物质财富是硬实力,文化财富是软实力,不论什么时候,二者都相辅相成。
(三)对文化价值不要轻易臧否,要存敬畏之心
文化可以转化为金钱,又没法用金钱衡量。如果非要衡量文化的好坏高低,那就是把文化放到人类进步的天平上,去称称它的分量;放到历史长河中冲刷,去看看它的黄金成色。文化是流变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文化有没有价值,有多少价值,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在文化面前,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对待文化,不能随意臧否。只有尊重传统,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能明白身处其中,今后该向何处去。
恰如诗言:“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看文化价值,几千年沙里淘金的代代相传,一定要存敬畏之心。何为敬畏?敬就是敬重,畏就是畏惧。文化博大精深,一个人再了不起,在它面前也仅沧海一粟。中宣部《党建》杂志总编辑刘汉俊博士说:“一个心中没有神圣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一个不珍视自己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力量的民族。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先贤都不礼敬,还能有怎样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文化可以讨论。但要指出,中国自明清以来,对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儒家学说,就有“疑古”思潮和学派,尤其怀疑代代相传的“三皇五帝”这段起源。但无论如何,“疑古”本意,是辨伪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近代以来,一些人以西学为代表,以“疑古”为理由,企图对中华文化推倒重来,对此应明辨是非,不应随波逐流。
(四)看文化价值,得有一个认识过程
文化似书,书到用时方恨少,有用才能体现价值。例如,现在人们普遍关心文明发展面临的危机,感到像西方那样,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征伐自然索取自然破坏自然,一条路子已经走到尽头,于是蓦然回首,想要到老子、孔子和庄子那里寻找答案,说里面藏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能矫枉过正。
有学者反思西方道路,那绝不是危言耸听:“人类文明,当时看一片光明,过后看喜忧参半,长远看乐极生悲。”这就提醒我们,看文化,犹如白居易诗中所说:“试金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也不是文化不可知论者,但问题是,看物看人,得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若看文化价值,则要有一个长的历史周期才行。文化面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二、中华文化的价值
(一)总结中华文化的百年教训
文化可以扬弃,但丢了不行。这些年来,很多海外同胞到大陆一看,近几十年革命荡涤,传统文化已所剩不多。有海外网民戏称: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的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曾派人去学习国内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要看大陆的传统文化,就所剩不多或成“四不像”了。
百余年来,我们对外来文化,吸收了一些皮毛而没得精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用台湾同胞的话说,大陆早就革了它的命。很多人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心惶惶、夫妻反目,邻里猜疑、师生相告,毫无仁爱善良中庸可言。更有甚者,1966年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众来到曲阜,洗劫“三孔”、掘开孔墓,毁坏碑刻、焚烧典籍,上演了现代“焚书坑儒”一幕。
然而,就在我们将传统文化当成“四旧”进行文化革命之时,台湾却发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将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留在了海峡那边。去过台湾的人都感到,那里是传统文化熏陶的温情脉脉的礼仪之邦。他们从传统文化的经典开始,坚持保留国文的繁体,生怕造成历史的断档失忆。台湾小学必修《国学概要》,以经史子集为主;高中必修《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是“四书”的内容。相映成趣的是,此书曾在福建拿来试行多年,效果很好,学生们普遍变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现已得到咱们官方认可,开始走进大陆学校的课堂。
(二)重回中华文化的历史原点
就在21世纪初,联合国发出一个声音: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思想智慧。人们呼唤重回原点,意义非同一般。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自源头流淌至春秋时代,当由孔子集大成。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在春秋战国实现一个飞跃,在孔子那里形成一个巅峰,齐鲁文化研究院王志民院长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高地”。他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化轴心时代。它是对之前的两千年中华文明大总结的时代,也是对之后两千年中华文明开启的时代。”
山东大学高等儒学院副院长颜炳罡也说:“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因革损益全收在孔子那里,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其生命最健旺、创造力最强盛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要“回到先秦时代去,回到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等等先哲时代去,寻找中华文化最富有原创性的智慧,让它重新点燃当代中华文化复兴的火焰”。
刘汉俊博士说得更是精彩:“孔子是人类的慧根。他指点了中华文明的圆心,也开辟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孔子师先儒而有独创,集大成而有深造,尊古但不守旧,坚守却能应变,包容又有创新,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他回顾说:“孔子以后,经孟子、荀子到汉代经学、唐代经学、两宋理学、宋明心学及至现代儒学的加入,使儒家文化蔚为大观,南北朝、元清北方民族策马中原,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诸子百家兼收并蓄,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慈悲为怀,墨家的兼爱非攻,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洋洋大观。”
儒学为什么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因为它以人为本、博采众长。儒学的“儒”,原是春秋时期主持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主礼官、祭祀官,孔子曾是鲁国的祭祀官,因此,后人称他的思想学说为儒学。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儒学博士傅永聚说:拿儒、释、道、法家的思想相比,“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儒家是粮店,一时一刻离不开。其他都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有时间可以逛逛,有病可以治治”。这个比喻很深刻。儒学的内核是仁学,“仁者人也”,儒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举凡人的生活、生存道理,囊括其中。
(三)开启中华文化的千年轮回
中华文化的命运,走了一段弯路,就像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原点开启了新的轮回。这就像许多学者所说:拨乱反正,培根固元,返本开新。
当今世界向中华文化伸出热切的双手,我们应当高瞻远瞩。这里,不能不说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情。1964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对他的政府部长们出其不意地说:“中国是一件大事”,“她就在那里,无视她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她的未来应当同她的实力相对应。我们不知道她会用多长时间来发展,但能够确定的是,总有一天中国会成为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巨大事实”。戴高乐接着说:“我们要翻过殖民地这一页了——不排除中国会在下个世纪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像她以前数个世纪所保持的那样。”戴高乐还驳斥一些反对派人士:“中国首先是中国,然后才是共产党的,它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并拥有几亿人口,占据了广袤的土地,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就这样,法国出其不意地宣布与中国建交,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抛在了一边。1965年,法国国务兼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出访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并到延安参观,之后写了《反回忆录》一书,说了这么一句伟大的预言:“三百年的欧洲能量已尽,中国时代开始了。”此话一出,在西方封锁围困中国的那个时代,无异于石破天惊。
这个故事很有启示。那个时候,东西冷战、铁幕紧锁,中法建交、开辟时代,根本在于两个民族的精神默契、文化认同。其实想来,19世纪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早就说过,中国是个睡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为之发抖。最近,习近平同志在法国访问时加了一句,“现在中国醒了,但她是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十分形象地描绘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特征。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为此,我们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三、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
(一)找找咱们的文化软肋
这些年,全球“中华文化热”乘势而上、方兴未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千余所,学生无数、好评如潮,引来一些反响实属正常:有人抱着傲慢态度,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指手画脚,专门说三道四;有人站在学术立场,谈些观点看法,旨在尽善尽美,多半好心好意;还有一种声音在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已所剩不多,弘扬中华文化有没有资格?”这一下子击中了我们的软肋,揭开了近代以来的一个文化误区。
近代以来,围绕几千年文化传统,面对西学的冲击,我们总是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折腾。有学者认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在国势衰亡的紧要关头,失去了文化自信,怀疑自己的祖先,提出“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把中华文明的族谱搞乱,把孔子乃至整个先秦诸子妖魔化,最终让人信无可信。直至今天,一提孔子,马上就想到“落后”、“保守”、“反动阶级的代言人”,这种负面消极的宣传,隔断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阻断了当代人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理性对话,污损了孔子思想的正面价值。
回顾中华文化所走过的历程,自孔子编经、秦人灭经、汉人尊经、唐人注经、宋人疑经,直到西学进来,传统文化命运多舛,或发扬光大,或毁灭殆尽。结果告诉我们,文化犹如大江东去,事物总是物极必反,传统还要辗转传承。百年以来,我们为了搞现代化,冲破千难万险,付出千辛万苦,摸索这样那样的主义,结果都没有弄个一清二楚。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明白了,西方的那一套不合国情,不管什么主义,终归要扎根中华民族的黄土地,在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中实现凤凰涅槃。
回想中华儿女几代接力、艰辛探索,我们尽管没有穷尽真理,但终于有了被实践证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理论总结、制度保证。让人不禁感叹,在文化问题上,该丢的怎么也丢不掉,该捡的还得捡回来。总结以往的成败得失,人们想起一句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二)反省我们的文化误区
我们的百年探索,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过去总以为“西学”是好东西,现代化就要“西化”,好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势如水火、有我无他。其实,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化从来不是空中楼阁,离开文化传统这个基础,就没有什么现代化。
过去,我们在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上,不尽人意。美籍华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结语中这样描绘:“今天中国人文生态较之清末或五四时代已远为贫乏,一般知识人的心态则依然未能摆脱‘视西籍如神圣’的境界,至少在潜意识中仍隐隐约约地认为‘真理’在西方。无数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等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发展规律,它假定所有的‘传统’的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它也再一次以失败收场。”因此,“今天是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究竟怎样重新出发?余英时借用“围城”,给我们画了一幅有趣的自画像:近代中国人不但在婚姻上陷入“围城”,在文化上也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他想到钱钟书《围城》中的一幕:“方鸿渐在无锡演讲,台下有一位秃头的国文教师,一直在摇头,但等到方鸿渐引了一句《荷马史诗》上的话,这秃头便立刻被镇住了,不敢再摇头了。可见这一心态,由来已久。这是今天必须加以深刻反思的。”他告诫我们,不要盲目崇洋媚外,只有深深扎根自己的文化传统,精心培育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走向现代化的明天。
(三)分析中国的特殊道路
文化不管怎么融合,现代化不论怎样创造,说到底,任何原理都要与一国实际相结合,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真理。理由很简单,南橘北枳,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发展规律,谁生搬硬套、随心所欲都不行。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深化改革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文化是历史的传承,如抽刀断水,哪段都无法分割。有人曾意味深长地说,即说晚清之后变革,也是腐肉新生。没有晚清腐败,何来五四觉醒?近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百多年学来学去,最后还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出本国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形成有三个理论来源,那么在东方中国,马克思主义则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原装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自己的传统文化。
文化是相通的。郭沫若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马克思进文庙》,很有意思:马克思有一天进了文庙,看到孔夫子正在啃凉猪头肉,孔夫子抬头一见,就说起他的“大同”理想,马克思听了不禁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一致!”这个故事虽说有点罗曼蒂克,但也说明英雄所见略同。诚如冯友兰所说:文化之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也如中外学者在尼山论坛所说:“人类不同文明,有着共同伦理。”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看得很清楚。据说施密特退下来以后有一个心愿,他想寻找离开西方的中国文明为什么能五千年绵延不绝且仍有现代活力的迷人之处。为此,他多次来华与邓小平会谈切磋,终于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进行的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实验,假如没有先前的儒家学说,这种实验不会取得如此的成效。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施密特慧眼独具,他不是把中国的成功简单归结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地给儒家文化记了一功。他深得其意地说: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儒学主义者。当然有人回忆,说这话是邓小平自己讲给施密特听的。其实这话是谁所说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们强调的都是现代化要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要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走出自己的路。
无数事例告诉我们,革命可以去搞,模式不能照搬,文化无法背离,道路只能探索。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最近,习近平同志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四)看看咱们的文化特色
中华文化,土生土长,无法离开。现代化的进程,都必定要走自己的路。问题是,中国道路何在?
过去很多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讲。春秋属原始社会,战国就成了奴隶社会,秦朝就是封建社会。其实,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早就指出,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有一个特殊道路,和西方不一样。他说,中国文化早熟,保留了血缘关系、氏族组织,一步跨入文明。中国文化与希腊相比,希腊是智者气象、哲人智慧,中国是贤人作风、道德为先。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血脉为缘、家国一体,人伦第一、道德至上,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历史路径,与西方就是不同。
为此,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全面深化改革研究班上强调:“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如果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
有学者指出,世界文化林林总总、此起彼伏。西方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都中断了,唯有中国文化历经无数冲击而连绵不断、一以贯之。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这样说:从世界人类文化学来看,中国文化一以贯之,是最典型的;西方文化断裂,是不典型的。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东方中心论”。
侯外庐也认为,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绵延不绝,中国的历史,恰如《尚书·尧典》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百姓好了,天下就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我们的祖先,把氏族组织转化为国家组织,是全面亲情。孔子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把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样才能天下太平。其实,中国文化讲忠孝仁义,都是家庭道德伦理的规矩,就是大到宇宙,也都看成家的体现,称之乾父坤母、天乾地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家庭,有家庭然后有人伦。可见,中国人以家为“天地之大义”、“以天地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家不但是人类生产繁衍的起点,也是中华文化的基石。
费孝通曾这样深入观察中国。他说中国是个乡土社会,在咱们中国,以家为中心,打一个比方,人际关系不是一根根捆绑起来的木柴,而是一块石头投到水上而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有一个离不开的圆心,讲究亲疏、等级、秩序,讲究人缘、人伦、人情。中国人身在其中,谁都无法摆脱。比较起来,绑起来的木柴,是一种类似西方的契约法律关系;而波纹之间,则是一种东方的伦理人情关系。同是社会关系,一种靠法律强行约束,一种靠伦理自发维系。
总之,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东西,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再如阴阳之道、会通精神、中庸思想、和合理念,皆一脉相通,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深层精神,是谓国魂。这国魂,不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渗透于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打上深刻烙印,决定着中国的发展道路。
四、历史的结论
综上所述,凡咱们有而别人没有的,皆可称之文化特色,凡咱们走而别人没走的,皆可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中华文化的价值特色所决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指出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根据之所在,我们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王 珊
View 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from the Point of Chinese Culture Value
LIU Lu-hui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Jinan,Shandong,250002)
Culture is pass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It does not come easy and is of certain value.The Chinese culture was born locally and lasted for a long time,with distinct features.The path selection of a country depends on its historical inheritance,cultural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y.It is historically proved thatwe could not copy other developmentmodels or deviate from our culture.We must explore our own path.This is whatwe call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ath confidence.
cultural value;Chinese culture;path selection
G02
A
1002-0519(2014)05-0069-06
2014-08-25
刘鲁会(1955-),男,山东临沂人,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主要分管中华文化学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