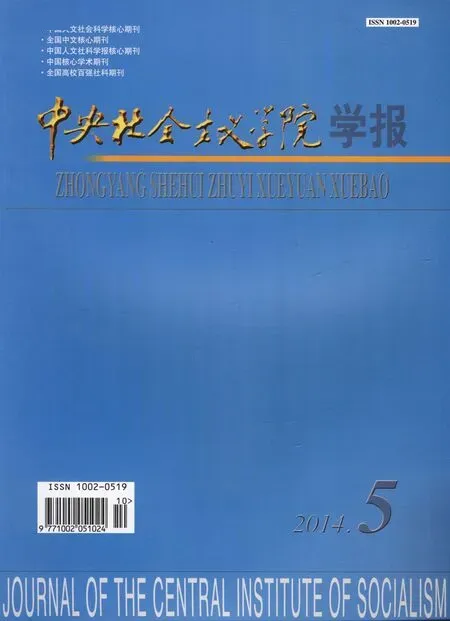论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组织优势
傅小随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34)
·统战理论与实践·
论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组织优势
傅小随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34)
目前,社会治理体系尚未运用统战系统的组织优势,也未准确界定其功能定位,使其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这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大缺陷,亟须予以完善。在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背景下,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正在成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平台以及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协调的新途径。其完整的工作链条、专业化的工作方法和历史传承的工作路径,决定其应该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据更加突出的特别位置。
统战系统;社会治理;组织优势
社会治理是党委和政府重要的基础职能之一,履职的主体通常主要由两大组织系统构成,一是党委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和政府的民政、社会保障、就业和教科文卫事业部门组成的公共服务系统;一是党委政法委的综治、维稳等稳控机构和信访、公安、人口、出租房屋管理以及街道、社区等基层管理服务系统,二者构成一个双柱支撑式的社会治理核心组织系统。党政其他工作系统虽然也从各自方面发挥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但从专业分工的角度看并不适合归入社会治理专职性工作体系。然而,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中拥有特殊组织优势,又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与管理价值,并且其价值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增长。因此,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应当重新予以设置,以使其能够在这个体系的特殊部位更好地发挥特别作用。
一、统战系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特殊构成部分
统战系统没有被全面布局于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源于两个基本的思想认识迟滞。其一是整体上不重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部分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敌人”已经难以寻觅,全体人民都在同一个阵营,统一战线也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因此,只需要一两个小型部门做一做特殊群体的工作就可以了。其二是在实践中觉得统一战线工作既不能管项目、管投资,直接推动经济发展,又不能行使审批权、控制权或监督权,介入社会事业发展,对地方发展来讲几乎无足轻重,在社会治理中最多只能做一个配角,起一些辅助作用而已。应当说,这两种观点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却是对统战工作、社会治理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缺乏清醒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亟须予以调整。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不是可轻可重,甚至可有可无,不能在实践中将其边缘化。在党委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中,统战系统各部门虽然都不是从事资源管理和实际事务操作的硬权力部门,但是,统一战线是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条件使这一重要法宝的价值不仅没有减少,而是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更加凸显出来,较之过去具备更大的广泛性、多样性、包容性和社会性。统战工作已经“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1],领域和空间范围扩大,使命更加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部署中,整合阐述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问题,告诉我们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突发期,同时也是国家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处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环境中。被境外各种势力利用的某些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国家顺利发展和社会和谐造成严重干扰。而通过民族、宗教和特定人群的工作途径化解各种矛盾,为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则正是统战系统的职责和优长能力。忽视或轻视统战系统的这一优势,都会给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造成损害。
其次,社会治理迫切需要以统一战线为重要支点来扩大和支撑一个新格局,拓宽视野并加大纵深,补充社会治理的政治属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在这方面,“统一战线与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内在关联”[2]。
这是因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单纯政府治理或以政府治理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正在逐渐失灵。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提供一切公共服务、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即便是有限地、局部性扩大治理主体范围并套用行政指令方式进行社会治理,也已经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新的社会局面。突出的表现便是对于传统体制内及其扩展部分不能直接触及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政府部门即使经常特意到他们中去调研、听取意见和诉求,听取他们在人大、政协会议上非常正式地用提案、议案提出建议,往往也难以得到更多更真实准确的信息,特别是批评性、诉求性的意见,难以取得他们更多对社会治理的参与配合。这是因为缺乏如统战工作这样专业性协商机制的支持,缺乏长期密切接触、建立信任、细致入微的沟通和在多种形式的共同活动中达到相互了解和理解的程度,从而让他们畅开心扉,如对待老朋友般讲出真心话。可见,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如果缺乏他们的积极参与,其意义将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在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良性互动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体制内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到的那部分社会领域也见到了一定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全国各地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思路仍然是试图以政府为圆心不断扩大体制内力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量调用退休公职人员加入社会管理发挥余热,安排现职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定点联系群众,这两种主要做法就是这种工作思路的最典型表现。这种做法具有确定工作成效,但并非可持续、常效化的社会治理路径,且作用半径仍然非常有限,尤其是对越来越壮大的新的社会阶层群体鞭长莫及,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新时代的力不从心。
“社会管理格局的改变对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有着深刻的影响,多元化社会群体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得以新的社会阶层为代表的新的社会群体正在成为统一战线的新生力量”[3]。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将统战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途径在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整体格局中加以部署,明确其针对广大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工作重点,突出其协商工作机制和方法的独特作用,在已有的统战部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各国家法团→政协工作的传统路线之外,再行发展新的从统战部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各国家法团→民间社会组织→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路线,并通过这个以发散型为突出特点,同时具备强大集聚能力的体系,将整个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囊括其中,广泛调动和积极引导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生力军,我们的社会治理才能够在最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形成良性循环新局面。看不到社会治理对统战系统的这种新需求和新趋势,是社会治理和统战工作的双重损失。所以,统战系统必然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组织优势
所谓组织优势,是指组织系统的属性、结构与成分、内外关系、运行机制等对履行特定职能拥有的更多和更大有利因素及其形成的潜在能力。统战系统对于社会治理的组织优势,可以从狭义和广义多个层次上进行考察。
统战工作主体意义上的统战系统是一个狭义概念,仅指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统战部和作为政府部门的各级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作为国家法团的各级侨联、工商联、知识界联谊会以及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等。广义的统战系统概念可以将统战工作主体与对象角色兼顾的各民主党派、黄埔同学会、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各宗教协会、各宗教院校等包括其中。最广义的统战系统概念则可以将统战工作的广泛对象全部包含在内,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香港、澳门和台湾“三胞”眷属、出国留学人员眷属、原工商业者、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海外华人华侨等。
这样的统战系统传统意义上都被视为且事实上一直是一个小众系统。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深刻变化,这个小众系统正在迅速扩展,其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在从参与者和协助配合者转变为重要构成部分,并显现出其特殊的组织优势。
优势之一是该系统的政治属性。统战系统是为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做的一个制度安排,其目标并非直接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而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集聚力量、创造环境,做好党外特定对象人的工作。社会治理实践中化解社会矛盾、调和阶层关系,广泛运用团结和协商的方式与海内外人士打交道,努力解决他们提出和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本身就是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一项工作,是统战系统发挥优势作用的最适合领域。社会治理既然存在政治性极强的这一个方面,当然就非常需要专门的工作系统。
优势之二是统战系统的涉及面和覆盖面的广泛性,系统结构的开放性及其强大吸纳能力。广义统战系统人员除党政部门公务员外,都具有身份的特殊性,其职业和社会角色不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某一个领域,而是全覆盖性的。同时,这个系统的结构并不封闭,在社会变革中更多的人走近或加入到这个系统中来,其在社会成员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态势。统战工作主体也不断因应这种变化,及时将他们纳入工作对象范畴。这种吸纳能力使统战系统触碰到更多新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现实社会问题,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行动能力。
优势之三是其自身具备社会治理较完整的工作链条。这个链条从党委最核心决策机构即各级党委的常委会,到它的工作部门、政府的业务管理部门,再到发挥杠杆作用的法定社会团体,还可以通过他们延伸到民间社会组织和特定行业,一直到达其他社会成员,并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信息和动力传递机制,加上统战工作主体成熟的协商协调工作机制,可以专业化地迅速进入并处置相应领域的社会关系和问题,起到有效的社会治理作用。这一点是其他部门所难以做到的。
优势之四是其成员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其在海内外和体制内外的贯通性、亲和力和粘结能力。工商联、侨联、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等在国内国外、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建立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同时也是体制内外关系的桥梁,其言论和行为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力。同时,统战部门细致而颇具历史传承关系的工作路径和方式方法以及长期形成的累积性成果,使整个系统既自成一体又四通八达,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阶级阶层的海内外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局面创造了良好基础,更能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有利的大氛围。
三、统战系统组织优势的实现路径
统战系统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不是要和其他构成部分履行相同的职能,而是要与它们错位运行并从两个途径体现出其特殊价值。
一是充当党的群众工作重要平台。社会治理主要就是做群众工作。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背景下,“群众”的内涵和成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阶级、阶层的绝对构成成分,因此,群众路线主要是一种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运作形式,并且两者具有极高的统一性。包括党外群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基本上都通过党所直接领导的途径纳入到统一的体制之中,群众在城市和在农村一样被以机关、学校、社队、工厂的编制、职籍、学籍和户籍制度固定在这套稳定的阶级、阶层架构中。这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可以由遍布于这个架构中的党的工作系统直接来运行,可以全覆盖并且非常有效。而现今时代,社会成员中的大部分已经由“单位人”、“厂企人”或“社队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成分复杂,流动性、变化性强,且境内外已经完全贯通。这给群众工作带来的变化就是,多数人已经脱离党委可直接面对和控制的直系体系,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再是某一个具体党组织固定的群众工作对象。原体制内的那一套群众工作机制已经不能覆盖他们,直接面对加适当控制的群众工作方法也已经难以奏效。这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适应这一新形势的群众工作新管道。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往往“非富即贵”,是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混合的群体。他们所掌握的财富特别是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正在不断扩大,所占国家智力资源的份量也日渐增长。统战工作就是要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充当他们智力和物力作用的保护者和引导者角色,也是他们参与国家治理意愿能力、建议诉求等的主要集纳渠道。但我们现行的工作体系还不能及时全面地将他们的活跃能力、建议诉求等通过通畅的递送途径反映出来,到达党委、政府的高层决策体系并被听取和采纳。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工作发挥统战系统的管道作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4]统战工作做的是特定群体的群众工作,是协商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期程序和重要基础,它不仅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统战工作就是要从党的政策引导、情感联络、思想沟通、路径指引、人员配置和提供服务等方面把这部分群众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党所指引的共同目标上来,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二是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特殊渠道。统战工作能够掌握动态、提前介入、耐心细致化解民族、宗教和涉外群众中的矛盾纠纷,防止事态蔓延,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民族、宗教和涉外事务既是政治性事务,也是社会性事务。在这里,统战系统的工作优势显著,价值不言而喻。
统战系统的组织优势还在于它可以在社会治理的两大实务操作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弥补它们在公共服务、综治维稳方面的某些弱项,对它们起到支持甚至基础作用。它与社工委系统的民政等公共服务部门可以相互配合,做好特殊人群、特定人士和特定社会组织的政治引导、观念培养、关系协调和特殊问题处理等专门性工作,通过调动如工商联、侨联这样的国家法团,发挥它们的杠杆作用,使特定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找到支撑者、粘合者和基础平台。同时,它与政法委系统的信访、维稳等专门任务部门和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器也正好错位履行使命。后者着重于事中特别是事后以行政和法律等硬手段处理各种矛盾,而统战工作则更着重于事前和事中运用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手段软化各种可能的和刚刚出现的矛盾,消解矛盾纠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社会和谐的冲击。这种“治未病”和“治初病”的特点使统战工作一般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从而忽视其地位,不容易看到它的价值。
四、重新设置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对统战系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不准或过于狭隘,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独特优势,难免造成党委和政府相关工作事倍功半的结果,甚至错失解决某些棘手经济社会问题的良机。例如,在社会和谐稳定问题上,对与民族、宗教和境外人员相关的一些敏感因素,就不能限于被动防控,而应该从基础工作做起,从正面更加主动地介入其中,扩大积极因素的阵线,压缩负面因素的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做好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商台胞、少数民族群众、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等工作方面,统战工作使命特殊,责任重大。做好上游的团结、引导和凝聚共识工作,就是从源头上消除危害性事件产生的土壤,为社工、政法系统减轻压力,创造更好条件。
同时,只有充分认识到统战工作作为执政党群众工作特殊管道的作用,才能减少和化解官民矛盾。对于由政府政策和管理方式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引起集体上访和带来不良社会影响的各种问题,要做好与居民组织、群众代表的民主协商,发挥各个群体中党派和人民团体人士、意见领袖和其他重要社会人士的积极作用,引导更多群众与政府部门良性互动,以增强政策的群众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政策一定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群众工作则要找准脉络并做在前面。在这方面,统战工作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党委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不能再视统战工作与自身无关。事实上,统战工作事关大局,无处不在,对此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正确理念。
首先,需要将党委的统战部门列为社会治理重要决策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战略制定、工作规划、项目安排中必须有统战部门参与其中,特别是涉及特定社会群体时,更要以统战部门为主,按照统战工作的规律性和原则要求,确定相应的工作方针和具体策略,以将统战工作的政治原则性全面贯彻进去。
其次,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综合治理中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和解决社会问题时,要将统战系统成熟运用的协商机制推广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去。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特别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用好协商民主方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再次,充分利用统战系统的平台优势和管道优势,把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等国家法团的枢纽作用更多释放出来。对统战工作对象及其辐射人群进行定向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通过他们将各类社会精英人士更多地组织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让他们在社会建设中充当公共服务、协调关系和智力支持等积极角色。
最后,在统战系统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智库机构,在为统战工作及其对象提供政策性咨询服务的同时,努力服务于党委和政府的社会治理事业。一方面,广泛搜集和整理统战工作对象社会群体的特殊诉求、批评意见和建议,成为他们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专业化、常规化途径,也充当他们群体情绪的一个正常出口;另一方面,智库机构也是党和政府的参谋,根据掌握的特定群体利益和权益诉求动态,群体关系状况信息和共同社会心理状况信息,从学理和现实多个维度进行科学分析,向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完善等提出可靠建议,以为社会治理发挥专门化作用。
[1]卢英,李崇英.浅论新时期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1):33.
[2]姚俭建.社会治理结构创新与统一战线功能定位[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8.
[3]袁春红.十八大之后的统一战线与社会管理创新[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67.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
责任编辑:王文京
On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U Xiao-sui
(Shenzhen Institute of Socialism,Shenzhen,Guangdong,518034)
At present,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United Fronthave notbeen utilized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United Front have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This is a major defect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needs to be improved.With continuous stratific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the targets and work scope of the United Frontwork are expanding,and the United Front becomes an important platform of the CPC’smass work and the new channel for coordinating social interests and social relations.Based on its complete chain of work,professional method of work and inheriting working paths,the United Front should b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and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United Front;social governance;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D613
A
1002-0519(2014)05-0049-05
2014-08-25
傅小随(1960-),男,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巡视员,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