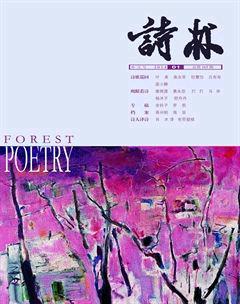从行走开始,又在哪里结束
霍俊明
蒋兴刚近期的小诗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的是“行走”在这个时代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在于我们在集体的城市化和现代性、全球化时代“行走”方式发生了转捩性的巨变,而且还在于“行走”时所目睹的风景甚或时代景观都几乎发生了了天翻地覆的“除根性”的改变。
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时代。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老旧的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是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而对于蒋兴刚这样一个江南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而言,其对个人精神性的地理以及行走方式的感受和体悟似乎要更深。对于“地方性知识”正在消失的时代而言,诗人再次用行走开始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时代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的诗歌可以在行走中开始,但是我们又该在哪里结束呢——“笑自己该去向何方/这条陌生的街/是这个离家千里的城市/唯一的赐予”(《夜宿浑南》)
由此,诗人如果希望将“行走”的诗歌只是局限在旅行观光的地图册式的介绍和浮光掠影的抒情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抱有对传统和当代融合视野下“行走”诗学的热望,那么我们就必然要在历史和当下交叉的精神谱系中来考察这类诗歌写作的难度、新变与困境。离开北京在深圳等地暂居的孙文波刚刚完成了1600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对于孙文波这样有着些明确的写作目的甚至“野心”的诗人而言,“新山水诗”显然印证了诗人与地理在新现实语境下的尴尬与分裂甚至拨动。而蒋兴刚近期的诗歌则大体为小诗,句式和形制都极其精简。这似乎对应了飞速前进时代的诗歌写作状态,而较为可贵的是蒋兴刚的这些关乎行走的诗歌放慢了速度——写作的速度和内心的速度——“我们需要/在旅途中停一停/我们需要在顿号/逗号或分号/这些房子里/歇一歇/使记忆牢固/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旅馆”(《旅店》)。这些节制的句子与内敛的情感基调之间正好达成了平衡。而在深层精神动因上考量,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将这些地方景观放置在秋天的时间背景上的原因了。当然也需要注意的是短诗的写作难度是很高的。比如断句太过频繁的话就会显得很琐碎,这样会破坏诗歌的节奏、流畅感和整体肌质。希望蒋兴刚在今后写类似的短诗时能够注意。
在蒋兴刚近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他大体的行走路线——东北三省(沈阳故宫、浑南新区)、锡林郭勒草原、临安、西天目山、塘栖古镇、开化。这些混杂着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地理景观激发的是怎样的情怀和想象呢?蒋兴刚在这些地方景观中以行走的方式保持了长久的疑问与自省。值得注意的是蒋兴刚在诗歌中抒情主体的位置放得很低。这样的姿势很利于情感的开放性抒发,而不至于在过度的主体抒情中放宽了情感的限度。这些诗歌实际上是打开向诗人内心深处的。他一直在追问自己在一次次行走途中所处的位置。面对着崭新的城市、工地,诗人是迟疑的、诘问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现实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清醒是必然要以孤独为代价的——“探究/浑河的秘密/就像我/风尘仆仆/孤独得/如同熄了灯的/马路//翻动/夜的书卷/树林/落下一场雨/我的/灵魂是一道/水迹”。在陌生而又同一化的城市、街道、建筑、车辆面前,蒋兴刚将视线投入到那些自然之物以及带有文化遗迹的细小事物之上。因为这些事物可能会比新事物更长久,它们也因为带有历史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基因而带来了诗人现代性的不尽乡愁情结——“凤仙结子”、“老桐露凉”、“丝瓜爬满屋顶”、“野菊蠢蠢欲动”。
是的,行走的诗学正在诞生!精神地理图景正在消弭!问题是,我们在行走中开始,又该在哪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