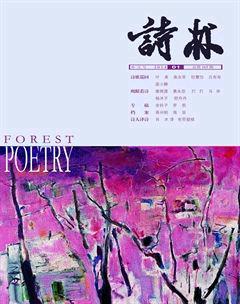谷雨:大地之灯(组诗)
韩簌簌
棉花谣
这是一片 向云彩借来的坡头地
一年两次受孕,它每一寸都是熟门熟路的母亲
春雨刚过,发胀的棉子们就开始心神不宁:
她们有解开皮肉的禁忌,又想
急着去慰藉 枯等一冬的内心
——母亲何尝不知她们这小心思
只是乍暖还寒,是涉世未深的孩子就不能放宽心:
“要三两个一组结伴,你们得乖啊
再盖一床保暖又挡风雨的太空被”
这些不知深浅 又藏不住的丫头啊
疯疯癫癫挤扁了脑袋 却挤不掉好奇心——
才按下这边的手,那边又伸出小脚
“年老的母亲快撵不上你们咧。”
噌噌噌,满头的蝴蝶结还应接不暇呢
红红白白的绢花 就插得满头满身
七月半,敬神仙。看——
再也藏不住怀里的子嗣了吧
白胖的姑娘小子 扑哧一声跳上木托盘
炸开了木头心
真是奇怪:
尖尖的小乳房从何时暗藏于身?
甜甜的桃子何时开始蜜汁满存?
羞羞羞——
原来啊,有心的棉花姑娘
早就学着 偷偷做一名小母亲
槐:一曲纯白的颂歌
君子求美,示人以馨香
你却用一根根箭羽,做了你香囊的佩剑
他们,是你花香里的骨头
他们是你,白玉城堡的忠诚守护者
而事实是
你用白玉的风铃,配以青铜的铙钹
执意去闹醒 梦中的小兽
春天里婉约的槐,是在用香气引领
一曲纯白的颂歌
她不妖冶,不色诱。就那么
纯纯地 白着。
作为春天的未亡人,我自知罪孽深重。
你竟不知:你这无辜,其实才是
最致命的诱惑
谷子外传
捏不住你,就寄养在掌心吧
这些性急的小不点,还没等找准位子
就吱溜一下钻进土里
——竟然不领情,面对这松绑的宽宥之心?
春天的美人就是矫情啊
一朵云一甩脸子,就是一场连阴雨
才多久啊,这帮坏小子
已长成莫须有的头,和形而上的四肢
你看他们,正歪着毛茸茸的小耳朵
扭捏在春风里
不行,我定要揪一下你那尖尖的耳伢子!
我还想问呢:
这么多天,你们都去了哪里?
望你,在北方的大平原上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刻,谁来敲门。
正午的三叶草眼神含蓄,你握不准
柳树的调子,该是抑还是扬。
开发区的厂房刚进入平原空旷的胃
谁在此刻,受到了谁暗中的指引?
北方的布谷叫醒了北。
在北方的大平原上,望你!
那时,你还在水边,捣衣的程序复杂而又艰辛
北方,是在沾着苦棘粉的雪线中醒来的
据说,雪山白发苍苍的面庞似乎提前了悲伤。
人间的更年期正在后退。事实却是这样:
你是一座活火山。她,作为当事人
恰好卡在,重度沦陷区
老槐树:一条站着的河流
你有没有见过,一条站着的河流
曾以一棵槐树的姿态
带着乡音,带着树根下那一捧黄土
带着一个地区 漫漶的流民史
顺着一条大河的走向
一路向东?
在入海口
在每一个黄河人的身后
都站着这样一株古槐:
刻着旧姓氏,刻着祖宗牌位的槐
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气
从此落地生根。所以在黄河口
赤碱蓬们才如此鲜丽
苇荻们才如此浩瀚
此去六百载,风霜两相隔
老槐树啊老槐树:
那在你的帽檐下迈出第一步的,
哪一个才是我的先人?
在根系遍布的华北大地上
哪一条沟垄边 埋着他们
还没有被验明的 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