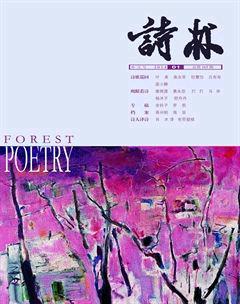行走的记忆(组诗)
文乾义
戛纳记忆
一片拐个大弯的白沙滩上
身体们闪耀的光,让我的眼睛
准备不足。背后一些餐馆、
咖啡厅、酒吧和名牌专卖店
没有人影。恍惚我坐在
一头连接着平静,另一头连接着
无法平静的长椅中间。棕榈树
沿海岸线高高竖起,叶子像翅膀
在头上无声展开。这时刻
我认为最适合闭目,和冥想。
香榭里舍大街黄昏
人们朝热闹的地方陆续走去。
迎面过来一群少女。她们一边闲逛,
一边吃薯条。人群里,几个小男孩儿
鱼一般游向年轻情侣。他们
推销着紫罗兰花,认真而调皮。
此刻,凯旋门正被暗红色的暮霭
缓慢覆盖。它就在眼前然而
又很遥远。它的那些石头可以仰视,
但它似乎并不高大——
用血换来的东西都不会高过地面。
在古罗马角斗场
下午光线强烈。一个不完整的
骷髅,被分割成两个世界。
进入里面的面孔躲闪于阴阳之间。
呼吸中觉出些腥味儿。有人拍照,
能听清附近快门声。有人
在本子上记东西。也有个别人
刀口疼似的把一侧嘴角尽量往上提。
人们不说话也不回头。停停走走。
出来时没有一个带着笑容。
慕尼黑南部那些村庄
慕尼黑南部那些村庄似乎
都不大。十几户或者几十户。
中午,一辆白色小汽车
从高速公路下来驶入乡间,
不紧不慢。它的影子有时在
阳光下耀眼似的一闪。
一家车库的门敞着。里面
是空着的,周围没有人。
那辆有时一闪的小汽车
是不是它的主人?敞开的门,
安静而放松,让人产生
一种源自原始的渴望——
后来,它是否已安静地关上
或者依旧放松地敞开?
那些村庄、森林、绿地,
还有围栏中的牛群、马群
和羊群,从车窗经过。
后来我曾模糊而用力地想:
那些村庄是在森林
和绿地中间,还是森林
和绿地在那些村庄中间?
海德公园
在一条长椅上坐下。
站起身来时,我以为
我是从另一条长椅。
躺在带斜坡的草地上,
我做不到像不远处
那个英俊小伙子那样
躺着还那么绅士。
临街栅栏上挂些油画。
我来回一遍遍地看。
旁边高个姑娘
可能是这些画的作者。
她并不像艺术家。
她递给我的那一点点
笑容,有些吝啬,
但不乏风度。那些画,
后来回忆起时,似乎
其中有雕塑、草坪、
一块不大的水面
和几棵把影子投到
坡底很远处的树。
我好像记得但已模糊。
来自天堂的声音
佛罗伦萨的夏天,除了
皮革味儿,就是皮革味儿的闷热。
在但丁故居,就想到他的爱与恨
都居住在这个城市。深夜里
但丁去了天堂。他的《天堂》
最后十三篇不见了,或者他
本没有写完。四个月过后他对
儿子说:“我已过上真正的生活,
但不是你们那样的生活。”
儿子问:“《天堂》可写完了?”
“当然。”他站起身摸摸房间
一块墙壁。“在这儿。”
最后那十三篇找到了——显然,
听上去这不够真实但这是真的。
而真的东西谁都可能不信。
因斯布鲁克
因斯布鲁克最迷人的东西
不是抬头仰视的
青色高山,不是硫磺味儿的溪流,
也不是玻璃罩内闪烁的水晶,
而是寂静。
当来自深夜的雪,月光般
铺在老街石板上,第一行脚印
还没来得及到达之前,那青色
高山、硫磺味儿、溪流和水晶,
这时都毫无理由地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寂静。
艾菲尔铁塔
那一天阴雨里,它的塔尖伸入很黑
很重的云层。密布于塔底的铁色
像英勇的男性一样坚定。仿佛巴黎
将被压垮,此刻唯有它
支撑住全部天空。我曾经认真地记过
一些感受,回来后想写点儿什么。
读过那本不厚的《艾菲尔铁塔》之后,
我再也没动过想写写它的念头。
海上威尼斯
每一分钟的威尼斯都摇晃不停。
从脚底反馈上来的波动
就是这样——它睡着它同时醒着。
在圣马可广场上喂一会儿
鸽子,就被头顶的太阳把我逼进
长廊阴影里。而孩子们不。
吃饱的一群刚飞走又来一群。
孩子们累了,困倦了。他们索性
坐在地上睡着,坚持着……
我跟紧导游,看过海面上的石头,
再看海面之下的森林。没错,
是森林——木桩坚硬如铁,撑开
一座城市咸鱼味儿的梦境。
海水黑暗下来。想起一部小说里
赞美某个女人的皮肤时说:
像威尼斯夜空的月亮一样白净。
而那几天把我累坏了。整天忙于
出汗和洗澡。不仅顾不上
看一眼海面上空月亮的皮肤,
而且沉睡得竟没有机会做梦。
柏林墙
星期天上午,柏林雨后
有些冷清。环卫工在街上远处
打扫落叶。留作纪念的一段
柏林墙附近,几个地摊儿
摆着各式墙皮。我买个三角形的。
粉色与灰色相间,三十马克。
工艺不怎么好,看上去
比较匆忙。不过,上面的日戳
还算清晰:9.11.1989。
一旁有人用汉语说,可能是假的。
不管真假,我想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柏林墙在这个世界上
被拆掉了这是真的,这就值了。
当很多墙已经或正在竖起。
金色大厅这个木制讲台
经过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一段不算短的红砖色长廊,
实际上是经过一个隐喻。
进入二层金色大厅,
我不得不把声音压低,
把脚步放轻。没有别的,
一只麦克放在讲台上。
几个同事几乎推着我,
让我到上面留个影。而我
怀里并没有揣着另一颗心。
身体上也没有翅膀。
在一些图片上,我见过
有人走上这个讲台领奖
并发表演说。这对我,
即便是做一万个白日梦
也从未敢想——这儿
不是幻想的场所,或者说
这儿是幻想完成的地方。
一座高峰在一群高峰之上
耸立。鹰在云层上飞翔。
塞纳河
塞纳河是黝黑的。它不清澈。
它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鱼群
早已不选择在这里生活。
它无法被看透。它是雕塑、诗歌、
绘画和垃圾的颜色。另有一些
在恶之花里至今无法辨认——
它从法国北部高地上一路流过来。
是有意无意?经过巴黎时
它打下一个疼痛而黝黑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