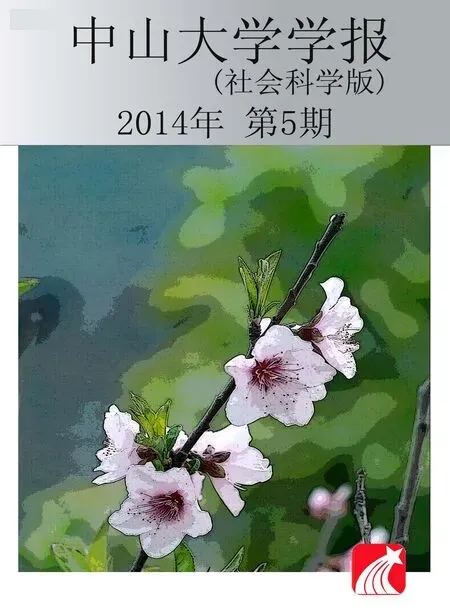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山大学的实践*
黄 悦
一、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形成及其学术背景(1888年—1920年初)
许崇清是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的第五代后人,出生于1888年1月20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八)。他的父亲许炳暐由户部郎中转调山东济南帮办治河工程,当时黄河水质清澈,为历年少见,因此将新生儿取名为“清”以纪念这个祥兆①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下称“中大版”。《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其后许炳暐升任江西盐运使,丁母忧服丧于广州,服满复官于江西洋务局办差②梁鼎芬:《番禺县续志》(宣统)卷17“职官”,民国二十年出版刻本。《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许崇清幼年时期随父母生活,及至1894年许炳暐病故,许崇清返回广州高第街随母亲朱氏居住。在许氏族学跟随薛子敬、姚韵笙两位先生学习旧学和新学,因为天资聪慧常获得先生的称赞③《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1900年许崇清应童子试,“初试发榜,竟得复选,并能终场,余母之心甚慰”④《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同年许崇清随兄长许崇灏前往湖北武昌,寄居在姑父冯子材家中,入读博文书院,此后毕业于博文中学校。博文书院是教会学校,许崇清在此接触到算术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基督教教育和道德观念。博文书院地理上邻近两湖书院,许崇清得以与宋教仁、黄兴等结交往还,从而受到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许崇清:《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先生》,《许崇清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页;下称“广东版”。山军、庆山:《现代中国教育界的卓越前驱许崇清》,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1904年,许崇灏和许崇清到南京投靠叔父许苓西,1905年许崇清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1,76,1页。 《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
许崇清到达日本后,入读第七高等学校③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1,76,1页。 《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就读期间,许崇清学习成绩优秀,因在数学课上采用有别于老师教导的方法解题而受到赞赏,有一次考试得了102分。某次学年终结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但日本规定第一名不能是外国人,只好将他降为第二名。当是时,日本正处于欧美科学文化大量翻译传入的时期,许崇清在其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吸收的西方文化占有压倒性地位,当论及国人不满向来的生活和思想,寻求新出发点时,他认为:“我们寻求创造的出发点的地方,不在国故,却在欧洲民族的生活和学理。”*许崇清:《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76页。
同时,日本也是许多中国先进思想学人和革命者聚集活动的地方,许崇清在这个大环境中受着影响,他经常阅读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民报》,导致有中国同学警告他:“看《民报》回国是要杀头的。”*张荣芳:《许崇清校长的孙中山情怀》,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98页。庄向阳:《矢志教育堪称“范式人师”》,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214页,原载《晶报》2008年12月2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日本正是其招收成员和策动革命的基地。1911年,许崇清由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为机关刊物《民报》撰写文章,向留学生和国内青年传播新知识和革命信息*许崇清:《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先生》,《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8页。李竟先、王祥:《风雨翰墨——粤盟先贤及其书法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第73—74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许崇清停止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12年重回日本继续求学⑦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1,76,1页。 《许崇灏回忆录》,未刊稿。。许崇清在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攻读教育学和哲学;191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研究题目为“修身教授”(可理解为道德教育)*许崇清:《我与杜威〈哲学之改造〉》,《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3页。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1页。 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VIII 页。。
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是许崇清走上学术道路的起点,他在自述文章《关于我的学术思想》中提到:“我在大学时,是由哲学而社会学,最后才走上教育学这条路来的。我搞哲学时,搞的是新康德哲学;我搞社会学时,搞的是孔德社会学;我搞教育学时,搞的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总之,那一学科的主讲教授是那一学派的,我也跟着搞那一学派的东西。”在对各个学派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之后,许崇清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和相互矛盾之处,开始寻求一个能够令他接受和信服的体系。他从康德哲学转向杜威实用主义是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一步。他自述道:“实用主义哲学——宁说是实用主义思想法——虽免不了只知适用而没根据,只知通融而没归宿底诽难,但在阐发思想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并实行改造了哲学一点,确比从来只埋头于么先天,么绝对,以为这就可以绳墨一切底那些哲学,高出一等。这是我当时底见解,是我从康德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底一个缘因。”*许崇清:《我与杜威〈哲学之改造〉》,《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3页。后来,许崇清又发现杜威的哲学“并不彻底”。他说:“我走的门路越多,那些学派的对立和矛盾,纷纭错杂在我的脑海里就越加使得我无从收拾。于是我想独自创立一个新体系。我几乎走遍了唯心论各种形态的哲学歧路,结局是摸上了唯物论的最高发展形态——辩证唯物论的道路。从那时起(1919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就成了我的理想。”*许崇清:《关于我的学术思想》,《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9页。许崇清走上辩证唯物论的道路是与政治无关的,在1918年前后,这个学说从欧洲传入日本,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许崇清不仅精通日语,而且掌握了英语和德语,他直接阅读欧洲学者的著作。他说:“我曾把辩证唯物论只当作哲学各种学派中的一个学派,只不过是在逻辑的领域内来玩味它的分析的精到和组织的严密。”*许崇清:《关于我的学术思想》,《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0页。
在大学和研究院期间,他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许崇清文集》中的多篇文章都是撰写于此时期的。其内容涉及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多发表在当时留日学生组织丙辰学社主办的《学艺》杂志上。有学者认为,许崇清在此时期发表的文章,“侧重于概念的分析”*黄凤漳:《许崇清教育思想简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许崇清教育论文集》,1981年,第365,379页。,这可能与他还未回国参加教育工作有关。但在他与蔡元培争论宗教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时,他已经能够在理论辩论的基础上,运用日耳曼民族的实际事例加以证明了。
1917年1月12—13日的《中华新报》连载了蔡元培在信仰自由会上的演说,谈论孔子、宗教、国家三者的关系。许崇清不同意他的观点,撰文反驳,分析了宗教和信仰的不同之处,认为“孔子之教,本与今之宗教(Religion)有别”,“孔子平天下大一统之思想,即我汉族之政治理想”,“其所谓大同,所谓大一统,既为我汉族之理想,则此大一统之理想,当然为汉族中心之世界一统主义也”。并且说明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故曰国与教二者界限不能相废而相赞助,是以有定其名而并存之以示其关系之要也。”最后运用图表演示蔡元培讲话中的自我矛盾之处*许崇清:《批判蔡孑民在信仰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孔教问题之意见》,《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7—15页。。蔡元培读了许崇清的文章之后,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订正并撰文进行答辩,发表在《新青年》上作为回应。许崇清再次与其争论,指出认识论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均不相同,蔡元培“所举之哲学问题,都非今日之哲学问题。亦非现今科学所能解决之问题,实则二千年前古代希腊哲学之问题耳”;并通过引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明现今自然科学的发展“实已深入玄奥之境”,哲学问题也“今与夕异”*许崇清:《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16—19页。。许崇清此文首次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见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93页,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3期。。蔡元培于1917年又在出席北京神州学会时发表演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许崇清亦不同意其观点,再次撰文《美之普遍性与静观性——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说者之二大谬误》予以反驳*《许崇清文集》中大版,第24—25页,原载《学艺》1920年第1卷第3号。。许崇清与蔡元培的三次争论,体现他对学术的执着以及对权威的无畏,这两种品格在此后多次闪耀,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历程。
许崇清的教育哲学理念在他学成回国初期已经初步形成,其标志是他在关于“学校与社会”和“教师与社会”的论述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的所在即教育的所在,教育和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他从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认为学校教育必须置于“社会的刺激之中”。他反对学校与社会脱离,反对将教师工作视为“个体行为”的观点,都是源于其唯物主义教育哲学*许崇清:《学校之社会化与社会之道德化》、《教师与社会》,《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55—160、166—168页。。
二、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定型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实践(1920年—1949年)
许崇清的教育哲学理念形成后,在他的教育工作实践中始终以此为指导。他于1930年在向广东省中学教员的一次讲演中,强调哲学与教育学的密切关系时指出:“哲学可以说是教育的一般的原理,教育可以说是哲学的具体的实行。”*许崇清:《教育哲学是什么》,《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92页。他关于教育本质的定义,被学者认为是他教育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⑨黄凤漳:《许崇清教育思想简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许崇清教育论文集》,1981年,第365,379页。。
关于教育的本质,从哲学范畴思考,不仅唯心论和唯物论有分歧,就是唯物论者之中也各有不同论点。许崇清认为,教育既不属于客观存在,也不是主观意识,而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一个形态。他指出:“人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人类自己底本性也随着实践的活动而变化,教育学的出发点就在于此。”他又认为:“教育是人底实践的一个形态”,“教育是教人自己去学习,自己从实践中作育自己,人是他自己底实践的活动底结果。”*许崇清:《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教育研究》第110期,1948年9月。许崇清有关教育本质的明确科学表述,初见于1941年发表于抗战时期在韶关出版的《教育新时代》第2卷第1期题为《所谓“社会底教育作用”其实是人类底社会的实践活动底自己发展自己学习》。抗战胜利后,他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人底本质与教育》(1946年)和《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1948年),对此问题作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论述,自此正式确立了“一家之言”。
他从自己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出发,坚持教育过程就是人在实践中改造环境,而环境又改造了人的理念。他在民国时期的教育工作中的许多举措,都与这个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第一次执掌中山大学前后
有学者认为:“许崇清的教育社会理论和教育革命理论来源于他任职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时组织参与的教育活动,而高校建设理论则是他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治校方略的结晶。”*胡杨:《试论民国时期许崇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高教探索》2010年第5期。但笔者认为,许崇清在日本留学时期已对欧美日各国的高等教育模式有所留意和研究。1920年5月在《学艺》上发表文章《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此时距1931年许崇清首次担任中山大学校长还有十年之遥。在此文中,他深入讨论了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大学发展沿革、学位制度、学院职能,指出:“我国大学之当取法德国,以专门科学之教授及学术之基础研究为本务。”并结合我国实际,认为“要在现在的中国设立完全的综合大学,实属难事”,若组织单科大学则须有完善的理科教室*许崇清:《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46—154页。。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迅速,许崇清可能亦未曾料到,此文发表后短短几年间,他就参与筹备华南第一所综合大学,将心目中的“难事”变成现实。1924年,孙中山先生筹备成立国立广东大学,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国立高等师范学院教授的许崇清兼任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是由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而成,含有预科和文、理、法、农、工五科的课程设置,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筹备过程中,许崇清为文科委员会成员,具体负责指导文科的课程设置、教师聘任、学生招收等工作*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2—10页。张荣芳:《许崇清校长的孙中山情怀》,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03页。。11月11日,广东大学举行了成立典礼,孙中山亲临会场写下校训,许崇清亦发表了演说*梁山、许军:《许崇清在中山大学》,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19页。。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将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许崇清再次受邀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此次更名,不仅仅是学校名称的变动,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和教育工作者对高等教育理念变化发展的一种体现和实际行动。筹备委员会制定新的中山大学规程,对其办学目的作了新的规定,要把三民主义的理论散播在学校工作的每一个方面,并强调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因此中山大学的行政组织和学科设置也作出了变动*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第40—41页。。在1927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许崇清发表演说,肯定中大改革后的新面貌,“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团体,发明新事物”,并殷切希望“改组后的中大,使广东成为一个革命文化的策源地”*许崇清:《在革命文化的旅程前进》,《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潘庆涛笔记,原载《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印行。。
1921年,许崇清在《产业革命与新教育》一文中提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总不外乎教育与产业的关系”,指出教育必须与国民经济相结合,中华民族的命运才不会“委诸天演”*许崇清:《产业革命与新教育》,《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62—164页。。但此时许崇清的教育观念仍偏向于理论化,较少涉及实际操作层面。经过5年在教育领域的学习和实践(包括开展工人识字运动,在国立高等师范学院任教,创办广东大学,筹备中山大学,在青年讲习班讲授《教育与革命》等),并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启发,他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新教育思潮批判》一文中,他批评了“一般教育者都想将教育与政治分离了,脱出它的影响范围以外,以为如是就可以维护教育使得遂其发展”。通过介绍、梳理和分析当时社会思潮,他提出“教育的根本原理罕有这形式及实质两方面,形式的原理注重个人的活动的方面,实质的原理注重国家的社会的方面”,因此,“教育断不是与国家社会绝无交涉的事”*许崇清:《新教育思潮批判》,《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69—178页。。1926年,许崇清响应推行党化教育的潮流,向国民政府提出《教育方针草案》,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现状,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只有摆脱旧制度,“超脱这种制约向前跃进,为今后发展的唯一可能”;他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定下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及发展实业的计划,即是我们今后的跃进所当遵由的一条线路”,“而且今后的教育政策,所指导的方向,亦只有与这个革命的一般政策所进取的方向相一致,然后所设施的教育,才能尽致发挥他固有的价值”,“学校教育当与社会生活的活动事务相结合,不独是材料的内容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络,并其方法的内容亦须与社会生活相一致”。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14条具体的教育纲领,涵括了中国教育的各个方面,为此后的教育工作勾勒出一个可实现的蓝图*许崇清:《教育方针草案》,《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412—418页。。有学者认为,许崇清提出的教育方针草案,是“以民生主义为出发点,以产业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次作为党化教育方针”,在理论和视野上都较为先进广阔。但它始终不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采纳使用,是由于方针中隐藏的“左倾理论因素”的原因*曹天忠:《辛亥革命与国民教育》,《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右派掌握了国民政府的主导权,许崇清虽在政治上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但他偏向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的中国必然不会得到实现。他在文章中写道:“1927年革命失败后,我认为我的教育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才能够实现,现在是无所作为的,于是便致力于教育理论的研究,着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一个新体系。”*许崇清:《关于我的学术思想》,《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10—11页。虽然有理想不得实现之憾,但许崇清依旧努力践行他在《教育方针草案》中提出的纲领,进行收回岭南大学主导权,整理广东全省省立学校,取缔私立学校,进行农村学校改造等实践。1930年,中山大学校长更替频繁,9月戴季陶辞任,朱家骅副校长升任校长,12月朱家骅奉命接掌中央大学,由金曾澄出任中大校长。因为金的派别背景,中大学生发起了长达两月的“拒金迎戴”活动,在校内戒严、罢课,金曾澄不得就职,校长职位虚悬*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第104—112,113页。。最后,戴季陶授意请派许崇清出任校长,事件才得以平息*《广东中山大学学潮》,国民政府档案2—11.01.4/1,台湾国史馆藏。。1931年6月,许崇清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事后许崇清曾自言被利用了做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缓冲人物*许崇清在1952年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自我检查”草稿,广东省档案馆,档号D00218—00011。。但执掌中山大学,许崇清得以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他在6月15日的就职典礼上的发言阐述了他对中山大学的期望:“我们要把它造成一个民主的、以学术研究做中心的,师生的共同团体,发挥先大总理的遗教,向世界的文化,迎头赶上去。”*《中大校长许崇清昨日就职盛况》,《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6月17日。9月,他召开了中山大学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学校的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学院制⑩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第104—112,113页。。学校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将文科改为文学院、法科改为法学院、理科改为理工学院、农科改为农学院、医科改为医学院”*易汉文:《三次执掌中大的许崇清校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10,111页,原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11月18日。。为了适应国内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于文学院增设社会学系,于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张荣芳:《许崇清校长的孙中山情怀》,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04页。。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3日上午,中山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在大礼堂召开反日救国运动大会,组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选举许崇清等21人为执委会委员。大会于9月24日组织中大学生游行请愿,并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9月26日上午,全市学生在中大操场召开抗日运动大会,会后到市区示威游行,中山大学成为广州学界抗日活动的中心。9月28日,执委会发出《告全世界学术机关电》,呼吁学界联合抗日*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176页。。许崇清对大学师生抗日救亡活动的支持和参与,为国民政府所不容,于1932年被免去中大校长职务④易汉文:《三次执掌中大的许崇清校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10,111页,原载《中山大学校报》2003年11月18日。。1933年,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主张“尊崇孔孟”,重刊孝经及注解,并在他任校长的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人手一编,朝夕探讨,以涵养其德性,濬发其孝思”*陈济棠:《重刊孝经注解序》,《广东文征续编》第3册,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第298—299页。,还准备进一步在广东中小学推行,欲将《孝经新诂》当作教科书。当时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处将此事转交广东省政府办理,由许崇清和金曾澄负责审查。许崇清负责起草审查意见书,他通过陈述日本“修身教授”模式的特殊之处及中国不能仿效的原因,并运用心理学、进化论、生物学等科学知识结合教育学,论证“道德之范围实包括人人相与间一切行为”,需要通过“学校的社会化”和“社会三民主义化”,才能实现民族道德的光辉和充实,并不是读经可以达到的。审查意见书经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通过,陈济棠推行读经的步伐遭到阻碍。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1期刊登了审查意见书的全文,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陈闻报大怒,立即召开西南政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免去我的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此后许崇清被迫离开广东。广州市中小学一律采用《孝经新诂》作为读经教科书,及至1936年许崇清重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才“重新扭转复古读经的逆流”*许崇清:《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陈济棠提倡读经和我审查〈孝经新诂〉经过》,《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461—466、13—17页。。
(二)第二次执掌中山大学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广州沦陷,许崇清撤退到粤北。国共两党合作形成,但对抗战持不同态度。他自述道:“按照既往的事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当权者是不会给我独当一面的职位的。”1939年春,陈济棠的亲信黄麟书接任许崇清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位*许崇清:《我的经历》,《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6页。。当是时,中山大学已迁到云南澄江,邹鲁任校长,由校长室秘书萧冠英主持校务。1939年度第二学期,师范学院院长崔载阳的免职引发了学生的不满。1940年春,部分教授和学生发动“倒萧护校活动”,各学院学生罢课,形成全校性的学潮,萧冠英被迫辞职。在重庆患病的邹鲁校长向教育部提交了4次辞呈,中山大学校长一职虚悬。在此情况下,1940年4月,教育部任命许崇清代理中山大学校长⑧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176页。。他上任的第一件要务,就是因应当时抗战的形势变化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将中大从云南澄江迁至粤北坪石。此举得到教育部与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的支持,得到共约70万元的搬迁费用,聘任重要人员组织迁校委员会和新校址筹备处。经过“多方策划,辛苦经营”,“满足了学校师生员工所企盼,实现了广东文化教育界的愿望”*许崇清:《我的经历》,《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6页。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176—178页。。1940年9月,中大召开迁至坪石后的第一次教务会议,公布1940年度校历和作息时间,学校的教务活动和学生生活踏入正轨*易汉文:《中山大学编年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迁校初期,许崇清本打算“与桂林遥相呼应”,“把中大做成文化运动的一个基地”,但因为任期短暂和客观条件所限,未能有所作为*许崇清:《我的经历》,《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7页。。虽然如此,他在任内仍做了不少实事,奠定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学术自由、进步开明的基调:第一,聘请经济学家王亚南、哲学家李达和石兆棠、法学家梅龚彬、戏剧家洪深等进步教授;第二,兼任研究院院长,在研究院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聘请前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前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担任研究院导师;第三,主持举行多次学术讲演会,如朱谦之教授讲演《天德王之谜》、洪深教授讲演《抗战期间的地方戏》、张云教授(教务长)讲演《关于今年9月21日之日蚀》;第四,提议由中山大学牵头,搜罗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手泽以及相关中外人士的著述和研究成果,建立中山文献馆,以便后学参考研究,继续发扬孙中山先生的至理*胡杨:《试论民国时期许崇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高教探索》2010年第5期。易汉文:《中山大学编年史1924—2004》,第37页。许崇清:《新年头的一个贡献——中山文献馆的设置》,《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507—508页。。“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对文化教育界的控制,“朱派分子”借口许崇清代理校长聘请了李达、王亚南等进步教授,联名向戴季陶密告他“引用异党,危害中大”。戴乘机推荐了朱派的张云。1941年7月,许崇清的代理校长职务被免,张云任代理校长*许崇清:《我的经历》,《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7页。易汉文:《中山大学编年史1924—2004》,第37页。。7月11日,中大法学院学生以护校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迎邹挽许拒张”运动,号召全校同学以罢考来抗议教育部的任命。当晚其他各学院纷纷响应,贴出“拥护邹校长回校”、“挽留许校长继续代理校务”、“请张云自避贤路”等标语;并于14日派学生代表面见张云,让他签字同意向教育部辞职。此次学潮提出“拥邹”口号是虚晃一枪,因他在重庆养病不可能回来,“挽许”才是主旨,但未能成功。最后在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主持的协商会议上,张云和新任教务长董爽秋同意保证“追随邹许校长之后”,“恪守成规”,不开除参加运动的学生,不解聘进步教授,保持中大学术自由等条件后履任代理校长*张江明等:《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挽许”运动》,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30—134页。。此次许崇清出任中大校长仅一年多,他的办学主张尚未真正实现就离任了。许崇清被免职后,赴韶关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许崇清虽然离开了中大,但仍发挥着影响,他主持出版的《新建设》、《教育新时代》、《学园》、《阵中文汇》等刊物,成为中大师生追求的精神食粮。《阵中文汇》在中大所在地坪石每期零售600多份,当时的中大中文系钟敬文教授称这些刊物是“浓黑中的几盏灯火”*黄焕秋:《许崇清和七战区编纂委员会》,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21—22页。。
抗战结束后,许崇清回到广州,在中大师范学院教育系讲授“教育哲学”,在文学院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期间他发表了《人底本质与教育》、《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等文章,结合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实践心得与学术思考,阐发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许崇清:《我的经历》、《人底本质与教育》、《人类底实践与教育的由来》,《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7—8、286—290、297—318页。。后一篇论文是他于中大教学时的讲稿,正是这篇论文成为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里程碑”*黄凤漳:《许崇清教育思想简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许崇清教育论文集》,第379页。。
在1920年从日本回国至1949年期间,许崇清的教育哲学理念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固然有受中国国情和时局的影响,亦有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想的缘由,还有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但他在教育界的实践,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对于他发展教育理念的影响尤为明显。通过筹备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任职于广东省教育厅,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代理校长职务,他有机会将胸中丘壑付诸实践,也切身体会了作为筹备者、一校之长、任课教授等多种身份需要承担的责任和面对的实际问题;得到直接与学生、教职员工接触交流的机会,也在多次的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中感受到国家、社会对高等院校的期望和要求。以上种种,促使他不断改造和完善自己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上出现了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是他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另一方面是他的实际工作屡遭挫折,难有他所期望的建树。这个时期的许多经验只能为他日后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思考提供更多新的角度、空间和依据。
三、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在中山大学最后的实践(1949年—1969年)
解放战争时期,许崇清因为其唯物主义教育学、哲学的思想言论以及《新建设》等进步刊物产生的影响,受到匿名信恐吓和国民党监视,遂于1949年初赴香港暂避。10月,他参加了港九教育工作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会,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迎接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底新方向》一文。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转变,许崇清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他似乎感到心目中的那个“理想”这回正在到来。广州解放后,许崇清随即返回广州。11月,他“秉承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意旨,接管了广州大学”*许崇清:《我的经历》,《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8页。。11月2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中大,至1950年2月20日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由军管会成立的临时校务委员会管治学校。在此期间,许崇清在中大任教授,与中大师生一起参加俄文学习活动,成为认真学习的典范*《热烈开展俄文学习运动》,《中大校报》1950年2月3日,第2版。。1951年2月,中央正式任命许崇清和冯乃超为中山大学正副校长,临时校务委员会结束,中大步入正轨*《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中山大学校史研究室,1993年11月,第5.1—5.5,5.85—5.88,5.19页。。
许崇清第三次执掌中大的时间长达18年,与过去两次短暂的任期成为鲜明的对照。在这18年中,以1957年整风运动作为分界线,他的处境经历了两个时期。1951年至1957年,许崇清与冯乃超、黄焕秋两位中共负责人合作无间,带领中山大学在新时期稳健发展。在此期间,社会上的文化环境并非没有干扰。1954年至1955年间,全国开展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随后扩展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并逐渐由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转到政治运动④《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中山大学校史研究室,1993年11月,第5.1—5.5,5.85—5.88,5.19页。。据说,当时北京曾有人告知中山大学,要开展对陈寅恪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但许崇清和冯乃超校长都没有理会*许锡挥口述回忆。。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术气氛趋向宽松。1957年夏季之前的数年间,无论文化环境是“春暖花开”还是“乍暖还寒”,许崇清与冯乃超、黄焕秋一起,始终稳妥地驾驶着中山大学的航船沿着繁荣学术的方向前进。
1957年整风运动后,冯乃超、黄焕秋相继淡出和离开中大领导岗位,许崇清鲜少再参与学校决策,他对当时的运动和革命也持不赞成态度。他的晚年是在无奈中度过的,直到1969年逝世。
(一)面对思想改造运动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1951年,中山大学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八年抗战和五年内战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新旧政权更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心浮动;在此情况下,还需要按照上级指示对学校进行彻底的制度性改造。但这一局面在困难重重的同时,也给予许崇清一个全新的施展和践行其教育理念的机会。他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回顾了中大曲折的历史,认为:“我们从此努力耕耘,今后的丰收是可以预期的。”*许崇清:《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的讲话》,《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519页。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2年6月,中山大学作为华南地区的试点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求他们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⑦《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中山大学校史研究室,1993年11月,第5.1—5.5,5.85—5.88,5.19页。。许崇清既是运动的对象,也是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也是要求进步的,但每个人进步都要有一个过程,也需要实践,不应该采取粗暴的方法。”他多次说道:“这些老师是中大的宝贵财富,他们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是进步的,是爱国的。今后中大要办好要靠他们的努力。思想改造要进行,但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他再三对当时在中大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国强叮嘱说:“国强,一定要跟同学们讲,对老师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他与冯乃超一起确定了指导原则:“集中力量,搞好中大,小心谨慎,宁慢勿乱,创造经验,推动全盘。”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贯彻“不追不逼,启发自觉,认真审查,宽大处理”的原则,使绝大多数教师得到通过*《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19—5.20页。李欣蔚等:《情系中大二十载,魂牵教育毕生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42—147页。陈国强口述回忆。。运动期间,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徐懋庸来中山大学检查工作,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发言,说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就是要旧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老底翻出来晒太阳,我们投鼠不能忌器,如果这老鼠躲在器里不出来,就连器一起打碎。据称,当时这位副部长在武汉大学就是推行这种粗暴做法的。许崇清和冯乃超两位校长都认为他的讲话不妥,要给予澄清。但许崇清感到自己的身份不方便出面,商定由冯乃超在党组会议上对这位副部长提出温和而中肯的批评,制止了武汉大学的粗暴做法在中大推行*王季思:《永怀与深思——悼念冯乃超同志》,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许锡挥口述回忆。。与此同时,许、冯两位校长对中山大学各学院进行课程改革,力求提高教学质量。1951年5月,两位校长与教务长一同召开工学院师生座谈会,充分听取师生对课程改革的意见,致力于解决工学院课程繁重、影响学生学习和健康的问题。随后,农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相继召开座谈会,课程改革和建设在全校范围开展起来,对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51,255—260页。。
1952年,中央教育部决定进行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2月,广东省广州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0月开始实施调整。中山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调出,分别成立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医学院。中山大学的文、理学院与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的有关系科合并为一所文理科综合大学。此外,中山大学天文学系调至南京大学,人类学系调至中央民族学院,哲学系调至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校址从广州市东郊的石牌迁至原岭南大学所在的河南康乐,校园从原来“世界大学中最大的占地面积”剧减至只有8万平方米。1953年10月,中山大学再次奉命进行第二次院系调整,将财经、政法类专业调至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同时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师范学院部分系科师生调入中山大学。1954年,又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至北京大学,至此,中山大学的院系调整告一段落*《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23—5.30页。黄焕秋:《给耀邦、剑英、紫阳同志关于成立重点大学的信》,《黄焕秋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这次院系调整的理由,是“对旧教育制度作彻底的根本的改革的需要,是为适应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但对于中山大学而言,它削弱了中大的实力和地位,从原来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仅有文理科的大学,原有的知名教授和闻名国内外的研究机构被调出。所幸的是,通过此次院系调整,从岭南大学等其他院校接收了陈寅恪、姜立夫、容庚、梁方仲、高兆兰等知名教授,充实了被严重削弱的师资队伍⑤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51,255—260页。。
对于“院系调整”,许崇清校长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曾与冯乃超副校长一道,和中央派至中大督促执行的中南教育部副部长徐懋庸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认为中山大学是有国际地位的大学,院校调整,中山大学被大大削弱了”,“中山大学应该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各个大学都有良好的传统,都应该保存下来”*黄焕秋:《光辉的一生——纪念敬爱的老校长许崇清教授》,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 第10页。许锡挥口述回忆。。虽然最终无法抗拒这个全国必须执行的政策命令,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许、冯二位校长尽力使这项工作平稳进行,减少波动。在师资调整过程中,他们为了保护和留任某些骨干教师,事先将他们转到不受影响的学系,让他们得以留在中大,等以后有机会再重建原来的院系。例如将经济系的梁方仲教授和王正宪教授分别调至历史学系和地理系。在迁址的过程中,他们对师资设备、科系调整、房舍调配以及家属安置等都做出妥善的计划和安排,并约见部分存有疑虑的师生,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交流,既保持了学校秩序的稳定,又保持了师生思想的安定*《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26—5.27页。李欣蔚等:《情系中大二十载,魂牵教育毕生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47页。黄悦:《曾汉民教授采访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38页。许锡挥、陈国强口述回忆。。“面对着院校调整后的种种困难,许、冯两位校长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创业。有一段时间,冯乃超同志身体不好,离校疗养,许崇清先生肩负重担,埋头苦干,保证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实施,并开拓了学校专业设置和科研的新局面。”*黄焕秋:《光辉的一生——纪念敬爱的老校长许崇清教授》,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0页。
(二)引领中大步入“黄金时期”
“院系调整”之后,国家进入“建设阶段”,中山大学也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稳定和兴旺时期。
“全面学习苏联”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家政策,教育领域当然不会例外,院系调整就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调整之后,全国各大学进入在正常教育秩序下吸取“苏联先进经验”的阶段*《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40,5.44—5.55页。。许崇清秉承唯物主义的教育哲学,对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建立起来的苏联教育制度有着认同感,他早于1926年就将美国学者所著《苏俄之教育》全书翻译为中文,并在《学艺》上陆续发表*[美]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著,许崇清译:《苏俄之教育》,《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583—704页。。同时,他发表的多篇论文所主张的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劳动结合以及批判和清除西方学者的某些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等,都与当时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因此,他对在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经验是持支持意见的。但是,许崇清也清醒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意“硬搬”苏联经验,而是要与国情相结合。1953年,他为《中大周报》题词:“加强思想领导,加强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育改革,克服困难,创造条件,稳步前进。”*转引自梁山:《建国后许崇清先生对中大的主要贡献》,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27页。依照教育部指令,中山大学从教学行政和组织、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实施了仿效苏联的做法。据1954年统计,全校97门课程,采用苏联教材、教学大纲或以苏联书籍作为教材的有59门,占60.8%,理科基本采用苏联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中山大学档案馆,1954年行政卷第1号,第83页。。教学方法则普遍采用欧洲式“课堂讨论”和考试考查方法,并推行“四级记分制”,推行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在教学组织方面,推行由班长、班主席、团支书管理班级的“班三角制”,实行上午集中上五节课的“五节一贯制”,实施教师工作日和工作量制度⑦《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40,5.44—5.55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习苏联”出现负面的影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得多,学得不好;限管很多,不仅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限制了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黄焕秋:《中山大学1956—1957年度教学工作》,《黄焕秋文集》,第70页。。事实表明,照搬苏联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超越了中国学生的接受水平;课程门数和上课时数太多,使学生、教师负担过重,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强调教材的权威性,压抑了学生的创造精神;照搬苏联的教学组织也忽略了中国大学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办学经验*《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58页。黄焕秋:《光辉的一生——纪念敬爱的老校长许崇清教授》,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0页。。
1956年8月,高等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校院长教务长座谈会,讨论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许崇清校长在会议上结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提出现行的教学改革导致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下降,违背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出调整教学计划,精简课程,改进教材教法的意见和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与首创精神的目标。8月10日,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司发出《解决当前教学工作中存在若干问题的临时措施》,在全国高等院校范围开展“纠偏”工作。9月8日,许崇清校长召开系主任会议,并安排组织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经验总结。在经过讨论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具体措施,将学习苏联引向更符合国情和校情的轨道。如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改革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要求各系自编教材、增加教师在教学中的自由度、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等。在校园文化生活方面,强调开展文体活动和增进学生健康,许崇清校长亲笔题写的“健康第一”牌匾悬挂在校医室。由于这些措施的及时和有力,中山大学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自觉性增强,独立思考和自由争论蔚然成风*《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57—5.60页。黄焕秋:《光辉的一生——纪念敬爱的老校长许崇清教授》,《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0页。黄焕秋:《中山大学1956—1957年度教学工作》,《黄焕秋文集》,第69—73页。梁山:《建国后许崇清先生对中大的主要贡献》,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27页。。
当时,各门学科大都由著名教授讲授低年级的基础课,成为中山大学的一个特色。这也正是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体现。他强调,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的人,都要有哲学头脑*许锡挥、曾汉民口述回忆。。
中山大学在抗日战争之前曾经拥有学术的繁荣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但在经历多年战乱之后,人员流散,机构萎缩,已处于衰微状态。1951年,许崇清重新执掌中大时,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冯乃超副校长的讲话中提到:离开北京时李四光先生说“中大有‘化外’之感”,那就是说中大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地位。这位学术界老前辈的话是语重心长的,那就是希望中大向加强学术研究这方面多加努力*冯乃超:《在中山大学员生欢迎会上的讲话》,《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许崇清上任后,与冯乃超一起采取有力措施开展学校的科学研究。虽经院系调整,中山大学仍然具有文、理科方面的精英优势,许多造诣深厚的知名教授可以成为研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中大因此提出依靠老教师,以老带新,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开展科学研究的做法。在校务教务工作方面进行了精简会议,减轻教师教学任务,重视教师科研时间。筹建了6个科学据点,给陈寅恪、梁方仲、容庚、徐贤恭等文理科教授配备了助教或教学助理员,并设法改善教师的居住环境,录用教师家属在学校就业,使用福利金补助教师生活等系列措施,尽力解决教师在科研、教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学研究当中*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64—265,268,270,268—271页。。为了推动科学研究和促进对外学术交流,中山大学于1955年3月成立学报编辑委员会,由许崇清、冯乃超兼任正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学报》分为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自1955年6月至1957年底共出版10期,面向全国公开发行⑤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64—265,268,270,268—271页。。为了有组织地推动中山大学具有优势的研究工作,在1956至1957年期间,增设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古文字研究室、东南亚史研究室、昆虫研究室等科研机构,集中学校的科研力量,并且增加图书、资料、仪器的采购经费⑥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64—265,268,270,268—271页。。
许崇清十分关注开展学术讨论的工作,他本人在中山大学教学时,经常采用课堂和课后讨论的方法与学生互动。因此他倡导中山大学举办科学讨论会,要求每年举办一次。1954年11月12日,是中山大学成立30周年纪念日,进行了持续3天的中山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1955年12月24日至1956年1月28日,举行了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包括2次全会和24次分会,许崇清校长在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共讨论了41篇科研论文。1956年12月15日至1957年1月16日,举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包括3次全会、30次分会和22次分组会,讨论论文180篇⑦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64—265,268,270,268—271页。。许崇清校长在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中作题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研究报告。在这篇论文中,许崇清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意和内容,并对历史上和当时的某些见解进行分析批判。他不同意当时的全国教育方针“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认为两者不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把“因材施教”放入教育方针,容易导致忽视全面发展“漫无目的围绕着个性团团转”*许崇清:《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359—383页。。论文随后分别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人民教育》1957年第4期、《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亦有相关报导,认为是解放以来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最富科学性和战斗性的文章,在全国教育界引起了重视和反响。虽然“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并未有所动摇和改变,但此后多位教育学研究者认为这篇报告代表了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最高成就,是许崇清晚年最成熟的一篇重要论著*赵锦英:《许崇清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黄凤漳:《许崇清教育思想简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许崇清教育论文集》,第381页。《校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83页。。从这篇论著背后,可以感受到他当年最操心的问题是:如何在建设新社会实践中培育“新的人”。
在许崇清和冯乃超两位校长的推动下,中山大学学生的科学研究也得到蓬勃发展。1954年开始成立了各种学生科学研究小组,在教师和教研室的指导下,结合课堂学习和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研究。于1956年成立中大学生科学研究协会,举办了“本校学生科学研究成绩展览会”,展出优秀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同学搜集资料制作的卡片和读书笔记等,并主编出版两期《学生科学研究》刊物,编辑学生科学研究论文集*《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5.81—5.85页。。至1957年初,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繁荣景象,学术争鸣空气尤其浓厚,许崇清深感欣慰。在这个时期,许崇清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不仅在中大努力实践其教育哲学主张,而且不时对全国性的教育问题发表意见。
(三)在风雨飘摇的中山大学里作最后努力
1957年夏季以前,康乐园师生正在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举行多次座谈会,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提出意见,对中山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有很大的促进。5月,党内整风运动扩展为反右派运动,一年一度的科学讨论会暂时停止举行,中山大学错划了190名师生为右派分子。10月至12月,学校进入整改阶段,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出现了粗暴的“革命”行动,师生受到很大的冲击。陈寅恪教授愤而写信辞职,向错误政策提出强烈抗议,许崇清、冯乃超、陈序经正副校长多次登门拜访挽留,陈寅恪教授才同意收回退休要求,不搬出校园*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72—273、284,274—276页。。
1959年,在全国进行“大跃进”形势下,6月下旬起中山大学以“政治挂帅”和“到生产劳动中去”为重心,提出改革教学和改革科学研究的“双改运动”。 9月至年底,中山大学师生放下书本投入生产劳动。这样的改革和运动,与许崇清向来的教育哲学理念有相吻合之处,他赞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但他认为劳动教育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途径。当他看到中大学生被安排去参加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土法炼钢、做工地搬运工人、杂工等,他指出适当进行这类劳动锻炼是可以的,但大学学生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科技基础上,不能使劳动教育变成手工业④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72—273、284,274—276页。。
1958年,全国性的“反右倾”整风运动波及中大校园,对师生造成很大冲击。许崇清第三次任中大校长以来,与学校党委主要领导人冯乃超合作无间。冯乃超因病退居二线之后,黄焕秋成为党委主要负责人。 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黄焕秋受到错误批判并调离中大。他离开前与许崇清挥泪话别,对于有长期合作经历与默契的同事的离去,许崇清感到惋惜和无奈。随后,教育部任命马肖云任中大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他作风比较简单粗糙,许崇清跟他虽然没有公开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但心中不悦。许崇清“已越来越不管事,许多事情,党委方面也不来征求他的意见了”*许锡挥:《黄焕秋与许崇清》,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27页。许锡挥:《李嘉人来中大前后》,《广州伴我历沧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页。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81页。。
面对全国性的违背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粗暴政治运动的做法,许崇清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含蓄的反抗和批评。1959年8月,许崇清发表《怎样解决人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现状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性质,教育革命不是“一天之内”或者“搞一次活动”就能完成,而应该是“一个新东西逐渐代替旧东西的过程”,不应该“通过爆发”的方式进行。后来有人认为,“该文实际上是反对当时‘教育革命’的做法”*许崇清:《怎样解决人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384—389页。许锡挥:《许崇清传略》,《许崇清文集》,第10页。。1960年4月,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重新掀起,中山大学仍然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旧有方式,对教学和科研正常秩序影响巨大。1961年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中山大学认真学习了条例内容,许崇清在《关于贯彻〈六十条〉的意见》中指出:“调整的目的性必须明确,是为提高教学水平。”并就调整学校规模和调整专业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中大再次恢复了教学秩序,执行以教学为主的方针,教学质量和科研都有了好转*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78—279页。许崇清:《关于贯彻〈六十条〉的意见》,《许崇清文集》广东版,第541页。。1962年1月至3月,中山大学借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之机,邀请华罗庚、苏步青、郭永怀、卢嘉锡、唐敖庆、童第周等著名科学家来校作学术报告和座谈,专家们介绍了有关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大大拓宽了中大师生的视野,推动了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出现了活跃的学术气氛*《国立中山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 》下册,第6.58—6.59页。。
但好景不长,1963年至1966年,政治热度再次升温,在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下,全国城乡开展了“四清”运动,学校也被波及,很快“烧掉”这次教育改革的成效。1964年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接踵而至,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许崇清很多时候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保护教师,很多方针政策是上级制定并要求执行的,他即使持不同意见,也无法与之抗衡*李欣蔚等:《情系中大二十载,魂牵教育毕生愿》,黄悦主编:《崇正树德 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第147页。。他的幼子许锡挥在回忆录中忆述:“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事态发展,令父亲深感困惑和不解。面对那些违反事物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的‘改革’和‘革命’,他虽有含蓄的反对表示,但无济于事。在中大身为校长,也不由自主了。晚年,他是在无奈中度过的。”*许锡挥:《关于父亲的教育思想若干忆述》,《广州伴我历沧桑》,第149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山大学是广东的风暴中心,学校主要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工被关押批斗,曾有力支持许崇清工作的冯乃超副校长被宣布为“中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学校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许锡挥忆述当时许崇清校长的情形:“父亲是中大的第一把手,但运动开始很久,都没有触动他。直到1968年‘夺权’和‘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公开宣布‘打倒’父亲。他虽然只被批斗过一两次,但已年届八十,又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更未受过这种侮辱,身心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许崇清约在1968年被炒家,闯入者是中大学生。1968年底,与许崇清一同生活的幼子许锡挥被派往坪石“五七”干校,年迈的许崇清夫妇留在中大继续面对冲击*吴定宇:《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294—297页。许锡挥:《天降人祸》,《广州伴我历沧桑》,第96—97页。。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没人提出批判许崇清的教育哲学理念,只是他在一份“自我检查”中反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许崇清:《我的历史检查》,写于1968年,许锡挥家藏手稿。。
1969年许崇清逝世,据他的两个儿子忆述,直接导致他心肌梗塞的刺激,不是来自中大,而是来自校外。他的去世与前文提及的“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有很大关联。幼子许锡挥在回忆录中忆述:“令父亲最气愤的是,外调人员多次上门逼供,要他证明抗战时期在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是‘叛徒’,想利用他去迫害那些老同志。”*许锡挥:《天降人祸》,《广州伴我历沧桑》,第96页。长子许锡振在回忆录中描述了3月14日的情况:“逝世当天,曾有从外地来的造反派到他家中,调查抗战期间他在广东韶关主持第七战区编委会工作时曾掩护过的共产党员张铁生等人的情况。在盘问中态度十分横蛮,语带谩骂和威胁,使这位老人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侮辱和刺激,晚饭后便哮喘不止。”*许锡振:《许崇清与七战区编委会》,《雪泥鸿爪文集》,未正式出版,第134页。家人请校医救治无效,于当晚离开人世。
四、结 语
1980年5月30日,在广东省政府礼堂举行许崇清追悼会,宣布他受“四人帮”迫害去世,表彰他对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后任的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曾汉民亦多次在不同场合中提到,许崇清校长第三次执掌中山大学期间的许多做法和理念,都很值得后来者参考。但纵观1951年至1969年这18年间,许崇清身任校长,但并不掌握将这所学校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治理的权力;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中央、教育部的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而存在的。许崇清校长对某些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他能够影响的往往只是实际执行的力度;他发表的文章在教育界和新闻界的确具有影响力,却难以对实际的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作用;他与冯乃超副校长在政治环境宽松时作出的有益建设,取得改善教学质量、提高科研水平等方面的成果,亦常常被下一波猛烈的政治风潮破坏。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运动的增多加剧,作为校长的许崇清,在中山大学有所作为之处日渐减少,最后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离世。但即使处于政治风气多变的时世,许崇清没有放弃自己的教育理念,亦没有无原则地跟随上级领导乃至中央的指令和决定,他一直坚持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并与冯乃超、黄焕秋等同事一起努力将中山大学引向他认为正确的方向。他们作出的种种努力,不仅造就了一批学业优秀的中大学生和学术水平领先的教师,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许崇清残余手稿的片言只语中隐约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教育家”的身份认同在1952年时就已颇有感慨:“不少人把我看作‘教育家’。起初,人家这样称呼我,我遂感到有点惭愧,后来习惯了,就任人家这样称呼,自己也不觉得什么了。但经过这次的学习,检查了自己以往的工作,循名核实,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弄清楚。不错,我留学外国时,在大学里曾专攻过教育学。我回国后,从一九二一年起,一直就在教育界服务。但看看我的经历,甚么局长、厅长、委员、大学校长……等等,一连串的官职,我几乎没间断过。”*许崇清在1952年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自我检查”草稿,广东省档案馆,档号D00218—00011。根据许崇清的同事、学生、家人的忆述,他的晚年亦常感无奈,这可能就是一种身在其位而不得谋其政的无力感。许崇清幼子许锡挥教授认为其父亲的教育理想,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未能实现*许锡挥口述。。笔者认为,经历多年的风雨和变迁,在此时探讨许崇清教育哲学理念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不能囿于他所发表的文章的文本解读,应该着眼于其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工作以及对当时校园乃至社会的影响。探讨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的影响,与其关心种种已经湮没在时间和风潮中的“功绩”,更应该注重他为中大留下的“学术自由”、“重视基础研究”的优秀传统,对学生“全面发展”、“独立思考”的要求,对于教育改革应当缓慢、有序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的清醒认识,以及尊重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