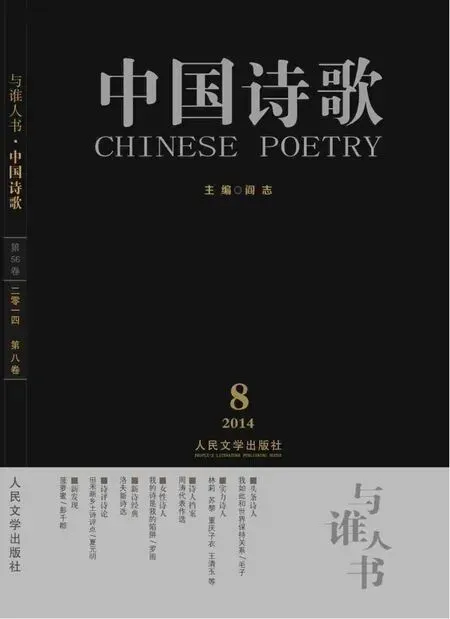我如此和世界保持关系(组诗)
MAO ZI毛子
我如此和世界保持关系(组诗)
MAO ZI毛子
四周皆是山脉,尘埃落定处,一张木案,一个人,用一支笔为竖着耳朵的世界写诗。这就是毛子。
他的诗意表达很重。读时,你能看见一个弯腰驼背的樵夫从拥挤的水泥森林中跋涉过来。但他的诗歌语言没有被沉重压迫变形,有纯粹制造的一些陌生,远离大言不惭的世俗。假设能让他的诗歌睁眼,与之对视,作者眼睛到心的那段距离里,没有商铺,不见大腹便便的土豪,彻底拒绝金钱对善良的污染。所以他的文字干净,像被大山里的空气净化过。
我喜欢读这样的诗,天真和真实进入同一个空间。好句子俯拾皆是,信手拈来。我是个在山里呆过的人,说真的,没有见过所谓成仙的人,但我感觉,进入诗歌写作,毛子就神秘加纯粹,很像一个准备成仙的诗人。
——车延高
匍匐之诗
畜生眼里流露的悲悯
让灵魂有了更为古老的追溯期
哦,狮子的孤独,水牛的下跪,一只山羊
挨刀时的温顺……
今夜,从你们之中,我领取无尽的轮回
你们这些胎生的、肉成的兽类啊
也许真的我们曾为父子、母女、兄弟、姊妹、主仆、眷属
这是我越活越顺受、服帖、虚心的缘由吗?
它们的眼神回答着一切,那里仿佛
是最后一块没有开垦的原始丛林
出没着最初的爱、宗教
和善的起源……
捕獐记
夜里没有事情发生
大清早醒来,南边的丛林有了动静
一溜烟地跑过去,昨天设下的陷阱里
一只灰獐蜷起受伤的前肢
多么兴奋啊,我想抱起它发抖的身子
当四目相视,它眼里的乞求和无辜
让我力气全无
只能说,是它眸子里的善救了它
接下来的几天,它养伤
我也在慢慢恢复心里某种柔和的东西
山上的日子是默契的
我变得清心寡欲
一个月亮爬上来的晚上,我打开笼子
它迟疑了片刻,猛地扬起如风的蹄子
多么单纯的灰獐啊,它甚至没有回头
它善良到还不知道什么叫感激
咏叹调1
那些穿越铁丝网的人
缠绷带的人
雨水中,对着雨刮器发呆的人
空中挖地道的人
黑白胶片上接吻的人
兵荒马乱里,还在彼此打听的人
从爱中归来,遍体鳞伤的人
临刑前,最后望一眼天空的人……
这些重的、疼痛的、没有声音的人
是孤独中,给予我安全的人
咏叹调2
活着。我从诗歌里获得一点自信
在女人那里,窃取温暖。
除此之外,只有书籍和我保持持久的关系。
它里面的人和事,快和我经历的生活混为一谈。
还有什么像文字,毁掉又把我唤醒。
想想总有一双鞋,一件衣服和一个日子
陪我化为灰烬。
这使我对一切琐碎的事物抱有悲悯之心。
昨天,我又一次去了墓地。
除了安静,它们什么也不能给我
它们告诉我:死亡,只是生命里的事情……
反爱情诗
我一直在消化着你
就像世界安排的那样
我为此豢养了妒意、小野兽、看守和潜逃
现在,我一一把它们消灭
直至彼此的肉体
平易近人
我愿在这个时候 说说生活
说说漫长日子里的平淡无奇
再也不会说爱了 只说唇亡齿寒
在愈陷愈深的衰老中
我的恐惧变本加厉
我说:请你像妈妈那样
把我再生一次……
失败书
扎西说,诗,还是少写为宜
是的,写来写去,无非是小天赋,小感觉
无非生米做成熟饭,无非巧妇
做无米之炊。
月亮在天上,写不写
它就是古代的汉语。
它爬进云层,就像王维进了空山
山,在他那里,就是不见人
我有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
他去了一趟西藏,呆了数月,却始终没有打开镜头
他说,哪怕打开一点点,就是冒犯,是不敬
是谵妄中的不诚实
谢谢这样胆小的人,持斋戒的人
谢谢他们在一个二流的时代
保留着一颗失败之心……
保罗·策兰如是说
写作也是一种自尽。而他说:
我只是从深渊中,和自己的母语
保存关系。
而他说:我不是去死,是负罪的犹大
走近那根柔软的绳子。
而他说:我死于一种
比你们要多的死亡。
而他说:这分食我的,也是你们的圣餐
——那德语的、犹太的、母亲的疼。
而他说:我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我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他其实什么都没说
一块孤独的石头怎会说话呢?
而他说:这是石头开花的时候
这是在一个“永不”的地方
赌石人
在大理的旅馆,一个往返
云南与缅甸的采玉人

赌石的经历
——一块石头押上去,或倾家荡产
或一夜暴富
当他聊起这些,云南的月亮
已升起在洱海
它微凉、淡黄,像古代的器物
我指着它说:你能赌一赌
天上的这块石头吗?
这个黝黑的楚雄人,并不搭理
在用过几道普洱之后,他起身告辞
他拍拍我的肩说:朋友
我们彝族人
从不和天上的事物打赌
来自厨房里的教诲
厨房里也有伟大的教导
——那是年迈的母亲在洗碗
她专注、投入。
既不拔高,也不贬损自己日常的辛苦。
写作也是一种洗刷
——在羞耻中洗尽耻辱。
可母亲举起皴裂的双手说:
我无法把自己清洗得清白无辜。
是的,母亲是对的。
厨房也是对的。
是的,在耻辱中
把自己清洗得清白无辜
是另外的耻辱。
水 库
在乡下,它是开明的
它的方言夹杂普通话
我怀疑它的胸膛有一架波音747
或一万台变压器
我想搭梯子,把它竖起来
我抽水、排泥
库底干了,露出修水库的人
这些当年的青年突击队,神气的拖拉机手
如今年迈,或不在人世
那些饥饿、灾年。不多见的
风调雨顺
而水依旧荡漾,荡漾
水库风平浪静,或深不见底
立 秋
月亮挂在磨基山上。我穿过火车站
附近的枕木,左耳一阵麻热、微痒
接着一小块东西松动、掉落
没有声响
百姓假寐 灯火惺忪
从铁路坝到果园路
突然一道流陨划过东南角
——哦,一枚天外的石头
一块只属于我的耳垢
它们落在不同的地方,也不惊动什么
想起今日立秋 气流分岔
宇宙星宿必有微妙的变化
而我们难于觉察……
我的乡愁和你们不同
在宜昌,我并不快乐
我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
为什么一直在后退
为什么我快把没到过的地方当成了祖国?
它们是布拉格、伊斯坦布尔和维尔诺……
其实,那么多的城市是一座城市,那么多的人也是一个人
昨天,我打开台灯,帕慕克对我说:
——我领会那个保险小职员内心的羞怯
而米沃什摊开手:我真的不知道波兰
但熟悉漆黑中的那一条条巷道……
真的很古老啊,那些我没到过的城市
像他们的晚年赶上了我
现在,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我的乡愁也抵触着
那块小小的宜昌……
隔山听啸
从山中下来。我翻飞在云水
和崇岭间。
古代山水的秩序,保存一颗汉语的心。
我翩游其中,直到那声音
也来为我送行。
多么空的声音,胜过空寂本身。
难于置信,那是从一个人胸膛发出的
它更像万物贯通,向本性靠拢。
我驻足,并回望身后的峰峦
它已稀薄、隐约
飘渺云端之中。
我想起居住其中的隐者,隔世、清苦。
他襟袍放下,用天地送我
酣畅的赠别之言。
许多年,也许是一辈子
那声音回响,传递
它们带着宇宙的容量,而我也有了
相应的容积……
短句:自画像
有一次 我步入一个公墓区
在众多的死者面前
我的活着反而显得虚构
——真实可靠吗?
下山的路上 我神志恍惚
这些年 迷惑一直在扩大
我承认:在存在之中
我看到的往往是不存在的事物……
安排之诗
有些河流是清澈的,有些河流
是浑浊的
它们都没有错。
有些风往南吹,有些风往北吹
有些风往心里吹。
它们都没有错。
有些为飞禽,有些为走兽,有些为草木
它们都没有错。
有些在太阳系,有些在银河系,有些在河外天
系。
它们都没有错。
——“万有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常数。”
爱因斯坦对宇宙说的话
此刻我对诗歌说。
山溪笔记
现在,我要说说这条溪流
在下一个雨季到来之前,它就这么无名无姓地
流着。有时,我会在溪边
遇到一只饮水的小兽,或几只叽喳的灰鸪
它们消失的速度,就像它们光滑的皮毛
而那众多的植物,我叫出的是多么有限
譬如冬青、紫藤、棕麻和泡桐……更多的
只能笼统地称为树木和杂丛。
山居的日子,我熟悉了溪水的性情、体温
以及它转弯处的阴暗或明亮
有时,一块褶皱的石头会挡住去路
或被凸裸的滩涂分割成更多的叉流
但要不了多久,它又会在不远的前面悄悄合拢
溪水流向哪里?我不知所终
我曾尾随它,到达最远的南山
那儿有个林场。有水泥的楼房、篮球场和商店
在深山 它们醒目;但也扎眼
就是在那儿,我搭上了一辆装满木头的货车
带着小溪的明快 回到我城市的家中
我是一个债台高筑的人
拉金曾在一首诗里,写到小便后
怎样摸索着上床;他也写过出生地考文垂。
看来我们有相似的经验。
只是我从不写宜都,它令人生倦。
这一点不像阿赫玛托娃之于莫斯科,本雅明之于柏林
博尔赫斯之于布宜诺思艾利斯,普鲁斯特之于巴黎……
他们都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去爱
去释怀,去咬牙切齿。
可为什么就不能像一列火车穿过它们并沿途停靠?
正如此,有时我更爱俄罗斯,更爱阿根廷,更爱巴黎
我抵押了他们的过去,也追加自己的生活
这是乡愁吗?哦是的。
它是乡愁的高利贷,是回乡的无底洞……
山中小记
一:山上
古代的浮云又回到了山上
一潭静水,存放它的过往史。
悠然一日,植物贴近气候
我潜入后坡,分辨出
丛林中动物残留的气味
若有若无……
而云朵终没有掏走
半山腰的两三户人家
他们一家姓陈,两家姓宋
远远地,一阵犬吠
唤出了月亮,也报出
它们各自的家门
二:投宿
枕头里的糠谷窸窣,像祖母
蹑手蹑脚
被盖满是棉花的味道
这让一个化纤的人
若有所悟
穿针引线的夜晚
农家的生活缝缝补补
——牛羊、黄豆、高粱、鸡鸭、药材、红
薯……
日子精打细算
像珠算反复的拨打
三:早晨
林子很大,
没有人来认领
空气藏着雾,容我进入
我刚醒来
应该与它们相符。
一只鸟在收集新鲜
又飞来三五只,一起往空气里
倾倒活泼。
大好的早晨,露水还没有人碰
蜘网也没有人碰
而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四:下山
青山并没有招手,但溪水
一直在流。
我顺势下山,与它
不谋而合。
你是从山上下来的吧?
——溪边洗脸的老和尚问道
我望见身后的寺院如耳根清净
我像山顶的浮云一样
点点头……
如此来过
当我来到这颗拥有海洋和陆地的星球
天地已经老去
我头顶上的白天和夜晚,像另外的天体
一一掠过
它们带走多少被称为怀念的东西啊
但时间不为所动,它既没有减少
也不会增加
某一天,退回到宇宙更远的角落
我该如何处置,那无处安放的乡愁?
现在,轮到处理我自己了
我把它们遣散到不同的物种之中
当我在太空中搜索,可能要去的地方
我已无悲无喜
退化之诗
爸爸从空气里来,又停在空气中
我肉眼看不见
畜生们看见了
一头老水牛打了一个响鼻
狗也觉察到异象
对着天空一阵狂吠
它们叽叽哼哼,比我还着急
——你怎么不和自己的父亲说话啊?
那些畜类啊
我有难处 有业障
想从前,我们也不进化,四肢妥帖
我们磨蹭皮毛 原地打转
我们有灵敏的嗅觉……
更黑暗地爱
黑暗自身的能见度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想起她们之后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
想起普罗旺斯的梵高
给弟弟提奥写信:你能再寄点钱吗
我需要土豆和颜料。
想起囹圄中的林昭,沾满月经的污秽
却保持圣女的贞洁……
当想起这样,黑暗陡峭、战栗
收缩成一根避雷针
而避雷针
从不躲避电闪雷鸣……
我爱……
我爱战争期间,那些等待丈夫
归来的妇女
我爱阵亡士兵墓碑上
悄然安放的玫瑰
我爱被征服的国家,秘密的聚会
我爱宵禁之后,那走上街头的传单和人群
我爱电车
我爱旅馆
我爱流放的路上,还在谈论诗歌与星空的心灵……
可我爱的那么多,却依然不够
爱多么丰饶啊,又多么的贫困
两地书
冬妮娅,现在我们也不玩革命了
时间把我们变成肥头大耳的人
你看大街上满是珠光宝气的妇人,那其中一个
就是后来的你。你怎么会变得俗气?
对这点我一直耿耿于怀。
我想要么是保尔搞错了,要么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其实他们都没错,错的是毁掉我们的生活。
冬妮娅,你的那个时代并不好,
我的更为糟糕。
为什么总是坏?好的只存在于虚构的书本中?
冬妮娅,你还在原来的位置吗,你还是
那个林务官的女儿吗?
如果一切完好如初,你找回了属于你的那一代人
我想替你把粗暴的革命拿掉
把庸俗的资产阶级也拿掉
只剩一个少女,用她的纯洁和体香
把一个时代重新哺养……
矛盾律
近日读《惶然录》,一段文字跳入眼帘。
幽居的佩索阿如此坦言:
——我在自欺,我总是在属于别人的乳房上,
躲躲闪闪地窃取别人的温暖。
想想也是,那些美丽的肉体。
她们不曾给卡夫卡、不曾给尼采、不曾给叔本华。
不曾给克尔恺郭尔。
不曾给荷尔德林。
不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也不曾给贝克特、梵高、加缪……
这些属于我精神家族的庞大成员
她们不会喜欢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而当我在不同的性事里,狠狠地做着。
一种深深的疲软,甚过我的勃起……
星 空
那么多的人,已回到繁星深处
即使在最冷的夜里,我都拥有一部
温暖的天书
一层一层地打开,他们都在那里
——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
隔着无数光年 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
多么匀称而守恒啊!
在辽阔的分布之下,我谦卑、幸福
我有幸加入到
川流不息的生机之中……
与谁人书
我爱的是另一年代的少女
在蒙尘的岁月,她们有着值得信赖的品质
我爱战壕的炮弹箱上,那相框中的少女
我爱少女穿过后方带来的宁静
我爱宁静背后她们的动荡、凌辱和落尘里对爱的忠贞……
如果你说她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会说她是刻着红字的海丝特
如果你说她是苔丝,我会说她是出走的林道静和萧红……
我爱她们的不幸甚过她们的幸福
爱她们磨难中的沧桑甚过她们的美貌
我的爱老套、守旧,不合时宜
而你从新一代里走来,如此轻盈
为什么你不重一点,像炮弹箱上的玫瑰
为什么你不老一点,老到和她们一样的年轻
哦,这不公平
但作为一个活到倒叙的人,
我要为她们托孤
犹大的祷告
亲爱的绳子,我是加略人犹大
也就是花园里出卖了主,被称为第13的人
我让那个数字也蒙了羞,这不是它的错
你们避讳它,就像你们用唾沫、诅咒
远离我。我卖了无辜人的血,该当如此
可你们不知道,一个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们也忘了,用石头砸妓女时,主对你们所说的话
绳子,只有你不嫌弃 不计隙
为我预备了洗净的水
我多想这个坚硬的世界,能像你一样软下去
而又能把我扶起来
现在,我前往你的路上
这是呼告的路,知耻的路,也是免除的路
你能接纳我吗?能像主耶稣
对待妓女和麻风病人一样对待我吗
请记住,我是加略人犹大
也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犹大
是所有人的犹大
亲爱的绳子,你知道我背负着他们
愿你能垂听,赐我予宽恕、安息和得救
如此的呼告,奉罪人犹大之名
也奉所有者之名
阿门!
一个美国老兵的简明幸福史
我和几个女人有过肌肤之亲,现在都已结束
但对于爱本身,我依然保持原始的关系
我的初吻给了米妮,校际唱诗班的漂亮女生
而那个女招待,引导我完成了
肉体的成人礼
我和房东的女儿好上又分手
后来,是长满雀斑的凯莉,是混血的黛丽
是推销汽水的芭芭拉……
那时我年轻,横冲直闯
我还没学会慢下来,还不知道爱需要耐心
要不是战争爆发,我不会认识那个改变我的人
那是反攻的第二年,我们一路向柏林挺进
渡过易北河时,我被炮弹炸飞
在野战医院的帐篷,她为我清洗伤口
她的眼神安宁、柔和,简直像圣母
那一刻,我要下了她的地址
战争结束后,我又要了她的全部
掐指算来,我们已一起生活了57年
我已八十有二,可感觉年轻得像个孩子
想想我拥有爱,并把它们带到老年,这难道不是幸福?
所以,对生活我没有什么抱怨
我每天尽情地享受日光,享受热水澡,享受周末的家庭聚会
我想,上帝也会这样
把我召回
听一个美国老人讲起他的生活
我召过妓
和萍水相逢的女孩上过床
相比这些年轻时荒唐的事,更压着我良心的
是我把失聪的女儿,给了酗酒的前妻
记得还是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天傍晚
我带三岁的她去湖心公园
她蹭在一个流浪的老人面前不走
她央求道:爸爸,他多可怜
我们带他回家吧。
而那个来自南方乡下的流浪汉,是多么好的
一个老人。他变戏法似的
掏出一个黄色的纸风轮
他乐呵呵地说:送给你吧,可爱的小天使……
如今,女儿有了自己的女儿
那个流浪汉,想必已经离世
可不管世事如何地变迁,不管经历
多少糟糕的逆境和挫败
那个傍晚,那个三岁的小女孩,那个乐观的流浪汉
他们连在一起,像串联的电路
照亮我生活的路
如果你问我:你爱这个世界吗
我会毫不犹豫地点头:是的,是的
那个傍晚,那个三岁的小女孩,那个乐观的流浪汉
他们就是我爱这个世界的
全部理由。
看一张摄于1903年的老照片
照片上有一个外国传教士
两个穿黄袍马褂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看不出
是信了耶稣。其中一个袖着手
另一个表情也木然。在他们的前面
一个戴虎头帽的男孩,含着指头
惊恐地盯着镜头。
他们的背后是一座城墙,那时看上去就已古老。
我无从考证照片的来历
他们中最小的那个孩子,现在都已不在人世
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一个下午,他们的目光
像另一个镜头,对准了我。
他们似乎在说:你也是短暂的,也会消失。
这时,我想起李宗盛的歌
他这样唱道:我怕来不及,我想抱着你……
我们如此逃避恐惧
夜半失眠,索性翻起了书
一个波兰人,谈起了战争中的蹂躏和人性
也许这之中有某种我们共有的东西
当试图寻找,我从奥斯维辛
找到了古拉格群岛
从古拉格群岛,找到了夹边沟
最终,我找到了那么多无名的人
他们可能是妻子的丈夫、童年的玩伴、热恋中的情人
是士兵、糖果商、艺术家和家庭主妇……
那么多的不幸,分配给我
可我不想谈论苦难,更讨厌以它自居
还是这个写诗的波兰人,有更深的体验——
当空气笼罩死亡,他们尽其所能地做爱
他们觉得性比爱,肉欲比灵魂
更速效,更兼容
更能麻醉周遭的恐惧……
所多玛,所多玛
怎样用一个米沃什,兑换“另一个欧洲”
那块大陆上曾发生的,也是我们身边还在继续的
有时候,波兰就是捷克,匈牙利就是罗马尼亚,
华沙就是北京
前几天读策兰,我震惊他直接从宇宙中
提取人类的黑洞
这个历经死亡营的犹太人,因为人的恶
而把奥斯维辛背负到耶路撒冷
难怪布罗茨基说:疼痛是传记性的,喊声是非个人的
难怪朵渔也愤然:写小诗令人发愁
这些黑暗中的诗人,让我引以为傲
他们之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词语
都是断头台
是核废料
是末日
论到末日。我想起2009年夏季
日全食临头
人们在天空下,目睹了天空的死去活来
那一刻,不可一世的太阳也有灭顶之象
那一刻,我看见上帝从头上走过
像走过罪孽深重的所多玛城

头条诗人
HEADLINES POET

毛子
MAO ZI
本名余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湖北宜都人,现居宜昌。出版诗集《时间的难处》。获2013年《扬子江》年度诗人奖。
- 中国诗歌的其它文章
- 杨景荣的诗
- 一个人在村庄的废墟上(组章)
- 周涛代表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