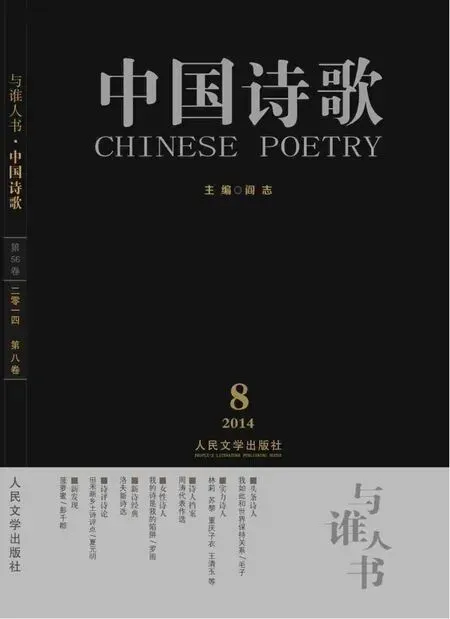一个人在村庄的废墟上(组章)
□亚 男
序。这是哪儿——
几间瓦房,一片水域。
山和田野都是干净的,都是沉默的。
从黄昏推开。广阔。绵柔。
田坎长了些花花草草。细嫩细嫩的。弯曲的是一条条交错的路,如血管一样盘绕。坡坡坎坎,伸手就可以捞到水中的鱼。
幸福的鱼,自由自在。
我不是鱼——
夕阳在我后背上,落了几片叶子。
手有一种黄的感觉,我触摸到了河流的卵石。在祖先的余温里,强颜欢笑。肩挑背磨的村庄。是的,老态龙钟了。
我不是水——
河滩种植的笑声早已远去。

有老茧的村庄,祖先遗留下来的善良就是一口水井,源源不断地养育我,或者一些杂物的坚硬。
我不是土——
坡坡坎坎上,牛和羊相依相伴。啃走了时光。古木与春天。
山野与旷古。
我生命的根源之地。
——我的村庄。
暗下来
天空。大地。
我看不见了,究竟笼罩着什么——
空气在血液里流动,时光刻在沧桑里。
不自觉地去触摸,大地一派空茫。这刻我走在一个叫村庄的地方,心生疑惑,这还是从前的村庄吗——
枯枝和杂草哪去了。飞鸟和炊烟哪去了。鸡鸭哪去了。残存时光里的凌乱,荒芜不见了,仅存的只有一声叹息。
流水和雨滴在我记忆里。
我不能失去的土地和村庄,陷入深夜的暗。
出现在我生命意识里的,不仅仅是一缕风,还有那些无孔不入的,从欲望里散发出来的毒。暗下来——
是最好的一处去处。
隐没在灵魂里,我看见了灵魂流离失所。
裸露在废墟上,我只能望眼欲穿。
不见了
灵魂的土壤,种植了月光和风雨——
我不想去回忆。
不想——
村庄被砍伐。时光被砍伐。大地等不及我呼吸。
村庄在古老的文字里隐去了烟火,或者人间的冷暖。
我用什么去修饰,一辆推土机,深入到夜里,在我的睡眠里,突然失控。我也无法视而不见,我的亲人的惊恐。山不见了,河滩不见了。树和鸟是相依为命的,也不见了。
不见了——
我可以省下时间去,伪装。内心的湖,波澜不惊——
不可能。
在一杯酒里,喝高。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词,灌醉了很多人。
接下来,是我看不见,天空下的村庄和大地上的人。钢筋和水泥不得不加固一些人的手段,在自己的命运里运筹帷幄。
瓦砾上
一滴血,在历史的缝隙里生生不息,流淌的那些日子,漫无边际。夜风吹冷了石头。祖先的遗恨,在打石匠的叮当声里——
梦见了,奔跑的羊群。
石头和泥土支撑起——
袅袅炊烟。
小桥去了远方,在流水的不舍里,我回不去了。
一个人在村庄的废墟上,吧嗒夕阳。落在尘埃里的孤单,比风冷。风吹不去的尘土,比月光还要轻。人间的冷和暖,在一念之间,我触摸着瓦砾上那些过往的烟云,已经飘散而去。
我从一滴血里走出来,瓦砾上的冷,落下了时间的霜。
大地。此刻的大地,只有石头知道我的心事。
一切沉入黑夜的事物,保持着历史的冷静和客观。
一滴血,足够染红大地。
如血的大地啊,瓦砾上没有细小的微生物,也没有可以循迹的历史,一些被忽视的人和事,一点点地放大。
半个月亮
小时候,如一枚落叶,已经捡不起来了。
水中的天,半个月亮正好照在我的身边。
大地是清冷的。
风吹乱了我眼前的景致。蛙声与鸟鸣和我失之交臂。
我问,还有半个月亮呢。
母亲回答,天狗吃了。
此刻的村庄,不在小时候,已经衰老的叶子悄无声息地落下,和树的根须一起不见了踪影。
现实的雨,带着尘埃。
半个月亮,在杂草上,不是从前那么清澈和皎洁。
白得有些失魂落魄。
我蒙着眼睛,那半个月亮哭出了声。
树的上空
我还可以找到——
一朵云。回到鸟的翅膀上,我与一朵云多么近。擦着云朵飞过,雁声阵阵。那时的天空多么蓝。
一棵树,一万棵树,聚集的蓝,而今流离失所的蓝,埋在了我的梦想,也埋在了村庄的未来。
我还可以找到——
一捧土。
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
远到我不能辨认。那些风吹去的往事,那些汗液里残留的喘息。
树的上空布满了阴云,不,是雾霾。
河流流进了往事。
山野突兀在记忆里,我只能攀着鸟鸣眺望。
大地,除了钢筋和水泥,就只有欲望了。
落 日
我看见祖父在一块瓦片上,托起最后一点光线。
删去了的鸟群和流水,在历史的夹缝里,我再也翻不到了。
父亲吐出的一口血,淹没了庄稼,血色的大地,沦陷。隆隆的机器声掩盖了我的悲伤。我想到即将到来的黑夜,村庄将隐没在哪里——
或许,父亲吧嗒的旱烟,早已被时光卷曲。
展不开的笑颜,换着了一夜的咳嗽。
高楼排出来的尾气,宣告我的故乡,
在落日下的孤苦伶仃。
瓦 片
我用最后一块瓦片垫高。
村庄,在一声声碎的巨响中撕裂。
瓦片的今世和前身,回不去了。
烈火早已熄灭。
打坐在瓦片上,泥土的温度,已经不适合庄稼的生长了。外出打工的兄弟,每一句话都打上了农民工的烙印。
在颠簸的汽车里,挤满了一年的收成。
当瓦片碎的时候,再来清点,只有一滴眼泪清楚,这些年在外的辛苦。
本来遮风挡雨的瓦片,碎成了一地的伤,
我再也回忆不起一只猫跑在屋顶上的欢快。
没有屋檐可供瓦片,
承载思念的时光。那些风雨都已经无家可归。
墓 碑
后山,密不透风的林子,生长出来的绿,退去了时光。
一块墓碑在林子里,隐藏了很多的故事。
祖父,爷爷和父亲,在墓碑上刻下了繁衍的路径。从湖广填川,祖先就背着这块墓碑。
祖母一针一线缝制的日子,
斑驳的光照亮过——
路上锻打。
山顶上站着的那个人不是我。
一棵树,去了。
干净的风,僵硬的雨,开不出娇艳的花朵。
我献上我的诚挚。
一滴血浇灌出墓碑上的野花。在我的梦里微笑。
一场雪下在村庄
种子失去了方向,一个人守候。
父亲走了,母亲走了。他们相依为伴的炊烟走了。
河流和山冈走了。
六月的飞雪——
我一个人站在村庄。体内的汽车声,滔滔不绝,那是另一条河流。
埋得最深的——鸟鸣,我牵了一根线,可是没有空地,也没有谷粒,更没有悠闲的鸟,与我对视。
我崇敬的,蛙声阵阵,早已凋落。
我不能拾起的童年,淹没在推土机的隆隆轰鸣之中。
雪啊,下吧。
我看见了洁白的灵魂。
去看一个人
这个人很普通。
吃力地说话,不能睡去——他清澈,我也清澈。
我只是沉默地站在他的床前,以为村庄给了他最后的落脚。他是不是想到了炊烟,或者流水,但他已经说不出来了。哦——哦——哦的。本能地不能点头,对我的到来只有眼泪是真实的。
时间不能以天,或者小时计算了,
一秒都是很重要的。
村庄,闪过——
云朵闪过。雨——
现在的他,与村庄是多么的不相干。
石头和泥土,去了哪儿——
我察觉不到他的身体的动。
要一根稻草,就是他的最后。
下雨记
石头开花了。
河流漫步。

一早推开,雾霾。
雨在我头顶,在石头的内部,酿造波澜壮阔。隐藏了大海。
村庄啊,是一块石头垫起的。
高处不胜寒。
滴滴答答一夜,在流动中,相信石头开出的花是美丽的。
一滴雨祭拜天地。剩下一些血丝,一些繁衍。
一滴雨就是一个世界。我可以孕育。
醉卧山川,大地设下鸿门宴。在挖掘机的掩护下,产卵。
水滴石穿,我却不能为村庄寻到良辰美景。
下雨,为村庄的一次送行。
雾霾——在前。
黄雀在后啊!
鸟 鸣
沉入梦中——
一个人。咀嚼。反刍。
舌尖上的鸟鸣回不去了。捕杀童年,第一声鸣叫出乎意外。冷静地拉开弓,射出的子弹,回旋在天空,倒映出天的蓝。
我不是一只缺少良知的鸟,羽毛的光泽,散发泥土的味道。
觅食的过程艰辛。我奔波在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心跳,都能嗅到时光的完美,都能反刍人的冠冕堂皇。
失去枝头,成为一则历史典故。
精卫填海,还是夸父追日,也许女祸补天,鸟成为了最为真实的使者。
而今,鸟——
复归大地,埋藏了村庄的宁静。
就在我的肩头,栖息吧。
不带有企图的站立,流着毒素的泪,不能发出鸣叫,只能宣告,这个世界与鸟鸣失之交臂了。
草 香
归为灵魂——
山是亘古的,陷入历史的传说;野旷天低,大朵,大朵的,花的飞絮,鸟流落。悲愤的一株草,生命的意识,举高我前行的火把。
一早推开雾和云朵,我看见了自己灵魂的路径,与鸟鸣交错,与山岚失臂。草啊,距离山的宁静有多么的相似,与水的流动如出一辙。
脚下的那些土,与云朵无关。
我还要坐多久——
回归。或者焚烧。云朵的红,大地的猝不及防,都在一瞬间。
完美的谢幕。
我还有凝望。
是的,在土地上站立,展现草的根部与泥土的关系。
我要问——
草啊,灵魂上的一滴露珠,蒸发出来的香,曾经诱惑了多少的人,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将祖先的遗嘱书写成一则历史。
就这样放下草的香,为世界的静装扮自己。
这草香足够了——
人间啊。
事 件
总该遗忘,总该重生。
村庄,繁衍。悲欢与离合,人间的旷世,漫步与一早的阳光,我看清自己的脉络,血管里,流淌的河。卵石与泥沙,风暴。
相信一株草的现实,一棵树的坚韧。
但推土机和挖掘机已经颠覆了——
村庄的平静。作为泥土的本能,风宣告了,大地的崛起,掀开了这个世界的一角,成为了一个事件。
生活的机能,在钢铁与水泥之间,我不能选择。亦如祖先按照生命的规律的交付不能阻扰。成为人的村庄,瓦砾与废墟,铸就灵魂的根。
枝叶繁茂啊,我的村庄,以及烟火。
缭绕。
山水之间,我以行走的方式,和世界对话。
这些内心的暴动,酝酿了千年。
而今的村庄,以不可改变的姿态回答了,事件的真实与虚伪。
人啊,究竟是群居的动物,接受了现实的拷问。
湖广填川,再一次考证了,这一现实。而今的我,在城市的角落,闻到历史的味道,与祖先的迁徙是何其的相似——
走 吧
误入秋霜。
湖水潮起。山野里,一个人的行走,以一棵树的姿势,以云朵的方式。
将风培育成泥土。
高粱和大豆种植了一代又一代。只有炊烟是亲切的,种植在我的感情里,看见母亲一天又一天地衰老。
和村庄斑驳的时光是多么的一脉相承。
开在一朵南瓜花里,我怀抱着灵魂,一路奔袭。
与一路的风景无关。
以山的纯朴,以土地的真诚,留下每一个脚印。
记住。大地在这刻苍茫。
记住。风在这刻狂澜。
记住。雨不能幸免。
我在推土机前,祖先一锄一锄挖掘的温暖,是多么的弱不禁风。
山啊,以坚实的臂膀,也扛不起了。
村庄生命的火把,举高了人类的繁衍。
从一段历史走向另一段历史。
器 皿
盛下——
我的时光,和祖先的望眼欲穿。
簸箕和斗笠,以不同的方式,盛下了村庄。那个披着蓑衣的人,在田埂上,越走越远,最后我看不见他的背影。
背影也是一个器皿,装下我那时的思念。
母亲在菜园子,一言不发。
躬耕的菜蔬,海椒和豇豆,是否记得炊烟的味道。
一声咳嗽,早已破了——
一件器皿的朝思暮想。
放下——
就在这刻,山水装下夕阳,河流装下孤独,晚风装下一望无际。
草啊,扛着春天,如蚂蚁一样蠕动。
大地装下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是的,大地这个器皿,可以盛下村庄——
槐树上的钟
铁,锻打的日子,支撑起,山的脊梁。
村庄敲响的时候,山就呈现出铁的气质。
语言的尺度丈量出夜的深浅。
槐树上的钟,已经锈迹斑斑,敲打不出清脆的声音。沉淀下的钟声,一夜未眠,就在我的耳畔,响起当年的激越。
守住村庄的流言蜚语,
钟走远了。
我的祖先啊,吊在钟上,晴朗的日子,照亮了山野。
那口钟啊,一千年,不锈的声音时时回荡。
屋檐落下记忆的碎片
很久了,我站在这里。
就是这么一小块地,饱受一只脚,可以顶天立地。这片天空啊,我们用泪水洗净,再洗净,让蓝镶嵌其中。
蝴蝶闯入檐角的蜘蛛网上,不能动弹的薄翼承载了时光的重。
那些不能搬动的痛苦和灾难,我看见了,一只蝴蝶的卑微。
弥漫着寒冷的村庄,
哀伤爬上了墙头,风吹不散。
我想浓墨重彩院坝上一棵树,一棵孤独的树,很多时候,我在树下,听大地的呼吸。
雪包裹着的天气,一个人在村庄,心事重重。
一滴雨成为我的知己,
小心翼翼地收藏起,落日的壮美。
风吹来
停下神的脚步,安魂的泥土,远方注定是一个流浪的词,我不能抵达。
望断秋水,干裂的土地,颗粒无收。
左边是一排烟囱,右边是一栋栋高楼。
笋子一样的目光,触摸江南的浩渺水波在梦里遗失。
风吹来,土地的痛,伤口流出来的血,不是红的——
大把,大把的盐,在早上的光线的突围中,下在汽车的喇叭声里。
味道不是童年的味道,也不是故乡的味道。
风来得太突然了,吹落树的千言万语,只有光秃秃的,土地,耸立在村庄的概念之上。这还是我的村庄吗——
从灵魂里取出火
身体错位了,我供奉在神龛上的灵魂,一夜之间,大火蔓延。
村庄,在水田的上方——
大堆,大堆的云,聚集了太多的雨水。
夜深。村庄,鬼哭狼嚎。
石头里,火焰升腾。
我背后的冷,是石头的阴谋。今夜的算计,大地倾斜。
语无伦次的山峦,大地包含了火的向往,从一滴水到月光里,我看清了一些人的险恶,的狡诈。
瓦片上——
风雨交加。
倾盆而来的厄运,淹没了村庄。
我的山村,我的土地,
种植的灵魂,火,火,火——
殃及了一大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