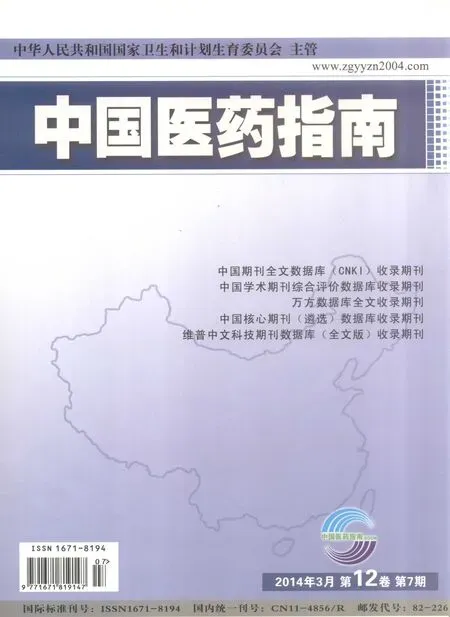经皮椎弓根内固定结合病灶内药物化疗治疗脊柱感染性疾病
刘志昂 张 陆 高松明 高军胜
(郑州人民医院骨二科,河南 郑州 450000)
经皮椎弓根内固定结合病灶内药物化疗治疗脊柱感染性疾病
刘志昂 张 陆 高松明 高军胜
(郑州人民医院骨二科,河南 郑州 450000)
目的 探讨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结合病灶内化疗治疗脊柱感染性疾病疗效。方法 回顾2007年4月至2012年6月,采用经皮内固定结合病灶内化疗的方法治疗脊柱感染性疾病20例,男9例,女11例;年龄36~85岁。所有患者均为初次手术。术前均行X线片、CT及MRI检查,实验室检查,手术时同时进行病理活检。诊断:脊柱结核15例,脊柱非特异感染5例。胸椎10例,胸腰段6例,腰椎4例。17例患者涉及单间隙两个椎体,3例涉及双间隙3个椎体。固定方法:两对椎弓根钉5例,3对9例,4对3例,5对3例。结果 术后随访时间12~38个月。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复发。术后患者Frankel分级明显改善。所有植骨均达到骨性融合,椎弓根钉固定在位,无松动、塌陷及断裂。术后后凸畸形纠正0.89°~27.33°,随访1年未见明显丢失。结论 后路一期病灶清除椎弓根钉内固定术能够一期完全清除感染病灶,脊髓减压,矫正后凸畸形、重建脊柱稳定性,是治疗脊柱感染安全有效方法。
经皮椎弓根钉;脊柱感染;化疗
脊柱感染性疾病因其部位特殊,并发症多,处理较为困难。在全身抗感染药物控制之下,及时彻底地手术清除病灶,可缩短疗程,有效地防止脊柱后凸畸形。我们自2007年4月至2012年6月,采用一期后路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联合置管药物灌注冲洗治疗胸腰椎感染20例,疗效满意,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20例,其中男9例,女11例,平均年龄64岁,病程1~16个月。入院时平均血沉55 mm/h,所有病例术后确诊为结核或椎间隙感染。纳入标准:①正规保守治疗后病情无改善。②椎体破坏较轻,涉及3个以下椎体。③高龄患者或体质差的患者,不能耐受前路或后路开放手术。排除标准:椎体破坏严重,后凸畸形明显,后凸角>25°。其中胸椎10例,胸腰段6例,腰椎4例。其中3例患者有不全瘫或神经损伤,按Frankel[1]分级:C级2例,D级1例。
1.2 手术方法
1.2.1 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
手术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下完成。患者俯卧位,髋、胸下垫软枕,腹部悬空,术前先C臂机定位目标椎弓根投影并做皮肤标记,常规消毒、铺巾。C臂机监视下以标记点经皮沿椎弓根轴向将穿刺针插入椎弓根内至椎体中部,以钝性导丝更换穿刺针芯,纵行在穿刺点切开皮肤约1 cm,沿导丝方向置入空心椎弓根钉。置钉节段的选择:对于单椎单间隙病变,选择病椎上下各2个椎体椎弓根置钉;对于2个间隙3椎体病变,选择病椎上下各2~3个椎体椎弓根置钉,保证椎弓根钉置于病灶外。对于单纯置管给药的病例行双侧椎弓根固定,而需要局部减压置管冲洗的患者施行单侧椎弓根固定。本组病例6例行单侧椎弓根固定,14例行双侧椎弓根固定。预弯椎弓根钉系统连接棒,配套工具经皮置入连接棒,并予锁定。全层缝合伤口。
1.2.2 给药方式
病灶内积脓不明显的患者,单纯行置管病灶内给药。具体方法是在术中C型臂或CT引导下将硬膜外穿刺管置入病变椎间隙或病灶内,推注生理盐水无阻力后将软管固定于皮肤。对于椎间隙及周围有明显积脓者,在置入椎弓根钉对侧纵行切口3~5 cm,椎板开窗直径1~1.5 cm,专用绞刀直接进入椎间隙,进行有限病灶清除,大量生理盐水冲洗,置入硬膜外穿刺管作为进水管,带侧孔的硅胶管作为出水管持续进行药物灌注冲洗。逐层缝合切口。
1.3 术后处理
全身应用抗感染药物。结核患者遵循“合理、规律、系统、长期”的化疗原则。结核病例应用异烟肼进行局部推注或药物灌注,非特异感染患者应用庆大霉素或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合适抗生素局部医用。定期复查血沉、CRP、血常规及肝肾功能。做好置管护理,避免脱落。
2 结 果
2.1 手术时间90~160 min。出血量20~200 mL。术中未出现脊髓及神经根损伤。无深部血肿、感染发生。
2.2 所有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无感染及窦道形成。术后3~7 d佩戴支具坐立和下床活动。灌洗管在灌洗液清亮、出入量平衡后拔除出水管;局部药物推注管根据病情和实验室化验指标应用1~3个月。
2.3 随访3~52个月,平均13个月。其中13例患者痊愈,血沉及CRP恢复正常,影像学检查显示椎体融合,恢复劳动。6患者病情改善,血沉及CRP持续下降,疼痛明显改善,继续全身药物治疗。1例患者原发病灶脓肿发展,在当地医院行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3例神经损伤患者Frankel分级:2例C级患者1例恢复至E级、1例恢复至D级,D级1例患者恢复至E级。随访期内,未出现椎弓根断裂现象。
3 讨 论
脊柱感染外科治疗的目的是:通过彻底清除感染坏死组织,改善疼痛症状,同时明确致病微生物的种类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伴有明显压迫症状者,手术治疗可以进行充分的脊髓或神经根的减压;预防或矫正脊柱畸形,恢复脊柱稳定;术后早期活动以避免长期卧床导致的并发症。目前常用一期手术方式有:①经前路病灶清除,椎体间植骨融合并前路内固定术。②经后路病灶清除并后路植骨内固定术。③前路病灶清除,后路植骨内固定术。而采用最为广泛的为一期前路病灶清除,后路植骨内固定术[2,3],但前路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远期后凸畸形发生率较高,且临床观察到大量经保守治疗的患者脊柱可以在不手术的情况下自发融合,致使很多学者质疑这种手术是否值得[4]。
近年来,王锡阳[5]、顾晓峰等[6]报道一期后路病灶清除植骨内固定术治疗胸腰椎结核,疗效满意。其优点是[7,8]:①操作相对简单,创伤小,可以一期完成病灶清除、重建脊柱的稳定性;②经椎弓根螺钉固定牢靠,不会出现螺钉切割椎体;③椎弓根螺钉良好的撑开作用能有效纠正后凸畸形;④术中无需变换体位,可以节约手术时间,减少手术并发症;⑤术后有效降低胸腔感染、腹膜感染概率。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用了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除上述特点外还具有:①大大减小了手术创伤,经皮椎弓根内固定结合透视下置管术出血微量,而结合椎板开窗患者出血量也在200 mL以下。②手术操作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对心肺功能要求较低,更适合老年患者和体制较差的患者。本组患者中,合并心脑血管病患者10例,糖尿病患者6例,肾功能衰竭透析患者2例,均顺利度过了围手术期。③所有的椎弓根螺钉都位于病灶外,从而避免了生物膜效应,减少了医源性感染扩散、窦道形成等并发症。
脊柱椎间盘病灶破坏、坏死、血流供应障碍等原因,口服或静脉给药时,灶内的药物浓度达不到理想的杀菌或者抑菌浓度。药物灌注已经广泛应用于非特异性的骨与关节感染。结核杆菌的药敏培养是以药物的血浆浓度为基础的。口服异烟肼后,血浆药物浓度3~5 µg/mL。常规剂量下病灶内药物浓度耐药,不代表高浓度依然耐药,因此提高病灶内药物浓度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杀死病灶内的血浆药物浓度下的耐药结核杆菌。微创治疗灌注冲洗病灶异烟肼的浓度大约是600 µg/mL,单纯局部注射的浓度大约是5×104µg/mL。在影像学引导下,穿刺置管可以精确达到期望到达的脊柱任何部位,或者借助有限开放手术的过程中,病灶内放置局部给药管。克服了全身用药无法解决的问题,避免了门静脉系统吸收带来的毒副作用。这与现在的肺结核空洞内纤维支气管镜给药的作用相近[9]。
脊柱感染引起的不稳定和外伤性不稳定时不同的,感染起的不稳定在破坏的同时修复已经开始,即使在炎症早期也是如此,而是否引起症状性不稳定是由细菌毒力和机体免疫力彼此斗争的结果决定的结果[10]。刘向东等[11]认为有限性结核病灶清除术与彻底结核病灶清除术在治疗脊柱稳定性未完全破坏的脊柱结核上疗效无显著差异;有限性结核病灶清除术手术时间及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彻底结核病灶清除术。
微创方法治疗脊柱感染的理念[12]是将从手术为主、药物为辅转变为药物为主、手术为辅。提高病灶内药物浓度,尽早治疗,终止病变的病理进展。因此我们认为:通过置管引流、局部化疗虽然清除病灶不彻底,但可以实现脓肿引流,减少中毒症状,改善患者的全身情况,同时提高病灶内药物浓度,利于杀灭病原菌,特别是对低浓度耐药、高浓度敏感的耐药脊柱结核更为有效,从而解决了结核杆菌感染的生物学问题。并且可尽早获取标本,利于及时药敏试验、调整化疗方案。同时辅助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使脊柱获得即时稳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减少长期卧床并发症,增强患者信心。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将可以减少手术的次数,降低手术的难度,将复杂的前路手术或前后路联合手术改变为的微创治疗。事实证明,在本组病例患者中,除1例患者行二次前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术外,其他患者都获得了可喜的预后。
但是,对于脓肿扩散较广泛、椎体破坏较严重、明显后凸畸形的患者,单纯后路固定引流可能达不到完全治疗的目的,从而延误治疗,加重病情。另外,单纯的后路内固定可能带来脊柱不稳和后凸畸形加重后内置物断裂的风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长期随访。
[1] 贾连顺.现代脊柱外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
[2] 万克.一期病灶清除植骨及内固定治疗胸腰椎结核[J].实用骨科杂志,2010,16(3):209-210.
[3] 王广积,沈宁江.椎间植骨内固定治疗胸腰椎结核的临床报告[J].实用骨科杂志,2009,15(1):38-40.
[4] Guven O,Kumano K.A single stage posterior approach and rigid fixation for preventing kyphosis tuberculosis[J].Spine,1994,19 (10):1039-1043.
[5] 王锡阳,魏伟强.一期后路病灶清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治疗胸腰椎结核[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09,19(11):813-817.
[6] 顾晓峰,程力.胸腰椎结核后路病灶清除一期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的疗效分析[J].中华医学杂志,2009,89(41):2898-2901.
[7] Lee SH,Sung JK,Park YM.Single-stage transpedicular de-compression and posterior instrumentation in treatment of thoracic[J].J Spinal Disord Tech,2006,19(8):595-602.
[8] Sundararaj GD,Venkatesh K.Extended poste-rior circumferential approach to thoracicand thoracolumbar spine[J].Oper Orthop Traumato,2009,21(3):323-334.
[9] 张西峰,王岩.活动期脊柱结核的微创治疗:提高病灶内药物浓度的探讨[J].中华外科杂志,2008,46(9):700-702.
[10] Jain AK.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of the spine withneurologic complications[J].Clin Orthop Relat Res,2002(398):75-84.
[11] 刘向东,吕智.脊柱结核有限性病灶清除术的临床研究[J].中国临床研究,2011,24(1):21-23.
[12] 张西峰,王岩.微创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治疗脊柱结核的疗效比较[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05,15(3):156-158.
R681.5
:B
:1671-8194(2014)07-02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