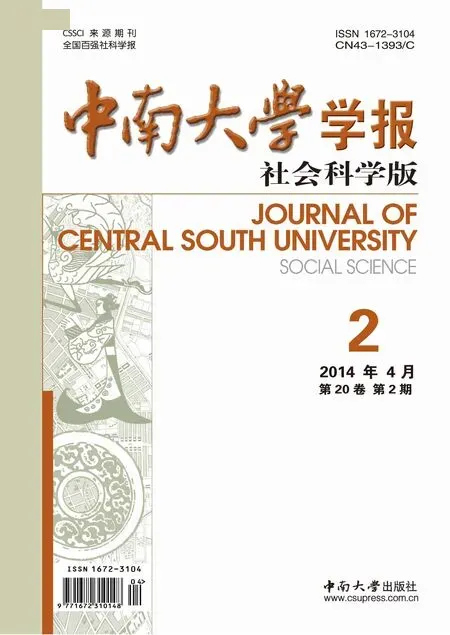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
——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带灯夜行:且行且吟的乡土悲歌
——贾平凹《带灯》女主人公意象解读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贾平凹长篇新著《带灯》聚焦于“乡村病”的书写。一是基于小说结构的“出走——外来”模式,阐释其视角陌生化与间距化的审美效果;二是通过带灯书信体的心灵独白,离析出农村基层问题的驳杂性与其性格组合的矛盾性;三是经由带灯“夜游症”意象分析,解构理想者的精神苦役与政治话语的游离;四是坐实在文本的叙事策略上,剥离出叙事交流的断裂性与实效性,内中探究作者叙事声音的罅隙性在场。
贾平凹;《带灯》;乡村裂变;现实主义;书信体;叙事视角;空间诗学
近十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基本都是围绕“三农问题”而展开,而文学视域对“三农问题”的叙述,即可视为乡土中国的经验表达。在贾平凹的城乡双向书写中,就其小说之维的社会病理分析来说,《废都》《怀念狼》《土门》《白夜》等小说中暗讽了“城市病”,而2013年长篇新著《带灯》则聚焦在“农村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书写上。小说中的樱镇地处偏远,属于欠发达的边穷地区,但樱镇又是“风水好”的所在。不过,樱镇除此而外,就是社会贫穷、古风不存、上访不断、发展迟滞甚至成了社会发展耻辱的象征。新世纪以来,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以樱镇为代表的当下农村处于变革的激流险滩中。当然,在“城市病”相反向度的乡村自然意象建构上,小说中的樱镇亦非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哲学的形而上书写。相反,却是对“风水好”的当代乡村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忧患意识的书写,因而与乡土文学抒情一派的审美意象化书写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差异化特征。
一、深阔的现实主义乡村书写
《带灯》中的乡镇综治办作为基层职能部门,既是“丑恶问题的集中营”[1](39),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冲器与减震器。“综治办”之“综”凸显了基层问题的错综复杂与交结。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根植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礼制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业已分崩离析[2](1)。其实,退一步来说,即便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乡间村落亦非古之士大夫隐逸与雅怀的世外桃源,因为古代文学史上的“悯农”作品可谓历代不乏,其中官逼民反的历代农民起义就是最直接的明证。在“治”与“乱”的社会更迭与历史潜进中,一部乡村社会史也可说是一部矛盾史与发展史。如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么带灯在基层工作的历练与洞察中,如上访、超生、农民工职业病、洪灾、旱灾与天灾,干部升迁、基层干部克扣、套取国家补贴等,一桩桩一件件的案件,乡村之殇再次刺激着国人的敏感神经。从全球化视野来说,作者经由本土方块字的文学叙事,其暴露式、批判式的乡村现代化书写,无不是“三农问题”的中国经验表达。在其显微镜的乡土社会转型叙事中,以樱镇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卷入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式阵痛、分化和蜕变的历史洪流之中。在急遽的社会转型中,农村不再是静古深幽的一潭死水,相反却是暴雨冲击后的活水,但在没有沉淀之前,可以说是清浊难辨。体现在小说叙事形态上,作者没有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反却是沉潜于坚实密匝的乡村社会镜像的描摹上,表现在叙事形式上,全书分为山野、星空、幽灵三大部分,然而每一部分中又有若干小标题。经过统计,小说共由281则小片段组成,这其中,除去“给元天亮的信”的重复性小标题25处,小片段实有256处。就其体例创新而言,如是创新不过是凌乱、无序、纷杂“三农问题”的当下呈现。但是,“三农”问题的呈现又剑指了原因式的探索,但是路在何方却是一个暂无答案的迷惘。
中国是农业大国,如果不认识中国的农村,也就很难认识中国。带灯位处乡镇综治办角度,应该说比较易于管窥出乡村社会的庐山真面。如小说叙写了樱镇的上访户、贫病户、暴发户等特殊群体的生存镜像。在天灾叙事上,旱灾之后的洪灾,百姓洪荒一般求生避难,然基层官员却瞒报、巧报、缓报死亡人数,同时则树立抗灾先进典型为己表功,继而为仕途升迁铺好道路,百姓却命若草芥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经济发展上,外来资本的涌入使樱镇薛元两家反目成仇,根由在于镇属沙场开发权的利益争夺。在市声如尘、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樱镇元家兄弟的暴富使其欲望急遽膨胀。如果说“人是英雄钱是胆”,那么金钱欲望则刺激着他们更大的野心与欲望。在这场“淘金”角逐与人性裂变中,宗族械斗的使狠斗强,其场面异常血腥酷烈,其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向钱看”的欲望被现代工商业社会激活。然在金钱欲望的背面,裹挟其中的是权力的规训与攀爬,如樱镇的一把手脚踹住院的元家兄弟以泄私愤,其封建家长式的做法源于一己升迁受到牵累。因而,按照当地百姓的说法就是“樱镇废官”。不过,在一“废”字褒贬中,实则是乡土民间的针砭之音。自古及今的官方主流话语中,如“以农为本”与“民为天下先”,然在“官本位”与“民本位”博弈中,激起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古音的在场。再则,官方在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太少,所以村民围堵施工队。在乡土民间,有句屈辱性的政治话语叫“民不与官斗”,但樱镇老百姓的与官斗,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百姓民主意识的觉醒。只是这种意识的觉醒却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有的视政府为“唐僧肉”,有的贫病交加却不知道如何向政府求助,内中的权利维护也是驳杂难辨。再则,小说也在重复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一味堵截式的维稳并不是济世良药,因为只“堵”不“疏”并不能从根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等多个层面的改革。在此意义上,小说实属批判现实主义的“三农问题”的坚实书写。
二、精神苦役的带灯夜行
带灯的名字本来叫“萤”。在小说的开头,带灯看见萤火虫“夜行时自带了一盏小灯”,于是自易其名为“带灯”。其实,改名之初已为后继的身心矛盾埋下了伏笔,喻示着她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因而“带灯夜行”隐喻的是现实问题的沉重与心灵佛灯的常在。应该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前者为现实制度所制约,后者为心性修养所涵盖。但是,带灯最终患上了夜游症。不过,从结局反观过程,带灯患上夜游症不是没有征兆的,因为随着带灯看到太多的农村问题,她给元天亮的短信也越来越多,表征的是现实问题的沉重与驳杂,加重的是其内心难以超逸的沉郁,因而,小说结尾写带灯患上夜游症可谓水到渠成。带灯身虽为官,心实属民,“萤火虫”与“带灯”的人虫意象的交叠与相互阐发,使得“萤虫生腐草”即为其且行且吟孤芳心曲的自显。作为综治办主任,官仅为其谋生的岗位所在,因为她“没想过当官”,因而“官”不过是其外在的身份符号而已,然内心则存有佛眼观世的一盏心灯。在综治办的基层工作中,她看得太真也看得太清。“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因为难得“糊涂”而使其产生厌世的生命倦意。古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聚焦在樱镇缩影版的官场镜像中,则更显人性底色的光亮与灰暗。带灯既想做到左右逢源又想做到超凡脱俗,但身置其中却又有口难辩,因而,她从问题纠结直逼到心灵的澄澈与轻柔,后者主要蕴含在她给省城“元天亮”的25次手机短信中。
在现代讯息社会,手机通信实属平常。不过在该部小说中,手机通信则是一则有意味的形式,本质上是“书信体”小说叙事形式的变种。这种叙事策略的目的,旨在虚设一个隐含读者。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省城的元天亮不过是一个听者的在场,是其内心郁结与无法告白的一个听众,换言之,也就是每位读者。就每位读者来说,只要熟悉农村生活,他们就既是旁观者也是见证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现在身居城市的城里人,然“三代以前,谁不是农民?”因而,也就在这场“说”与“听”的叙事交流过程中,铺开了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在这场心灵私语的单向倾诉中,有两个显著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在性别意象上,是女性向男性诉说;二是在空间意象上,是乡镇基层公务人员向省城公务人员诉说。就在这两个特征中,内中可以离析出一个基本的视角结构,即现代文明对乡村社会的审视。基于此,在这场诗情忧郁的单向倾诉中,就带灯与元天亮的名字而言,“灯”也好,“亮”也罢,其实皆与“光”相关。就“带灯夜行”的隐喻而言,见证的是“三农问题”的盘根错节,因而身居“综治办”,她在“能办不能办”与“不能办却要办”的问题交集中,元天亮是其心灵缓释与表白的私密对象。之所以私密,就是带灯的私语不被外人所知,当然,其弦外之音,就是这种倾诉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即便是其闺中密友竹子,也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此意义上,竹子是秘密的不经意的发现者。当然,竹子意外的发现,又不过是与读者心灵思域与期待视野的融合。在私密的诉说中,说者隐匿了现实沉重的深切,相反,物极必反地蹈向心灵飘逸的空灵,两者张弛有力疾徐相间。如是叙事从叙事技巧上来说,即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然,带灯不过是作者心灵镜像的一个投影,闪现出作者的苦心与悲心。从带灯作为管理者的“有为”到化身为民的“难为”移位思考中,也反映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拯救者的无力与无奈,因而,“带灯夜游”表征的无非是一个理想者的生存悲剧与精神内伤,其“夜游症”可以说使这个世界受损良多。
就带灯的悲剧性来说,亦可说是性格决定命运的体现,而性格既体现于尘世的处世中,也潜隐于心灵私密的一隅。首先,就尘世的工作常态来说,在综治办这个社会问题的火山口上,她既耳聪目慧又机敏干练,既菩萨心肠又金刚怒目,既潜身官场又混迹于民间,既带着人格面具又饱含内心澄澈的柔情。在俯视角的问题审视与仰视角的衷肠如歌中,外显与内敛交替潜进的话语脉络,使得前者为现场近观的在场,后者为心境超逸的远游。这种“我非我”与“我是我”的角色冲突,既喻示着现实与理想的紧张关系,又寓意着性格组合的矛盾关系。当然,正是这种矛盾冲突,使得带灯在面对浊气的同时,又有着灵气的心灵回返,短信灵动温润的倾诉,即为其心灵密码佐证的材料。换言之,带灯则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而,这种心灵私语显得尤为珍贵。其次,就内心之雅来说,带灯有着传统文人的诗情雅趣,如带灯喜欢吹埙与作画等。在其个人婚姻选择上,当初嫁给县城中学的一位艺术老师,就是因为她特别喜欢丈夫所画的梅花与兰花。显然,喜好梅兰竹菊是典型的文人精神的象征。但是,丈夫最终去了省城,他从雅怀之画到卖画赚钱,意味着两者价值取向的南辕北辙,也是两者后来劳燕分飞的原因所在。同样,樱镇的副镇长组织去歌厅唱歌,大家模仿的是大众流行歌曲,然带灯清唱的则是越剧版《红楼梦》的古曲。如是当代流行歌曲与传统古曲的并置,前者为下里巴人之俗,后者为阳春白雪之雅,其文化心理显得独自高格。在俗的大文化环境中,雅的提升更显得心曲寂寥与知音难觅。第三,带灯栽有指甲花,然在洪灾之后,红花已奄然化为尘泥,隐喻其生命仅有诗意的谢幕与枯萎。但是,小说结尾写道“带灯如佛”,因而带灯的“我佛慈悲”却也是精神苦役的孤行者与幸福者。
三、历史与现实的告白无援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治的结果,就是国家无论在宏观决策还是在户籍制度上,以及在人力、财力、物力的配给上,城市以绝对的优势领跑中国社会的发展,相反农村却发展相对迟滞。就城乡发展失衡的社会大峡谷而言,它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体现在小说空间地理上,樱镇之樱的“樱”可谐音为“阴”,暗喻着乡村社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边缘;再则,带灯身为女性,显然属阴。在空间与性别双重交叠隐喻的背后,指向的是社会现实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在场,即内蕴其中的是城市与乡村空间之维的性别化隐喻。当然,这种性别化的隐喻也不是附会穿凿,因为在向元天亮单向度倾诉中,带灯的人生与情感双重依附性甚为显著,这也许会招致女权主义的诟病。但是,在从城乡空间的文化诗学维度上来说,城市显然呈现出“父权”文化特征,乡村呈现出女性特征,因为一则不争的事实,就是城市发展成了现代新农村发展的时代标杆。在樱镇的发展历史上,当年的元老海阻止修高速公路,理由就是保住樱镇的好风水,但结果却成了全县最贫困的乡镇。从文化深层次矛盾来说,元老海的决绝反抗是对现代文明的敌意与恐惧;不过,元老海的反抗还是无意识层面的。但是,现任的书记引来了大项目,美其名曰是发展循环经济,但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一场政治秀?据小说交代,樱镇是秦岭山脉最美丽的所在,但作者通过带灯之口,意在警戒世人的惯常意识,即经济发展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破坏的代价,甚至留下的只是残山剩水。在带灯看来,“不开发也许就是最大的开发”。这种理想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巨流中却又显得空谷足音,继而使其陷入无物之阵的知音寥寥。但问题是,如果带灯本人就是书记呢?她会不会也像书记一样为了政绩工程而求得仕途的晋升呢?其实,在中国官场上有个潜规则,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而,带灯的生态批评不过是边缘者批判视角的体现。或许这种后现代的解构思维过于苛刻威猛,即无情解构了带灯作为批判者之批判的最后阵地,但起码能解析出批判者亦有被批判的可能性。
面对综治办的诸多问题,带灯一味地给元天亮发短信诉说,然元天亮则很少回复,这其实也喻示着带灯处于政治话语的边缘。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形同于无的听众意味着叙事交流的断裂与失效。但是,正如叙事学家热奈特所言:“叙事的真正作者不仅仅是讲述它的人,而且也是,有时更是,听叙事的人,而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叙事针对的听众,因为隔壁总有人。”[3](186)于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元天亮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真正的听众则是每位读者。然这种“所诉非所听”与“所听非所诉”的矛盾,则给小说题旨的阐释带来似直实曲的意义解读空间。究其根源,一方面,元天亮虽为省府副秘书长,后升任至省委常委,但他来自樱镇的农村,农村有其难忘的生活经验,他比带灯更心知肚明农村的现实。说得更尖锐些,或许他正在暗自庆幸自己走出了农村,他与故乡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功利关系,有的或许就是一点家乡观念与诗意的乡愁。另一方面,元天亮称故乡为“血地”,内中体现的是爱与恨的复杂情感[1](235)。再则,在血缘“父子关系”隐喻上,元天亮也背叛了自己先人的理想,但这种背反却又暗合了基层官员升迁与百姓致富的渴求,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此意义上,带灯看似空灵的抒情地方,是其叙事最失败的地方,因为她倾诉的对象却也是樱镇人引以为豪的功利化的一张名片。当然,即便元天亮与带灯的思维一致,但时处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巨流中,其结局也不过是螳螂当车。遗憾的是,带灯却一厢情愿地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伴侣。实际上,在带灯遭致不公正待遇之际,真正同情带灯遭遇的则是她的那些情同姊妹的“老伙计”。当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最得意的神来之笔,或许就是竹子将带灯成为“替罪羊”的隐情透露给了王随风,而王随风此前是综治办重点布控的上访户,然王随风马上心领神会竹子的意图,这或许就是他们“化敌为友”的最大和解。这种化解与一切政治无关,它不过是道德良知的自然体现,这也许就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大胜利。再看小说扉页上的带灯心曲,即“或许或许,我突然想起,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其实,既然心有佛意,而“我佛慈悲”,因而,带灯向元天亮倾诉也就显得世俗的多余。既然如此,那么小说结尾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中,写松云寺下萤火虫阵中的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光晕。如是结尾的处理,不过是对带灯现实的败退的想象式精神安慰的表达,也就是说,在告白无援的现实困境中,作者赋予了带灯一种超越政治的审美批评,即心中有佛则佛力无边。
四、问题表述的叙事策略
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从看到说,再从说到听,樱镇的带灯与省城的元天亮一直是在场者。两者在空间性别诗学、“三农”问题发现与叙事交流意义上,都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叙事策略。作为“说者”的带灯不过是作者设置的一个叙事人物;而作为“听者”又转移至省城的元天亮身上,这种视线转移不过是从文学界转向官场的障眼法,因为元天亮终不过是作者伪饰一己心迹踪影的虚设对象,因而在如是心迹罅隙的背后,内中存有作者自传式文化心痕的在场。小说中的元天亮是樱镇走出去的第一位农裔大学生,毕业后因文采出众而走上仕途且仕途顺风顺水;相反,带灯则工作在乡镇基层,她所遇到的是诸多痛点、难点与焦点问题。于是,小说文本生成了乡村“出走者”与“外来者”的基本情节结构。从结构主义叙事学上来说,这种“出走”与“外来”不过是作者城乡游走心路历程的变通式的体现。因此,这种构建于空间化基础上的陌生化、距离化的视角暗置,亦不过是作者自传式通过“返乡者”与“外来者”视角,继而揭示出“三农”问题的峻切与复杂。
从创作心理学上来说,作者本是农民,后因创作而成了农裔城籍作家,但却难忘生身故土与文化身份的始源,这典型体现在《我是农民》的心路自传中。因为是农裔身份,继而将叙事声音移花接木于带灯身上,这种移情无非是通过异性化的心理转移,继而彰显作者冷眼观世的心路历程的丰赡与苦楚。但问题是,随着带灯倾述衷肠的深入,带灯越来越视元天亮为自己的“知己”与“家人”。于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元天亮与带灯是怎么产生爱恋的,爱情的缘由是什么?小说缺少的是坚实可信的情感铺垫。当然,从小说情节的枝干上来说,避免的是情节的过于散漫,继而便于当下“三农”问题的凸显。不过,针对这种缺失性而言,只能说是两者神交已久,或亦可理解为作者神来之笔的表述策略,因为,后来带灯说自己与元天亮的关系,就是“你是我城里的神,我是你山里的庙”,继而“成了你庙里的尼姑”,她坚信自己在庙中静心修行与边修边行,因之倒也觉得安然与释然,也似乎能从庸俗中解脱出来。遗憾的是,带灯精神危机的体现形式,就是她患上了夜游症。因而,带灯向元天亮倾诉得越多,那么她的内心也就愈加落寞,喻示的是官场元天亮声音的孱弱与无力;然,越是元天亮无声缄默的地方,却越是作者叙事策略最达意的所在,因为,作者经由文学的表述形式,构建的是政治话语无力的元天亮的人物形象。对此,有两种解读策略,一则是作者或许弄巧成拙的叙事败笔,一则是作者有意而为却又不露声色地对政治话语的反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问题的表述上,在“说”与“被说”的叙事结构中,农村成为了当代作家创作资源的一座富矿,亦可说是后乡村文学的一种生长点,体现着文学与历史的共振效应,诸如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莫言的《蛙》,刘醒龙的《凤凰琴》等,这些都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文学表述,内中有着太多的问题式写作且已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就《带灯》而言,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小说中的群众上访事件层出不穷,然如何民主化、法制化、合理化地处理这些问题,恐怕是仅凭一个带灯的“带灯如佛”与“带灯夜行”所难以胜任的,因而,在乡土悲歌的叙事背后,留给社会的则是问题求解的无尽思考。
[1] 贾平凹. 带灯[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3] [法]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Sad melody in China’s countryside: Walking along singing in the Nasty World
XU Xinho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School of Literature, Art & Media, Bengbu, 233030, China)
Jia Pingwa’s new novel “Dai Deng”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ural disease in China’s countryside. Firstly, the aesthetic effect on the subject of rural diseases unfolded by way of defamiliarization and aesthetic distance based on the “leaving-returning” narrative structure; Secondly, the monologue ofDai Deng, the leading character was shown by the novel’s epistolary style which described the contradictory complexity in the grass-roots units and her character combination; Third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Dai Deng’ssomnambulism image, the novel suggested the deconstruction of idealist mental servitude and the dissoci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s. Finall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throughout the novel, probed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gaps on the narrative voices by coming off the breaks and effectiveness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s.
jiapingwa;Dai Deng; rural fission; realism; epistolary style; narrative perspective; poetics of space
I247.5
A
1672-3104(2014)02-0234-05
[编辑: 胡兴华]
2013-07-23;
2013-10-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99)
许心宏(1979-),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