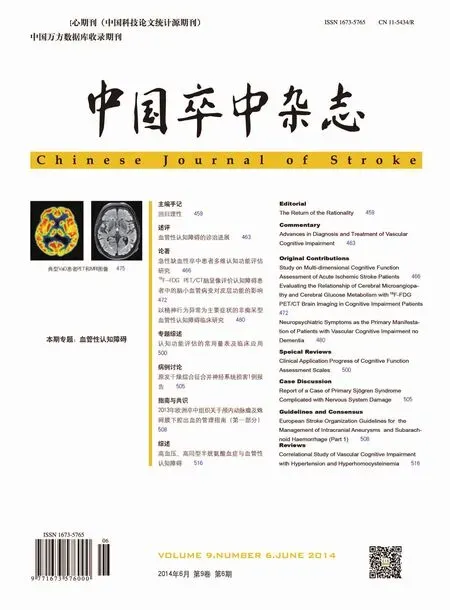中国缺血性卒中早期静脉溶栓的现状、阻碍因素及改进策略
徐安定,丁燕,李牧
1 AIS静脉溶栓循证证据及指南推荐简介
1995年,美国国立神经疾病和卒中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NINDS)研究首次证实了AIS发病3 h内静脉rt-PA溶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5]。2009年,AIS静脉rt-PA溶栓的时间窗扩至4.5 h被欧洲急性卒中协作研究(European Cooperative Acute Stroke-Ⅲ,ECASS-Ⅲ)直接证实[6]。中国AIS患者发病4.5 h内静脉rt-PA溶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到AIS中国溶栓应用及监测研究(Thrombosis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 of AIS in China,TIMS-CHINA)的证实,且标准剂量(0.9 mg/kg,最大不超过90 mg)亚组疗效优于较低剂量亚组,出血风险一致[7-8]。AIS发病6 h内静脉rt-PA溶栓的国际卒中研究(International Stroke Trial,IST)-3整体上为阴性研究结果[9]。
基于上述证据,国内外指南或共识均高度推荐AIS发病4.5 h内使用静脉rt-PA溶栓,强调越早溶栓越好[10-12]。基于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研究结果,静脉尿激酶溶栓得到中国脑血管病指南的推荐(发病6 h内适用)[12],但其研究证据不被国外同行所认可,2013年版美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明确推荐尿激酶静脉溶栓仅限于临床研究时使用[11]。包括动脉内溶栓在内的血管内治疗虽可能对部分大血管闭塞患者适用,但未获得其优于静脉rt-PA溶栓的证据,目前指南均推荐发病4.5 h内适宜静脉溶栓者应该首选静脉rt-PA[11-12]。2013年发表后的3项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又进一步证实了指南推荐的证据,因为对大血管闭塞患者,血管内治疗并不优于传统静脉rt-PA溶栓[13]。
2 我国AIS的静脉溶栓及规范化干预现状
虽然时间窗内静脉rt-PA溶栓是治疗AIS最有效、最应被推广的方法,但因为时间窗限制等因素,其全球范围的使用率都很低,美国近年报告显示仅占所有AIS患者的2.4%~5.2%[2]。而在溶栓时间窗内,溶栓所占比例也不高。收集2009-2010年数据的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发病4.5 h内到达医院的AIS患者中,仅14.7%的患者接受了溶栓[14]。而我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纳入我国2006年62家医院数据的中国卒中干预医疗质量评价(China QUality Evaluation of Stroke care and Treatment,CHINAQUEST)研究显示,发病3 h内到达医院接受溶栓者为8.9%(91/1019),占所有AIS患者的1.9%[15]。2006年在中国7个一二线城市31家中心(80%为三级医院)进行的一项为时50 d的横断面前瞻性研究发现,仅2.7%(20/754)的AIS患者接受了溶栓,其中15例为静脉rt-PA溶栓(2.0%)[16]。纳入国内多中心2007-2008年的中国国家卒中登记(Chinese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CNSR)中,溶栓比例为1.9%(284/14 702),占发病3 h内到达急诊患者的11.3%(284/2514),其中静脉rt-PA溶栓仅占在发病3 h内到达急诊的7.16%[17]。而同期在美国开展“跟着指南走”的医院中,发病2 h内到达急诊的AIS患者中,其平均静脉rt-PA溶栓率已经提高到70%[18]。
除总体溶栓率、特别是时间窗内到达医院溶栓率低之外,我国AIS溶栓还存在以下特点:①使用低剂量rt-PA行静脉溶栓。七城市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中,15例静脉rt-PA溶栓者有13例使用了低剂量[16];CNSR研究显示静脉rt-PA溶栓患者中的44%采用了低剂量[8]。②由于中国指南推荐发病6 h内可以采用静脉尿激酶溶栓,以及rt-PA的相对高价格,我国部分患者接受静脉尿激酶溶栓,少数患者接受静脉rt-PA的时间超过4.5 h。此外,在可以开展血管内治疗的单位,存在部分适合静脉溶栓指征的患者接受了动脉溶栓,而且血管内干预指征存在被盲目扩大的现象。但目前缺乏全国性或多中心研究报道的具体数据。
3 阻碍AIS静脉溶栓的因素及改进措施
3.1 院前因素 AIS溶栓率低下最重要的原因是患者不能在时间窗内到达可以开展溶栓的医疗中心而失去溶栓机会。即使在发达国家,能在溶栓时间窗内入院的患者也仅占所有AIS的17%~20%[19],澳大利亚的一项近期资料显示只有31%的AIS患者能在发病4.5 h内到达医院[14]。综合我国前述七城市研究、CHINA-QUEST和CNSR资料,约80%的AIS患者不能在发病3 h内达到医院[15-17]。
3.1.1 公众健康教育 导致患者不能在时间窗内到达医院的首要原因是未能及时呼叫急救系统(emergency system,EMS)或未及时就诊,而其主要原因为患者或家属对卒中知识的匮乏,包括卒中早期表现以及在发生疑似卒中表现后应该作出的正确反应,尤其是当症状较轻或症状有改善,或等待症状是否有所改善时[2,14,19-21]。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仅22%的患者在发现异常后意识到可能是卒中表现,而在症状出现1 h内呼叫了EMS[22];美国密歇根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3的被调查者知晓rt-PA溶栓为卒中的治疗手段,只有1/6知晓溶栓时间窗[23]。我国的资料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城市居民中,对“肢体麻木、瘫痪、语言障碍、口角歪斜、严重头痛”这所谓5个“卒中警报征”的单一知晓率虽可达约70%,但全部知晓者比例仅为3%~16%,而表示一旦发生卒中后会立即拨打急救电话的比例则更低[24-26],提示对AIS溶栓知识的高度匮乏。另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已经发生卒中表现的患者中,只有1/4的患者知晓其可能需要溶栓并需要急赴医院,约1/4的患者忽视已经发生的表现,而选择等待[27]。
此外,国外研究表明,通过非呼叫EMS来求助会导致相关救治时间延长,而通过急救车转运患者可减少院前及入院后时间延误,增加进入卒中单元并实施溶栓的可能性[19-21]。美国近年采用非EMS到达医疗中心的急性卒中或亚急性卒中患者的比例依然高达50%[21]。CNSR研究资料显示我国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0%,其中54%经出租车、18.5%经私家车、2.5%经自行车或三轮车,仅18.9%采用了呼叫EMS这一模式到达急诊[17]。CHINA-QUEST研究提示寻求社区医生而不是EMS也是导致我国院前延误的重要因素之一[28]。
美国、欧洲、日本等数个平行或前后自身对照研究已经证实大众健康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公众对卒中早期表现以及发生卒中后应采取正确措施的认识,提高呼叫EMS电话比例,明显减少院前延误,提高溶栓比例,但干预措施停止后又回复到基线水平[2,21]。北京一项针对5万社区人口的研究也证实强化健康教育使卒中患者院前延误时间从180 min降至79 min、3 h到院率从55.8%增加到80.4%、呼叫EMS电话者从50.4%升至60.7%[29]。
院前公众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卒中早期表现、发生疑似卒中应拨打EMS电话以及早期溶栓的重要性和时间紧迫性。5个“卒中警报征”曾被推荐作为识别卒中表现健康教育的工具,目前已经被以FAST评分为代表的更简单、实用、更能识别早期卒中表现的工具所替代,并获得临床研究证据的支持[11,21,30]。所谓“FAST”为口角歪斜(Face)、单侧上肢平举无力(Arm)、语言障碍(Speech)时,立即寻求救助(Time),当出现单一或多个表现时需要即刻拨打EMS电话。
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及不发达地区广泛,其公众卒中健康教育任务艰巨、迫在眉睫,而常态化的要求更是增加了长期坚持的难度。应该建立我国公众卒中健康教育的完整体系,建议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财政投入、专业人员组织实施,组织各种医疗机构、媒体、民间及慈善组织积极参与。特别呼吁各种媒体长期开展公益性公众卒中健康教育广告;医院、卒中团队成员及其他医务人员成为具体实施环节中的关键力量,在医院、媒体、社区举行常态化的卒中健康教育宣讲,而医疗场所的每一个卒中患者及其家属都是宣讲对象;长期免费发放各类卒中健康教育资料等。
3.1.2 院前转运 疑似卒中患者被送往不具备溶栓能力医院是院前延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21,30]。瑞士一项研究显示20%发病3 h内的AIS患者被送往不具备溶栓能力的医院[31]。急救人员对卒中认识不足、不能尽快正确识别卒中患者并将疑似卒中患者作为优先处理对象、不了解AIS溶栓时间窗以及将患者送至未开展溶栓的医院是时间延误的主要原因,而针对EMS医务人员的卒中知识培训可以明显减少因为转运导致的时间延误[2,21,30]。FAST、辛辛那提院前卒中评分、洛杉矶院前卒中评分等作为急救人员快速识别早期卒中工具的有效性得到证实[2,19-21]。美国开展的卒中中心以及急性卒中救治医院(Acute Stroke Ready Hospital,ASRH)的认证工作,为EMS优先将卒中患者送往合适的医院提供了基础,并据此给出了转运患者的具体推荐意见,而伊利诺伊州、加州更是已经从法律或行政手段规定疑似卒中患者只能被送往卒中中心或ASRH[2,21]。
我国目前尚缺乏系统性针对EMS人员卒中知识培训的工作,也尚未开展卒中中心或类似ASRH的认证制度,且不是所有医院乃至三级医院均开展了AIS的溶栓。因此我国EMS将疑似卒中患者送至无条件行溶栓医疗中心的现象可能更为严重。2007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北京48家三级医院、76家二级医院中只有54家单位开展了静脉rt-PA或尿激酶溶栓[32]。CHINA-QUEST研究发现转运到三级医院是我国AIS患者院前延误的另外一个因素[28]。我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各地区120指挥系统所支配的急救人员和救护车的管理体系不一致。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部地区医疗中心救护车统一由120系统分配,以就近原则派各医疗中心救护车和急救团队前往。另一种是将120指挥系统、车辆直接挂靠给某一家医院,急救团队由挂靠医院负责。在目前缺乏卒中中心或ASRH认证、急救体系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的基础上,在目前缺乏卒中中心或ASRH认证、EMS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的基础上,这两大类体系都无法有效保证将疑似卒中患者快速送到具备溶栓能力的医疗中心。
一直以来,英美法系未给与“排除合理怀疑”一个准确的定义,虽然未妨碍该制度发挥着良好的效用,但是终归不妥。如果法律不能被其本身所理解,既不能为法官所把握,更不会被大众所接受。我国刑事诉讼原来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纯粹的客观主义证据立法,而“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的主观主义证明标准,这其实体现了我国证明标准已经走向了主客观的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功能定位,就是要从主观方面为“证据确实充分”提供判断依据,使之更具有操作性。“证据确实充分”需要三个条件:
因此,建议政府机构或学术团体尽快启动卒中中心认证以及类似美国的ASRH认证项目,或者将卒中医疗质量管理指标明确纳入二级及以上医院等级评审标准;让公众和医疗EMS知晓应将疑似卒中患者尽快、尽可能送往具有溶栓资质的医疗单位;积极开展针对EMS医务人员的卒中健康教育。
3.2 院内因素
3.2.1 院内延误 院内延误是阻碍AIS患者溶栓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针对发病时间窗内到达急诊的患者。患者从到达急诊至开始静脉rt-PA的时间(door to needle time,DNT)是评价院内时间延误的指标,其中涉及入院后对患者进行紧急处理的多个部门、多个环节。院内延误虽然不可避免,但是未经流程干预的DNT一般远超过60 min,如我国七城市研究资料显示其平均DNT高达167 min[16],CNSR研究平均DNT为115 min,DNT<60 min的比例不到10%,与美国、加拿大同期指标相比差距巨大[17]。DNT的延长,使得一些可以在时间窗内溶栓的患者失去溶栓机会。
导致DNT延长的主要原因包括[2,14,21,31]:①急诊不能对患者进行快速正确评估及简易干预,对于卒中症状、卒中治疗及卒中溶栓时间依赖性认识不足;②不健全的急性卒中管理系统,如缺乏随时准备的急性卒中团队、缺乏适合溶栓患者紧急神经影像学及必要检验的临床路径等多个方面;③不必要的多模式影像学检查;④卒中团队医生对实施溶栓的不确定性等。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静脉rt-PA溶栓获益的证据是来自于基于临床和计算机断层扫描筛选患者的研究,而多模式影像学检查会使DNT明显延长[33],现有指南均明确推荐多模式影像学检查不应导致院内延误时间的延长[10-12,21]。
英美等发达国家静脉rt-PA溶栓无需知情同意,而我国由于国情不同,溶栓需要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由于患者及家属对卒中及溶栓知识相对欠缺,加上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目前医患矛盾突出,容易使知情谈话失败或签署时间明显后延,导致具有溶栓适应证患者溶栓率的进一步下降和DNT的延长。CNSR研究显示从获得影像学检查结果至开始使用溶栓药的平均时间为85 min,较同期欧美国家多出30~60 min,是我国目前DNT较欧美国家明显延长的主要原因[17]。
欧美国家缩短DNT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主要方面[2,21,34-36]:①对EMS/急诊医务人员进行卒中识别及正确干预的培训。②组建院内卒中团队。③简化和优化干预流程:由院前EMS直接激活医疗中心卒中团队、抛开急诊科而直接将疑似卒中患者送往影像学检查;将静脉溶栓战场直接前移到影像中心或急诊科;2013年美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为简化溶栓流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它明确指出溶栓前必须获得的辅助检查指标只有急诊血糖、末梢血氧饱和度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结果的解读(不是书面报告),强调“虽然最好能在静脉溶栓前获得血常规、血电解质、肾功能、凝血功能、心肌缺血血液学指标及心电图检查结果,但不能因为等待这些结果而延误溶栓,除非临床考虑出血性疾病或血小板减少、患者正在接受肝素、华法林及其他抗凝药物治疗”。④以核心指标的目标管理为重心,建立相应的医疗质量指标监控及持续质量改进体系。其中3个关键的时间指标为:患者到达急诊至卒中团队医生接诊患者时间<15 min;患者到达急诊至获得影像结果时间<45 min;DNT<60 min。
3.2.2 阻碍时间窗内AIS患者溶栓的因素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研究,时间窗内到达医院而未实施溶栓的原因主要为:年龄>80岁;轻型卒中或溶栓前症状快速好转;医生认为有溶栓禁忌证[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25分,CT大面积脑梗死征象或显示低密度灶等]。我国七城市研究资料显示未进行溶栓的原因如下:年龄(>80岁或<18岁)(28.9%)、卒中症状太轻(24.0%)、病情迅速恢复(16.5%)、CT影像已有病灶(15.7%)、时间>3 h(15.7%)、卒中症状太重(7.4%)等因素,而患者/家属主观拒绝占了18.2%[16]。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单中心研究资料显示,最重要的因素为NIHSS<5分或溶栓前症状快速好转(44/60,73%),其次为患者/家属主观拒绝,约为20%[37]。此外,国内的一些研究中心认为以心房颤动为代表的心源性卒中不适宜溶栓,但缺乏因此而未溶栓的具体数据。
事实上,基于现有证据,美国最新指南及中国专家共识对以下患者给出了明确积极开展静脉rt-PA溶栓的推荐:年龄>80岁(发病3 h内);以心房颤动为代表的心源性卒中;轻型卒中和溶栓前症状快速好转;发病时口服抗凝剂,但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 ratio,INR)<1.7[10-11]。美国指南明确指出CT上低密度灶超过大脑中动脉区域1/3是溶栓禁忌,而其他早期脑梗死影像学表现的患者和重
症患者溶栓依然获益[11]。
2010年我国卫生部正式发表了单病种质量管理手册,将发病3 h内到院AIS患者的静脉rt-PA溶栓率作为首要指标,采用了上述3个关键时间指标的前两个[38]。按照这一管理要求,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自2010年3月开始实施关键医疗指标监控,截止至2012年2月,将2 h内静脉rt-PA溶栓率由28.6%升至50%(19/38),3.5 h内到院溶栓率也有所升高,达到36.2%(34/94)[37]。2011年卫生部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立,随后成立了各省级的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全国建立526家哨点医院。全国许多医疗机构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脑梗死单病种质控以及卒中医疗质控的相应工作,但尚未见相关成效的具体报道。
鉴于减少院内延误、提高时间窗内到院患者静脉rt-PA溶栓率是目前各医疗中心所能做到、应该尽力做到的工作,各医疗中心应参照国外先进经验,尽量缩短DNT,提高时间窗内到院患者的溶栓率。结合我国特点,应积极开展针对轻型卒中、溶栓前快速好转、以心房颤动为代表的心源性卒中的溶栓;建立标准化、通俗化、科学化的知情谈话同意操作规程,提高知情谈话同意率;严格掌握血管内治疗适应证,避免用血管内治疗代替静脉rt-PA溶栓,优先推荐静脉rt-PA而不是尿激酶溶栓;采用美国指南推荐的简化的溶栓流程,结合各自医院特点建立适合的绿色通道;尽量提前激活卒中团队和急诊CT,将溶栓战场前移到急诊或急诊影像检查室;实施关键指标目标管理和持续医疗质量改进等。
综上所述,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静脉溶栓治疗AIS在中国应用明显低下,时间窗内的应用则差距更大,同时存在更长的院前和院内延误。国内外经验显示,采取针对性措施,上述指标均可得到明显改善,改善患者的预后。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获得我国目前更为全面的现状,了解存在问题的环节,提出解决方案。应形成广泛共识,全面推广已经获得的国内外优秀经验,有计划有系统地改善我国缺血性卒中早期静脉溶栓的医疗质量。已经启动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脑血管病急性期诊疗技术规范化应用和医疗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技术研究”(2011BAI08B02)已经全面开始,应用管理流程再造理论“脑卒中医疗质量改进项目:缺血性卒中急性期溶栓治疗改进体系的建立”的子课题即将开始。两项课题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中国AIS静脉溶栓的规范化开展,提高医疗质量。
1 Wardlaw JM, Murray V, Berge E, et al.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acute ischaemic stroke: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Lancet, 2012, 379:2364-2372.
2 El Khoury R, Jung R, Nanda A, et al. Overview of key factors in improving access to acute stroke care[J].Neurology, 2012, 79:S26-S34.
3 Meretoja A, Keshtkaran M, Saver JL, et al. Stroke thrombolysis:save a minute, save a day[J]. Stroke,2014, 45:1053-1058.
4 Fonarow GC, Smith EE, Saver JL, et al. Timelines of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herapy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patient characteristic, hospital factors and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door-to-needles within 60 minutes[J]. Circulation, 2011, 123:750-758.
5 No authors listed.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and Stroke rt-PA Stroke Study Group[J]. N Engl J Med, 1995, 333:1581-1587.
6 Hacke W, Kaste M, Bluhmki E, et al. Thrombolysis with alteplase 3 to 4.5 hours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J]. N Engl J Med, 2008, 359:1317-1329.
7 Liao XL, Wang YL, Wang CJ, et al. Thrombolysis with intravenous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3 to 4.5 h after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China[J]. Stroke, 2012, 43:A62.
8 Liao XL, Wang YL, Pan YS,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acute stroke patients receiving different dose intravenous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J]. Stroke, 2014, 45:AWP63.
9 IST-3 collaborative group, Sandercock P, Wardlaw JM.The benefits and harms of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within 6 h of acute ischaemic stroke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troke trial [IST-3]):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Lancet, 2012, 379:2352-2363.
10 Xu AD, Wang YJ, Wang DZ,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intravenous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o treat acute ischemic stroke by the Chinese Stroke Therapy Expert Panel[J].CNS Neurosci Ther, 2013, 19:543-548.
11 Jauch EC, Saver JL, Adams HP Jr,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 Stroke, 2013, 44:870-947.
12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撰写组.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0[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10, 43:146-152.
13 Chimowitz MI.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still unproven[J]. N Engl J Med,2013, 368:952-955.
14 Eissa A, Krass I, Levi C,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low utilisation of thrombolysis in stroke[J]. Australas Med J, 2013, 6:152-167.
15 中国脑卒中医疗质量评估(QUEST)协作组. 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现状[J].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09,42:223-228.
16 王伊龙, 吴敌, 周永, 等. 中国七城市卒中患者急诊溶栓情况分析[J]. 中国卒中杂志, 2009, 4:23-26.
17 Wang Y, Liao X, Zhao X, et al. Using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o treat acute ischemic stroke in China:analysis of the result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Stroke Registry (CNSR)[J]. Stroke,2011, 42:1658-1664.
18 Fonarow GC, Reeves MJ, Smith EE, et al.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inhospital outcomes of the first one million stroke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dmissions in get with the guidelines-stroke[J]. 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2010, 3:291-302.
19 Kwan J, Hand P, Sandercock 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arriers to delivery of thrombolysis for acute stroke[J].Age Ageing, 2004, 3:116-121.
20 Mazighi M, Derex L, Amarenco P. Prehospital stroke care:potential, pitfalls, and future[J]. Curr Opin Neurol, 2010, 23:31-35.
21 Higashida R, Alberts MJ, Alexander DN, et al.Interactions within stroke systems of care:a policy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 Stroke, 2013,44:2961-2984.
22 Mosley I, Nicol M, Donnan G, et al. Stroke symptoms and the decision to call for ambulance[J]. Stroke, 2007,38:361-366.
23 Anderson BE, Rafferty AP, Lyon-Callo S, et al.Knowledge of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for acute stroke among Michigan adults[J]. Stroke, 2009,40:2564-2567.
24 孙海欣, 王文志, 江滨, 等. 中国四城市社区居民卒中知识水平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卒中杂志, 2012,7:618-625.
25 Zeng Y, He GP, Yi GH, et al. Knowledge of stroke warning signs and risk fac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previous stroke or TIA in China[J]. J Clin Nurs, 2012,21:2886-2895.
26 Yang J, Zheng M, Cheng S, et al. Knowledge of Stroke Symptoms and Treatment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in Western Urban China[J]. J Stroke Cerebrovasc Dis, 2014, 23:1216-1224.
27 毕齐, 张茁, 张薇薇, 等. 北京等15个城市脑卒中患者院前时间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 27:996-999.
28 Jin H, Zhu S, Wei JW,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ehospital delay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cute stroke in urban China[J]. Stroke, 2012, 43:362-370.
29 Chen S, Sun H, Zhao X, et al.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rotocol in decreasing pre-hospital stroke delay among Chinese urban community population[J].Neurol Res, 2013, 35:522-528.
30 Fassbender K, Balucani C, Walter S, et al.Streamlining of prehospital stroke management:the golden hour[J]. Lancet Neurol, 2013, 12:585-596.
31 Engelter ST, Gostynski M, Papa S, et al. Barriers to stroke thrombolysis in a geographically defined population[J]. Cerebrovasc Dis, 2007, 23:211-215.
32 Wang YL, Wu D, Zhao XQ, et al. Hospital resources for urokinase/recombinant 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herapy for acute stroke in Beijing[J]. Surg Neurol, 2009, 72 Suppl 1:S2-S7.
33 Uenaka T, Yoneda Y, Yamamoto S, et al. Brain imaging modality before systemic thrombolysis for ischemic stroke within three hours[J]. Eur Neurol,2010, 64:241-245.
34 Ford AL, Williams JA, Spencer M, et al. Reducing door-to-needle times using Toyota's lean manufacturing principles and value stream analysis[J].Stroke, 2012, 43:3395-3398.
35 Fonarow GC, Zhao X, Smith EE, et al. Improving door-to-needle time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principal results from the Target:Stroke Initiative[EB/OL].(2014-02-14)[2014-04-16]. http://my.americanheart.org/idc/groups/ahamah-public/@wcm/@sop/@scon/documents/downloadable/ucm_460266.pdf.
36 Coote S, Frost T, Singhal S, et al. Direct to CT:overcoming barriers to reduce door to needle time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J]. Stroke, 2014, 45:AWP177.37 赵颖, 辛秀峰, 徐安定, 等. 关键医疗指标监控对提高缺血性脑血管病临床医疗质量的作用[J]. 暨南大学学报, 2013, 34:186-190.
38 中国医院协会. 单病种质量管理手册[M]. 2版.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142-197.
【点睛】
分析我国急性缺血性卒中当前静脉溶栓现状、阻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