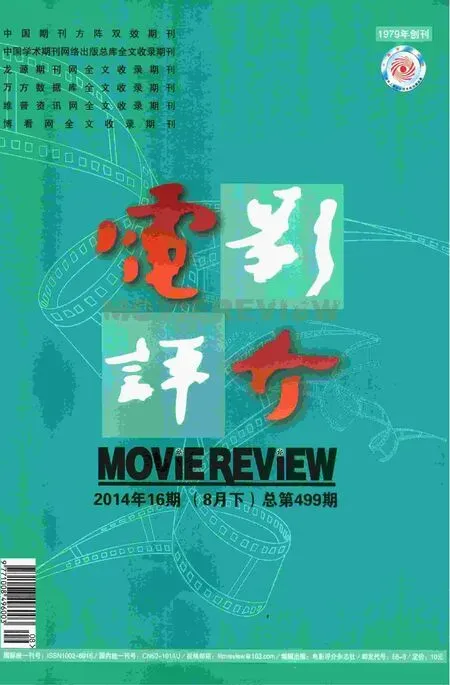西部神话的破灭与西部片的衰落
李 亚
西部神话的破灭与西部片的衰落
李 亚

电影《日落黄沙》剧照
西部片曾是好莱坞庞大的类型电影地图中最为耀眼的明珠。在其所有的类型片中,西部片的程式最为成熟,风格最为鲜明,也最受观众喜爱。在1926年至1967年的40年间,好莱坞所出品的电影中有四分之一是西部片。西部片也被认为是最为典型、最具美国风味的类型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了好莱坞的名片。上世纪50年代西部片迎来了发展的巅峰,10年间好莱坞共出品了800多部西部片,但就在这个辉煌之后,60年代西部片的数量开始大幅减少,至70年代,西部片已经几乎从大银幕上绝迹。
西部片的繁荣持续过这么长时间,着实令人惊异,而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曾创造了无数辉煌的类型片就这样迅速地走向了衰落。类型片的更迭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不但是电影产业内部变动的结果,也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西部片的衰落是西部片神话的破灭的必然结果,而西部神话的破灭又深受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重大变动的影响。
一、西部神话的繁荣
在巴赞看来,西部片就是一种神话。虽然西部片植根于真实的西部开发的历史,但它却与历史的真实截然不同。通过神话式的改造,发生在这片真实的土地上的一切事件都拥有了共通的内在本质,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西部片的表面杂质,就会发现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神话的基本原型,也正是西部片中所蕴含的神话本质使其获得了持久的动人魅力。
(一)文明
西部神话是一种文明发展的神话。西部拓荒的进程在美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扩展并巩固了美国的边疆,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概念,而且西部农牧业以及矿业的发展也成为了20世纪初美国经济腾飞助推器。在移民到达西部之前,这里不过是一片广阔的野蛮之地。通过移民辛勤的拓荒,文明的种子在这里萌芽并成长起来。而西部文明的发展又将这片新生的土地同东部连接在一起,并最终纳入了更大的美国的版图,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已经完成了西部开发的进程,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高速增长而逐渐成为了全球第一强国,其扩张主义自信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人心中,文明的发展是万事之首,其重要性不容置疑,这种集体性的精神诉求投射到了西部片中,便形成了西部片的文明神话。
文明是西部神话的核心元素,许多西部片以直接的文明开发为主题而构建。《大追踪》(The Big Trail,1930)在开场的字幕上直接宣告:“谨以此片献给:播种文明的拓荒者,以及继承他们勇敢拓荒精神的后辈。”故事正面表现了来自东部的移民车队,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向西前进的艰苦行程。而更多的西部片以文明发展为宏大背景,展现西部土地上的所进行的各类艰苦卓绝的斗争。
西部新生的文明敏感而脆弱,随时遭受着外部力量的破坏。脆弱的文明需要英雄的守卫,通过英雄的努力,威胁文明的力量被清除,社会秩序被重新建立起来。以文明为向心力,西部英雄和他们的敌人们在西部的土地上展开着持久的斗争,而西部片便围绕着这些守卫文明的战斗而建构起来。西部片的一个典型程式也因此形成——文明受到某种自然或者人为的力量的威胁,西部英雄向威胁文明的势力宣战,最终这些势力被清除,文明得以继续发展。
(二)权威
西部神话同样是权威的神话。经历了内战的美国社会认识到了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战后的美国以空前的速度扩大着自己的版图,短短几十年内便获得了超过三倍于东部的疆土。如何将这些新生的土地同东部连接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而正是权威发挥了它的强制作用,通过建立起法律与秩序,权威将东西部连接在一起,围绕着中央集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现代美国。并且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腾飞中,美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战胜利之后,美国政府更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此时,美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空前强烈,而美国政府作为团结美国民众的权威势力,也赢得了尊重与信任。美国社会对权威的好感体现在了西部片中。
权威由国家、政府、军队以及法律体系所共同组成,它在西部片中拥有不可置疑的强制性与正确性。权威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西部文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西部原本是一片荒蛮之地,正是权威的作用,才在这里建立起了新生的现代社会并赋予其秩序。完全可以说,权威缔造西部。
在西部片中,权威可以是具体可见的,事实上很多西部英雄就是服务于权威的工作人员,比如警察、法官、军人。权威也可以是不可见的,以观念的形态发生作用。但是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权威都统治着西部世界的一草一木。《黄牛惨案》(The Ox-Bow Incident,1943)中,追捕逃犯的队伍欲将三个嫌疑人在未经审判的前提下吊死,遭到了西部英雄的坚决反对。这些西部英雄所捍卫的正是美国的法律精神,虽然不可见,但它的尊严毋容置疑。《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1946)里的警长极力追捕的是杀人盗牛的白人牧场主,作为一种可见的权威,他捍卫的权威是法律与秩序,而这些都是文明发展的根基。
(三)正义
如果一种行动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或者符合权威的要求,那么这种行动就是正义的。正义是一种道德判断,在西部神话中,它与文明和权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违法乱纪的歹徒肯定不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违背了权威,威胁了文明。袭击移民的印第安人也不是正义的,他们是文明的大敌。而那些与不法之徒和印第安人英勇战斗的西部英雄们,因为维护文明和权威的行动,从而获得了与文明和权威一样的正义性。这是一个截然分明的两元世界,一边是正义,一边是非正义。它们之间的对抗,正是西部神话的永恒主题。
而即便是在文明和权威缺席的情况之下,正义依然能够单独发挥作用。西部是一个荒无人烟之地,很多时候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西部英雄们又经常独来独往,经常需要独自面对问题。英雄们可以不去考虑文明进步这种大的命题,也可以不去考虑权威的要求,但是他们必须顺从社会的道德要求,行正义之事。《原野奇侠》(Shane,1953)中的牧民们不断被大牧场主骚扰,政府并未帮助他们。独行的枪手肖恩偶然路过,出于行侠仗义之心,消灭了大牧场主和他雇佣的杀手。在权威无法保护弱者的情况下,是英雄依照正义的要求而救助了他们。
二、西部神话的破灭
美国独特的文化氛围孕育了西部神话,也孕育了传统的经典西部片。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动,西部神话随之破灭。
(一)文明弊病的出现
文明曾是西部神话的核心元素,文明的发展是西部英雄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文明的弊病也随之出现。此时,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发生改变,都市人的职业独立性被剥夺。现代文明束缚人、压迫人、异化人,白领阶层感受到了普遍的愤懑。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的人口不断膨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经济的发展又破坏了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复存在。文明曾是美国人所苦苦追求并引之为傲的事物,而在文明到来之后,却又受其所困。
美国社会的文明神话破灭之后,西部片的传统价值体系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文明的发展曾被认为是西部开发的终极目标,而一旦美国社会对文明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西部片的文明神话也不可避免地随之破灭。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西部片不再像传统西部片那样无条件地歌颂文明的进程,而开始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对传统尤其是对印第安人的伤害做出反思。
约翰.福特(John Ford)1964的《安邦定国志》(Cheyenne Autumn)一改其之前西部片的倾向,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将印第安人描绘成了西部开发的受害者,同时批判了美国政府的残忍与背信弃义。影片歌颂了印第安人的勇敢、聪慧、宽容、坚韧、不屈不挠以及对忠实于故土等优秀品质,而白人的移民则暴露了自己的残忍、粗鲁、胆怯与浮夸。事实上,两年前的西部史诗《西部开拓史》(How the West Was Won,1962)中对文明发展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这部电影对西部开发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词。在片中“铁路”的段落,铁路公司为了缩短进度,擅自改变线路,穿越印第安人的狩猎区,从而引发了和印第安人的冲突。铁路带来了大批白人猎手和垦荒者,西部的和谐与安宁受到破坏。亨利·方达(Henry Fonda)饰演的猎人在失望与无奈中躲进了深山。他就像一个从60、70年代穿越而来的美国人,早早地透过文明的繁华表面,看到了它对自然和传统的深深伤害。
美国人向来以西部开发为傲,并且深信“西部缔造美国”,也正是这种感情创造了传统西部片的文明神话。而一旦这种文明神话破灭,西部片便像被根基陷落的大厦,变得摇摇欲坠。60、70年代的西部片不再像传统西部片那样歌颂文明,取而代之的却是对西部文明的负面价值的反思。这种负面价值不仅作用在西部的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身上,也作用在西部英雄身上,不过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罢了。
当印第安人不再是文明的敌人而成为了受害者,英雄不再为了文明的发展而奋斗反而受其困扰,西部片的文明神话便宣告崩塌。作为西部片的核心价值观,文明的失落所带来的影响是放射性、源头性的。既然文明已经不值得维护,那么权威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在文明和权威都发生动摇之后,西部片的正义边界也随之模糊起来。
(二)权威受到了质疑
美国政府的权威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了严重挑战。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60年代的美国爆发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包括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氛围,而在诸多运动中,政府都成为了民众宣泄不满的对象。1965年越南战争扩大,美国对越南直接用兵,此举掀起了全美范围的和平与反战运动。美国人曾为之骄傲的美国军队,成为了民众眼里残忍的刽子手。7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继续遭遇挑战。1972年的水门事件使民众看到到了政府虚伪和腐败的一面。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又重创了美国经济,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扩大、居民生活水准大大下降。经受了60、70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动,以美国政府为主导的权威力量的声誉滑落至谷底。
文明的发展、正义的维护都需要权威力量发挥作用。而一旦文明的神话破灭,权威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权威的正确性也动摇了。在传统西部片中,权威从来不会成为反动的、非正义性的力量,也永远不会站到英雄和移民的对立面上。但60年代之后的西部片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权威经常会成为迫害英雄和无辜移民的邪恶势力。权威的传统代表,比如警长、法官、政府官员,曾利用法律扬善除恶,维持秩序,而现在他们却成为了真正的违法乱纪者,法律则成为了他们用来获取个人利益,迫害打压英雄和移民的帮凶。
法律与秩序并没有错,错的是人。这个时期西部片中的权威,逐渐都失去了往昔的那种美好品质,开始变得自私、贪婪、残忍、反复无常。《安邦定国志》中的美国政治家呆在豪华的政府官邸中,挥动着手中的笔就将几百名印第安人推向了死亡之路。《小巨人》(Little Big Man,1970)里的美军中校卡斯特暴虐而又骄傲,以屠杀印第安人为乐。《西部执法者》(The Outlaw Josey Wales,1976)中的参议员在南北战争后招降了南军士兵,但在士兵们刚放下武器的时候,就下令屠杀了他们。在这些影片里,传统西部片中的正面权威形象早已荡然无存。
(三)正义的边界变得模糊
在文明和权威都失去了重要性和正确性之后,正义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起来。这个时期,文明和权威也可能成为非正义的力量,而西部片中的不法分子却成了遭受文明和法制社会压迫的正面价值。《日落黄沙》里的劫匪抢劫了银行,枪杀了银行雇员并引发了小镇上一场屠杀,导致更多的无辜民众的死亡。他们后来又抢劫了美军的军火,然后贩卖给了墨西哥军阀。如果是在传统的西部片中,这群匪徒会是毫无疑问的不法分子,终将被法律和正义所制服。而在这部影片里,他们却被描绘成了被政府和军方迫害的带着反叛和悲剧色彩的英雄。传统英雄们身上的美好品质依然在他们身上闪烁着。这些美好的品质使人想起了约翰.韦恩所饰演过的一系列人物,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故事中权威所无法获得的正义性。
将这些与权威针锋相对的社会反叛分子视为正义的,也是深受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氛围影响的结果。60年代的美国社会涌动着一股反权威、反传统和反社会的思潮,并因此爆发了影响重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包括“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这两个运动中的年轻人都以反叛为傲。他们反叛的是那些权威所教育他们是正确的东西,传统社会对正义的判断标准也因此被他们抛弃。在他们看来,那些被文明社会迫害的人是值得同情的,那些敢于反抗现有体制的人是勇敢的,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有自己的苦衷,只要他们带有那些传统的美好品质,他们就比追捕他们人的更值得赞美。这就是为什么《日落黄沙》里的银行劫匪是正义的,为什么《比利小子》里通缉犯比利小子是正义的,《西部执法者》里对抗美国军队的乔西.威尔斯(Josey Wales)是正义的,而追捕他们的警察和美国军人却是非正义的。
至此,西部神话的三个核心元素组成要素,文明、权威和正义都逐渐崩塌,西部神话随之破灭。西部片的魅力正来自于其所塑造的神话,正义和邪恶鲜明地对立,西部英雄为了社会利益同邪恶的敌人激烈地对抗。西部片的观众也乐于一次次走进影院,反复,甚至有些仪式化地消费西部神话,而西部神话的破灭便破坏了传统西部片花了几十年同观众建立起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正是类型片生存的保障。他们无法忍受这种失落,就像他们无法忍受他们心中英勇的西部英雄就像《花村》(Mc-Cabe& Mrs.Miller,1971)的主角麦凯比那样,在一场胆颤心惊的枪战之后悲剧地死亡一样。
西部神话的破灭并不完全是社会文明氛围影响下的结构,也是好莱坞类型片主动调整的结果。同美国社会一样,60、70年代的好莱坞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动,旧好莱坞逐步解体,新好莱坞登上历史舞台。为了适应新的制作和市场环境,好莱坞的类型片纷纷经历着更新与解体。旧类型或者消亡,或者纳入了新的题材与风格,新类型也不断涌现,好莱坞原本稳固的类型地图逐渐变得面目全非。传统的西部片在这个变革的风潮中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一批全新的西部片以截然不同的姿态面向了观众。但总体而言,西部片作为一种保守、单纯、程式严格、风格鲜明、拥有着深厚的创作传统和忠实影迷的类型片,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激进的变革与重构。一旦西部神话宣告破产,传统西部片便走向了尽头,西部片的衰落也不可避免。虽然在90年代曾有几部西部片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西部片至今仍处在无尽的黑暗之中。2013年迪斯尼斥巨资拍摄的西部片《独行侠》遭遇票房惨败,正是其境遇的真实写照。
李 亚,男,山东荷泽人,西南大学电影学硕士,主要从事电影产业与文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