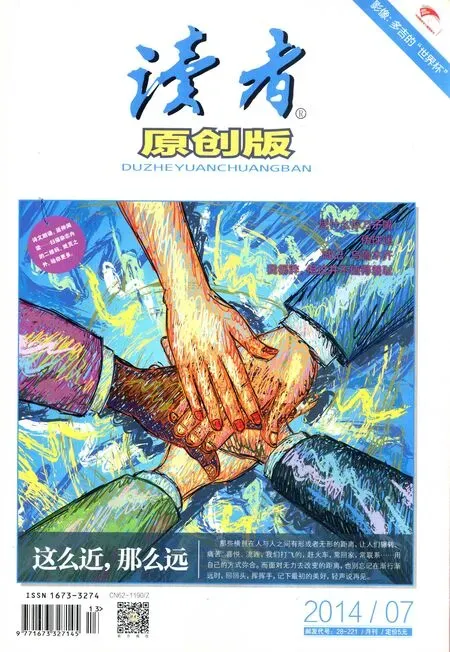倍耐力
文 _ 卢十四
倍耐力
文 _ 卢十四

和很多人一样,我关于忍耐的最初记忆来自打针。我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上绞刑架是什么感觉,想来想去,也只有酒精涂在屁股上的瞬间可以与之相比:那一刻,皮肤和心脏同时冰凉,全身僵硬,灵魂出窍。我用残余的一点理性不断告诫自己:“忍住啊!千万忍住啊!”只要最终眼泪不流下来,这次忍耐就算成功了。惭愧的是,幼年时代的我在这方面成功率极低。每当两道热流从脸上滑过,我总是感到懊恼羞耻,垂头丧气。
多年以后,我一位邻居的女儿当了护士。有一次她说起当天的工作经历:一个中年男人来打针,但他过于紧张,臀部肌肉紧缩,硬生生把针头夹断了。她不知道,当我听这个故事时,也不由自主地身体一紧,仿佛又有酒精涂到屁股上。
上小学之后,我的体质大有改观,打针这种事渐渐少了,但还是不时感冒、发烧、肚子疼。那几年恰逢我爸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钻研了几本《按摩推拿治百病》之类的书,迅速自学成才。现在想来,我爸那时一身本领无处施展,看到我生病,心里一定挺高兴。电影《东成西就》里,王祖贤瞪了一眼张学友:“你就是我第一个受害者!”事实上我不仅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受害者:在我爸的指挥下,我亮出周身穴位,供他练习“大力金刚指”和“九阴白骨爪”。这套流程冗长而复杂,一般以掐虎口七七四十九下为开胃菜,然后就是全身捶打。不得不说,我那时的忍耐力比起幼年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汗出如浆,咬碎钢牙,我也不停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红日光!胆似铁打,骨如精钢……”
然而每每到了最后,我还是功亏一篑。虽然我是个铁打的汉子,但我爸他是个打铁的汉子!这套流程的最后一关真的是“九阴白骨爪”:他双手按住我的后脑勺,大拇指找到某个凹陷处,用力按下去。那个穴位就像开关一样,只要他一按,我就惨叫一声,飙泪哭喊道:“不按摩了!不按摩了!”
偶尔回想起这些事,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那么能忍呢?显然不是因为我在忍耐力方面天赋异禀,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忍”的临界点应该在哪里,只要大人说你应该打针时不哭,我就尽全力不哭,如果忍不了,那一定是我的错。
令人欣慰的是,在咬牙怒忍的不归路上,我并不孤单。某一年,我表哥生了病,二姨打听到一个据称可治此疾的偏方:在木桶里倒上半桶开水,把脚放进去熏。我表哥依计行事,我二姨怕热气散得太快,还在木桶上搭了块毯子。只见我表哥龇牙咧嘴,身子扭来扭去,硬是不曾把脚抽出来,活活熏了半小时。我二姨在旁边鼓励他:“忍一忍啊,忍一忍病就能好了。”此疗法果然立竿见影,第二天他就起了满脚大泡。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觉得自己该忍,就真的都能忍。我人生的前17个冬天,家里和室外一直保持同一个温度,虽然冻得哆哆嗦嗦,我也并无怨言:“冬天就该冷啊。”到北方生活了几年后,顿时觉得没暖气简直是反人类。我还是我,只是“什么该忍”在我心里发生了变化。
说起没有暖气的冬天,还有件令人悲愤的事。上初中时,我和我爸在家想法子取暖。跺脚之类的扰民行为自然不可取,我爸灵机一动:“我们玩击掌吧!”此处所谓击掌,是两人各自以扇耳光的力度挥手相击。啪的一声脆响过后,我觉得自己的手已经四分五裂。然而在我喊痛之前,我爸抢先开腔了:“爽!再来!”
那就再来。
我们不仅再来,而且再三来;不仅再三来,而且天天来。此种运动对取暖确实有益,看我爸那么爽的样子,我简直不好意思不配合。当时我已经有了些文化知识,知道作用力的大小等于反作用力:我爸打我是那么大力,我打我爸也是那么大力啊;我是这么痛,我爸也是这么痛啊;他不喊痛,只说爽,难道我能比他差?
几年之后,我上高中了,击掌游戏也许久没玩了。某个冬天的晚上,我爸突然又想起了这一出,一时技痒,邀我同乐,我欣然应允。啪的一声脆响过后,我爸捂掌跳脚:“啊!痛死我了!”
那一刻,我震惊了。因为就在他跳脚的同时,我的手居然一点都不痛。我突然明白了:虽然作用力的大小等于反作用力,但我的痛不等于我爸的痛。几年前我年幼体弱,痛的人是我,如今我的个头已经高过我爸,痛的人变成了他。
可是,当年我痛的时候我忍了,现在他痛,他居然叫了出来!
我上当了!
我心中充满悲愤:当年吃了那么多亏,如今难道不该还回来吗?可是他已经喊痛了,我总不能说:“不准喊痛!给我忍住!再来!”
世间事大抵如此,其实痛不痛,自己知道;忍不忍,自己决定。那些劝你忍耐的人,要么不怀好意,要么并不在乎你有多痛。
这个道理我明白得太晚。虽然我现在长得像个米其林,但其实我骨子里还是个倍耐力,改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