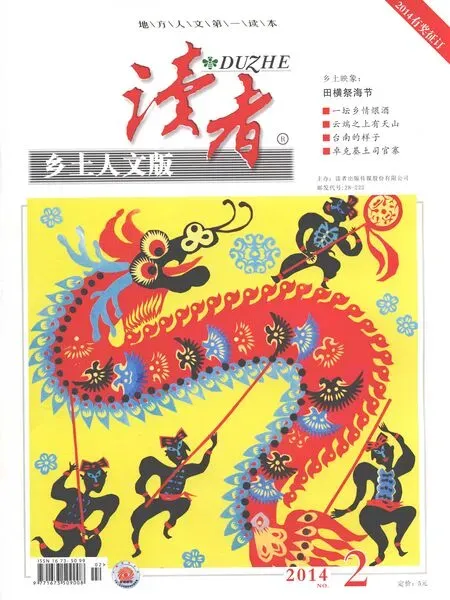下乡北大荒
文/邹静之 图/沈骋宇
下乡北大荒
文/邹静之 图/沈骋宇
我有一只陶瓷茶杯,30多年了,一直没用过。上次搬家时从箱底将它翻出来,还是崭新的,杯子上印有“上山下乡光荣”6个红字,旁边有一朵红花,红花下有绿色的梯田。
看着杯子,耳边响起了很热闹的锣鼓声,还有红色的布告、草绳、木箱、新发的军绿棉衣、兴奋或悲伤的眼泪、血书、母亲深夜缝被子时的灯光……
1969年8月,北京火车站。父亲从站台的圆柱背后走出来,他顶着“反动权威”的帽子,从牛棚中告假来送我。镜片后边,父亲的眼睛里没有太多悲伤。他拿了一把小提琴来,说是可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余搞搞娱乐。我接过了那把琴,没有太多的话想说。我一直盼着离开北京,离开家,离开那个歧视我的小区。
父亲在列车开动前就走了,他说只请了一会儿假。父亲走了,我想他可能忍受不了开车前的铃声。我把窗口让给其他同学。开车铃响时,车上车下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多的哭声,像一条河流崩溃了一样。我没哭,我端坐在椅子上,觉得没什么可哭的,我把北大荒想象成能使我畅快呼吸的地方。
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兴奋地看着沿途不断变换的风景。同学们彻夜不眠,交谈、打闹。我再也想不起来一群16岁左右的大男孩们,一天一夜都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把这当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北大荒”这名字真形象。头上是天,脚下是地,站起来是个人。在这里,人显得很渺小,你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土地、云朵、星空,那是自然的世界,人只是自然的附属品。
1969年10月1日,我们所在的德都县下雪了。这雪像是来得太快了点儿。没来得及拿出棉衣、没有炉子、也不会生火的三三班的同学们,拥坐在一座未竣工的礼堂寒冷的舞台上,听天安门上正在举行的国庆庆典的广播。那些熟悉的声音被窗外的雪花隔开,被半导体不清晰的声音隔远了。20多个大男孩,被寒冷和怀乡之情搞得很消沉,没人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拿出小提琴想拉个曲子,其实我就会拉三四首简单的曲子。我拉了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这首歌讲的是一个马车夫将死的故事,很忧伤,与窗外的雪花构成清冷的情境。我拉了一会儿,放下琴时,发现大部分人都哭了。有的人躲避着别人的目光,用胳膊盖着眼睛哭;有的人睁着泪眼,无声地看着我。我把琴放进琴盒,瞬间,有泪流出来,滴在躺倒的琴上,发出空洞的声音。
那是我们三三班唯一的一次集体流泪,以后再也没有过。
在北大荒,拉沙子的活儿挺苦。零下40℃的天气,坐在车厢里,车一开,风就把全身的棉衣穿透了。那种冷,是哭都哭不出来的冷。20多公里的土路,快得话也要走40多分钟。车到了,找到沙子就装,两个小伙子装3吨沙子要花半个多小时,总盼着司机说:“行了!关大厢。”关了大厢,身上的衬衣被汗浸透了,这时再回车厢坐下,那种冷比平时又加了一倍。风一吹,贴身的衣服像冰一样。
那时最盼望的是干完活能钻进热被窝睡一觉,但每晚定额要拉4趟,使人觉得苦海无边。
有一次实在太冷了,两个人商量好,拉完两趟就不干了。我们偷偷溜回宿舍,把通讯员的两辆自行车横放在走廊里,躺下就睡。过了一会儿,司机来叫,被走廊里的自行车呼啦啦绊倒,摔得挺重,就算躲过去了。
最苦的一次是车陷在河套里出不来了,从深夜到凌晨,我们在寒冷中熬着。那种安安静静的冷使人逐渐麻木,看到的星星又大又亮。那一夜,现在想着挺美妙的。我像是在散步,走进很深的夜,在一座沙堆上还看到一双狐狸的眼睛。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敢停下来,怕冻僵,就那么散了一夜的步,早上才搭乘一辆拉沙子的车回到连队。
(马思翼摘自新浪网邹静之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