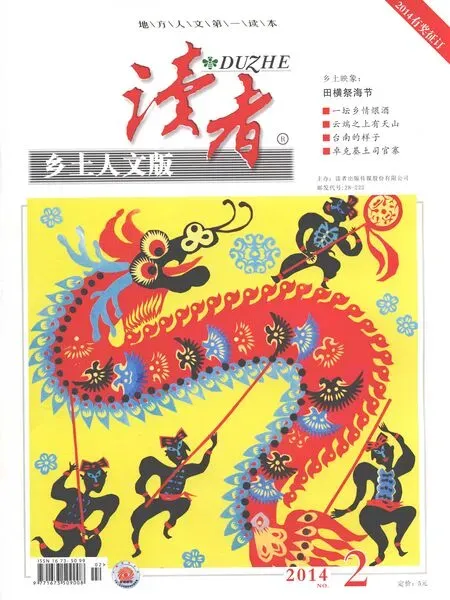葬 礼
文/风举荷 图/黄煜博
葬 礼
文/风举荷 图/黄煜博

爷爷的葬礼,办得很像一场乡间社戏。
从邻乡请的锣鼓队,开了辆面包车来,直接在大门口摆开台子。一个年轻姑娘拿着麦克风,震耳欲聋地唱着《真的好想你》。老宅前方的打谷场上搭着个蓝色的塑料大棚,里面塞了五张八仙桌,旁边支着两口大灶。一个村的人轮番来吃流水席,从早晨就开始吃烤鸭、喝啤酒。
乡间的夜很黑,也很静。塑料大棚里拉了电线,点着两只40瓦的白炽灯,在初夏的星空下像两只发呆的萤火虫。守灵的,有一桌人在玩扑克,另一桌人玩的是麻将。偶尔会传出几声悲恸的长哭,中间还夹杂着听不懂的言语,那是锣鼓队的附赠项目—哭丧。老宅里乱糟糟的,长久不住人了,地面泛着潮气,四处散落着麻袋包袱,方便爷爷的子孙、乡邻奔丧时跪拜。厅堂正中央摆着爷爷的棺木,红彤彤的,刚刷过新油漆,散发着刺鼻的味道。爷爷没有躺在里面,而是直接被送到了殡仪馆,等待着三天后的火化。
爷爷要是活着,一定会拄根拐棍,戳戳捣捣,对这场葬礼暴跳如雷—简直没一样能如他的意。
爷爷20多年前就准备了好自己的棺木,用的是乡间最结实的枣木,现在子孙却要把他塞到炉子里化成灰;平日里他百般节俭,每逢年节,奶奶要杀一只鸡,他都要难过半天,现在居然摆起流水席;这辈子爷爷最恨的就是赌,以前除夕夜,儿子出门打牌,他都会摸到别家堂屋,一把将桌子掀翻,现在大伙竟然在他的葬礼上打起了麻将……但都没有用了,他彻底沉默了。其实很多年前,就再也没人听他的了。
有一次我回家,二姑和小姑也在,大家敦促爷爷把他攒的钱都拿出来,整理清楚。一辈子都是他在管钱,奶奶永远不知钱放在哪儿。他搬来大桌,又架上小桌,哆哆嗦嗦地爬上大门头,在某块砖的背后,摸出一个锈得看不出原样的小铁盒,里面有一大卷现金,还有他在信用社的存折。理了半天,怎么也对不上他记忆中的数字,他开始慌了,浑浊的眼里简直要溢出泪来,暴躁地大喊:“肯定被谁偷走了,肯定被谁偷走了!”后来还是二姑说:“你上次不是给了双银(我的大姑)3000块钱,让她帮你存起来嘛……”他想了半天,才安定下来,嘴里诺诺地重复:“我要她还给我,我要她还给我。”那天整理出了他一辈子的积蓄,4.6万元。这些钱可能刚够买一枚钻戒、半辆汽车、城里一套房子的一间厕所……
爷爷知道他这辈子有多小气吗?我活到30岁,他给我最大的一笔钱是某年的压岁钱—20元。他好像总共也就给过我那么两三次的压岁钱。每年春节前,他只赶“光蛋集”,就是除夕前的最后一次集,那时,对联、红纸、爆竹、香火都是大甩卖,他买什么都能比别人便宜。
我成家的那年,中秋节回家,爷爷看到我,又神秘又兴奋地把我拉到西厢房,像献宝一样轻轻推开木门。墙边靠着一张巨大的锈迹斑斑的钢丝床垫,不知谁把席梦思床垫用坏了,布面全无,那堆烂弹簧就扔在了路边。爷爷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那堆铁丝捡了回来。“你带回家,铺上几床新棉絮,睡上去一定很舒服。”他语气里充满着兴奋。
爷爷70岁时,还下河摸河蚌,带回来砸成粉喂鸭子。80岁时,干不动农活了,他就去别人收割过的稻田和麦地里,一点点捡拾散落的稻穗和麦粒,饱的自己磨粉,瘪的喂小鸡、小鸭。
他的太公和爷爷都是贫农,拼死干活,积攒了几辈子,才在他这一代买了几十亩地,盖了三间草房。可很快,新中国成立了,地又被分给了大家,他只好默默在自家的几亩地里耕耘。
他年轻时是大队书记、种田好手,会杀猪,会给牛接生。
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念了书,如今都当了老师,一个成了县城里的裁缝。
他的儿子—我的父亲,是恢复高考后乡里出的第一位大学生。听说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爷爷高兴得在河埂上打滚。
爷爷过了70岁,耳朵越来越不好使。身边的老人一个个离世,年轻人不是出门打工就是整天忙碌,爷爷越来越沉默,开始整天在田间地头游荡,不论严冬酷暑,他在他熟悉了一世的田里,寻找安慰和自足。
爷爷84岁那年,被送进了养老院。
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坐在那条气味浓重的甬道的尽头,靠在一张歪歪斜斜的木椅上,有气无力地低着头,好像什么也不想。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都是在那个死亡气息浓厚的地方度过的。每个周末,他能看到儿子或女儿一次,享受一次加餐。每当季节交替,他都会生一场病,只有那几天,他的孩子们会陪在他身边。因为在养老院住了两年多,再没干过农活,爷爷虽然干瘦,却被养得很白皙,看上去养尊处优。一辈子塞满了泥巴和灰尘的指缝和指甲,干净得很。
他走的前一天,小姑去看他,给他理了发,洗了澡。一辈子都在泥地里打滚的爷爷,走的时候,和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干净极了。村里的人都说:“这老头是白喜事,有福气。”
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他的葬礼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张甫卿摘自《安庆晚报》2013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