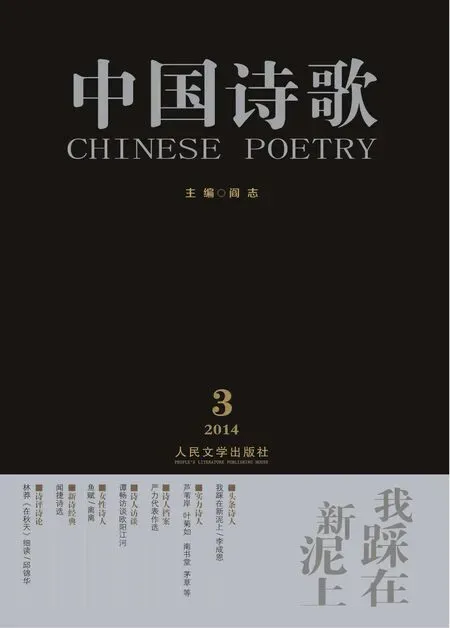严力代表作选
穷 人
无数块补丁
一左
一右
在月光下劳动
好面熟的
风
你补着
残破的天空
蘑 菇
谁能说服自己
在阴暗的处境里
生命不见了
尽管是背着光
朽木
怀了孕
失 约
寒冷并焦急地
我在约会地点抬起脚
把已过的五十分钟踢进到一个小时
头也不回地穿过这个黄昏
但是
她拎着一袋苹果
堵住了黄昏的长廊尽头
她解释说
苹果晚熟了一个钟头
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
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早上叫醒我的那只雄鸡
哪怕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
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
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
也请把笛子还给我
还给我
请还给我爱的空间
哪怕已经被你污染了
也请把环保的权利还给我
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
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
请还给我整个地球
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
一千个国家
一亿个村庄
也请你还给我
超级英雄的反省
这一年里没有作业
铅笔刀削着橡皮
这一年里没有石头对你的脚开玩笑
鱼刺也不想把花绣在你的嗓子眼里
这一年真是平静之极
嫩芽没有伸出懒腰
依然是去年脱下的衣裳被风塞在角落里
这一年里只能把死人挖出来再埋一遍
炮弹们用安眠药充饥
这一年里书籍都团结在书架里
酒瓶子烂醉如泥
空虚在你去年咬出的一排排牙印上
弹奏得极其卖力
这一年里只有风在风尘仆仆
你掸了一年才看见灰底下的日历
我是雪
我是雪
我被太阳翻译成水
我是水
我把种子翻译成植物
我是植物
我把花朵翻译成果实
我是果实
我被父母翻译成生命
我是生命
我被衰老翻译成死亡
我是死亡
我被冬季翻译成雪
我是雪
我被太阳翻译成水
阳光明媚的星期天
星期天的阳光明媚
我们几乎把露天咖啡馆
坐成了度假的沙滩
我们谈到了美妙的生命和爱情
甚至谈到的死亡也是浪漫的
我们谈到了
自杀者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后
如果再自杀一次
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星期天的阳光啊
真他妈的太明媚
早市的太阳
看着自己在早市上拎着一袋食品
一袋
各种各样的叫卖声
一袋
经过精打细算的脂肪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一袋
生活的重量
很久很久地
我继续站在路口品味自己的生命
日常是多么自然
太阳拎着一袋自己的阳光
纽约
没到过纽约就等于没到过美国
但美国人对纽约抱有戒心
到过纽约就等于延长了生命
一年就可以经历其他地方十年的经验
集中了人类社会所有种族经验的那个人
名叫纽约
在纽约可以深入地发现
自己被自己的恶毒扭曲成弹簧
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弹簧
都出自纽约的压力
与犯罪和股票每分钟都有关的新闻节奏
百老汇的闪烁与警车的嘀鸣
街上的即兴表演
纽约这个巨大的音响设备
让你的肌肉在皮肤底下情不自禁地跳舞啊
纽约的司机
好像要带领世界的潮流去闯所有传统的红灯
但是
别忘了小费
到过纽约这个社会大学的学生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充满了犯罪学老师的地方
学生中间混杂着不少将要一夜成名的
最新的老师
其中
法律的漏洞是律师们最喜欢表现其智力的靶心
嘿
住在纽约的蜜蜂们
甚至学会了从塑料的花朵里面吸出蜂蜜
绰号“大苹果”的纽约
这苹果并非仅仅在夏娃和亚当之间传递
而是夏娃递给了夏娃
亚当递给了亚当
大声咀嚼的权力掀起了许多不繁殖后代的高潮
入夜的纽约啊
在吞噬了白天繁忙的阳光之后
早就迫不及待地解开了灯光的钮扣
坦率的欲望
就像所有的广告都擦过口红
妓女
妓女虽然是纽约非法的药
但生活常常为男人开出的药方是:
妓女一名
喔
繁荣就是纽约骄傲的毒品
撩起你的袖子
让繁荣再为你打上一针吧
凶杀虽然很够刺激
但纽约不眨眼睛
纽约纽约
纽约是用自由编织的翅膀
胜利者雇佣了许多人替他们飞翔
多少种人生的汽车在纽约的大街上奔驰啊
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创造发明者
或者你使用了最大的历史的轮胎
但纽约的商人已经在未来的路上设立了加油站
纽约纽约
纽约在自己的心脏里面洗血
把血洗成流向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
鱼 钩
经过了许多年的等待
我的鱼钩啊
终于在没有鱼的池塘里
自己游了起来
游着游着
索性一口吞下了自己
谢 谢
国家占有了所有的地理表面
我只能往下建立自己的内在
政府占有了最大的餐桌
我端着的盘子就成为了我的桌子
社会制度占有了所有的骨节
我只能用血肉搞点情绪的浪漫
学校占有了教育的制高点
我的理论只能打打游击战
妻子占有了家庭的脸色
我只能把镜子擦得更亮一点
孩子们占有了未来
我只能帮他们买鞋
这样的安排
我只能说声谢谢
精致的腐化
请运用你的想象
想象每个时代都有成千上万个工匠
前赴后继地
打磨着这块人间最大的玉石
所以它不可能不光滑
让你的手感四通八达
它不可能不坚硬
你撞上去就必定会头破血流
它也不可能不反光
你能看见整个世界因为它的弧度
而变形
美妙的词
“输掉了”
输掉了是一个美妙的词
我们把贫困输掉了
我们把痛苦输掉了
我们把疾病输掉了
问题是输给谁
哪一家赌场
哪一届政府
甚至
哪一位上帝有如此的雅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的雅量更大
我们一直在赢
强 奸
强奸这个词充满暴力
空气被强奸了
食物被强奸了
河流与文化被强奸了
甚至反省也被强奸了
某些还很年幼的事情
被强奸了
除了内心的创伤
强奸的后遗症
包括怀孕
包括人工流产
还包括不得不生下来
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强奸
在许多国家里
全都生下来了
清明时节的同胞
清明时节的墓地旁
我遇见一群掉队的亡灵
一看就是苦难深重的同胞
比战争还要暴力的毒辣手段
把他们杀了以后没有落葬
一拖就是几十年啊
他们说
离家时儿女还小
算起来,再疯狂的档案
也该到了解密的年限
我热心地上网查找有关的政策
他们说
别费工夫了,
我们被删掉的那个年代,
用刀不用鼠标!
心有不甘
多种力量把我从树做成了家具
常言所说的三十而立
说的就是要完成人生的突变
以前
我在树里仰望成材的将来
现在
则以某件家具的身份
感叹被固定了的位置
尽管我仍然享受内心的绿
但我更喜欢用锯齿般的目光
打量与其他家具
被命运摆出来的距离
生 活
往前走
生活提着自己的架势
像提着裙子
如果哪一天把裙摆放下来
生活就不知道
双手该往哪儿放了
这就像寺庙里弥漫着
下跪的香火味
如果它站直了
就不知道该是什么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