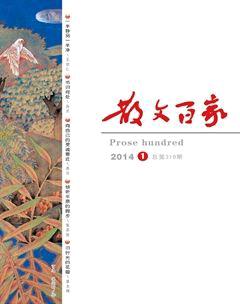源头的水依然清澈
李城
1
如果一条河愿意回首,它将看到自己的源头,并为曾经的孱弱难以为情。实际上河流是不会回首的。只有人可以找到它的源头,而且相反,会向那孩童般纯净快乐的溪流致以敬意。
郎木寺是一条江的发源地。最初,溪水从镇子西北和西南的峡谷间潺潺流出,汇聚成一条清亮的小河,唱着歌儿蹦蹦跳跳穿过镇子。那条小河迅速壮大,一跃成为惊涛拍岸的白龙江,在甘南的高山深壑间左冲右突向东穿行。过了陇南市它突然调头向南进入四川,一路腾云驾雾飞泻而下与嘉陵江汇合,接着穿越四川盆地,于重庆投入长江的怀抱。三千多米的巨大落差,如何让一条激情澎湃的大江回首自顾?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会懂得饮水思源。在郎木寺临河一家旅馆,我看到一位四川老诗人的题诗:“白龙江注嘉陵江,远济渝城情倍长;饮水思源源不断,云山千里意难忘。”
那张落款题名梁上泉的四尺宣未经装裱,就那样皱巴巴贴在墙上,看得出来,旅馆主人并不在意那是一幅值得收藏的书法作品。我没写过旧体诗,也不敢肯定它是否合乎格律,但可以肯定的是,老诗人沿着嘉陵江、白龙江一路行来,终于找到了隐藏在深山峡谷间的源头。他显然不是探险家和寻宝者,千里迢迢跋涉而来,为的只是表达对一条江的感恩。
长江和黄河发源于更为遥远的西部群山之间。它们孕育了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惠及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和人口。作为生命之水的受益者,如此的回顾是多么必要。
今天我们注意到一条河流的存在,也许明天,我们接着会对空气和阳光投去深情的一瞥。
2
郎木寺距离我所在的合作市不到200公里。从前搭过路的长途客车在三道桥下车,进西边河谷步行5公里即到,如今有班车可以直达。
那是个岩峰与针叶林环绕的小镇。石头和木头垒砌的房屋坚实而古朴,由于向阳,即便在冬季也不会觉得过于寒冷。甘、青、川三省接壤处堆积起来的群山拱卫着它,外围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因而对外来者来说,总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郎木寺是个以仙女命名的镇子,它曾经的地名是达仓郎木。那藏语名字的意思是“虎穴里的仙女”——达仓乃虎穴,郎木即仙女。相传那里最初是一片野兽出没的幽深森林,峡谷虎穴里一只猛虎常常伤害人畜,不但当地无人居住,过路商客也屡遭劫难。有一日清晨,随着自然而鸣的海螺声呜呜响起,一位霓裳羽衣的仙女自天而降,降服了称霸一方的猛虎。那仙女不仅可爱也有几分顽皮,她驯服猛虎作为自己的坐骑,常常骑着它巡游山林,警告其它猛兽不得为害地方。
镇子西边峡谷的一个巨大洞穴里,如今还供奉着吉祥仙女的天然塑像。其实那不过是一尊被白色哈达层层包裹起来的人形钟乳石,但人们总是摸黑进入洞中点燃柏香,供上一盏盏酥油灯,双手加额默默祝祷。据说镇上的寺院里保存着那只预示仙女降临的神奇海螺,寺院因此而声名远播,镇子的名字也就渐渐称为郎木寺了。
峡谷深处的溪水边,常有四脚小鲵伏卧于岩石,气定神闲犹如小小的恐龙。到了冬季,顺着溪流总是蒸腾着一道雾气,灌木枝条上挂满了洁白的雾凇。伸手试试水是温的,摸一块水底的石头出来也是热的,仿佛即将孵化的恐龙蛋。
郎木寺处于甘、青、川三省边缘,实际上也处在东部和西部的边缘。那里没有令人感到沉重的积淀,也没有供人凭吊怀古的废墟,它只是徜徉在神奇的传说中。自然而鸣的海螺,降服猛虎的仙女,开启了万山丛中一方祥和之地。居民们传诵着如此的故事,甚至将其作为一种荣耀。没有人求证传说的真伪,也没有人会断然否定。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孩子们才喜欢那样的传说故事。是的,郎木寺人是不介意说他们单纯得就像孩子的。有次我与一位牧马的老人坐在草地上闲聊,一只拇指大的黑色甲虫直奔他的领口而去。我急忙提醒他,他却笑着说,让它去吧,它只是好奇而已。那虫子钻进他的袍子,在他的胸口和胳肢窝仔细巡察,他始终坚持不动,只是像孩子一样被瘙痒得呵呵大笑。
后来镇子上有了两座藏传佛教寺院,分属甘肃和四川两省。由于经商的回民陆续增多,两座寺院之间也出现了一座清真寺,尖顶上的星月在太阳下闪光。
喧闹声总是停留在遥远的草地之外,时尚的涟漪也因崇山峻岭的阻隔,终至于消减殆尽。郎木寺的天空总是一碧如洗,实际上并非一无所有。它被传说的油彩涂抹得斑斓绚丽,让人突然领悟到“空无妙有”的寓意。
3
在外人眼里,郎木寺仍是一方净土。
表皮干燥脱落的柏树高大而宁静,在河边草地上投下它们墨绿色的影子。河谷及山坡上都是居民的沓板房,屋顶不覆瓦片,只用石头压着一层层劈木板,看上去雪鸡的羽毛一样自然美丽。屋梁与檐板之间甚至不用榫卯,而是用原木的天然根杈作为搭钩。久经日晒雨淋,屋顶铺设的木板与青白的石头融为一色,看上去柔和而温暖。室内生火时屋顶板缝间便有炊烟冒出,牛乳一样四处弥漫开去,空气里总是飘散着柏枝和糌粑的清香。一些朽坏的栅栏几乎被茂盛的高原橐乌和唐古特莨菪湮没,街道两旁的波斯菊也开得热烈,似乎永不凋谢。镇子对面山头横亘着暗红色的丹霞裸岩,如同燃烧着的巨大煤块,即使第一场雪染白山峰,目光所及也会给人灼热感。
据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位名叫詹姆斯的美国传教士来到此地。他醉心于奇异的传说和风光,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他穿上皮袍、戴上皮帽,每天跟当地人一起喝酒聊天,或者跟他们去骑马狩猎。十多年后他离开时已写成了一本英文著作,带回美国出版发行。他的书让许多西方人知道,中国西部的群山之中还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所在。
在如今的郎木寺,见到最多的仍是西方背包客的陌生面孔。他们端着相机穿行于寺院与板屋之间,旁若无人地在活页本子上写写画画,偶尔俯下身去逗惹那些鼻涕流过嘴唇、目光纯净如水的当地孩子。而来自内地城市的年轻人,那些身体单薄却自命不凡的诗人或画家,总会孤独地坐在旅馆的窗口,一边品尝劣质咖啡,一边不停地抽烟。他们额前长发遮住了一只眼睛,却不妨碍用另一只忧郁的眼睛发现令他们惊讶的东西。
街边木桩上拴着马匹,嘴上套着毛线编织的饲料袋,咯嘣咯嘣嚼着豌豆。泉水在街头水槽里哗哗流淌,远道而来者卸下满是风尘的行囊,弯下腰双手接住水柱,清亮的水花在手心里飞溅起来。幽暗的车马店里隔夜的火塘总是余温尚存,镇子外的草地上也可看见行脚者们打尖烧茶的黑石头。
镇子上的藏人以畜牧为业,牧场却在很远的山后,因而他们除了镇子上有个固定的家,还有几顶随季节不断游走于原野的黑牛毛帐篷。汉人和回民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为躲避战乱或经营畜产品生意而来,也跟当地居民无异了。镇子主街两旁有许多店铺,以藏、汉、英三种文字书写着招牌,门楣上往往挂着巨大的牦牛头骨。店铺里除了堆积着酥油、糌粑和青稞,还可以看到尼泊尔铜佛、印度檀香、内地的景泰蓝花瓶,以及红铜茶壶、折把漏勺、圆木雕成的酥油盒、毛褐子褡裢和碗套。
所谓净土不过是相对而言。当许多地方遭受污染的时候,能够幸免的土地便是净土。因此,机警的鸟儿便会飞往深山,感知冷暖的鱼儿总在游向源头。郎木寺是个阳光充裕、山头上白云缭绕的镇子,镇子里也算不得干净整洁,远道而来的人们总是双脚粘满黑色的泥浆,石头垒砌的墙壁上甚至密密麻麻贴着牛粪饼。但空气和水都是纯净的,就像郎木寺的居民一样淳朴厚道,值得信赖。
郎木寺似乎被时光所遗忘,但我想说的是,盲目而焦虑的脚步最好不要打扰到它。值得珍藏的东西,应该小心存放在时光宝盒里。
4
走过寺院活佛府邸下侧的斜坡,向西北翻过一道山口,便可望见远处山脚下经幡林立的天葬场。那是西北藏区最有名的天葬场。
当一个人踽踽行走于通往天葬场的小路时,巨大的空寂几乎将人吞噬,就像海绵即将吸干一滴水。接近天葬场,草丛里到处是死者的遗物,毡毯,褥垫,还有一些袍子、内衣挂在灌丛上,旗帜般在山风中招展。也有精致的木碗、手杖之类,或许是死者生前的钟爱之物,还可能由于别人动了它们而生过气逗过嘴,最后都慨然舍弃了。再执着于自己的人,在那里也可能学会放下,在人生旅途上变得步态从容。
石块铺筑的天葬台上横陈着凹陷的解尸墩,摆放着各式各样锈迹斑斑的刀具。伫立于天葬台中央,仿佛站在通往另一空间的门槛,似乎看得见死者与众神一起凌空高蹈,欢庆生命的圆满归宿。
鹰鹫吃剩的骨渣会被家人捡起,烧成灰掺和到红胶泥当中,拓成一个个庄严的佛像。那融合了骨灰的佛像被放置于山坡上专门的房间,或是人畜不易侵扰的山岩之下,至此,再平凡普通的人生也完成了与佛的最终合一。
那里流传着一个说法,活着的人只要割破手指在天葬场洒一滴血,即可放下所有的牵挂。早年我也曾那样做过。因而,我一直在努力放下,哪怕做不到完全彻底。
5
每次去郎木寺,我都喜欢住在沓板房改造的简陋客栈里,听房东复述达仓郎木的故事。黄昏降临,镇子趋于安静,峡谷间传来的松涛声渐次高扬,激越的河流声也成为它的伴奏。那壮阔雄浑的天籁,仿佛迎接吉祥仙女踩着天界金闼再次莅临的乐章。在那样的氛围里,再离奇的故事也显得平常自然,如同屋后生生不息的荨麻和莨菪。他们会说,看见西边峡口石壁上那个巨大的掌印了吗?那儿原是海眼,连接着东海呢。有一年突然大水喷出,淹没了房屋牛羊,恰好来了一位圣者上前猛击一掌,就将那海眼封住了。于是晚上躺在板屋的地板上,总觉置身于一叶轻飘的舢板,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夜颠簸。
板屋里的光线是迷人的。阳光穿过屋顶的缝隙斜射下来,看得见微尘的颗粒在纯净的空气里闪闪发亮。女主人在火塘里生起火,那些边缘齐整的光带里便有浓稠的乳色流动;熬着松潘茶的铜壶热气蒸腾的时候,光带里又闪烁着绚丽的彩虹。有次我在街头遇见一伙装备精良的摄影师,他们将长长短短的镜头对准寺院的红墙金顶疯狂地按着快门,我建议道:带上你们的三脚架去板屋拍摄吧,那里有世界上最干净最奇妙的光线。他们只是耸耸肩,继续在正午的强光下追逐那些裹着袈裟的僧人。
郎木寺人敬重神灵却不会受制于它,他们懂得神性就在自身而不假外求。据说,居住在板屋里的老居民可以将衣服搭在光线上,如同搭在一根斜拉的毛绳上,而且具备如此能力的人其本身也是发光的。按他们的说法,最初人人都是罩着一轮光环的,后来误食了一种名叫麻麦的谷物,渐渐变得气浊体重,与神灵拉开了距离。这种说法似与进化论相悖,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外在的东西变得庄严神圣乃至金碧辉煌的时候,人自身的光便会黯然熄灭。
西部诗人昌耀曾经写道:“他在这里脱去垢辱的黑衣,留在埠头让时光漂洗。”这句话似乎也为我而写。有次我坐在板屋里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当我偶尔回首之际,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身影,那是一个脸上没有皱纹也未生出胡须、面目生动犹具活力的自我。也许那只是一个幻觉,但无疑是件令人欣喜的事。虽然我的生活平淡无奇甚至多有不堪,但我仍保留着另一个自己,他未曾被现实的尘埃完全遮蔽。由此我将变得自信而踏实,将一度虚言应酬的事务抛置脑后,甚至不惜对那个由物质主宰的世界“决然背过脸去”。
6
据说郎木寺曾经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20个魅力名镇之一,在西北省区是唯一的。魅力是什么?如果要我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喜欢”。
我喜欢郎木寺。在感到疲倦或无聊的时候,总会放下手头事务,头也不回地直奔长途车站。我会坐在镇子对面的山坡上,嘴里咬一截草棍儿,像个年老的牧人那样惬意地享受阳光。我眯缝着眼睛,看不够那树木和山岩。有着坚实的山岩、有着茂盛的树木、也有着清澈河流的地方,便是能养人的地方——人需要摄取的养分不仅仅是食物。那是自然的力量,也是自然的慷慨馈赠。
如今的郎木寺是有变化的,女人们将背水的木筲换成了肩挑的两只铁桶,但她们仍坚持不用塑料壶。红红绿绿而又轻薄的塑料器具,肯定不适于盛装纯净的源头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