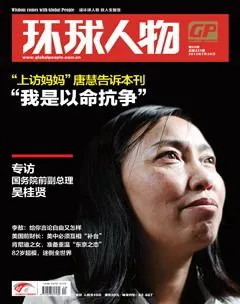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走

她,1949年生人。1岁时,母亲死于产后热。弟弟也于几天后夭折。
她有父亲,只是父亲另外还有家,有妻子,以及6个孩子。自她的母亲死后,父亲除了每月给5块钱外,几乎不通音信。
她还有个哥哥,同父同母,年长2岁。
她和哥哥依靠外婆生活。外婆丈夫早亡,唯一的女儿死后,留给她一双孤儿。
外婆裁衣缝纫为生,有祖屋一栋,一半自用,一半出租补贴家用。世事艰难,外婆只得把女孩送到远房亲戚家,名为寄养,实为下女。亲戚是开私人诊所的,正应了鲁迅的话,越有钱越抠门,她因为偷吃了一个酱鸭头而被暴打,左手小拇指骨折,从此一生不得伸展。那个鸭头,已在橱柜里放了几天,没人想去吃它。
几年之后,因为政策不允许,她重新回到自己家。外婆年纪更大了,父亲给的生活费涨到了8块。一年到头,举家食粥。隔几天,外婆会在灶上蒸一碗干饭,那是给哥哥的。她不嫉妒。哥哥是男的,理应吃好的。
她和哥哥极好,是穷苦人家相依为命的那种好。哥哥喜欢背着她飞跑,她在背上欢快地蹿着,终有一天,蹿得太高,一下子从哥哥头顶翻了出去,一头砸在石板路上。脑门砸破了,血流下来,两个孩子惊慌失措,偷偷溜进家门。哥哥从门背后捞了一把经年的蜘蛛网,抹在妹妹的伤口上。外婆说过,这个可以疗伤。额头的伤疤留了一辈子。
后来她上学了。蹉跎那么些年,她的年龄比同学大了好多,她卑微地沉默着,习惯于待在教室一隅,成绩平平。她在与不在,似乎于这个班没有丝毫影响。再后来,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外婆说,挺好,不怕没饭吃,回家一趟,还能带点柴火。
在乡下种了几年地,她招工回城,进了一家玻璃厂。玻璃厂做台灯、水杯、瓶子……彩色的玻璃玲珑剔透。她看工人吹玻璃,又佩服又好笑。一团融化的硅酸盐,吹着吹着,就变成了漂亮的瓶子。这个厂可真好啊!
进厂要培训,一大群新工人去了杭州玻璃厂。她依旧寡言少语。周日,年轻人泛舟西湖,雷雨忽至,大家进湖心亭躲雨。她和他相遇。
28岁结婚,在那个时代,相当晚了。新婚不久,他们去看外婆和哥哥。火车晚点,她想给侄女买一包桔红糕。卖点心的商店就在铁轨对面,她下了月台,想穿过铁轨,晚点的火车却在这时进站,把她撞出几米远。三天三夜,昏迷不醒,谁也没想到她能活下来。头上又添了疤,不时发作的头痛从此伴随一生。
1979年,女儿出生。两个人的工资,要养孩子、养外婆,还要给侄子、侄女们买这买那。每到月末,她都得跟朋友借5块、10块,等工资发下来时还。又到月末,还是差这5块、10块,再借,再还。但是她知足,相比于以前,这种日子让她打心眼里满足。
女儿10岁时,玻璃厂倒闭,夫妻俩都下岗了。人到中年,生活重回起点。她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小镇,进城再就业。
生活压力巨大,一路走来的两个人,也会磕磕绊绊,口角不断。但他们始终相守,不离不弃。
2004年,她终于退休,2006年却确诊得了癌症。手术后两年,发现脑转移,开颅、化疗……在医院的日子越来越多,身体机能一项项丧失。她的爱人一直陪在身边,睡一张窄小的躺椅,紧挨她的病床,一直到2011年她离开。骨灰一直放在家里,旁边插一把鲜花,花朵稍有颓态,马上就换新鲜的。
她无声无息地来了,又无声无息地走了,除了最亲近的家人,没有人在意。她这一辈子,跟大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艰难困苦居多。对她而言,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杭州培训时,大好年华,在绿水黛山、烟柳画桥之间,遇见他。生活粗粝,可剧终时,她的爱人愿意每日献一束花给她,经年累月,从无停息。
她,是我的姑姑。
编辑|王晶晶 美编|苑立荣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