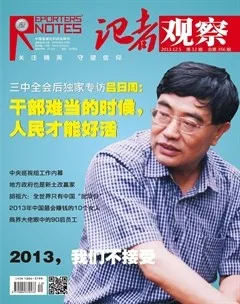108岁拼音之父周有光:汉语拼音是一把钥匙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假如我去考,一定考零分……原来规定有7D00个通用汉字,现在把通用汉字增加到8000多个,这个数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力,实在有点太多了。”
周有光的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装修风格:屋里铺的是地板革,还是早已不再流行的米色系;家具的款式也有些老旧,不足10平方米的小书房里,小小的书桌看上去甚至有些寒酸,上面留下了斑斑痕迹。不过,这个家里却有两个还算时尚的物件儿——摆放在客厅里的电脑和液晶电视。借助这两样“宝贝”,这位108岁的老人始终还关心着时下最热门的事情,在他看似随性的言谈中。说得最多的也是他对这些新鲜事的看法。
当年 身无分文出国推广拼音
今日 汉语拼音让手机更易用
对于国人来说。周有光最为人所知的头衔,当属“汉语拼音之父”这个称谓,由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汉语拼音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或者小孩进入文化领域的一把钥匙;在国际上,它又是个文化桥梁,许多外国人都在讲,没有拼音他们到中国来很不方便。”
近些年,周有光有了一个新发现:在手机普及的掌上时代,汉语拼音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了。“我起初买了一个手机,但我耳朵不灵,用起来不方便,就给了保姆。”周有光说,他后来发现,保姆天天用这个手机发短信,而且是用拼音输入进去的。周有光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位保姆在小学就学过汉语拼音,所以即使不用人教,也能无师自通发短信。
今天,汉语拼音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周有光曾经历了不少波折。他回忆说,早在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197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才使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
周有光对1979年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的经历印象颇深。当时,领导突然通知他去波兰华沙开会,可周有光却面有难色:“我的衣服都破光了。”领导发话,赶紧去做衣服,国家报销。于是,从袜子到大衣,周有光焕然一新地登上了飞机。“但我上飞机时没有一分钱。”他哈哈笑着说。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允许携带人民币出国,于是他的钱夹子只得临时上交。
“汉语拼音方案”的国际之路,起初并不顺利。周有光回忆说,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有70万种中文书,如果采取拼音更改编目,就要花2000万美元,图书馆方面对此持反对意见。“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用得慢一点,有了钱再用汉语拼音编目,他们这才同意。”三年之后,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了资金支持,中文图书编目改了,拼音方案在国际上也终获通过。
以前,在国际上鲁迅的名字有二十多种译法,北京的英文名字最广泛的译法曾是“Peking”。周有光说,正是因为有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些都成为了过去。
当年 从消灭汉字到创造拼音
今日 汉语拼音走进千家万户
其实,今日广泛普及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当年也曾经历过曲折的创造过程。
1840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一些人认为发现了中国落后的“秘密”: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故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10NOMQwap7tV6FXX3lMcXfpOFxmrxIe9XkMj/tVD4qM=目睹此情形,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要求对汉字进行改革,甚至要废除方块字,改用字母文字。改革呼声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甚至一度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此后,有志国人开始致力于制订属于中国人的拼音方案。至1949年,已有威妥玛拼音法、《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拉丁化新文字等几种拼音方案为人们所用。但其中都有不同的缺陷,有的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有的很难为普通人掌握。
这种各类拼音法并存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49年10月10日,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童为常务理事会主席。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终于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不料,毛泽东在详细审读后,认为这套方案虽然在拼音方法上较为简单,但是笔画太复杂,不利于普及。看着文字改革即将进入死胡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遂于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个改变中国文字改革进程的重要人物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就是周有光。当时。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尽管周有光的老本行是经济学。但解放前他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
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有光还发表过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童。在文中,他这样说道: “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此后不久,周有光便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鉴于当时苏联已将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中国与其是盟友,一些人又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于是,关于汉语的字母形式,再次引起激烈争论。
此种形势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经过仔细酝酿,他于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毛泽东说,“……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1956年2月20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出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1958年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正式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从此。汉语拼音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年 最早弃笔用电脑码文章
今日 八千个通用汉字有点多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我看了,很好。”周有光说着,话锋突然一转,“但假如我去考,一定考零分。”在他看来,央视这档热门节目里的有些字不好写。也不常用。“原来规定有7000个通用汉字,现在把通用汉字增加到8000多个,这个数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力,实在有点太多了。”周有光说,即使是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汉字量也超不过6000个。
最近有一种言论认为,中国人汉字书写能力在退化,都是电脑惹的祸。而在26年前,周有光是最早一批改用电脑码字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仰仗着电脑的高效率,他才能在80岁高龄之后重新修订了《比较文字学初探》等学术著作,又创作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颇受读者喜爱的新作。在他看来,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并不应当归咎于电脑,毕竟电脑的好处多于坏处,“电脑用来处理文字是好事情。”
还有一则新闻,周有光有话想说。最近北京公布了中考、高考改革方案,英语所占的分数比重均有所下降。不少人拍手称快,但他却不赞同。“教育最应该取消的是无效劳动,而不是降低英语的水平。”他认为,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在世界上是低的,英语不好很多事都干不成。“其实英语没什么了不起,小孩子学英语快得很,中学应该好好学英语,到了大学是用英语来取得知识,如果中学英语学不好,到了大学再学,学知识的时间就没有了呀!”说到这儿,老先生的语气明显有些着急了。
当年 拿百科全书当课外书读
今日 网上材料未鉴定应慎用
“我85岁离开办公室后,出书比较多,粗制滥造。”看着身旁洋洋洒洒的新著,周有光笑着说。资深编辑叶芳这样总结周老的写作风格: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普通人都能看懂的意思。“他的语言很简练,很清晰,文字用量并不很多。不需要很多词汇就能将事情讲得一清二楚。”叶芳认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让周有光的作品风格独具魅力。
百科全书情结的确贯穿了周有光一生。“我当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每门课程完成了,老师会指定学生读课外读物,其中很多都是百科全书。”周有光说,像《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两百多年历史,由四千名学者编写,作为大学生的课外读物最方便。“百科全书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准确、简明、扼要,是世界上有名的人写的,不是普通人写的。”但他也很感慨,“中国人向来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
在周有光的书房中,有一个三层的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改革开放后,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其中一项就是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而周有光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看百科全书、编百科全书、用百科全书思维写书,但周有光不得不说:“有了网络以后,百科全书的作用就减少了,很多东西都能从网上找出来。”不过,对于来自网络的信息,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慎重的,“百科全书的材料是有鉴定的,网上的材料没有鉴定过,网上不太准确。”这位治学严谨的老人对后辈如是说。
人物观察从不悲观的“风中之烛”
“我已经108岁了,再有三个月就109岁了。”周有光平静地说。
因为岁数太大的缘故,老先生虽然戴了助听器。但与人交谈的时候还是经常听不清楚对方的话。这时候,他就会拿来一张纸,让对方把问题写下来,只是轻扫一眼,便敏捷地作答,谈吐风趣,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人过了一百岁,退化很厉害,首先是耳朵听不见了,还有记忆力不行了。”不过,周有光又说,虽然自己记忆力衰退了,但理解力还没有衰退,“记忆力是个系统,理解力是另外一个系统,如果人的理解力衰退,就没用处了。”
周有光说,自己有过两次侥幸逃生的经历。这让他对生死看得很开。古人说,老人如同风中之烛,他很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身体,自认假如再活一年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过两三年仍活在人世间的可能性就小了。“这不是悲观,也不是玩笑,这是自然规律。”他淡然地说道。
来源:《北京日报》《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