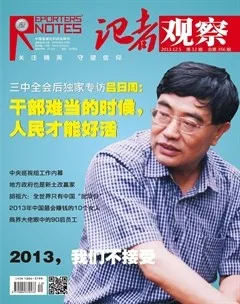“大V”商业链
所谓“大V商业”,是一种奇特的景观。跟国外的Twitter不同,微博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大V”身上。而在Twitter上,专业新闻机构在话语权和关注度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粉丝数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明星。
“薛蛮子事件”之后,一切都讳莫如深。
官方打击“大V”话语权行动,不仅使得新浪微博的活跃度持续下降,更重要的是,以前依靠“大V”或者联合“大V”的微博营销组织,瞬间沉寂下来,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杜子建。号称“中国微博营销之父”,在薛蛮子出事之后,他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其微博营销公司华艺传媒做出重要战略调整。即日起关闭“营销执行部”,把整个公司的经营重点放在“营销培训”和“营销咨询”上,也就是华艺传媒从“营销公司”直接转型为“培训公司”和“咨询公司”。他竟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不再为水军背黑锅”。
而曾和薛蛮子走得很近的申音——NTA创新传播的创始人和《创业家》前主编。则不愿意谈及他声动江湖的“大V”业务,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而据NTA某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NTA已经不再做《蛮子文摘》,那只不过是一个尝试,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公关的主业上。
有趣的是,很多做微博营销的受访者都一股脑否定了“大V商业”的真实存在。
什么是“大V商业”
所谓“大V商业”。是一种奇特的景观。跟国外的Twitter不同,微博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大V”身上。而在Twitter上,专业新闻机构在话语权和关注度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粉丝数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明星。
而微博则完全倒过来。微博认证账号里面,新闻机构的粉丝数目很少有千万级的。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新浪微博粉丝在千万以上的“大V”超过80人,大部分都是自然人(明星、商人、公共知识分子)。以至于有人戏言:
“一个任志强的转发,可以抵上中国所有媒体的报道。”
“大V商业”显然就容易生长起来:中国微博“大V”拥有如此广大的传播权力,并且没有任何传播上的成本项支出,他们可以接纳一些“营销活”:宣传或者否定,只要支付钱财给他们。当然。这自然也催生了中介经纪业务,“大V”格局确立之后,微博营销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们打理“大V”,并从中收取费用。
微博迅速变成一个“传播生意链”,一个“转发付费的江湖”,有明码标价、有效果评估(“水军”),也有其他产品做二次开发(例如《罗辑思维》《蛮子文摘》)。
但是这一切,在“薛蛮子事件”之后,极速冷冻,甚至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话语禁区。
几乎所有微博营销业内人士在被问到“微博是不是进入后大V时代”,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两个意思:首先,话题很敏感,最好别碰;其次,“薛蛮子们和我无关。我有底线故我在”。
“大V”生意很简单
四方互动合伙人贾志生是一家社会化营销机构的合伙人。该公司体量不大,核心业务一直是针对“大V”做营销传播。在微博营销上的路数很简单,比如找一些明星做植入式广告——比较简单的方式是,送某明星一部手机,然后该明星用手机发一条微博,也会借助一些营销大号把要推广的产品放到其话题中。
贾志生表示业务越来越难做了:“营销大号的伎俩吧,现在不管厂商还是消费者,基本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对产品的推销能力越来越弱。而明星现在的要价越来越高,可不比前几年了。”
贾志生跟记者沟通时,既不否认自己在微博上“同流合污”,比如请“水军”,做过一些比较没有技术含量但足够恶俗的传播案例。但同时又强调:“比起某些太过火的同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底线的。我们会放大一些东西,会制造一些事件和话题,但绝对和造谣、传谣划清界限,不去突破一些底线和节操。”
在“薛蛮子事件”之前,微博上就开始高度马太效应了。一部分优质的“大V”开始成为稀缺资源,一部分“大V”由于过度开发已经导致影响力在减弱。所以有一些微博营销机构能挣到钱,但大部分其实没赚到什么钱。
最令人迷惑的是。其实社会营销的传播效果是没有衡量标准的。贾志生说:“目前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量化办法,所以客户只能看评论和转发,所以,你懂的。此外,目前的客户感觉对社会化营销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有影响力就够了。”
但客户并不是冤大头,客户也在进化。贾志生承认:“如今和以前的变化确实很大。一些事情会迫使行业越来越规范,同时受众对传播方案的识别度越来越高,接受度越来越低,或许是该把传统广告时代的一些东西拿回来,比如以内容为核心。”
策划过“天仙妹妹”、“别针换别墅”的社会营销人士“立二拆四”在看守所对媒体忏悔,承认自己过去对社会营销理解上存在巨大的错误。
在没有被拘之前。“立二拆四”一直认为:“社会营销策划是迎合网民的需求制造出网络热点;不能拿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我们这样的网民,不能因为我们做了有趣的新闻(尽管是假的)就认为我们道德败坏,把我们抓起来。另外。应根据网民的情感、情绪、情欲来做网络推手,比如你要让网民站到道德上的制高点肆意扫射某个靶子,获得快感;再如不要觉得自己很牛,要故意放几个漏洞让网民获得智商上的优越感,不断通过和网民的智商博弈来炒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策划最好能获得“大V”许可或者诱惑“大V”来转发。
但这种热闹的运作模式不长久,“立二拆四”在回忆其和某知名饮料企业合作时,提及这样的场景:“给他们做了一次活动后,大家自然就疏远分开了。想了想。也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和我们这样的公司绑在一起。”
“后大V”模式
NTA的李磊(化名)对记者表示,要梳理“大V”的体系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大致可以按照真实人格归为两大类:人和账号。其中“人”又可以分为几类:真实粉丝在百万以上、经常参与公众事件讨论的被划归到公众名人;聚焦在特定圈子里被定义为业界的意见领袖,而在微博上又以电商、零售、互联网圈子比较活跃;此外,微博红人也算一类。而账号又由两大类占据:媒体官微和营销大号。
而“大V商业”最令人争议的部分是“大V”中“人”这一部分的商业。实际上,媒体官微里面的商业,同媒体的主业传播运营是捆绑的,并没有单独“分拆”来运作。
在香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杨理博士告诉记者:“中国的大V是一个构成非常繁杂的群体,有不同的类型,他们覆盖的人群其实也是很不同的。比如有李开复类型的,有李承鹏类型的,当然还有任志强类型的。如果有社会冲突事件,大家会关注李承鹏;如果有经济冲突事件,大家会看任志强。”
杨理认为,作为自然人运作的“大V”,由于缺少信息甄别能力和机制,他们的举动会有一些随意性,比如,“他们可能瞬间被一条消息打动了,从而转发。而没有想到这条敏感消息可能是虚假的。”但随着很多微博营销机构的介入。一些“大V”的微博撰写和转发又变得“非常具有目的性和盈利性”,一旦这样的事情被揭露出来,“随意无目的的微博撰写和转发都被打上阴谋论的色彩,从而大规模地败坏了大v在传播上的口碑。”
杨理的结论是:“大V的巨大粉丝群和社会影响力同自身的实力是不对称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一个脆弱的结果。”
“薛蛮子事件”之后。一些微博营销机构开始淡化“大V”业务,但是他们强化“粉丝经济”的概念。像罗振宇就非常聪明地打出了“打赏求包养”的牌,从过去的公知感和道德感的“大v形象”,直接变成“天桥艺人模式”。就像郭德纲说的那样,“是被衣食父母供养的。回报是逗大家一乐”。
“后大V商业”的特征。杨理认为,“经过薛蛮子事件,微博营销者已经很害怕微博的话语广场放大器功能,因为这会惹麻烦。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阵地转移到跟粉丝更容易点对点接触的微信平台,比如像罗振宇以微信平台做粉丝俱乐部,他们信奉凯文·凯利的‘一千个铁杆粉丝’理论,并极力用在微博上赚取的大V名声实施线下套现。”
作为“后大V商业”的新锐平台——微信也不愿意走微博的老路。在微博的“大V”商业时代,微博平台没得到什么好处,好处被“大V”得到了不少。而腾讯则比新浪精明太多,他们不愿意雇佣很多人去监督“大V”的自媒体言论,忍受监管部门的呵斥,同时还在这个过程中没得到任何商业好处。微信5.0有一个很凶狠的举措,就是将所有媒体和自媒体号“折叠”到一个订阅账号里面:让他们不要搅坏了微信。
现在贾志生在和“大V”合作的同时,也试图“包养”一些新“大V”,尤其是借助微信平台火起来的自媒体。
互联网圈内一个比较出名的自媒体账号操刀手,如今是贾志生的合伙人,在被问到贾志生看中了该媒体人哪些价值时,贾志生表示:“其实我们不希望过多暴露我们的关系,尤其是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观点,其中涉及到的企业(也许是对手)又和我们有业务关系,外人难以去质疑他的公信力。但同时,他确实又是我们会见客户的重要背书,因为许多客户知道他,甚至比较欣赏。”
看来新“大V”们的生意关系更加脆弱。
摘自《21世纪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