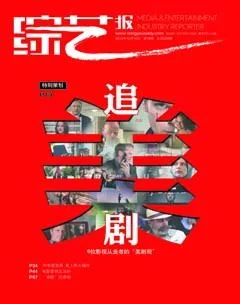终于《团圆》专访王全安
虽然王全安不怎么在媒体上针对他执导的影片发声,但他很能说,有点北京侃爷的意思,表达欲强烈。对于拍摄完成数年后才登陆国内大银幕上的《团圆》,王全安显然“对影片和市场都很满意”。该片早已在海外收回成本,也卖出很多版权,三年后在国内影院上映,“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毫无票房压力”,这种情形估计会让很多“文艺片导演羡慕嫉妒恨”。
目前,王全安在筹备新片《外滩》,也是关于上海的电影。对此,王全安说北方人对南方人总有一种好奇,就好像中国文明的流向,也是从北向南。
《综艺》:时隔三年之后,在国内大银幕上重看自己执导的影片,感觉如何?
王全安:一般而言,回头看自己执导的电影时都会有些忐忑,但这次觉得还好,内心比较踏实,没有感到太大的落差。除了这部电影当时完成的品质比较高之外,和它选用的形式也有关系。这种简练、缓慢的形式本身随着时间产生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综艺》:《团圆》的叙事很精巧,故事结构上前后都有对应。
王全安:表面上看似随意、自然的剧作,都经过反复推敲精心编排,就像一栋大楼里面,每一个构件的承重必须经过精密计算。对一个好故事而言,结构的力量很重要。这也许是柏林电影节对剧本会有一个褒奖和认可的原因。
《综艺》:《团圆》表面上平淡,其实内在冲突很激烈,就像一块大石头扔进无风的河面。
王全安:这属于个人偏爱。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喜欢比较生活化的东西,表达大家在生活里很好理解事情;此外,我又很喜欢这种戏剧的爆发力。电影不可能是生活本身,它只能像生活,有生活的质感,必须考虑戏剧冲突的质量。
《综艺》:这两方面其实很难平衡。
王全安:做起来确实比较吃力。就像绑着手打架一样,还要打赢,这需要有真材实料才能做得到。对生活的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对戏剧铺排的功力,做到两者相融是很现实也很苛刻的考验,但我更愿意迎难而上。
《综艺》:《团圆》和《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在故事上很相像,都是在讲一个女人如何面对两个男人的问题。
王全安:正常的一对一的男女恋情不足以引起冲突,没有三角恋的故事,很难展开一段银幕戏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写男女感情时,基本会写到三个人以上。电影总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我们解决问题时付出的那些努力。

《综艺》:《团圆》主要靠上海方言对白推进剧情,作为北方导演,你在把握上海文化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全安: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理解——什么样的人会想什么样的事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话。这确实有地域上的差异。北方人可能心直口快,南方人则相对迂回含蓄。但这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导演,我会通过各种途径确立上海人的表达方式。作为北方人我可能看得更直观更清楚。
《综艺》:看完影片,《团圆》的结局其实并不“团圆”。
王全安:“团圆”是中国人最爱念叨的一个词,代表着我们文化和习惯里的一种精神追求以及对人生的理a5r4theq0PmAO18U0gnHIA==解。这与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历史上注重家庭稳定都有很大关系。无论对人或事,团圆是最大的事儿,虽然团圆并不意味着快乐,往往矛盾爆发正是团圆的时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认同这种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尽管多数时候,人生不会像我们期待的那般圆满,但我们依然如此热切地追求着团圆的生活理念。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显得那么孤独。
当我们团聚的时候,所有的喜怒哀乐汇聚在一起,矛盾也会爆发,但离散的时候又会去思念。这里面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综艺》:“吃”,在你执导的电影里很有意思,《白鹿原》中的“吃”,看起来很香,但在《团圆》中,“吃”显得很压抑。
王全安:吃饭代表一种沟通途径,我们的胃比我们的大脑更深刻,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习惯对人类的影响很大,台湾和大陆长时间的分离造成的隔膜在饭桌上就会相对减缓,因为我们的胃口是那么地相似。至于压抑,因为《团圆》的故事背景比较沉重。
《综艺》:你曾说中国导演对现实生活非常陌生,现在这种看法有变化吗?
王全安: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导演和编剧更多在为制片公司创作,为商业创作,相对而言更自由。但一下子被彻底甩到商业市场里,我们又在不断趋利,就会有一种挖空心思、急功近利的心态。任何对生活的积累都需要成本,现在很多人显然认为这样做成本太高,希望什么都不干还可以去赚钱,结果离生活更远了。很多导演有时候被这种剧烈的商业态势逼得进入到一种幻想、臆想的状态。就像淘金热时,人们必须千方百计不落人后地从沙里淘到金子。
《综艺》:但类似《人再途之泰囧》这样的影片,市场反馈很好,观众还是很买账的。
王全安:我们不能用一种角度和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影片。《人再囧途之泰囧》属于商业产品,比较娱乐,承担的功能是让观众轻松。但《团圆》是另外一种类型——希望观众在看的过程中和看后,还可以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人再囧途之泰囧》主要诉诸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生理快感,不需要思考,就像坐过山车,停下来就没意思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最糟糕的是把二者搅在一起,让一部影片既要承载娱乐,又要承载思考,什么都想要,最后必然是什么都得不到。
《综艺》:你怎么看商业化对我国电影的作用?
王全安:对电影产业来说,商业化是一大进步。我国电影必须在商业上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形下,才能谈得上其他类型电影的正常发展。从比重上来讲,主流应该是商业电影,有文化承载的艺术电影永远是少数,这在世界范围内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