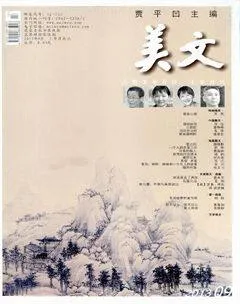军马,钢枪,钟表和一个凡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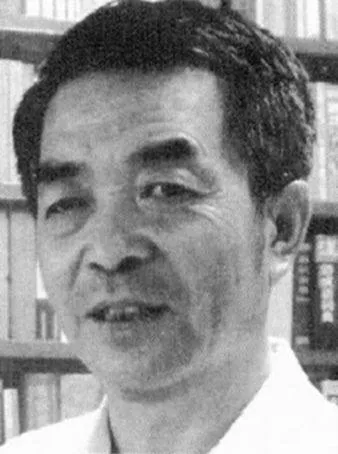
金刃
1954年生于河北河间,当过石油工人,电台报务员,文学杂志社编辑。出版作品集《安魂曲》等,主持编辑撰写《烽烟铁血录》《沧州名人传》等。河北省作协会员。现任河北省沧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父亲辞世几年了。身体原本健壮的他走得十分突然,那年初二,全家人还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为他欣祝八旬整寿,初五凌晨他却与家人阴阳两界。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一生无大作为,但对工作却极为认真,以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而赢得同事们的赞许,但又因性格暴烈而难得人们接受。一生平平淡淡又充满坎坷。
父亲年幼时家贫无着,未能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后被强求扫盲才识了几个字,勉强摘了文盲帽。也许是表达能力不强,也许是觉得没有什么可夸耀,他极少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到我成年后才从他的战友和同事的口中知晓了父亲传奇色彩的星星点点。
父亲身材魁梧健壮,特别是一身膂力少有人可比。在年轻当骑兵时,连队接了一批新马训教,其中有一匹枣骝马刚烈无比,全连无一人制服还伤了几名战士,分区派来的驯马教官屡施手段也未能驯服。在一旁观看的父亲脱下外衣说声“我来试试”,待狂躁的烈马稍一减速便跃上马背,双臂紧紧抱住枣骝马的脖子,两腿插入马前腿中间用力向外狠别,硬是把狂跳的悍马摔倒在地。父亲死死摁住前驱任它四蹄乱蹬,泥土如雨点般洒满全身也不松手。待烈马气力耗去大半才松手,一伸手从驯马官手中要过长鞭,待烈马刚刚站起身照着后臀狠狠一鞭,烈马疼痛难忍狂跳欲逃,接着闪电般朝左右耳稍“叭——叭”甩出两个响鞭,枣骝马立时骇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父亲站在马头前震慑地晃着手中长鞭,烈马双眼直直地盯着父亲,四条腿不停打颤。他拍拍马头,又一挥手,战士们上前给马套上笼头,备上鞍鞯,父亲一偏身跃上马背,轻磕马镫,枣骝马威风不减徐徐小跑,在驯马场兜了两圈之后,父亲抖抖手中的缰绳,枣骝马箭一般射向草原。半个小时后,浑身汗如雨淋的烈马载着父亲回到了驯马场。父亲跳下马吩咐战士:“细心地给它洗洗,让军医在它屁股上抹点红药水。少饮水,喂青草,晚上再加料。”
原来,他这一鞭子在马后臀打出了一条二尺长半寸高的肿痕,加上耳边甩的两个炸雷般的响鞭彻底震服了桀骜不驯的枣骝马。这也把在远处观看的蒙古族牧民给震惊了。从那以后牧民们都称他是“能摔倒烈马的老刘”,并由衷地佩服他。
从此,凡有烈马都交由父亲驯服。但他十分爱护军马,说是“烈马虽烈但有胆有力,驯好了绝对能上战场,不畏枪弹能护主人。”驯时从不施殴惩之法,多以拿手的响鞭甩耳,一两鞭即慑服,再如膏药般贴在马背上,任它蹬跳驰奔直到用尽全力而驯服听令。所以,驯好的烈马对他都很服帖。他每次出差回来,先不回家吃饭,而是在马厩卸下鞍具,仔细检查有无硌伤,用棕刷认真地刷两遍马的全身,再用软毛刷小心地梳理鞍鞯部位的压毛和鬃毛,再牵着遛几圈,饮少许水,添上草料看它吃去大半才回家。
他对军马有很深的感情。从小到大我只见他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1961年收到家乡祖母去世的电报,他长叹了一声,蹲在地上无声地流了泪。另一次是在1968年,一匹曾立过军功、身健体硕的大花马改做驭马多年,年迈体衰,得了一种怪病——先是烦躁不安,厌食;接着频频甩头,四蹄刨地,蹄甲发软,有些溃烂;后来连水也很少喝了,掉膘很厉害,只剩嶙峋的骨架支撑着还很高大的躯体,饱受折磨。上报军分区后指示下来:立有军功的大花马早已进入老年,这是衰老的症状,同意结束军役。并建议为减少其痛苦,可由人工代为结束生命。
从大花马显露衰亡迹象时,父亲就没有回过家,每天在马厩陪他心爱的大花马。有时母亲做了他平时爱吃的红烧肉、手抓羊肉,他也懒得动筷子,大花马不吃料他也无食欲。后听他的战友讲,从接到分区命令他就再也没有休息过。一会刷马身,一会喂水喂料,还把分配给自己的苹果用马刀削皮喂马(他自己吃水果从不削皮,有水就随便冲冲,没水就拿来在衣裤上蹭两下就吃)。大花马真的老了,磨平的牙口连苹果都难以嚼烂,父亲便用刀把苹果切成薄片喂它。大花马含着眼泪,一点点地将片片苹果磨烂咽下。直到最后一夜,大花马什么也不吃不喝了,父亲回家找出部长两年前送给他的茅台酒,朝水瓢里兑进一两多,喃喃地说:“大花马,你跟了我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我不会喝酒,也没让你尝过一口,今天你就尝尝吧。”大花马似知似懂地一口气喝下了掺着茅台酒的半瓢水,两眼泪流不止。
早晨的时候,执行任务的战士来到马厩,父亲已把大花马刷洗得全身一尘不染,棕白红三色相间的毛发在阳光下闪着彩缎般的光泽,挺立的鬃毛修剪得如同整齐的韭叶,马尾编成了油亮的发辫,末梢还扎了一个红绸子的蝴蝶结。马身上的披挂是它多年前在剿匪征战时的行头,腰臀上搭苫的军用马褡子,里面装了两床军被两条毛毯。父亲将缰绳递给战士,大花马似乎知道已到永别时刻,不叫不闹,流泪的双眼紧盯着父亲就是不走。父亲搂着它的脖子在它耳旁轻轻含叨:“走吧,走吧。过些年兴许咱们还能见面做伴呢……”大花马三步一流泪,五步一回头地随着战士走出马厩。
父亲将自己的围巾递给另一战士,声音有些哽咽地交代:“到时盖好它的头,一定要把两眼蒙住。”
几分钟后一声枪响传来,父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事后大花马用军被毛毯包裹好葬在了土包前,墓前立了一木碑:荣立二等功三十七号军马之墓。
父亲几乎天天去墓前,看到“军马”二字很为不爽,不依不饶地找教导员理论,“不能写军马,应改成烈士。”还多次讲出充分理由:剿匪立二等功的有几人?追走私犯四天三夜不吃不喝谁能比?八九年间驾辕拉土方、木料、钢铁、砖瓦砂石,搞生产拉粮、蔬菜,去昆仑山打猎……有上千车吧,有多少吨?有多少公里?不善言辞的他还真说服了众人,另写了一块木牌矗立于大花马墓前。
后来,军分区要求将大花马立功的奖状送交分区,他先是死活不答应,要自己保存。直到分区来人说军内规定烈士奖品要入档,建了军功馆要进馆展出,让大家都受教育,他才依依不舍让人家带走。
父亲也爱枪,因当骑兵,特喜爱762骑枪。转业后再没能骑马挎枪,很是郁闷了几年。1974年通过在省军区我的叔叔摸到了一支新式小口径步枪,一次能押五发子弹,瓦蓝锃亮的枪管,手感特别舒适的木托漆得亮如美瓷,很是惹人喜爱。他常常提着枪到朋友们中间夸耀,却又不让人家过瘾,惹得一伙朋友讥刺说:“枪真是好枪,可惜落到了枪法很臭的人手里了。”他也不计较,嘿嘿一笑,倒背着枪扬长而去。
他有一个酷爱枪的朋友在部队是优等射手,转业到劳改农场当管教科长,三番五次来缠磨着要这支枪,每次都拿着当时紧缺的东西,诸如录音机、高级毛料、电子表等来交换,但每一次都不能如愿。过了一些时日,他又带着一块全自动梅花手表来换父亲的小口径步枪。
父亲见到漂亮的梅花表动了心,思忖了一番说:“你是优等射手,老说我的枪法臭,今天咱俩就用表和枪赌一把,谁枪法好东西就归谁。”
科长说:“老刘,你的枪法臭谁不知道啊?这样赌不明摆着我欺负你吗?赢了也被人笑话,要赌可以,但要换个赌法。”
父亲说:“就这赌法。愿赌就干,不愿赌拉倒。”
科长抓耳挠腮地犹豫了半天说:“哪你输了可不能给别人说是这种赌法。”
父亲回答:“没问题。你这表是多少钱买的?”
科长不解地问:“不是赌吗,还要问什么价呀?”
父亲说:“你不说清价钱我就不明白值不值,哪就没法打赌了。”
科长忙不迭地讲:“要赌,要赌。这是我香港的大舅哥上个月带来的,488港币。”
“港币?是香港的钱啊。合咱们多少钱?”
“大概380元吧。”
父亲叫着我的小名说:“祥子咱们走。打麻雀。你当证人。”
我们三人到了一棵大杨树下,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父亲装上子弹,把枪递给科长:“你先来。”
科长也不客气,接过枪左眼一闭,“乒”的一声,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了下来。我跑过去把拣回来的麻雀交给科长。科长用手掂了掂死去的麻雀得意地说。“鸟都飞了,老刘你还是打个树杈吧。打中了算平手,咱们再赌别的。”
父亲以少有的严肃神态说:“打的东西要一样,不然不公平。”
向东走到二百米开外的一片小树林边,就听见林中有麻雀在叫。父亲拣了两块小石子给我,让我打树上的麻雀。我疑惑地向树林随便投去,雀群“呼啦”一下飞起来,几乎同时父亲手中的枪响了,一只麻雀从空中栽了下来。科长吃惊地拣了回来,将两只死麻雀摊在一块平地上。只见科长打中的那只肚子没了,肠子等脏器都流了出来,父亲打中的麻雀是从前胸和脖子贯通,中间的骨头没了,两边的皮肉却还连着。
科长吃惊地喊起来:“老刘你今天吃了什么药,这么神?”
父亲淡淡一笑说:“走,回家再说。”
到家后父亲打开箱子拿出一沓工农兵钞票(拾元面额)说:“儿子大了,要谈朋友,正缺一块表给儿媳准备,你正好送上了门。”说罢催促我:“还不快谢谢叔叔?”
几天后父亲听人说人民币与港币1∶0.8左右的比价是官方牌价,实际上人民币要低于港币,大约在1∶1.05左右,又带了一百多元到农场给科长送去,科长死活不收,父亲无奈,只好到牧业村买了两只肥大的羯羊送去。
此事虽说赢了赌注,但我十分疑惑,以枪法臭闻名的父亲,那天为何那么神奇?如说是运气,可自始至终他都十分笃定,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态。事后探问他几次,没想到都惹得他十分恼怒,阴沉着脸吼斥:“小孩子家问那么多干什么?”这让我感到其中一定有他难以启齿的隐情和痛楚,直到他过世后,询问母亲才知晓一点其中原委。
1959年春夏平叛时,与西藏相邻的柴达木形势也很严峻。四月间,一伙叛乱分子挟裹了一个部落的人朝南开拔,欲进藏声援。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赶上并拦住数百民众,但又不清楚他们走哪条路入藏,便派出几个小组分赴各条道路追赶。父亲骑着大花马与一个会藏语的甘肃籍班长为一个小组,追寻了三天后的清晨,在唐古拉北麓一小山岗处赶上了这伙人。父亲和班长绕到山冈南坡,简单做了工事。班长用藏语喊话:“西藏叛乱已平息,你们不要再去西藏了,回家去放牧,好好生活。”
带头的几人哪里肯听,端着枪、挥着刀就往山头冲,后面还紧跟着几十个亡命徒边喊叫着边朝山上冲。父亲先是朝天开枪示警,这伙人一怔,听听是朝天开枪,就策马再冲。眼看只有几十米了,父亲一枪将冲在前面的头目打下马来,其余随从被吓住了,急忙策马逃走,那个班长赶到被父亲击下马的头目跟前,给没有死亡的头目又补了一枪。后面的大部队听到枪声赶了过来,安抚被挟裹的牧民,护送他们返回了家园。
父亲对那个班长朝受伤的头目补射致死,心里有看法,但又不善言辞。他更不会想到班长在首长那里颠倒黑白,把战功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后来,父亲离开部队时才知道当时班长的表现。他像一个出色演员告诉首长说:“我们两人追了三天两夜赶上了这伙叛匪,我一枪就打死了叛匪头子,吓住了叛匪,稳住了牧民群众。老刘嘛,不懂藏话,打枪也不行,子弹全飞到了天上。”
最后的结果班长荣立一等功,大花马也立了二等功。父亲非但寸功未获,反而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在副排职军衔上就此止步,也留下了枪法太臭的名声。
存留在心里多年的疑窦让我为父亲伤感。这是他一生的耻辱,也是难以启齿的伤痛呀!
父亲不饮酒,只吸香烟,而且不讲牌子,只要冒烟就行。但却非常喜爱钟表。母亲带我们随军赴青海高原安家后,他置办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只黑盘的罗马闹钟,直径有十二三公分,镀金的侧板金光闪闪,小时数是罗马数字,分针、时针和数码顶端都有夜光,一到夜间闪闪发光,十分好看。更妙的是闹铃,每次先是缓缓地“丁零,丁零,丁零”慢慢响起,然后逐渐加快,成急促的“丁零……”声,疾响半分钟后逐渐缓下来,慢悠悠地、一声长长的“丁——零”才停止,十分清脆悦耳。这只闹钟质量非常好,到现在还能使用。我曾问过父亲1958年花多少钱买的,他总笑而不答。直到我儿子上小学五年级问他时,父亲才给孙子说是1958年缉捕走私犯立了功,领导让立功者自选奖品时他一眼选中的,象征性地交了十元钱。
他对钟表的执着和酷爱还体现在对我们子女的关怀上,我们兄妹不论谁走出校门参加工作时,他总是想办法买块手表赠送,作为子女步入社会的纪念品,并反复叮嘱:“参加了工作就成了公家的人。上班、开会一定要遵守时间,不能迟到早退。交友约会要守时,尊重别人才能交往真诚的朋友。”这个看似平淡的教诲我们兄妹都铭记在心,践行之后也使我受益终身。
父亲老年后回到沧州,我们兄妹知他虽身居故乡,但缺少战友和同事,除了偶尔看看电视之外,没有多少爱好。识字少读报也难,生活较寂寞。我们兄妹都想法给他找点欢乐。不论谁外出出差、考察或出国,总设法买块手表捎回来给他。一有空父亲就把几十只表全部摆在写字台上,一只只看,一只只听,有时还考问串门的邻居或亲友。听到不太在行的回答即认真纠正,一一道来讲解各种牌子手表的工艺、价值和特点。他最看不上的是石英表,父亲说:“针在动,没钢音;不用弦却不显数字,是个非电子又不机械的‘二串子’。”
每每看到他沉醉在对钟表的鉴赏评判时的神态,就看到了一位年近八旬、孤独老者少有的满足和欢悦。
父亲壮年时工作十分繁忙,无暇顾家,更谈不上疼爱儿女。但到了老年,分外疼爱隔辈人。当他唯一的孙子刚上小学,青海的冬天寒冷无比,我的妻子给儿子织了一双毛线小手套(当时市场根本没有儿童手套),他看了看说:“不行,毛线有窟窿眼透风。”第二天便跟牧民朋友讨了张羔羊皮,自己熟好,铲刮净细毛,按手套画线剪裁,细线密针地缝好,再套在毛线手套外面,于是,一副灵巧御寒的小手套就戴在了儿子的手上。别的家长都称赞手套做得又巧又好,缝线又细又匀,如同机器制作的一般。儿媳惊问父亲的手艺为何如此之好,他却羞涩不语。还是母亲一语道破:“多年缝补马鞍鞯、缝补围脖和肚带练出来的。”
父亲嘿嘿一笑,眼睛里就闪出了泪花。我知道母亲的话又触动了父亲内心深处那根最脆弱,也是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