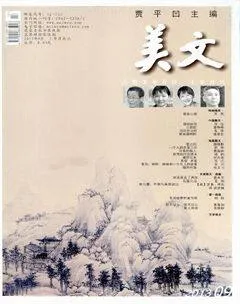生活世界的爱与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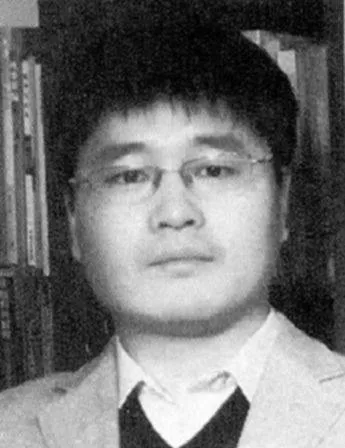
杨辉
1979年生,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在读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师。发表论文及小说多篇,著有《终南有仙真》《小说的智慧》《骊山释道》等。
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精神方式,它向人生的具体世界,即生活世界敞开,切近有血有肉的感性生命,接纳色声香味触法,却在这里获得精神飞升的权利。因为“人,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它是心灵和生活世界相遇之后的精神发生,出自日常经验,却意味着一种突破和超越,它呼唤有可能实现的意义秩序,让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变得秩序井然,它是对世界的意义的阐释和守护。如同那个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所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若无文字的世界对意义的守护,我们的生活世界将是一片混乱和虚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深层次里,说的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上,个人的精神旨趣和价值偏好,是理解生活世界中诸般物象及人事不可或缺的先在条件。比如“鱼”,不过是生活世界中司空见惯之自然物象,本无“意义”可言,然一旦与一颗诗心相遇,便生出万种风情和万千气象,生出或飘逸或潇洒或空灵或多姿多彩多情;有了自如的自在的自我的舒缓的奔放的落寞的惊慌的柔韧的姿态;它的收放有度、风华正茂和风情万种,或许只是爱生活爱生灵爱万物爱自然的养鱼之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鱼之乐鱼之需,“是在大江大河中弄潮”从而“相忘于江湖”,还是在“温床里怡然自得游弋”?无论何种答案,都不过是人的“臆断”,是“想鱼的人在做梦”。然而这臆断或梦,却实实在在能启发人深入领会养和爱的学问。
唯有对这人世间存着一份同情的理解和爱,才不会槛内人动辄作出世语,一味不着边际凌空蹈虚。也不会贸然以一己之价值偏爱,遮蔽这世界意义生成的多样可能。一如作者记住的梅“是小学教室里的那副梅?是课堂上老师描摹的那片梅……亦或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专注的梅“是隆冬公园里的那片金黄……是扶疏枝头的遒劲……是沮丧时提神的灿烂”;走进的梅,是傲岸傲骨傲然,是温润温和温暖,是淡定淡泊和淡然。而以“是,又不全是”作结,暗示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背后是个在生命于彼时彼地独特遭际中,心灵与物象相遇之后不同的精神表现。而对书的爱,可以贯穿一个人自幼至成人的整个过程,书能在顺利时“告诉我人生不仅有得意,还常会有挫折,得与失才是完整的生活”;还会在倦怠时劝勉自己“要经得起冷落,要耐得住寂寞”;书能在你面对诱惑时,向你“发出必须坚守的忠告”。一言以蔽之,无论何种际遇何种情境,心灵何所需何所求,书均能如你所愿。因为它向你敞开的是理想、境界和情怀,是“属于人的价值追求和心态平和”。在那里,你能与伟大的心灵相遇并倾听他们之间的交谈,通过他人理解自己,而理解了自己,也就理解了整个世界。
并非单向度的、扁平的、单一的抒情声音的存在,多少有点像博尔赫斯笔下虚构的不同年龄的自我之间的对话,甚至更为复杂,他呈现出多个自我的并置和共在。他们聚在一处,构成复调式的对话的和声,共同表征着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和生命体验的变化。在这里,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压制和矛盾,正如作者不会简单地以中年时的沉稳否定青年时的不羁,不会在“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间作境界高下的区分。每一个自我都是作者精神的映像,但又不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