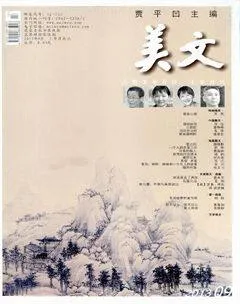分类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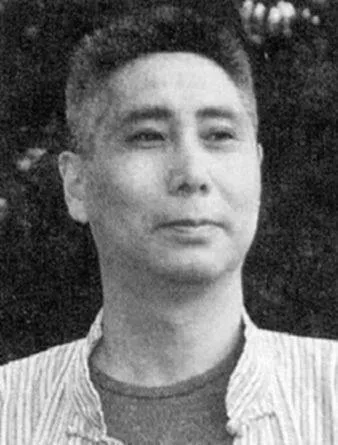
费振钟
作家、历史文化学者。1958年出生,江苏兴化人。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等。
现在,我们转向一个具体的较小的病案讨论上来。
案例起于一位男童捉蟛蜞跌进水中,救起后发大热,幼科医师用镇惊清热药治疗,服药后第二天,却昏迷不醒。喻嘉言受邀往诊该病童时,只见他“胸高三寸,颈软,头往侧倒,气已垂绝”。本来是一个偶发性外症,但演变成“死证”,让喻嘉言感到十分惊异,他对同时参与会诊但已经绝望的医师说:“此儿受症,何至此极!”接下来,喻嘉言略带几分玄虚地要所有人都离开,让他“一人独坐,静筹其故”,过一些时间,他才开口说道,我知道病因了。于是大家都来听他做讲解分析,其后自然按喻的意见治疗,先用“理中汤”煎服,清除那些不恰当的药物,再“玄明粉化水”等生津药灌服,第二天病儿刚刚苏醒,便大喊一声“我要酒吃”。死证再生,皆大欢喜。
其实喻嘉言面对这个病例时,不会是临时想法,他应该早有深思熟虑。在自述个人医学经历时,喻嘉言明确地说,早年他与一些幼科医师就“惊风”发生过争论,后来从另外一位当代医学家的著作中,才深刻了解到,有关这种幼儿疾病的分析早已有之。为了使这次临床事件产生生动的教学效果,看来喻嘉言的做派确有点戏剧化。换个角度说,喻嘉言在这里显示出一个高明的医学教授的教学艺术。
在接下来的长时间讨论中,疾病的类型问题呈现出来了。这是一次关于“惊风”的否定性的讨论,喻嘉言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看上去受惊而病的典型病例,来追究“小儿惊风”的真实性。正如当时几乎所有幼科医师所持的普遍看法,“惊风”为儿童专有疾病。这一疾病种类的认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太清楚,医学典籍上也未见记录,但在临床史上已持续了漫长的时间。然而“惊风”是真实的疾病吗?约定俗成的看法,如何形成知识的混乱和分类错误?而相似性造成的模糊,又如何导致对疾病认知的偏见?等等,都有待这次讨论得出结论。
作为疾病的“惊风”,属于历史性误读。形成误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认识论上的来源,喻嘉言指出:“方书中有云,小儿八岁之前无伤寒”,即因这样的绝对认识,导致一些幼科医师“为惊风之说树帜”,长期影响了人们对幼儿“高热”“筋脉牵强”等症状的错误判断;二是语义的缺省,前人观察到,幼儿由于“阴不足阳有余”“故身内易于生热,热盛则生痰、生风、生惊”,常见的疾病症状为“热痰风惊”“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以惊字领头,风字煞尾”。后人不能全面理解,望文生义,视“惊风”为幼儿“奇特之病”。在喻嘉言看来,这“百年之间,千里之远”,误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颛颟顽固的医人,他们罔顾医理,因而看不清疾病的本质,让无数热病中的孩子陷于误治险途。而在临床上,这些无知医人,一见病势危急,就“汤药乱投”,大量使用“金石寒冷药”来“镇坠外邪”“日杀数儿,不自知其罪也”。
疾病讨论在十七世纪,没有可能进入医学公共话语,喻嘉言全力批判“惊风”,显然限于私人领域,他的例子,如福柯分析临床医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时所说,是为了“训诲”。不同于临床教学建立师生共有的医学经验,喻嘉言的目的只在“传道授业解惑”。他以对该病儿的确诊,以及有效治疗,否定了“惊风”的真实性,在他的学生面前,一种绝对结论,使学生们在临床前除聆听和接受他的知识外,不需有其他犹疑。他的一位姓王的学生,因为在治疗另一个病儿过程中,稍有犹豫不定,受到嘉言的愤怒斥责,几乎要被逐出师门。yxYu7JgYLuIf4SNFN/53cg==
回到讨论现场,关于“惊风”的陈述与辨析,自然转移到“伤寒”在幼儿身体的表现,这意味着,直接的临床经验语言在讨论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将幼儿疾病从相似性的混乱中,拉回统一的知识立场,制止医学过度分类对于疾病真实的迷惑、干扰和破坏,纠正“惊风”这一疾病病种的“妄造”。按照喻嘉言的见解,所谓“惊风八候”,即抽掣、目邪、心乱、搐搦、角弓反张机等机能障碍,表面上看是“受惊”造成的病症,实际上是“小儿伤寒”后,寒入太阳经,引起的病理反应。“惊风”之说在表面的相似性上误导了疾病的本质,“小儿易于外感易于发热,伤寒独多”,才是符合“伤寒”这一知识体系的正确认知。这里清楚表达了喻嘉言对“伤寒”知识统一立场的坚守,任何离开这个立场的“分类”,都必须受到严厉批判和清理。喻嘉言特别举“产后惊风”的类似例子,“新产妇人,去血过多,阴虚阳盛,其感冒发热,原与小儿无别”,然而,却被很多医师不分青红皂白称为“产后惊风”,甚至形成女科传统中的一致看法,这样违背伤寒医理的病种分类,他绝对不能容纳宽待。
不难看出,这次由一个病儿引发的讨论,有作为“伤寒”专家的喻嘉言对个人权威的捍卫,甚至他对“惊风”的否定,也不无自私和独断之意。但我们仍然得承认,喻嘉言的例子说明了中国医学的一个事实,优秀的医人不仅仅出于专长,对某种医学知识体系极力维护,而是中国医学知识体系培养出来的敏感,使他们特别自觉地警惕作为统一性知识的敌人的分类。
任何体系的存在与分类的企图都会缔结敌对的紧张关系,就医学而言,中国医学的特点,决定了它从来都以体系的多样性解释,代替疾病的分类,从而避免这种敌对关系。问题在于,一方面如“伤寒”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可动摇,另一方面由于身体与疾病的复杂性,在已知一系列疾病之外认知未知疾病的冲动,作为医学运动的内在推动力,潜伏在每个医人的知识需求之中,诱惑着医人们背离体系规定从事分类活动。从中国医学历史蛛丝马迹中不难发现,疾病分类其实一直暗里明中进行,而体系虽然常常不动声色,却总以否定性力量,控制与抵抗着分类对疾病新病种的认知和命名,尤其当分类造成医学误导和危险结果时,在中国医学立法森严的殿堂上,体系常常以一种法官的姿态,宣布新病种命名的非法和失败。
因此,喻嘉言在有关“惊风”讨论中居高临下、激昂的医学权威行为,实际上代表了这个体系的否定性力量在十七世纪的一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