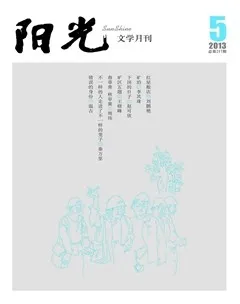高度的敬畏,深处的疼痛
我和江耶的相识,大约是在五年前,那天和著名诗人叶臻等几位好友的小聚。后来,便陆续读了江耶的一些诗歌。2007年我给《诗歌月刊》《安徽诗歌巡展·淮南卷》写评论《诗意地栖居于淮河之南》,其中谈到了他的一组诗歌,说他诗如其人,“善良而自信,宽厚而内敛”,很本分忠厚的感觉。一个月前,闲来到他的办公室坐坐,他一下拿出两本书送我,一本是散文集《天在远方弯下腰来》(作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就是诗集《大地苍茫》(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才发现,短短几年,江耶创作如此勤奋,收获如此丰硕。我在惊喜之余,得以较系统地读了江耶的作品。读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相见恨晚。这不独是因为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他其实和我一样,内心很卑怯,很内向,怕社会怕人事,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有很打动我的东西。
《大地苍茫》是《绿风》杂志社“金驼铃诗丛”中的一本,显然,《绿风》是在重点推出这一批比较看好的青年诗歌才俊。主编曲近在“丛书总序”《融生命于思考之中》这样评价这批诗人:“思维触角开始贴近生活和时代,关注底层人的命运、生存环境及状态,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几位诗人的共同特点是:创作起点高,艺术敏锐性强,思想和情感能较好地融入诗歌之中;在深入生活、深度思考、深刻呈现、拷问生命终极意义方面,都把握得较好。”他还特别提到:“江耶在关注底层人群命运时所具有的强烈的朴素情绪感人至深。”我从内心里是十分认同曲近的评价的。
《大地苍茫》这部诗集,从题材来说,主要分两大块。一是写煤炭和矿工的,一是写乡村和农民的。江耶自己这样说道:“乡村和煤矿都是与大地有关的意象。一个在大地的表土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在大地深处作业,回到地面时,大多与阳光擦肩而过。因为深入,所以觉得神圣,也感觉到其神秘,觉得它们都有天意的成分。除了我们眼前的情景,其前因后果,其曾经与未来,都是一片茫茫。我认为我必须也应该保持高度的敬畏。”(见《从最小的可能做起》)从这些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的那份真诚,那份对底层的敬畏与关注,一种在当今世道十分罕见的善良、悲悯与深情。
我一直以为,读一个诗人的作品,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你一定能从作品中倾听到诗人的心灵之声。照尼采的说法就是,诗人不是告诉你“这是什么”,而是诉说着“这对于我是什么”。一切事像都关乎心灵,世间苦难皆与我有关。江耶说,我就是要把它呈现出来。如此,我们得以发现那被遮蔽了的大地深处的疼痛,那隐秘之中的创伤。
一、煤的现象学还原
《大地苍茫》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煤的。“煤”,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天天照面,好像十分了解,然而,我们当真能有这样的自信吗?江耶是这样写煤的:
多少年了,一直如此
并不是为了什么
就这样认命
从不曾想过要有所改变
甚至没有过真正的思想
一味地接受人们赋予的秉性
仍然不发一言
一以贯之地保持
什么都不像,乌黑,脆硬
无动于衷,没有低调和高潮
即便被点燃
火也是从从容容的
看着看着就会
让人掉下眼泪
——《煤意》
江耶眼中的煤沉默,逆来顺受,甚至还有些木讷和不伦不类,但是,这才是真实的煤,受难的煤。江耶透过人们强加给煤的种种“秉性”,书写了煤的宿命,那是煤的真实的历史。江耶知道,要看到煤的创伤,必得悬置长久以来人们预设给煤的种种标签,哪怕是善意的标签,使煤还原它真实的存在。用江耶自己的话说,这就叫“去蔽”。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曾这样说过:“说出或写下‘面包’这个词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了这个词,曾经进行过战争,也出现过谋杀,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见《伯尔文论》4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以往我读这段话,也就是觉得“面包”或者其他一些词,有着字面背后的含义,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联想来帮助认知和把握。可是,读了江耶的写煤的诗句,我明白了。伯尔是要我们用心去听听“面包”词语深处的疼痛。江耶就是因为听到了煤内心的疼痛,所以,“看着看着就会,让人掉下眼泪”。这是对于“煤”的认识吗?不,这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冷冰冰的认知,这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倾听,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领会。江耶是这么看待生命的。他说:“大地上的每一个事物,不管多么细小,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都是大地母亲养育出来的,与我们同样重要,是我们存在的环境中一道必须的风景。”(《从最小的可能做起》)在他的眼里,“煤”是有生命有尊严的,是值得我们仰视的。但现实是“一块煤/在正常人的眼里//怎么看/都像是一抹灰”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煤”不只是被遮蔽,煤还被亵渎,被遗弃。“这一块煤,它抬不起头/它害怕一不小心弄脏了/高贵人的衣服,玷污了/他们的目光和心情,害怕弄脏了/他们高高在上的干净生活。”这里,江耶代煤说话,说出煤深藏在内心的卑微与羞怯,也展现了煤的那种可贵的朴实与本分。在与高贵者面对面的生存中,江耶在写实中寓以反讽,使我们对高贵有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和审视的目光。江耶告诉世人,正是这样的煤,“燃烧成干净的火/发出干净的光芒和热/使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能够高贵地生活。”(《一块煤》)这就不只是单纯的现象学还原了,诗人以他的“热爱”和热爱支持下的持久关注,为我们打开了一块煤的真实内核,实现了对煤的灵魂的照亮与敞开。正如大哲学家谢林所说的:“灵魂不是生硬的,没有感受性的,更不是放弃爱,灵魂倒是在痛苦中表现爱,把爱表现为比感性的此在更加青春永驻的情感。这样,灵魂便从外在生命或幸福的废墟中升起,显现为神奇的灵光。”(《艺术哲学文选》)诗人正是这样以他的艺术之思,还原了煤的独特生存状态,使得煤的真实的存在得以澄明,并为煤的灵魂重新命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从煤的过去、现在的生存呈现,进而预见到煤的将来,预言着煤的救赎与新生。诗人说“是的,这块后来的煤/不停地走动在时间的深处。他在打捞、救活/更多的煤。”(《他是一块走动的煤》)诗人看到了煤的清醒与明智,更看到了煤的自信与自尊。谁也拯救不了煤,拯救煤的唯有它自身。诗人诗意地想象着:“大树还要活下去/大树心里都是阳光灿烂/ 大树即使改名字为煤/大树仍然高大着/高大的大树从地层深处上来/在阳光下一站/这些叫煤的大树/立刻就顶天立地。”(《地层深处的大树》)如此,江耶的写煤的诗句,揭开了以往加在煤身上的重重遮蔽,照亮了煤的卑微而真实的生存,使得煤内心深处的疼痛得以表达。同时,也描画出煤的生命运动的轨迹与命运走向。他的煤炭诗,是一种命名,也是一种预言,更是一种喟叹与咏唱。
二、把诗写在苦难的现场
在《大地苍茫》中有一组诗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些诗是《他在大地深处却感觉不到母亲的温暖》《他的热情被风里高昂的温度埋没》《一切仿佛都不是真的》《二月十四日,一百二十四朵玫瑰突然开放》《事故损失》《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瓦斯爆炸的巷口小坐》《兄弟,请原谅我》《残缺的天空》《在瓦斯爆炸的巷道行走》《上半身诗人》《拄上拐杖的煤》等。这些诗篇是写矿难的。像这样集中写矿难,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别说是诗歌作品,即使是新闻报道,也没有这样密集地全方位地直击灾难的现场。我们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国度。我们的民族几千年习惯了大团圆的自欺欺人的收场。可是,对于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诗人来说,他无法做到熟视无睹。诗人写道:
曾经的光芒照亮不了现在的黑暗
在这个深夜时刻
我坐在巷道口的铁轨上
看不到里面还是黑洞洞的深处
八十八个生命就在一瞬间倒下
我感觉他们分明还在巷道里
呼呼的风声从风门里挤出
就像他们掺杂了煤灰的呼吸
还有一些嘶哑的声音,仿佛他们
憋在胸口的呼救,像一把刀子
划破这个外表完整的深夜
让我的身上到处疼痛
——《在瓦斯爆炸的巷道口小坐》
西方哲人不是说过“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吗?可是,同样是这个哲人却又说过:“苦难,而不是肯定,是艺术的人性内容。如果抹掉对累计起来的苦难的记忆,是难以想象作为历史缩影的艺术会变成什么的。”(阿多诺《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让人矛盾,真实就是这样撕裂着诗人的内心。江耶的诗写在了苦难的现场,不如说是现实把苦难和诗人紧紧连在一起,那是一种无法挣脱的纠结与缠绕。因为那是88条活生生的生命,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活在诗人心中的不灭的魂灵。有人擅长遗忘,可也有人固执于记忆。江耶就是固执于记忆的人,因为,那些“嘶哑的声音”是“刀”。只有这样的真爱,才会有血浓于水的深情的铭记!也只有这样的深爱,才会有诗歌的良知与正义。
这是一个死亡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
我在反复寻找,我的诗句已经失去血色
不管风能否带去,云走过月再走向日
一心想把这一天阴暗下去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常说,对于苦难,要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我对这样的话常常怀疑。什么事业需要这样的悲痛来化成力量去做?如果我们对生命的悲痛轻易可以化去,如此伟大的事业真的存在吗?我倒是更爱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这是心灵中无法承受之痛!而江耶,不独是担心,更有着深深的忧虑和无名的悲愤。所谓“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真正的痛苦也丧失了意义”。以生命的名义,诗人拒绝遗忘!于是,诗人以笔为刀,划开了尘封的伤口,在灾难五周年之际,留下了这样的诗歌档案:
责任者的责任进了档案
过了惩处期限的历史,砌出一个个台阶
还有希望一路攀登上去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档案,它载入了煤矿诗歌史,是诗歌的一次勇敢的介入。这样的诗歌行动在当今实在是凤毛麟角了。惟其如此,这个行动堪称为一次诗歌事件。正如萨特所说:“作家选择了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全部的责任。”(《什么是文学》《萨特文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江耶以为这未必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但对他这样的生者,却只能如此而已。诗人深知,血的恣肆与生命的毁灭,使得任何文字失去了分量。但至少诗人没有逃避或者远离苦难,吟唱爱和心灵的诗歌毕竟来到了苦难的现场。诗人只剩下痛苦的呻吟:
于是,这煤炭的生命
成了一块痉挛的记忆
它的黑色
在残缺的天空下
成为所有人生命的记忆……
从残缺的天空升起
我不知道,这块煤能否到达天堂
——《残缺的天空》
三、在疼痛的最深处
《大地苍茫》的后半部分就是关于乡村的诗歌。江耶是这样阐述矿区与乡村的关系的。他说:“我生命的源头来自于乡村。我在体验中反思,我把作为农民的细微疼痛呈现出来。”而“煤矿诗只是呈现一种状态,它们是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仍要承受的一些疼痛的表达。”(《从最小的可能做起》)显然,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我理解,如果说煤矿诗主要呈现的是“煤”的疼痛,借此澄明一种矿工们的生存之痛的话,那么,乡村的诗歌则主要是呈现农民的一种生存之痛。而后者对于江耶既具有着一种先验的因素,是沉浸于血液中的记忆;又饱含后天的生存体验。生在中国的农村是不幸,而生在当今中国的农村则是不幸中的大不幸。因为,农村相对于城市,生存环境自是无可比拟的。而中国的农村由于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上没有城市现代文明的辐射与扶持,“缓慢、滞后、落伍”,与城市生活质量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更何况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窗口打开,网络等现代传媒更清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村人主体意识觉醒,自卑感格外放大,这就成了农村人心灵深处的巨大的伤痛。作为诗人对此就格外敏感。
你哭了,一种绝望的伤感
说着痛。我看不到你,但知道
从今天就要开始
一切都不可避免
锋利无形,划开原始的混沌
时间“哗哗“流淌出来
不多,就一年。我们在上面漂着
乾坤不会逆转了,我们只能顺流而下
——《人间十二月》
这是一种宿命之痛,更是一种祖祖辈辈潜意识里的痛的自然流露。有人把一个城市人的诞生称之为“太阳出世”。清醒的诗人浪漫不起来,他知道生为普通的农村人,生存苦难“不可避免”。这种苦难还会顺着时间之河流淌,对此,我们只能“顺流而下”。农村是江耶生命的源头,更是他痛苦的源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他”,应该是大写,是复数意义上的“他”,要以亿来计算。因为江耶是在讴歌大地,他是大地的他,大地是他的大地。
简单而圆满的秩序里面,一种习惯
不温不火的,没有一个高潮出现
一条短路上可以走到黑
多少人的一生
这样一圈一圈地消耗
现在的石磨已经老了
断齿,豁口,牙床渐渐平息
不能再好好研磨到口的东西
它的身子骨还好
它还在坚持,坚持身体里面的硬
多像一个乡村的父亲
全非的面目里
咬紧牙关,却咬不住命运
——《石磨》
这是一种生存之痛。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呈现,一个非常清晰的生命轨迹,周而复始。它的生命形态是重复,它的生命意义是消耗,它的生命理想是坚持,它的生命动力是“硬”,而它的生命归宿是只能走到黑的命运。如果没有对农村人生存现实的透彻理解,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真诚关注,如果没有生而为农村人的亲身体验,如果没有一个诗人的不死的良知与无可推卸的使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深刻锐利的书写的。
祖国啊,我的祖国
我要继续感激你,感谢你
给我良田一亩三分
我的营养充分,骨骼强壮,可以背叛我的乡村
在城市的出租屋里
我用泪水把自己清洗得发白
只有这一点颜色
我仍然用心热爱,用手写字
大声唱着一首没有意思乡音的歌
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我的祖国
我是一个人的内脏,一个农民的善良和温顺
我让一个人的生命更像生命
——《祖国啊,我的祖国》
这是一种人格之痛。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有权利要求被他的祖国重视,哪怕他只有良田一亩三分;哪怕他是在城市出租屋里谋生,哪怕他还残存着早已不合时宜的“善良和温顺”……他依然有权利有资格道出“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是人格的觉醒,这是尊严的呼唤,这是公平与正义的呐喊!可是,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诗人认为一个农村人这样迫切地需要祖国认同他的“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的诉请?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诉请,我们忽视得太多太久!所幸我们的政府已经有所警觉和作为,农村人的人格和尊严,不仅要在经济上得到重视,在精神文化上也应重视起来。
不死心,不打算把村里的田地转让
也不打算离开城市回去侍弄那一小片田地
他和他的村民都知道,在城市流浪的他
不能把种子种进水泥地里
一切都是一次暂时的过渡
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和他那一小片田地
在不适合庄稼生长的城市转久了
肯定会越来越荒芜,会在某一天
完全流失
——《流失在城市的一小片土地》
这是一种荒芜之痛。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圈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以致国家划出土地“红色警戒线”;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进城里。流进城市的农民和留守乡村的家人,承受着土地、家园和心灵的三重荒芜。或许我们可以解释为这是改革的趋势,是文明进步的代价。然而,诗人只关心生存的苦难和真实的存在。他对乡村情感的扭曲与震荡不能无动于衷;他对农民心灵的异化和撕裂,不能麻木不仁。更何况,谁能说乡村的荒芜就是现代化乃至一个大国兴起的必然代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理性思考之深邃,也看到他诗意书写的忧伤与喟叹!
那么多的人
前面,后面,左边,右边
白茫茫的一大片
走来走去的
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方向
有多少弯路被人走过
有多少歧路即将发生
有多少捷径已经被人
捷足先登
我是其中的一个偶然
我找不到来或者去的路
我在人群中不知所措
这是一种迷失之痛。改革潮流的席卷之势,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城乡格局的剧烈变动……这些不是单纯的GDP所能描述或者概括的,也不是人均货币持有量所能反映的,更不是城乡消费指数所能衡量的。它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存在的把握,是生命意义的拥有,是“我”在这个世上的领会与规划……现实是乡村很多时候是迷失的,它让人想起《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典型症状就是“不知所措”。这里有迷茫,有苦恼,有绝望,有烦心……
自然的,在这一篇短文中,我无法详尽描述江耶《大地苍茫》中的“疼痛”种种。我想提请读者思考的是乡村之痛与矿区之痛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上文所说的,乡村之痛是江耶矿区之痛的源头。因为文学中的苦难,首先折射的是作家或者诗人内心的苦难和危机。按佛家的话说一切障碍皆来自心魔。更何况,中国的矿区与乡村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照江耶的话说:“农村和煤矿是血缘关系,绝大多数的矿工来源于农民。”这就决定了对于矿区,或者说“煤”的疼的领悟,必得以对农民之痛的领悟为基础。是的,这里就有宿命的历史的不公正在里面。所以,江耶称之为“大地”之痛。
我看到神已经睡去
多少罪孽正在生长
大地偷偷翻过身来
很多地方裂开缝隙
长出一小块疼
——《大地翻了一次身》
这是一段关于新春土地的书写,可是,我们毋宁将之理解为一个时代的隐喻。因为它不仅道出了大地最深处的隐秘的疼痛,更重要的是它还道出了那疼痛最本真的根源。
注:江耶诗集《大地苍茫》于2011年获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同年获安徽省政府颁发的2007—2008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文学类三等奖(即安徽文学奖)。
刘斌:安徽淮南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学语文教师。有作品散见《世界文学》《诗歌月刊》《诗潮》《新疆回族文学》《西湖》《红豆》《阳光》《散文选刊》《中国散文家》《淮南文艺》《银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