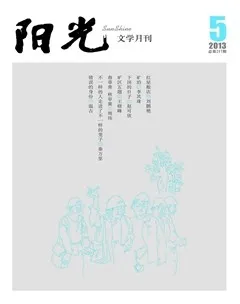精神不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正在复苏,但距离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时日。据报道,中国人的年平均阅读量尚不及美、德、日等国的八分之一。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国人缺少读书兴趣?我想,这固然与图书市场的现状有关,大量的重复性以及缺少知识和文化含量的书刊无法激起人们的读书兴趣;另一方面也和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有很大关系。社会上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即时兑现欲和当下享受欲。不少人可以在酒席宴上、麻将牌桌上一掷千金,却舍不得花几十元买几本书灯下夜读;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在滚滚红尘中,人们的心灵被物化的程度与日俱增,怎么能不令人心忧!
离休老干部成善一同志出了两部书:《活着,不要辜负生命》《活着,要有点精神》。读后使我上述的担忧有所释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爱书、读书、写文章出书,这本身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他活着,就不会辜负岁月和生命。
成老1925年生于山东黄县。今年,2013年,是他88岁米寿。他有着值得骄傲的经历,十几岁参加八路军打日本。解放战争,他所在的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也就是后来的27军。那是陈毅、粟裕麾下的一支铁军,从胶东一直打过长江,攻克上海。进城后,成老调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工作;之后,转业到煤炭系统一家大型企业当党委书记。他只读过五年私塾,没有学历,但爱读书,退下来之后,酷爱文学。
1982年9月,全国煤炭系统举办首届文学讲习班。老作家苗培时领衔,成老坐镇,我当教学秘书。苗老戏称,三个人是“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先后请来了箫军、田间、何洛、王一达、苏叔阳、邓友梅、林斤澜、李庄、秦川等文艺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为学员讲课,可谓集一时之盛。
成老年长我20岁,他是行伍出身,老革命;我是科班毕业,“三门”干部。因为年龄、经历上的不同,对社会上、文艺上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差别。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交往。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尊他为前辈,一位可以信任的老人。成老还有一个长处,他的观点、看法都十分鲜明,讲在当面,不掩饰、不首鼠两端。在观念上,他努力地与时俱进,不固执己见,自觉地向真理、真知看齐。不断校正自己的视角,紧跟时代的节拍。他和煤炭系统众多的中老年、青少年作者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成老的两部书最大的价值,是以一个老战士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的视角,努力地为读者勾划出现当代中国历史行进的一个侧面。从乡村到城市、从军旅到机关、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机器轰鸣的工厂,血与火的锻炼、成功与失败的考验,改革开放的洗礼,一个有血有肉的老战士在峥嵘岁月中艰难而又坚定地向前走。如今,他老了,88岁了,但身板挺拔,步履稳健,思维清晰。他努力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望过去,思绪万千。于是,写出来,印出来,这既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个老兵发起再次冲锋前的呼唤!
从这个意义上讲,成老和他的两部书不失为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成老的书,不是论述严谨的历史专著,也不是思维缜密的学术论文,而是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清晰回忆和随兴感悟。成老在他的书里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的就是“精神”二字。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为中华振兴,一路走来,滚滚风烟的背后蕴藏着的精神灵魂是一脉相承的。成老在《序言》中说:“精神就是意志,是抗争。”我想,用文学语言形象地表述,精神,就是征途上的高山绝壁,是激流险滩;是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是上甘岭上战友粮袋里最后一口炒面,是沙漠中勘探队员水壶里最后一滴水,是藏在风干的牛粪里最后几粒青稞,是“98”抗洪中一个个紧挨着的肩膀,是汶川地震时小学生砸碎的攒满硬币的钱罐,是万里海疆守卫岛礁的战士晶亮的目光……
如此这般的精神不仅跨越了两个世纪,而且,将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万代千秋!有了这种精神的承传与接力,中华民族焉有不复兴崛起之理!
我十分赞同“老有所为”的说法。有人统计,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平均年龄69岁,说明其中大多数人是花甲之后才有所斩获的。许多宝刀不老者,耄耋之年,还能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波兰大天文学家哥白尼71岁时发表《天体运行论》;德国诗人歌德81岁写作名著《浮士德》;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82岁写作《我不能沉默》;意大利建筑大师、艺术家米开朗基罗88岁设计出圣玛丽大教堂;英国戏剧家肖伯纳93岁完成剧本《牵强附会的寓言》;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100岁时相继完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许多事实证明,进入老年,是人生智力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能否实现“老有所为”,关键在于自己有个良好的心态。卓别林93岁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你的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他回答:“这还要问吗?当然是我的下一部作品。”
相信成老的下一部作品一定会更好!
周翰藻:文史学者,编审,曾任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淮北矿务局文联主席。发表散文,论文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