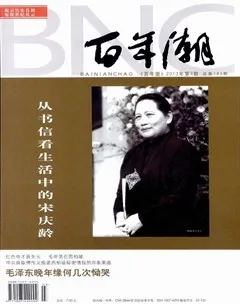一张1959年的结婚证
结婚证是婚姻的文字证明,是婚姻的法律文书。我与妻子张莉莉的结婚证,伴随我们走过了54年的岁月。寒来暑往,风雨沧桑,这张已经褪了色的结婚证留下了共和国时代的足迹,也印证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
状态。
我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县育民村,于1959年1月1日在吉林市结婚登记,领到了有国旗、麦穗、牡丹和喜字图案的结婚证,上面加盖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委员会”的赤红印章。
当时单位领导批准给了我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一张旧木板床,两床线绨被面的棉被,两屉桌上放着一个“金钱牌”暖瓶和四个水杯。我用积攒了许久的50元稿费,给新娘和自己分别买了一件丝绸棉袄和一套上海服装厂制作的卡其布中山服。还用“工业券”买了一个铸铁锅。从此,这个新家的吃、穿、住就算一应俱全了。
婚礼就在这间新房举行。凭结婚证买了6斤苹果、5斤糖,还准备了两包前门烟,泡了一壶茉莉花茶,披上红绸彩带的领袖像高高挂起,主婚人高呼“三鞠躬”。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婚礼。
结婚登记有了婚姻,生儿育女有了家。1961年生老大,1962年生老二。两个孩童都是降生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儿子宋宁宁的出生报告书粗糙、蜡黄和脆薄,但却很神圣和权威。凭它到副食品店能买到1斤红糖、2斤饼干、3斤猪肉、4两豆油。新生儿和他妈妈伴随着“一二三四”的人生起步咏叹调,省吃俭用度日。二儿子宋菲菲出生的1962年是最困难的年头。出生报告书虽然还那么“神圣和权威”,但供应的品种和份额极度锐减—猪肉1斤,豆油2两。我作为两个娃娃的爸爸甚感
愧疚。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结婚证辗转隐藏三处才得以保留。20世纪60年代,一张大字报把我定位为“三家村”,我是富农成分又兼“黑五类”,还与资本家女儿结婚,已进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行列。当时唯恐抄家时造反派搜到富农子弟与资本家女儿结婚的证据,我把结婚证藏在了床铺底下。后来听说红卫兵抄家的“首选地带”就是床铺,又急忙“换防”塞到厕所水箱后边。又怕水箱溅水弄湿了,经我、老伴和她妹妹三人“共谋”,把主席相框打开将结婚证夹到了里面。
1976年,作为秘书,我随被中央任命为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领导一同进京。临行时,叮嘱老伴带好我们珍贵的结婚证。
1999年春天,两个儿子为老爸老妈举办银婚茶叙会,话改革聊家事。60年代生儿,80年代抱孙,三代同堂,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个家庭步步登高,人丁兴旺,和谐美满。大儿子成为电影人,审剧本,搞制片,银幕上时有小名出现。二儿子创办个体菲菲书社,卖好书,搞捐款,扶贫救灾。5位部(市)长、3位将军亲临书社视察。登报刊,上银幕,播电视,声传海内外。孙子宋家大学毕业就职三联书店,孙女宋歌正在读研。
2009年1月1日,在人民委员会颁发的金婚证的监护下,我们的婚姻航船风雨同舟驶到了“50号码头”。全国总工会老干部局从北大照相馆请来摄影师,为我们拍摄金婚照。我特意到荣宝斋,将结婚证裱糊作框。装裱师傅说:“我头一次看到盖着人民委员会公章的结婚证。”
2013年1月1日,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聚会。老伴将珍藏完好的结婚证、两个儿子的出生报告书和我俩的金婚照展示出来,这可是见证我们幸福家庭的“三大件”。兴奋之余,我拙笔吟下婚姻三字经:
家之初,结良缘。互敬爱,牵红线。
心地宽,要信任。讲真情,更善待。
多涵养,有包容。福共享,累同在。
三思行,善冷静。要认真,有宽松。
讲责任,尽义务。行其事,各内外。
五十年,过来人。情爱论,多感慨。
老中青,取所长。承上下,代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