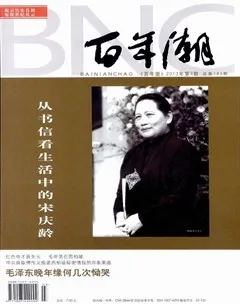同傅高义先生谈《邓小平时代》
今年年初我赴美国纽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同志的建议下,前往哈佛大学拜访了目前仍在热销中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2006年,李捷同志和我接待过他)。当我叩开傅高义先生家门,这位学术大家温文尔雅的形象,便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有“中国先生”之称的他,年近83岁,双眼炯炯有神、充满智慧,慈祥而又健谈。这次拜访的话题,主要围绕他这部新书展开。
一
首先,我祝贺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先后在美国、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出版发行获得非常圆满的成功。我说“非常圆满”,绝对不是恭维他的话,而是实事求是的话。
一是,出版发行地多,发行量大。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5月香港中文(繁、简)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6月,又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版权仍归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书名则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今年1月18日由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的北京、成都、深圳同时发行。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21周年的纪念日。三联书店第一次就印制了50万册,仅仅1周就卖完了。1月26日第二次开机印制了30万册。这部著作,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大陆2013年开年第一畅销书。
二是,政治倾向积极、正面,情感真挚。这部著作肯定了邓小平,肯定了邓小平所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给予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功臣”的历史定位。傅高义先生在书中写道:“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中国。”“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2012年5月15日,在香港中文版的售书仪式上,一位女士亲切地问傅高义先生:“十年来,您的生命是否与邓小平交织在一起?”他微笑道:“是,我的生命和他交织在
一起。”
三是,写作目的明确,用心良苦,充满理性。傅高义先生说,这本书“主要是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理由是我认为了解中国的本质很重要。以我钻研中国事务半个世纪之久,个人深感,中西人民若能很好相处,实是全体世人之福,这就需要双方对彼此更加了解”。“不过我明白,现在的全球传播是即时的,所以我也是为全世界而写,为中国大陆、日本,为台湾、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华人而写。”这样,这部著作在客观上就适应了当今中国、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对传奇式人物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历史地位与作用既有权威又能系统了解的期盼心理。
四是,著作出版不久,便接二连三获奖。在2011年、2012年及出版后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邓小平时代》接连获得分量都很重的八个奖项。它们是:2011年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经济学人》2011年最佳图书;《华尔街日报》2011年最佳图书;《华盛顿邮报》2011年最佳图书;《金融时报》2011年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书评》2011年编辑推荐书目;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2012改革动力奖·特别致敬”;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其中盖尔伯奖,是用来褒奖在探讨全球事务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学者,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非文学类著作奖,在西方学界享有崇高地位。有个小插曲,同时入围盖尔伯奖的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2012中国十大畅销书之一),但该书最终未能获奖。仅从这里就可看出这部著作的高质量和它的影响力。这部著作的获奖,对于大名鼎鼎的活跃在世界舞台几十年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基辛格来说,却是一个意外,是一件令他不免有些尴尬的事情。但是,听傅高义先生讲,基辛格先生不失世界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的风度,非常大度地向他表示了祝贺。
综上所述,我认为用“非常圆满的成功”七个字,来对傅高义先生表示祝贺是合适的。
二
傅高义先生在签名送我书后,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对我书中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讲。这使我颇感意外而有些尴尬,又有受宠若惊之感。
当然,在拜访傅高义先生之前我也做了认真准备,应该说对书稿内容和社会反映,我已经有了较多了解。这样,我同傅高义先生就《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一些重要观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看法,展开了讨论式的对话与交流,真可算得上开诚布公、坦率
直接。
傅高义先生认为,邓小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后再难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所不能触动的政治底线,一是中国不能乱,二是中国政治制度不能变。
傅高义先生谈到邓小平在国外的留学经历,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作用非常大。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与中共绝大多数人相比……这些旅法归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止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关键角色”,“他们对中国需要做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我接过他的话茬说:据周恩来总理的卫士成元功回忆,1954年4月至7月份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欧留过学——作者注)看到瑞士社会发展状况感到十分惊讶,尤其对当时就有双向四条车道的高速公路感慨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30年来西欧国家的面貌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重要思想,并且发出了中国要“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的确,傅高义先生的上述评论和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对傅高义先生提到邓小平没有严厉批判毛泽东,是为保护共产党的权威,我除了表示相当程度的赞同外,补充说道:最根本的原因是,邓小平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这是中共继续领导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他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同时,我对他不赞成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应该是“总经理”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我说:“我提出来,供傅老先生进一步考虑。”我陈述的理由是:应该以动态性的发展观点来理解“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复出之初并没有提出改革开放的一揽子方案,他只有在经过一系列深入调查研究、透彻了解中国国情、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渐进地提出一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不断地加以完善,这样才不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脱离中国实际,这样才有效地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成功,否则就会中途夭折,这正是邓小平的可贵之处、高明之处。他略微思索了一下,颇为平静地说道:“这大概是中西方学者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理解吧。”冷静地一想,我觉得他这样的解释还是有道理的。
原先大致确定为一个小时的拜访,应傅高义先生的提议,一直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三
拜访之后,引起我的良久思考: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发行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功呢?避开三联书店成功的营销策略与方式不说(这方面虽然重要,但绝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借用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说过的话,“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认为,这部著作的优良质量,是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首先,设定了写作的高标准,确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雄心勃勃的傅高义先生从开始写作初稿时,就设定了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我的野心很大”。“自2000年笔者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便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我认为是了解今日中国最重要的关键上”,即反映“有千百万的中国人亲身参与1978年开始参与的改革开放”,反映“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变局的”邓小平。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会说:你要了解那个时代,这本书对你会有帮助”。为了实现他所设定的高标准,傅高义先生在中国大陆版的序中吐露出了自己在写作中要始终一贯地坚持实事求是写作原则的肺腑之言:“我尽力摒除自己可能有的偏见,尽量客观地看待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种种状况。邓小平在被人问起他在中国的作用时说,不要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再写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时,既要写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写错误。”“不管我的书中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他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为此,傅高义先生在试图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的过程中,大量地阅读和研究了赞扬他、批评他的人所写的书籍,以便从中提出更加客观与中肯的分析。
第二,不急功近利,舍得投入时间全方位地收集材料,并在写作中融会贯通。为了写好这本书,傅高义先生大量地系统地收集了文献资料、回忆和访谈材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年谱》《邓小平自述》和《回忆邓小平》等众多书籍,包括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文革”岁月》,包括陈云、周恩来和叶剑英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年谱等,还包括中外学者写作的中文和英文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同时,傅高义先生大量地有重点地对政界、学术界、商界等各个不同界别的知情人士(尤其是高层人士)进行了采访。被采访人有中国的也有国外的,有政治家与外交家也有学者与家属,有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甚至还有在国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光是采访中外著名政界人士就有数十位之多,例如江泽民、钱其琛、任仲夷、卡特、基辛格、蒙代尔、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布热津斯基、吴作栋、彭定康、霍克,等等。从这部著作为数众多的注释中,可以看出傅高义先生收集、利用过的材料,当有几百种之多。傅高义先生在前言中写道:“过去几年中,我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的时间在中国,用中文采访那些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人。”不仅如此,为了写好这部著作,傅高义先生甚至还看过记录邓小平演讲、会见外宾、出访等的文献纪录片。傅高义先生把从上述几个方面收集的大量资料进行有机结合、交叉展开、相互贯通,有效地保证了书稿写作的优良质量。
第三,得益于长期对中国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中国成果的积累。傅高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做“关于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研究”,由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封闭情况,收集资料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在香港可以收集和了解到广东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况,这样广东就成为他的中国研究学术生涯的突破口,196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成为姊妹城市。州长邀请“知粤人士”傅高义先生做代表团的随行翻译。当时的广东省领导人了解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广东的书,内容比较客观,于是主动邀请他再写一本当时广东情况的书。这位省委领导人认为,广东希望外国人到这里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由中国人写介绍广东的书,国外也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有他这样一位知名大学的教授来写,可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样,傅高义先生受邀去广东做研究。傅高义先生提出的条件是费用自理,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他还提出,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在广东省委领导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后,1987年傅高义先生在妻子艾秀慈的协助下,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广东之行,系统地收集资料,开展全面采访。他得到了以张高丽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为他提供的很多帮助,向他提供了广东30多个县经济发展情况的简报。他一口气跑了70多个县,获得了大批生动鲜活的采访材料和贴近实际的书面材料。1989年,傅高义先生第二本关于广东的专著《先行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出版。应该说,这两本著作对于傅高义先生写作《邓小平时代》有着潜在的必然联系。
傅高义先生前后总共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写作《邓小平时代》这部著作, 真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铸成一剑就见真功夫,其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在《邓小平时代》这部著作中都得到体现。当然,也在他之前写作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亚洲四小龙:东亚的工业化》等系列著作中都有很好体现。尽管对他书中的某些取材方式,特别是因为分析问题所持立场而带来的一些观点还不能苟同,大有商榷之处,尽管有的史实还有差错或不尽准确之处,但毕竟傅高义先生作为西方学者来观察、写作,并从基本方面积极评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当属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了。《邓小平时代》出版的成功,对于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讲,都有必要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加以认真思考,以便获得某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启示和经验,写出更多的经得起历史检验、读者普遍欢迎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