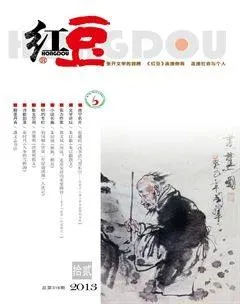老木(短篇小说)
老木在竹林村,名声不是很好,出了名的游手好闲,背地里,有人叫他懒汉,有人叫他闲人。老木知道竹林村人对他的看法,但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游手好闲。
一天晚上,有个关心老木的人,趁着朦胧月色,敲响两扇破败的木门,老木把此人放进屋。两个人吃着烟,坐在一盏昏暗的灯泡下。此人对老木说村上要修公路了,需要小工,三十块钱一天,如果想去,可以跟包工头说一声。包工头是此人的小舅子。老木并不领情,说他对修公路没有兴趣。此人说你对修公路没有兴趣,对钱该有兴趣啊?三十块一天啊。你在地里刨上一月两月,还刨不到三十块钱呢!卖大米,二三十斤,才换得上三十块钱呢!老木埋头听,头也不抬,说他对修公路没有兴趣,对挣钱,也没有多大兴趣,有口稀饭,就满足了。此人又费了不少口舌,见说不动,踩着朦胧月色回去了。
公路是从宜宾南岸修到赵场。
南岸至赵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公路,大家走的是田埂泥路石板路,如果不是南门大桥一夜间突然垮塌,修公路的事情,恐怕还遥远。南门大桥的不幸,给赵场人带来了福气。南岸以前是菜蔬区,现在是繁华的城市,住进南岸的人,天天过南门大桥去老城上班办事买卖,汽车也过南门大桥在老城与新区间来来往往。南门大桥垮塌,一条奔涌的金沙江,将两岸隔断,为了急于解决通行,从南岸修一条公路至赵场,迂回曲折,汽车行人可以从二二四过金沙江下宜宾上柏溪。路程虽绕点,总算能过江进城。垮塌的桥,不是短时间内修得好的。从南岸修一条二十多里的公路,比修一座大桥容易。这条公路连接赵场镇,过鱼池坝过轿子寺过金沙江大桥在二二四与宜柏公路汇合。镇上有条到宜宾柏溪的公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修的,有班车天天从赵场上柏溪下宜宾,又从柏溪宜宾回赵场。
公路开工,竹林村的男人女人跑去修路挣钱,老木照旧过着他游手好闲的生活。这个曾经结过婚的父母双亡的男人,婆娘跟着一个来赵场做生意的人跑进城后,再也没有娶妻生子,一大把年纪,年年守着他的一块田一块地过清寒日子。田地少,活不多,四季有三季闲着,老木这种人,早该进城打工,早该成为富裕人,不少人约他进工地,老木就是不心动,大言不惭说他喜欢在土里刨食,喜欢游手好闲耍。
老木的游手好闲,并不是无所事事,但在竹林村人眼里,他干的那些都是不务正业。有事没事拿把苦竹鱼竿蹲在池塘边钓鱼,有事没事从这座山坡转到那座山坡,有事没事跑别的村找些树木果树回来乱栽,有事没事还喜欢捧本破旧的砖头厚的书瞎读。这种不务正业的懒汉,竹林村,只有老木一个,大家都有点看不惯。看不惯归看不惯,老木也不要大家看得惯,多年来,都是按自己的性子在竹林村过他自己的日子。
公路修拢下槽,老木有点坐不住了,蹲在池塘边钓鱼。开山劈石的爆炸声弄得他心神不定;坡上转悠,远处传来的轰隆声也弄得他心神不定。晚上睡觉,梦里都是开山劈石的爆炸声,老木睡不踏实,大清早起来,碰着露水去下槽看个究竟。这一看,老木更睡不踏实了。公路沿着一条古老的石板路修造,沿途的田地连石板路一起变成了公路,老木的一块地,恰好在太阳坡的大路旁,也将变成公路。老木在那块地里,种了多年的庄稼蔬菜,那些油菜麦子包谷红苕花生豌豆胡豆和老木亲如一家,如他喂养的儿孙一样,当然,也是他侍弄的这些儿孙喂养了他。前几年,老木还在地坎边栽了两棵腊梅,一棵玉兰,一棵梨树。梨树村上有,腊梅和玉兰,不知老木是从哪里弄来的。太阳坡对面有坡梨树,村上栽的。起先村上想着用它改善经济,每年结的梨子倒是多,交通不方便,不好卖,不如工地上挣钱多,贱卖的几个钱,还不够跑脚费。这几年,无人管理,自生自灭,年年春天,满坡的梨花雪一样明亮,成为竹林村的美景。这美景,无人欣赏,只有老木这种游手好闲的人,喜欢去梨林转悠,喜欢下午坐在一棵梨花下听清风声鸟叫声,喜欢看蜜蜂蝴蝶起舞,看春天的太阳在雪白的梨花上空,慢慢西斜,直到落山。晚霞露面,夜幕降临,老木才从梨花下起身,穿过缤纷的花树,慢悠悠回家。有人在远处,看见老木独自走进梨林,看见他独自在花树下一坐就是半天,这时,正好有人走拢这个人的眼皮下,这个人朝花喷喷的梨林上努努嘴,说:“你看,又发神经了,又去树林子了,又坐在树下发呆了,年年都这样,莫球得事干!”来人听后,嘿嘿笑两声,说:“你又不是不晓得,神经不正常,是个怪人!”来人继续走,上坡去她的菜地砍菜。这个人不要她走,说:“你看他那个日眉耸眼的样子,婆娘跑了,屁都不放一个!这些年,也不说再讨一个!男人们都晓得出去挣钱,他杂种一个人吃了全家饱,无牵无挂的,也不说出去挣点钱!你看他那破房子,连人家的茅私棚棚都不如,简直是在让我们竹林村丢脸!屋里头,连一个黑白电视都没有,天天拿个破收音机听过来听过去,还自以为是!你说,他龟儿子杂种一天到黑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闷不闷?要是我,嘴巴都要闭臭!”来人又嘿嘿笑了两声,说,“你狗日的操的哪门子心啊?人家不讨婆娘不出去挣钱不盖新房不买电视关你狗日屁事!你操的哪门子心啊?你男人过完年就出去了,是不是想啊?正好,晚上找他说话去啊,他嘴巴就闭不臭了!就有人跟他嘘寒问暖了!”来人说完,嘻嘻哈哈笑着,跑上坡了,屁股后面传来一串话:“狗日的死婆娘!你男人过完年还不是跑了?你有本事,晚上你去找那个杂种找那个怪物啊!他正缺你这种不要脸的死婆娘呢!看你肥得跟猪一样,人家恐怕还不要你呢!不得好死!”这个人骂完,也嘻嘻哈哈笑起来。
老木坐在梨花下,看天看云看蜜蜂看蝴蝶,并不晓得两个女人在嚼舌根,拿他开心。
一天早晨,老木来不及吃饭,去了村长家,说修公路的事情。
两个人坐在敞坝里,门口就是一块半月形的水田,四周草色苍翠。老木递了杆烟给村长,为村长点燃火,自己也点上一杆吃。老木一向嘴笨,不善言辞,不善与人交往,烟吃掉小半截,吞吞吐吐地还冒不出一句话。
村长急了,问老木:“老木,一大早跑来,究竟有啥子事?说嘛。我忙得很,事情多球得很,大清早,你总不可能来找我吃顿烟吧?总不可能我们一个早上就坐在这里吃烟吧?我忙球得很,找我啥子事,说嘛。
老木使劲吃了两口烟,慢吞吞说道:“也没球得啥子事,就是公路的事。”
村长说:“修公路是件好事,盼了多年,要不是南门大桥垮塌,轮得上我们?”
老木说:“是件好事,就是,不应该那样修?”
村长张大了眼睛,看了一会儿老木,干笑了几声:“老木,你又不是修公路的,又不是工程师,不该这样修该哪样修?你说该哪样修?”
老木又点上一杆烟,吃了两口:“不该把石板路造了,应该绕开石板路修。”
村长又干笑了两声:“笑话,绕开石板路修?从哪里修?现成的路线摆在那里不走,绕开修?想得好,你去修嘛?”
老木接过话:“要是喊我去修,我就要绕开石板路修,不会把一条好端端的路毁掉!把祖宗留下的路毁掉!”
村长脸色阴沉,说:“你回去把你那烂房子好好修下吧!这种事轮得上你来管?连我也轮不上……”
这句话似乎刺伤了老木,他半天没开腔。
村长接着说:“没有别的事,我忙去了,像你,成天没有事干!”
老木慢吞吞说:“这修公路的事情,跟修房子,是两回事,你不能把它们扯在一起。再说,修公路是件大事,你是村长,我可以向你反映反映。”
村长说:“我一个村长,哪里管得了这么大的事情。当初上面说修公路,大家都拍手欢迎,也没听说你反对……”
老木抢过村长的话:“我现在也同意,我没说修公路不好,现在才想到,不应该毁掉石板路,这石板路,我们祖祖辈辈都走过,你不是不晓得,不应该毁掉。”
村长说:“当初说修路的时候,你咋个不跟上面提出来?现在找我说,我一个村长,管得了这种事?再说,公路都修到下槽了,7608a07928e8ebdd2910ce0be0412c4428ed8a954c4ebe0066d3e1dc4cc54f63马上就要修到我们村了,莫非重修?异想天开!这事我管不着,我忙球得很,不陪你了!”
老木从村长家出来,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乡上。
他要找乡长,乡长进城开会了秘书接待了他,老木把修公路的事向秘书说了一遍。
秘书把他反映的事认认真真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说是等乡长回来转告。
回家时,走在石板路上,老木想,当初上面说修公路,糊里糊涂的,也没问问怎么修法。早晓得这样修,就不慌答应,公路修到下槽,离赵场还有一半的路,如果有人管,改变路线,还可以保住一截石板路。
接下来几天,竹林村留守的女人看见老木天天往镇上跑,晓得他又去找乡长,又去闹事了。
老木并没有见到乡长,乡长很忙,不是开会就是下乡了,秘书说修路的事乡上无权管,他的意见已经向上面反映了。老木每次去乡上等回音问结果,兴冲冲去,蔫不唧地回来。老木不再往乡上跑了,公路离竹林村越来越近了。
竹林村留守的女人,看见老木又天天往城里跑,早上去下午回,阴沉着一张脸,见了人脸上也不露笑容,有人招呼:“老木,又下城去啊?又去找政府啊?”老木“哦”一声,看看问话的人,继续走路,听见背后传来几句:“老木,你硬是闲得发慌,没事找事做,修公路哪点不好?盼了这么多年,以后汽车来汽车去的,下城买卖个东西也方便,石板路又不是你家的,又不是你修的,你管它在不在?瞎起劲!”
老木正走在还未变成公路的石板路上,听了这话,并不回头,坐在地坎上的一窝李子树下,伤伤心心哭了一阵,继续走路。
下午,老木从城里回来,一个人在石板路上发呆,望着正在忙碌的一截截延伸的公路发呆。没有人来管他反映的事情,一条石板路该不该留下来,与大家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有老木这种人天天操这份他管不着不应该管的闲事。老木进城反映,与去乡上一样,回来时抱着希望,接待他的人态度温和,把他反映的都作了记录。他以为会引起重视,再去,人家就开始给他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态度温和,道理服人,要他顾全大局,顾全大家的想法和利益,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节奏。人家还温和地批评他思想落后,抱残守缺,缺乏时代意识。人家温和地说:“老乡啊,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总是石板路石板路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已经不是石板路的时代了嘛!我们要向前看嘛!那条石板路留着,有了公路,哪个还去走石板路嘛!留着也是荒废嘛!”
公路快修拢竹林村时,老木天天去到大路上,站在太阳坡嘴,看见庞大的机械同渺小的人一起在工地上忙碌。机械连同石板路两边的田地一起碾成了一条宽大的泥巴路,湿润的黄土簇新,打眼。开路的是一台推土机,所到之处,风卷残云,树木庄稼蔬菜片刻间被卷进泥土。坚硬光滑的青石板也被卷进泥土。老木站在太阳坡嘴,看着机械怎样把土地上的植物卷走,怎样把一条古老的石板路卷走。机械一路蚕食着开进竹林村时,首先要卷走的是一片簧竹林。簧竹林是刘家的,老木小时候,喜欢去竹林耍,喜欢和几个牛草娃儿,躲进竹林打扑克。不打扑克,几个牛草娃儿躲在竹荫下睡觉,睡醒,再去割草。老木看见推土机开进竹林,飞叉叉从太阳坡嘴跑下山塆,跑进簧竹林,站在几竿竹间,一动不动,死死盯着推土机。司机愤怒地吼叫:“找死啊找死啊!没看见挖过来了啊!闪开闪开!快点闪开!”老木没有闪开,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对司机说:“留下这竹林,好不?留下这竹林。这竹林,比我的年纪还大!”司机吼道:“怪事!我是奉命工作,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没用!当初干啥子去了?”看热闹的在旁边说:“竹林不是他的,是刘家的。”司机一听,又吼道:“怪事!又不是你的竹林,主人家都不开腔,你跑出来放屁!闪开!!”司机说着,开动了机器,朝着老木和竹林开来,老木闪到一边,看着几竿倒下的翠竹发了一会儿呆,又跑进竹林,抱着一竿青竹,失声痛哭。没有人劝老木,由着他哭去,看热闹的人说:“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他家的竹林,哭个哪门子!人家爹妈死了都不哭,他去哭!哭个锤子!”推土机风卷残云般开到老木跟前,老木还在抱着竹子痛哭。司机吼了声:“闪开闪开!”老木不得不闪开,眼巴巴看着推土机顷刻间把一片青幽幽的竹林吃掉。
推土机吃掉竹林,接着吃水田,塆里的几块冲田,推土机走过,变成了黄泥路,先前的石板路,已经不留一丝痕迹。推土机与挖掘机联合着,从塆里朝着坡上开来,老木站在太阳坡嘴,看着机器饿狗似的,所到之处,庄稼蔬菜石板路消失得无影无踪。机器开拢坡嘴,老木又站在了推土机前面,这次他是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地坎边的几棵树木,老木早已移栽进他的房前屋后,地里种的是莴笋,嫩油油的,还吃不得。青苗费,大家都领到了手,老木也拿了,虽不多,总比没有强。司机看到又是神经兮兮的老木,大声武气喊道:“你又要做哪门子事?又要做哪门子事?!”老木站在嫩油油的莴笋地头,轻言细语说:“师傅唉,你走别的地方吧。你看,我这块莴笋,刚栽下个把月,再过个把月,眼看就卖得了,你走别的地方吧?”司机说:“你开啥子玩笑!好笑!开啥子玩笑!你以为修路是整起耍的?想咋个走就咋个走?勘测公路时,找你们谈过,地里的损失,赔了钱的,现在来闹!要不是南门大桥垮了,南岸的人没法进城,恐怕你们想修公路还修不成呢!人家看着公路修拢你们家门口,都羡慕呢,你还好意思有完没完地闹!”老木觉得司机说的在理,自己是有点无理取闹,修公路,的确是件好事情,村上的人高兴,老木也高兴,看见机器毫不留情地卷走一切,老木就是受不了,控制不住情绪要无理取闹一番。
老木站在地上,沉闷着,找不到话说,拿眼睛扫着司机和机器,又扫着地头的莴笋。
老木扫视了一阵,突然蹲在地上,放声痛哭。
司机看着老木哭了一阵,平静地问:“哭够没有?哭够了,麻烦你让开,我该干事情了!”
老木让开,一边看着机器吃掉他的莴笋,一边哭着喊叫:“我的莴笋啊!我的——莴笋——啊!”
看热闹的人,觉得好笑,其中一个对老木说:“莴笋又不是你老子,哭个球!”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公路修好,老木也享受到了公路的快捷。下个城,不再走二二四转,南岸到赵场的客车,来来往往,半个小时一班。老木也常坐车下城卖些蔬菜瓜果的,高兴了,也坐车进城看场电影,进小馆子喝几杯烧酒。
竹林村的男人,长年外出打工,年轻女子,都喜欢往城里跑。那些在异地挣了钱的人,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家的房子,一座一座瓦房,慢慢地,都修成了水泥楼房,安了卷帘门铝合金玻璃窗,墙外镶了廉价瓷砖,地上也贴了廉价瓷砖。老木看着,心动,跟着村上几个男人坐火车汽车跑贵州去修路,正月间出去,腊月间回来。过完年,老木留下,说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出门,钱是挣到了,但日子过得不安逸。老木又过起了游手好闲的生活。老木的游手好闲,是在干完农活之后,再怎么贪耍,也要把自家的生活弄起走。老木现在种了两块田两块地,修公路,他家唯一的一块地被占用,老木剩下一块田,现在种的两块地一块田,都是人家的。村上的田地,大块大块放荒,四季长满野草,老木要种十块八块都有。老木不贪心,只把挨房屋近的田地开了荒种上粮食蔬菜。像老木这样的庄稼人,每年种这点田地,是件轻松活。村上留守的妇女老人,常常看见老木不是蹲在池塘边钓鱼,就是一个人在坡上转悠,还看见他上七星岩,早出晚归。有人问他上岩做啥子,他说是转起耍。真是闲得无聊,七星岩上除了松林还是松林,有啥子好耍的!老木啊,你没得事情到处转个球,多种几块田地,多卖点粮食青菜,也把你那烂房子翻修一下不好嘛!老木听着,不言语,干笑两声,继续转悠。
老木的房子,在竹林村,实在是破败。像他这样的土墙瓦房,竹林村乃至整个赵场,都难找了,村上的人都为他羞愧、难过。老木没有一丝羞愧,也不难过,天天自在悠闲地过他的日子。碰见村上的有钱人,也不自卑,走进人家的楼房,也不觉得矮一截。村上人的心思不同于老木,从老木破败的房子前经过,看都不想看,又禁不住要看几眼。老木低矮丑陋的土墙瓦房,掩映在树木翠竹间。老木有心思有精力在房前屋后栽各种各样的树木,却没有心思没有精力出门挣钱将丑陋的房子重新修一遍。土墙上的几棵野草,也不拔掉,春夏秋冬,枯了又长,长了又枯。野草旁边的窗棂,烂兮兮的,也不换换。两扇木门,也是烂朽朽的,野草长到门槛下,也不铲掉。小偷看见这样的房子,都觉得寒碜,从门前走过都不会进去。老木在家,有人看见他坐在树荫下读一本厚厚的书,和他的房子一样陈旧。有时,又看见老木编竹器,筲箕撮箕簸箕筛子背篼箩筐,样样都编。赶场天,竹林村的人,看见老木坐在街檐下,卖他的竹器。竹林村,不缺编竹器的竹子,竹子都是有名有姓的,老木要用,人家也不会说啥。竹子年年发新笋长新竹,也需要有人砍伐几竿。
老木的房子不光亮,两块水田却整得光亮。
竹林村的水田,不再是古老的耕种。春天,留守的妇人走进水田,用双脚将头年残留的谷桩踩进泥巴就栽秧子,等秋天收割完谷子,谷桩留在水田,发出新的秧苗,到春天栽秧时把这些长出新苗的谷桩踩进水田又可以栽上秧子,年年如此,省工又省力。老木不是这样种田,老木种田还是沿袭着老方法,不省工也不省力。收割完谷子,老木要租条水牛,把田犁一遍,田里的谷桩,被犁铧翻进土。晾晒一段时间,老木又要租条水牛把田耙一遍,耙得平平展展。水田里蓄满雨水,风一吹,水波荡漾,眼睛落进水田,就能看见四周的景色。这是秋犁秋耙。寒冬腊月,还要冬犁冬耙。春寒料峭,要春犁春耙。仲春,才将秧子栽进平展展光亮亮的水田。现在的竹林村,多年看不见这样的光景了,看见的都是残留着谷桩,谷桩上发出青苗的水田。老木两块亮堂堂的水田,在竹林村,显得特别。老木年轻时,竹林村的冲田梯田,谷子收完,都被犁耙得平展展亮堂堂的,块块田蓄满清澈的雨水。老木记得那时大冷天,他喜欢屁股上吊个笆篓,拿上划鱼竿竹囥囥,下田打几条鲫鱼下酒。现在不管哪个塆哪个冲,田里要么是野草,要么是谷桩,想打鱼,也难找到清粼粼的水田了。
老木的日子,就这样过着。
过着过着,老木在竹林村的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竹林村,在老木的眼里,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像他熟悉的家乡。改变竹林村的,首先是公路,它的出现,使竹林村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公路经过的地方,原先那些完整的丘陵,缺胳膊少腿的。当然,公路也给竹林村人带来了方便,下城买卖个东西比没有公路快多了。省力又省时。后来是一座厂房出现在竹林村,在一坡松林一片竹林上盖起了灰扑扑的石棉瓦。机器开拢松林竹林那天,老木又神经兮兮地去拦机器,拦不住,又抱着松林翠竹痛哭。这种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好大房产”在梨树坡上建商品房时,满坡的梨树,正开着雪花,远远近近白蒙蒙的。机器开进梨树坡,满坡的梨花被机器吃掉,老木在最后一棵梨花下,抱着梨树伤伤心心哭了一阵,仿佛机器吃掉的不是梨树,而是老木的命。这种事情发生多了,村上的人也习惯了,一旦老木发神经,疯子一样在机器前抱着这样那样的树木哭喊,大家看都懒得去看了。
现在的竹林村,已经不是从前的竹林村了。现在的竹林村,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所谓的竹林村,已经看不见一竿竹子。坡上坡下,塆里塆外,都是楼房工厂。
老木还像从前一样四处转悠。
转去转来,所经过的地方,不是工厂就是楼房,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坡啊沟啊塆啊坳啊田啊地啊都不存在了。
竹林村仿佛是老木记忆深处的乡村!
某天早上,一个熟人看见老木挤在竹林村的工厂楼房间,向着七星岩那边走去。
此人问老木:“你龟儿子又要去哪里耍?”
老木说:“找故乡。”
此人望着老木越走越远的背影,忽然回过神来:“找故乡?找故乡?找故乡?!呸!狗日的又发神经了!又疯了!竹林村就是他龟儿子的故乡,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龟儿子还要去哪里找故乡?莫非他还有第二个故乡?神经病!”
有人说,不久,老木狼狈地从远方回来了。
也有人说,老木再也没有出现在竹林村。
这是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