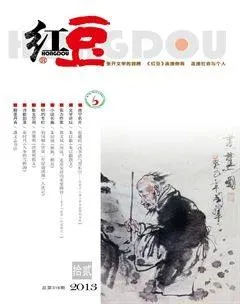小镇图书馆(外一篇)
我对城市唯一的羡慕是那里有很大的图书馆。我用“很大”这个稚气的词来形容,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过,也不知道怎样去想象。我只在电影的场景中见过城市的图书馆。
如果生活在城市,那么图书馆将是我常去的地方,或整天就泡在图书馆里,就像一条把鱼缸当作整个海洋的快乐的鱼,我会满足于图书馆里的风景和氧气。
在我的甘棠小镇也是有图书馆的。很多年前,只要一回小镇,所去的地方必定是图书馆。我记得图书馆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中通广场对面,那里以前是工人文化宫,有三层。底层是大厅,沿着可以三人并行的楼梯上去,转角处就是图书馆。顶层的空间最开阔,是活动室。白天活动室用作会场,晚上用作舞厅——小城里的青年男女天黑后会一拨拨地拥来跳舞。那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跳的舞比较呆板——慢三、慢四、两步摇,快舞也有——伦巴、恰恰、快三。小城的舞厅里跳的就是这些了,再快一些的就是迪士高,中场放两曲,结束时放一曲,恰到好处地制造出舞会高潮,让年青人过剩的荷尔蒙在加速度的节奏中得以消耗。
图书馆在晚上是不开放的,上午也不开放,只在每天的下午开放三个小时。开放的时间这么短,大概是因为来这里读书的人并不多吧。事实上这个图书馆是不提供阅读场所的——空间太小,比现在阔绰人家的书房还小,靠墙四排书柜,中间几排书柜,书柜与书柜只间只容一人通行,若有两人在过道上相遇,就得收腹、侧着身子,才能走过。图书馆的门口拦着一张桌子,管理员在桌子后面坐着,来人得先在桌前站定,把借书证交给管理员,再侧身绕过桌子走进。借书证是一个可以握在手掌的小本,红皮的封面,里面贴着持证人的照片,写着姓名、工作单位,压着图书馆模糊不清的印章。
管理员有两名,都是中年女性,举止言谈有明显的家庭主妇的味道。在不登记借书证时,管理员就在手里端着毛线衣,右手的小指和食指上勾着毛线,熟练地绕着,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家长里短的事。
管理员在接到从门口递过来的借书证时,会翻开来,看一眼借书人的脸,再看一眼借书证上的照片——我怀疑她们只是佯装着看——我曾把借书证给同事用过,照样借到了书。借书人进去选书时,借书证就在管理员的桌上摆着,待借书人选好了书,走到她们面前,递过书去,管理员就将书名和编号登记到借书证上。偶有一些时候借书人较多,管理员就得费时间翻找了——借书证胡乱堆在桌子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很难辨认。去过几次图书馆后,管理员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这让我有亲切的感觉——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能记住每位借书人的名字。
两名管理员里有一个长得很不错,即使是中年,仍然颇有风韵,天然鬈的短发打理得整齐有型,皮肤白而细腻,下巴微微地双着,使她看起来有一种被好日子滋养着的丰润感。长得不错的这位管理员说话也好听,声音有柔软的质地,不急不慢,好脾气的样子。我喜欢在她手上办理图书的登记,当她低头写字时,我便从她覆着刘海的额头看下去,想着,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吧。
小镇的图书馆其实更应该算是图书室。虽说有两扇对开的窗,空气还是显得有些陈旧,仿佛很久m39vb3hfBEQzpfWh8VO0qBrQYY5YkNsrZ/GEWJvwDWQ=以前似的。那些书是不是也在呼吸着空气里的氧呢?并把自身的气息吐纳出来—— 一种吸了潮的时光的味道——仔细辨认,还能闻到老房子和旧布匹的味道。午后的光从西边的窗口斜探过身子,缓缓移动脚步,把窗格子的影子拉得细长,投在桌子上、桌后正在编织的女人怀里,和一排贴着“外国文学”标签的书柜上。我就站在书柜跟前,在苔丝姑娘和查泰莱夫人之间,泛黄的斜照像一双会意的手,替我翻开书页,一只石青色的长着触须的书虫从里面爬出来,原地转了几个圈,仿佛不能适应突然降临的光,又返身迅速地逃向暗处。
书虫多像一些隐居在书里的灵魂,世界之大、之精彩,对它们来说皆是不相干的,形同虚设,唯有书是它们的安心之所——寂静无声的栖息地。
小镇图书馆里的隐居者除了书虫是不是还有天使?在一部外国影片里曾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图书馆里走来走去、站着或坐着的不只是阅读者,还有面目纯净的天使们。那些天使是城市的守护者,他们看得见人类,听得见人类一切思想和内心的声音,但人类看不见他们的存在,哪怕他们就在对面。
那部电影里的天使为什么会聚在图书馆里呢?当然他们也出现在别的地方,比如医院和街道,但他们最喜欢的去处还是图书馆,大概是因为图书馆有着城市难得的安静吧,又或者图书馆里的氛围更接近他们的故乡——天堂。
那部电影里的图书馆真是大啊,简直就是一座图书城,又那样明亮,仿佛世界所有的光都在那里——仿佛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在那样大的图书馆里人会不会有特别渺小的感觉?看着那些书会不会觉得又富足又无助?——和看不见尽头的书比起来,人的生命是太短促了,不够用,转眼就翻到时光的尾页。
我在小镇的图书馆出入了三年,三年后那个图书馆再也吸引不了我了,就像一个被我知悉了所有秘密并吮尽了氧气的洞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再次前往。
最后一次去图书馆借的书是日本作家有岛武朗的《叶子》。这本书已被我反复借读过,并在笔记本上摘录过许多段落。我感触于这本书的作者对女性的心理了如指掌、如发丝——又细致又精准,有些描写简直令我有身体上的切肤之感——太可怕了,一个男性作家竟能把女人丰富又隐秘的情感写得如此透彻,仿佛他的灵魂潜于笔下的女主人叶子身上,和叶子一起经受着挣扎、痛苦、欢乐与折磨,那些细微得连叶子自身都可能忽略的内心动静,却被作者的眼睛敏感地抓住了,放大,用又温柔又冷酷的笔尖,抽丝剥茧地表现了出来。
我实在太喜欢这本书了,如果以后写小说,这本《叶子》就是一个典范。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写作,准确地说那时我虽也写一些东西,但还没有在刊物上正式发表过作品。我不能确定自己以后是否会走上写作之路,我只知道这是一条我最想走的人生道路。
就像对一个心悦之人的难以忘怀,我挂念着图书馆里那本已破了封面、毛了边的《叶子》,小镇的书店是买不到这本书的,城市的书店对我来说更是遥远,要得到这本书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它再借一次——永久地借一次。
借了《叶子》之后我便不再去那个有着陈旧空气的图书馆,之后没多久它就消失了,包括三楼的活动室——舞厅,也消失了。工人文化宫的整栋楼改建成了超市,过了一年三楼又成了歌舞厅,晚上从那里经过能听到楼上的舞曲声——劲爆得能掀翻半个小镇。
图书馆里的那些书去了哪里呢?当废品卖了吗?有时我会这样想一下,心里有一些不明确的怀念,就像很早认识的人,后来听说不在了,便在心里模糊地追怀一番。
小镇现在还是有图书馆的,新修建的大楼,在中学附近。四年前我去过一次——文化局要求本地作者为图书馆的落成捐赠作品,我便带着自己的散文集——也是我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去了。相对于这个人口并不密集的小镇来说,新修建的图书馆确实够气派的,有三层楼——或者四层。我去的时候楼梯上上下下的人很多,面孔都熟着——小镇实在太小,在这样的小镇生活了几年后就不会再有陌生人——即便叫不出名字。我没有停下来观看图书馆内部的样子,把书交给馆长就匆匆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在新筑的图书馆里久留,后来动过要去看书的念头,随即又打消了。
我十岁的侄儿倒是这个图书馆的常客,整个暑假都泡在里面——这是真正的可以阅读的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读书的人大多是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有来读报的老人,总之人不少——这是侄儿告诉我的。大概正是因为“人不少”的原因使我不再想去吧。
有一次侄儿说他在图书馆看到我的书了,就摆在门口显眼的地方,在“本土作家”的柜子里。我问他有人读吗?他说有。我问他你读了没有,他挠了一下脑袋,说没有。
关于马尔克斯的阅读及其他
“没有爱,性只是安慰”,这是老年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借他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的话。这句话还有另一种翻译:“如果你得不到爱,那么性留给你的只有安慰。”
但凡和文学沾点边的人没有不知道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如同和美术沾边的人没有不知道凡高和《向日葵》,只是知道的深浅不同而已。我认识的一位写者甚至能背诵《百年孤独》开篇的部分,一口气背上好几百字,如同相声演员背诵扁担长板凳宽的绕口令般熟烂。同他不多的几次见面中我听他背过三次,三次都在酒桌上。几杯过后,面红耳酣之时,他就对酒桌上的人们说写小说的人一定要读马尔克斯,一定要把阅读《百年孤独》当做写作小说的必修课,随后就大声地背起来。
我是在很早的时候——还不知道马尔克斯那么有名,就读到《百年孤独》的。那时我二十多岁,没有开始写作——其实也是秘密写着的,也秘密地、忐忑不安地投过稿——当然是石沉大海。我是被《百年孤独》这个书名吸引翻开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太有魔力了(不知道是不是和封面加注的“魔幻现实主义”有关),像一个引诱着人往里面探寻的洞穴。我走了进去,摸着黑不知深浅地走进去,但是很快我就退出来了——我发觉自己根本就无法进入这个洞穴——它看似开放,但它有着一扇隐秘的门,我被拒之门外了。
那时我还太年轻,尽管已读过不少名著——差不多把小城图书馆里能读到的名著翻遍,却无法进入《百年孤独》。我沮丧地关上了这本书,关上这本书并不意味这本书的魔力消退,而是变得更有魔力了。
过了一段日子后我又翻开《百年孤独》——这回我要硬着头皮把它读下去——我发狠地对自己说。我就不信自己竟然啃不动这本书。可是,和第一次进入洞穴的结果一样,第二次我还是被拒绝了——对不起,你没有进入的密码——这本书用苍老、傲慢、古怪的声音对我说。
我勉强不了自己,又退出来了。什么东西嘛,这本书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乱糟糟的,根本不合我的口味。我对这本书有了另外的看法(酸葡萄心理?)。
又过了两三年吧,是在知道马尔克斯结结实实的、国际文坛霸主的名声之后,半是疑惑半是不服气地又一次翻开《百年孤独》——这是那时能读到的马尔克斯的唯一作品。
第三次的洞穴之门总算是进去了——是逼着自己硬着头皮进去的——如同逼着自己对一个庞大的、九曲环绕的迷宫的探险。奇妙的是一旦耐下心来克服了开篇部分的阅读困难之后,接下来的阅读就顺畅起来,渐渐地豁然开朗。
第三次阅读《百年孤独》的最深印象是:这本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给了我对小说全新的认识。在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没有像以往合上一本书时暗自怅惘——这种怅惘感就像与一个人的永别——我们亲密地相处了几天,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并且永不会再见。合上《百年孤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这本书并未永别——我们还会再见的,我会再一次地——第四次地翻开它,真正地融入它、消化它。这第四次的翻开也许要在很多年以后——在我愿意把时光的快马拉住,放慢,慢慢地在生命的草地上消磨的时候。
距离第三次阅读《百年孤独》已过去很多年,如今想起这本书我丝毫不记得书里任何的情节(如同书中马孔多镇那些得了失忆症的人),能记得的只有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许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行刑队时,准会记起他爹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多年前的下午来……”之所以记得这句大概得益于那位本地写者在酒桌上的朗声背诵。
在我的床头有本《霍乱时期的爱情》,2011年出版,忘了是在哪个书店买的了——应该是在合肥的某个书店吧。这两年我所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合肥,去过两三次,每次必去书店,且都是和诗人红土一起。
由于很少出门,很少与人交往,生活中需要花费的地方便不多。我最大的花费是衣服和书。这几年书买得也少多了——碰不到想买的书,即使怀着猎艳的欢悦买到的新书也很少读,抱回家,拆掉书封,粗略翻过,只把最想读的那本摆在床头,其余的便摆入冷宫样清寂的书橱。
如今买书似乎只是为了满足拥有的欲望而不是阅读的欲望,这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书的问题呢?每次站在书橱前,想在众多的新书中寻一本最想读的书,翻找半天终是无果——我最想读的那本书不在这里——我听到自己心里的一声叹息。
《霍乱时期的爱情》摆在床头有大半年了吧,阅读仍然停留在第一章。每次拿起来都是从头读起,读到七八页的时候放下,之后是长久的搁置,再次拿起又是从头读起,读到七八页的时候放下……如此反复——这和当初在书店遇到它时如获至宝般的心情是不相符的。
在书店买这本书有一半是冲着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另一半是冲着书的简介。我站在书架前,几乎没有变换姿态地读完了几千字的简介,这本书的简介写得极为魅惑:小说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它堪称是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教科书。”读过这段简介后我便认定这是我想要读的书了——即便我也知道,书的简介大都隐含着推销的功用,就像夸张的广告词,与实际产品的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就这样我又有了一部马尔克斯的小说——放在离我最近的床头,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阳光和灯光都能照得到的地方。这本书没有像它的兄长《百年孤独》那样用魔法吓唬翻开它的读者,庞综错杂得令我生畏,但是,为什么大半年过去我还是停留在开篇之处呢?是我的阅读胃口已经衰退?不能够再咀嚼生猛海鲜,还是这本书不如直觉中那般合我的阅读口味?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有其性情和气质,这气质大多是通过叙述的语言表现出来——安静的或是喧闹的,单纯的或是复杂的,优雅的或是粗俗的,忧伤的或是轻快的……一个读者喜欢上一本书,大多是因为这本书的气质与这个读者的内心气息相契合——就像两个气息相投的人,不需要相互适应、磨合、妥协的过程便能融入彼此。
回想近些年我所读过的书,大多是诗性的,安静到有些忧伤的,比如每年都会读一遍的《小王子》,比如《朗读者》《入殓师》《细微之神》和黑塞的小说,而另一些书,比如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为拉美文学大师的略萨,他的小说我在拿起后翻上几页便放下了。这不是我要读的,气息完全不对——我对自己说。
也或许是翻译的问题吧?当一本颇具盛名的小说在展开后觉得不堪阅读时,我便想:这或许并不是小说的问题,也不是作为阅读者的我的问题,而是翻译者的问题。
是最近才知道,《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于今年8月才得到作家授权,在中国翻译并公开发行——且是唯一获得授权的马尔克斯的作品。这就意味着,之前书架上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均是“水货”了。这样的“水货”无疑能为出版社牟一笔财富,但其翻译中的文学性与准确性是否可以不必置疑呢?
在我打开文挡,用习惯使用的智能ABC输入法敲出马尔克斯的名字时,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对他的作品在中国遭遇“水货”之灾的正义立场。作为读者的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很模糊的,也可以说没有立场。我觉得只要翻译上的文学性没有缩水,阅读“水货”书著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在购买的价格上比“行货”要便宜很多吧。我所购买版本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标价为人民币20元,在当下书市的行情里,这个价位算是中等偏低了,多实惠。
我甚至也不能确定地说,摆在床头的未被阅读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翻译上就是有问题的。翻译上有没有问题得专家来说话——由翻译家或文学评论家来说,或者拿两个不同的译本对照着读,孰优孰劣便见分晓。
那么,当我用笨拙的输入法在文档里敲下马尔克斯的名字时,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回到本文开头的地方,想想,其实促使我在这个初秋的午后坐在窗前,停下正在写作中的专栏文字,而把时光用来闲谈马尔克斯的原因,是他在其作品中说下的两句话——是这两句话击中了我,使我内心涌起波动,觉得需要表达一点什么才能平静。
这两句话中的其中之一就是本文开篇的那句:“如果你得不到爱,那么性留给你的只有安慰。”
另一句是:“对于死,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为爱而死。”(这句话也有译成“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有为爱而死”。)
这两句话并非是在他的书中读到,而是在网络上——在有关他作品的评论中读到。坦白说近几年来,在有了电脑之后,我的阅读更多是在网络上——可能这才是我近几年来少买书和买而不读的缘故吧。
“如果你得不到爱,那么性留给你的只有安慰。”
“对于死,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为爱而死。”
——这两句话多像是爱的碑文。
写下这两句话时马尔克斯已在一生的暮晚时光:得过文学的最高奖,患过癌症,也体验并参透了生命中的各种情感。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两句话——尤其是第二句,当做马尔克斯为生命和爱写下的墓志铭?
如今马尔克斯年已八旬,并且不可避免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家族性的)——就如他在《百年孤独》里所描述的患了集体失忆症的马孔多镇人那样——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记得自己写下过什么,爱过什么人。
当我在将近十月的初秋午后,与不在场的听者的闲聊中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将马氏的这两句话搬出后,心里要表达的话语已归于寂静——那个在心里涌动的东西落下去了,像一轮熟透的夕阳落入草丛。
此时的窗外归舟缓缓,秋水澄澈,一切都是安宁的。
一切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