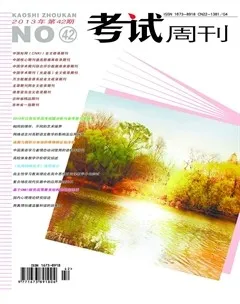相同的情怀,不同的艺术境界
带着对散文的一腔热忱,我把苏雪林的散文通读了一遍。回过头来看了题记,再从开篇慢慢品味。
最初认识刘亮程是因《名作欣赏》,上面登载了古代、近代、现代,国内、国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让人养眼的是读者对作品的赏析。韩富叶教授向我介绍了刘亮程的作品,韩教授对他的总体评价是“生命诗性的天然漫步”。我再度想到刘亮程,是在看完苏雪林散文后。
“艺术活动是人的本真生命活动,是一种寻觅生命之根和生活世界意义的活动,一种人类寻求心灵对话、寻求灵魂敞亮的活动。”①艺术需要情,情要来自本源,来自人与万物的通灵。苏雪林与刘亮程都本着细腻、敏感、多情的本色,用心灵观察着、深思着、同情着、关爱着万物,以感性的笔调收集日常琐事,娓娓道来,每个字、每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事物都透着灵性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同样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比如苏雪林对溪水的描写:“水是怎样的开心呵,她将那可怜的失踪路的小红叶儿,推推挤挤的推到一个漩涡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团转儿,那叶儿向前不得,向后不能,急得几乎哭出来,水笑嘻嘻的将手一松,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这样喜欢捉弄人的,但流到坝塘边,她自己的磨难也来了。你记得么?坝下边不是有许多的大石头,阻住水的去路?”
水与石都具有了人的温情,没有与万物的心灵对话,哪能有如此感受?刘亮程也是如此,他总是以平等的眼光关注周围事物,乐之所乐、悲之所悲,赋予生命深刻的内涵,让你体会到的是真实,是不加伪饰的本色情怀。比如在《一只蚊子的死》中,他描写了这样的细节:
“一只老蚊子,已经不怕死,又何必置它于死地。再说,我挥手也耗血气,何不让它吸一点血赶紧走呢……想一巴掌拍死它,又觉得那身体里满是我的血,拍死了可惜。”
一只老蚊子,在他的眼里,不是害虫,而只是一个生命,一个与人类平等的生命,所以怜悯它,哪怕他最后真恼了也没舍得拍下它。“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都是人的鸣叫。”(《剩下的事情》)这就是刘亮程的悲天悯人情怀的真实流露。
这也许和两位作家的童年生活有关,唯有童心才是透明的、无瑕的。苏雪林生于19世纪末,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仕宦之家。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意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在她的《儿时影事》《童年锁忆》中均有对多彩童年的深刻记忆。刘亮程出生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小镇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鸟叫》《先父》等作品中,皆能找到他童年的足迹。两位作家总是以童心、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万物,故而他们笔下的万物皆能折射出人类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理解、尊重和感叹,这种感叹来源于作者常有的换位思考,刘亮程质疑:“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人畜共居的村庄》)由此可见悲天悯人在他们的意识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有相同的情怀,但由于时代、生活背景的差异,他们的作品带给我们是不同的境界。导致两位作家艺术境界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写作技巧的不同
苏雪林散文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以“想象恢宏,辞彩瑰丽”见长②,写景散文透着清丽、真实而又缥缈,总会对眼前的实景进行幻化,神思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去,将读者轻轻摇摆到美妙的仙境中。比如她对戈贝湖的描写:
“那片湖虽不大,也有数华里的周围,因其位于万山深处,高峰顶上,人迹不易到,所以湖的四周,长林丰草,麋鹿出没.又汊港歧出,芦荻丛生,凫雁为家,那苍莽中的妩媚,雄浑中的明秀,疏野中的温柔,倒像一个长生蛮荒的美丽少女,不施脂粉,别有风流;又似幽谷佳人,翠袖单寒,独倚修竹,情调虽太清冷,却更增其悠然出尘之致。”③
作者对这种表达技巧如此钟爱,也许是当时乱世中人们对一切美好事物心灵向往的表现,是心理治疗的最佳良方。
刘亮程的文字朴实无华,在朴实中感受到真实,在无华中体会到成熟、厚重。他笔下的一只狗、一只蚂蚁、一丝风、一段朽木除具有物像的本质特征外,你还能看到与人类相通、相似的地方,你会觉得人类存在的渺小和孤单,同时又会生出一种平和而亲近自然的力量,但你找不到从现象到本质的那个坎,因为这些本质性的东西是你在审美过程中不自觉感受的,而不是它直接告诉你的。
二、参与主体的不同
打个简单的比喻,苏雪林的散文就如俄罗斯的舞台剧《天鹅湖》,而刘亮程的散文就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编自演的生活麻辣烫。一个是台上的表演,一个却是台下的表演。台上的表演精彩,引人入胜,荡气回肠,但始终和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观者永远只能是心向往之;台下的表演永远都是观众自己的戏,演得好与不好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也成了演员,过足了瘾,他(她)们能不感激导演吗?
三、引领观众到达的目的地不同
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最高的境界是观者在审美过程中不断升华艺术内涵直至重新认识世界本质。如果说苏雪林是把观者带到瑶池的话,那么刘亮程则是把观者带到人间;前者是在观众心里搁点什么,后者则是将观众的心归零。
把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散文作家无缘无故地突然拉在一起相提并论似乎有些唐突,但我认为万物只有对比才会显出各自的优越,才会挖掘出平常没发现的宝贝,所以有些唐突又何妨呢?因为是赶鸭子上架,时间又匆忙,就连这两位名家的作品我也没能读完读透。有时间再容我细细咀嚼,也许我会品出比以上更有价值的东西,更甚者还可能与上述内容相悖,也未可知。
注释:
①鲁枢元主编.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1:225.
②苏雪林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1:13.
③苏雪林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1:26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