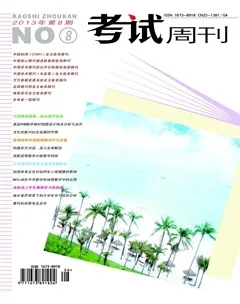生产与分配并举
摘 要: 梁启超一方面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方面对欧美社会进行实地考察,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解读,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也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本文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梳理、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 梁启超 社会主义思想 流亡海外
一、流亡海外期间的探索与考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他广泛接触西学,凡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学说和思想,他都会研究和介绍。他自称“新思想界之陈涉”,在输入西方思想时强调思想的“本来面目”。1902年的《新民丛报》,专文介绍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对进化论、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作了高度评价,“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称马克思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适宜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1]P2166,“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虽然,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1]P2166。他主张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警惕它成为煽动人心的思想工具,造成国人思想混乱。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分配方法,是均贫富以缓和社会矛盾的学说而已,所以他认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1]P2315。
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一方面他看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美国蒸蒸日上的情景,盛赞美国的繁荣富强,表达了无限的羡慕之情,“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1]P1853-1854。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他不无感慨地写道:“《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1]P1855他发出了“岂不异哉,岂不异哉!”的感慨,并由此断定“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1]P1855-1856。此时的梁启超仍然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手段和方法。
根据梁氏的记述,当时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拜访他,劝说梁氏将来中国社会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梁启超则认为社会变革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婉言谢绝了他,“余以其太不达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多询其党中条理及现势而已”。他认为极端的社会主义不但中国不可实行,即便是欧美也不能实行,否则将流弊无穷。但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符合中国的国情,比较适宜中国,“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1]P1851,但是他又认为当下谈论国家社会主义,“非其时耳”。那么梁氏心目中合于其时的改造中国的方案是什么呢?
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梁启超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对托拉斯垄断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它的利弊。在本文结论中,他写道:“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1]P1102他认为产业是否发达关系到一国的强弱和生死存亡,为中国经济上的贫困落后,无法与他国竞争而感到痛心,“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辣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1]P1102-1103。他希望中国能够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奋起直追/3Od4ENBVDZ020px0r9QRA==,摆脱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从上看出,梁启超为中国指明的道路是发展实业、摆脱贫困,“世界战争不一,有军事战争,有学问战争,有宗教战争。而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1]P2780。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日渐解体,经济凋敝,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被剥削的地位,“在优惠关税下,外国商品的涌入和1895年以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方面享有的特权,给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2]P341。对此梁启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数十年来所谓势力范围者,即各国经济之势力范围耳。所谓瓜分者,即各国经济之瓜分耳”,“是非世界无端而有变迁也,是乃各国之经济势力,侵入我中国之后,破灭我中国之职业,吸尽我中国之利益故耳”[1]P2781。他希望中国发展经济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而摆脱被奴役剥削的地位,但他反对仿行社会主义,“是以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舍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1]P2782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二、梁启超与社会主义思想论战
1920年9月罗素来华讲学,他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也无须进行阶级斗争,把矛头指向了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张东荪写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赞同罗素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是贫乏,因而只有一条出路“增加富力”。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李达、陈望道、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写文章,对之进行抨击和反驳。
梁启超站在张东荪一方,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对中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有所疑问,但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的产物,“欧美忠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但“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1]P3616。梁氏认为欧美与中国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相同,“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们得以变为劳动者”[1]P3616。
梁氏认为欧美社会已经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中国应该避免重蹈覆辙,但认为时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而此种畸形的发展,从一方面观察,虽极可厌憎;从他方观察,又极可欢迎。其可欢迎之点奈何?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厉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十中八九,不能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前既言之矣”[1]P3619。他认为中国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奖励资本,发展生产,对资本家应当采取“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浡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1]P3621。可知,梁启超一面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以图自救,一面又要提防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十分重视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是改造社会的主体,“不能以其人数尚少而漠视之”,应该在这方面“下工夫”,“下工夫之法,则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1]P3621。他强调要区分“劳动者”和“游民”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此项有职业之人,结合团体,拥护其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毋俾人掠夺,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游民而分有业者之利益,其事还同于掠夺”[1]P3619,他认为二者对社会发展有着截然相反的作用,“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1]P3619。
由此观之,梁启超认为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为了解决分配不均而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是十分幼稚落后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且无组织、无智识,还难以担当社会改造者的角色。所以,他认为当下中国首要是发展实业,又在注意财富分配问题,组织劳动者,在劳资较量中发挥作用,并逐渐成长为社会改造者的力量,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三、余论
梁启超考察欧美社会主义的起源,认为它是为了解决财富分配不均而兴起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而发生的运动,而中国的现实是经济落后,也没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力量,可以作为改造社会的主体。姑且不论梁启超对欧美社会主义的考察是否准确,然而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不主张照搬西方的理论,却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派所不及的,表现了他冷静的思考。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让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梁氏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具有先见之明。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的问题随之而来,梁启超生产与分配并举的思想,仍然可以作为当下的借鉴和参考。诚如有论者所说:“站在今天的立场,梁启超、张东荪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主张不应再被简单地视为‘反动’的了。梁启超赞成社会主义精神,又认为当时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这虽然与列宁主义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同,站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看,这个观点在当时仍有其合理性。”[3]P53
参考文献:
[1]吴松,卢云昆等.饮冰室文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3]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