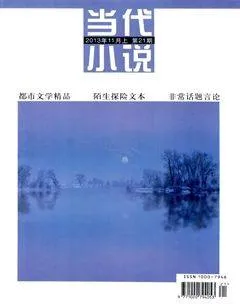油罐子
油罐子是一个人,油罐子这个称呼,是乡亲们给他取的绰号。很多人的绰号因为太恰当了,往往被人叫得转了名,他真实的名字是什么,谁要是突然提问,情急之中,反而想不起来了。
油罐子的脖子很粗,看上去,他的脖子跟脑袋一样粗。
肩膀以上的脖子和脑袋,本该有粗有细,有起有伏,这才显得错落有致,符合大家的审美习惯和生活趣味。油罐子的脖子跟别人的脖子很不相同,比较起来,就太粗了。
油罐子的脖子这么粗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脖子里,比普通人多了两个“因呱呱”。
什么是“因呱呱”?
有些人的脖子,因甲状腺肿大而在皮下生成的肉瘤状的东西,乡亲们形象地叫它是“因呱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脖子病。“因呱呱”是由碘缺乏引起的。好在“因呱呱”不疼不痒,仅仅是对脖子的转动有所妨碍,并无其它,在几十年前的农村,碘缺乏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病症。后来按照国家规定,在食盐里添加了碘,这种病也就很少再发现了。
油罐子的脖子一左一右,在下巴两侧,各有一个“因呱呱”,都有拳头那么大。就是它们,把油罐子的脖子补充得跟脑袋一样,又粗又大。这样的脖子与脑袋组合起来,再加上身体,就显得缺少起伏,大致看来,他的身体就跟一只玻璃酒瓶子的样子非常相似。酒瓶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人们很少使用,也极为稀罕。一个农民在那种艰难而贫困的岁月里,是喝不起瓶装白酒的。人们把公社干部喝酒后扔掉的空酒瓶捡回来,洗干净,当作一件时兴的器皿,宝贝得什么似的。他们在酒瓶勒口的部位拴一根细麻绳,提着它,常常拿它到供销社去打煤油、打清油。一只瓶子,不多不少,刚好能装一斤油。一斤煤油一家人照煤油灯,至少可以用一个月。在我们村,三个月才用一斤煤油的家庭也不是少数,用半年的都有。清油比煤油贵得多,家家都有,家家都舍不得用,一斤清油,一家人一般要半年才吃完。
用来打煤油或清油的酒瓶子,乡亲们一律称之为油罐子。
家乡有句俗语,说是:油罐子倒了也不晓得扶起来。这句话常常用来比喻懒人。
给这个人取了油罐子的绰号,并拿这个绰号代替他的名Plhm5KYaPtxv/1GwDWHvZw==字来称呼他,很贴切,很形象,也很逼真,实在是恰如其分。
我这么说是因为,油罐子这个人的皮肤,是人们常说的油性皮肤,他的皮肤的油性特征比别人的,还要更严重些。他的皮肤好像一直都在隐隐约约连续不断地,向体外分泌着油状物,这使他的脖子和脸,老是给人油光可鉴的印象。那么,把这个人称之为油罐子而不是酒瓶子,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油罐子的脖子里长了两个“因呱呱”,脖子和脑袋就不分彼此,浑然一体了。这么一来,就让人设身处地地,替油罐子难受得慌,也替他感到憋得慌,似乎,油罐子老是有什么想说而又不能说出来的话,全都压抑在咽喉或脖子的部位,是一副不吐不快却又欲吐不能的样子。
油罐子的话,的确很多。
油罐子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发议论,尤其在人多的场合,更是如此。他说的,往往又不怎么靠谱,是对评论对象本来意义的化解或曲解,是乡亲们称之为“淡浆水话”的话:幽默、有趣,既言之无物,亦无所能指,往往没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他这么说,只是为了自己取乐,同时,也是为了博得众人的一笑。
比如,人家干活干得好好的,油罐子会冷不丁地,突然咋咋呼呼而又极尽夸张地,大声喊起来:你们快来看看呀,我的屁眼咋长到尻子里面去了哇,我想放屁也放不出来,这可咋办才好啊?当人们故作吃惊或笑嘻嘻地回过头来打量他的时候,油罐子还要摆出一副努力放屁而又果真放不出来的艰难神态,这时,他的脸因使劲做放屁状而憋得通红通红的。大家忍不住哄笑起来。这正是油罐子想要得到的效果。
没有油罐子为大家逗乐,沉重而机械的体力劳动仿佛就是一种苦役,一个炼狱,有了他的添油加醋,无论骄阳如何酷热难耐,也不管身体是怎样疲倦而僵硬,人们一下子放松下来,轻松起来。
油罐子如果好久都沉默不语,人们就会感到寂寞。这时往往有人忍不住要出面点拨他:油罐子,你的瓶子口口子(瓶口)莫非让谁喂了一把草,塞住了?
这句话另有所指。这个说话的人显然是把油罐子比做吃草的牲口了。油罐子当然明白这个人是在打趣他,并不是骂他真的是个牲口。油罐子不气恼。他更受不了的,是人们的挑逗。他又说起“淡浆水话”来了。
总之,任何人有了想要听他说说的欲望,油罐子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不让大家开怀地笑起来,他是不会罢休的。
油罐子说的笑话,历来都是拿自己开涮,他从不以伤害或打击别人为目的。
当然,这只是在通常的情况下。
又比如,生产队里批斗老地主的社员大会刚刚结束,油罐子就信口开河起来:啥叫地主?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嘛,我们的公社社员现在都是土地的主人,我们现在就都是地主了嘛。社员同志们啊,你们也说说吧,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呀?我们不批斗现在的地主,却来批斗老黄历上的地主,你们倒是说说,这么做可笑不可笑啊?
这一番话,油罐子说得油腔滑调阴阳怪气的。
油罐子最后总结说,我们应该批斗的,恰恰应该是我们啊!
有人说,那就先批斗批斗你吧!
油罐子说,要批斗也应该先批斗队长嘛,现如今他是我们村里最大的地主嘛,你们也来说一说,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呀?队长该不该也让我们批一批啊?
队长气呼呼地回过头来,白了油罐子一眼。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
谁要是跟油罐子计较,哪怕他是生产队长,也会招来更大的难堪。
油罐子朝着队长的背影手舞足蹈,挤眉弄眼。人们在生产队长的身后,忍不住轰的一声,大笑起来。
油罐子的这一番言论,当然就耐人寻味了。真正上纲上线的话,油罐子会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吃不了兜着走。好在队长是他的亲三哥,不跟他计较,社员们没有人跟油罐子较真,油罐子本人也只是说说。在一阵哄笑声中,人们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油罐子这么明里暗里地袒护老地主,还要不时地替老地主鸣不平,也是有他的深层原因的。批斗老地主对于村里人来说,纯粹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人们的自愿。村里的人无论如何,对老地主都是恨不起来的。老地主的辈分比油罐子高得多,油罐子和老地主是同龄人,他是跟老地主一起长大的。老地主这个地主阶级接班人的童年生活,过得比油罐子这个贫农的儿子还要清苦。
解放的时候,老地主还是一个孩子。油罐子替老地主觉得委屈:他只是从早死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老地主这个名号,老地主本人,并没有剥削或压迫过村里的任何人。即使是老地主的父母,在黑暗的旧社会,也是完全凭借着勤俭持家的古训,把力气积累成粮食,把粮食积累成钱财,把钱财积累成土地,再用土地把自己积累成一个地主的。他们从来没有剥削谁压迫谁,他们剥削的、压迫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惟一心疼的儿子。老地主的父母把对土地的积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们舍不得吃好的,舍不得穿新的,舍不得供儿子读书,说是费钱,他们一门心思想把更多的土地留给儿子,他们想不到,他们留给儿子的,只是深深的耻辱。
世事,真是难料。
油罐子对老地主很好,队长跟油罐子,处得也不错。
在兄弟姐妹之中,油罐子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队长从小就对两个哥哥不怎么尊重,却对油罐子这个惟一的弟弟很照顾,也很包容,无论油罐子怎么冒犯他,队长最多只是拿白眼盯一盯油罐子,一转眼就忘记了刚刚发生过的不愉快。可能是,队长从油罐子身上找到了做哥哥的感受了吧?谁知道队长是什么心态呢?
也是因此,油罐子在拿自己开涮的同时,常常地,也拿做了队长的哥哥开涮。这让队长常常没了干部的威严,也不那么高大,——这反而使队长这个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亲近了不少。
有一段时间,一个娶进村才一年多的新媳妇,对队长产生了感情。论起辈分来,这个女人是队长的侄媳妇,说年龄吧,队长也比她大了十来岁。她咋会迷上了队长呢?真是令人费解。可这一点,队长既不知情,也看不出来。问题在于,全生产队的人,都看出来了,连这个女人的男人,也看出来了。
那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还比较混乱,人们只是背地里说说,即使真有了什么说不清楚的关系,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更不会因此瞧不起当事人。相反,很多人甚至暗暗地,以此为荣。
我亲眼所见,有个女人跟另一个女人对骂,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这个女人突然冒出这么一通话来:老娘再没本事,好歹还跟大队支书睡过觉,有本事你也去跟支书睡睡,让老娘也见识见识?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这个女人当即反败为胜,反而是那个此前明显占了上风的女人,自知难以有幸跟大队支书睡一回觉,只得一脸通红,落荒而逃。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这个年轻媳妇对生产队长暗自动情,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喜欢上队长的小媳妇,名叫勤娥。
勤娥从不掩饰对队长的好感。一般情况下,大家男男女女,都在同一块地里干活,尿憋了,很多人懒得走那几步路,也是为了不耽误干活,只需背过身子就可以痛快淋漓地处理掉,即使有人瞥见了那根亮晶晶的抛物线,男人当然不足为奇,装作没看见就可以了,女人在不经意间看见了,就低了头,抿嘴,无声地一笑,跟未看见一般,就算是完了。水火无情嘛!男人脸皮厚,可以就地解决,女人脸皮薄,就不好办。她们只能走很远,到僻静的地方去处理。队长尿憋了,也跟女人一样,非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人多的场合,队长撒不出尿来,他还认为,当众撒尿,与他的生产队长身份,不那么相符。
有一次,队长又去解决尿的问题,他不知道勤娥紧随其后,也对人们说,她要去“浇尿”。两个人一前一后,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其实,勤娥只是远远地跟着队长,她并未靠近他。她原打算对队长说点儿什么,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张口,就没有近前,更没有说。队长撒完尿,回头走了。他没有发现尾随他的勤娥。
这一天,油罐子也在干活的人群中,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的心里是透亮的。他的生产队长三哥回来了,油罐子也没有说什么,等到他的远房侄媳勤娥也回到人们中间来了,油罐子终于开了口。
远远近近的农民,都管尾巴叫“野杆”。牛野杆、狗野杆、猪野杆、马野杆、猫儿野杆,等等等等。油罐子装模作样地用手扒拉着旁边的一个人,大声说:嗨嗨嗨!你有没有野杆?那人佯装生气地说,你看你这个油罐子!我能有野杆吗?我有野杆不就成了畜生了嘛!油罐子不动声色,又一本正经地问旁边的另外一个人:你该不会长了野杆吧?另一个人仿佛被火烧了似的,立即对油罐子说,去去去!你少跟我穷开心!
油罐子当然不是为了跟他穷开心。他站直了身子,转身对他的队长三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生产队长,可是有本事得很呢。
油罐子话里有话,可他只说了半句,就不说了。
人们全都回过头来看油罐子,他们知道,油罐子一定还会再说下去的,他们显得很有耐心。
果然,油罐子慢条斯理又假装无辜地说,你们看我干啥呢嘛!你们要看就看队长去,人家撒尿的时候,前面端着一根野杆,后面拖着一根野杆。
人们轰的一声,都笑了起来。
油罐子当然不笑,他满头满脸,都是严肃。
油罐子懂得适可而止,他低下头,锄他的草去了。
队长不明白油罐子这是为什么,但他知道,这个油罐子弟弟,又在跟自己过不去。
队长对油罐子说:你不如直接骂我畜生算了。
队长还说,我们是一母所生,你把我骂成了畜生,只怕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油罐子不愠不火地说,三哥真是抬举我,可是,我太笨了,笨死了,还没有“进化”成一个畜生呢。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勤娥身上。人们看见,勤娥满脸通红,她的头也深深地,低了下去。
后来勤娥就不再当着众人的面,对队长表示她的好感了。
油罐子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他的语言和行为,难免粗俗。油罐子的女人,小名叫作黑女子,黑女子在跟油罐子成为夫妻之前,曾嫁过一次,还生了个取名闷牛的儿子。这个名义上的儿子并未跟油罐子在一起过过一天日子,看上去,油罐子似乎不关心他。黑女子是本村长大的女子,因婚姻的失败,回到娘家以后,多年未能改嫁,油罐子娶不上老婆,后来不知怎么,黑女子就跟油罐子一起生活了。
黑女子要死要活地跟了油罐子,她的母亲,曾拿闷牛要挟黑女子,黑女子一根筋,铁了心,不为所动。最终结果是,闷牛跟外婆一起生活,黑女子去了油罐子家。
黑女子长了一张很漂亮的瓜子脸,她的脸白白净净的,一点也不黑,在村里,她是个很有韵致的女人,不知为何,居然取名黑女子,让人想不到。
闷牛从来不把油罐子叫爸爸,他遇见了油罐子,也跟不认识似的,既不打一个招呼,也不尊重油罐子这个名义上的父亲,他总是拿轻蔑的眼光看一眼油罐子就走开了。人们一起议论起来,油罐子常常不屑地说,我一没生他,二没养他,他又不是我的儿子。油罐子说不出来的原因是,不依靠他这个后老子,闷牛生活得比他还要好。这让油罐子的心里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
人们和油罐子一起说这些的时候,闷牛和黑女子都不在场。闷牛见了黑女子当然是会叫一声妈的。可是,也仅仅只是叫一声妈,闷牛从来不到母亲家里去,闷牛的外婆外公,同样从不到黑女子的家里去,油罐子也从未去过他的岳父岳母家。两个家庭,几乎没有往来。
黑女子后来又给油罐子生了一子一女。
油罐子的儿子取名碎牛,碎牛就是小牛的意思。很显然,油罐子是顺着闷牛的名字,给他亲生的儿子取名的。
生了儿女之后,黑女子过一段时间就瞒着油罐子,去一趟母亲的家。我跟另外几个村里人,就看见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人们都与黑女子一道,心照不宣地,瞒着油罐子,谁也不跟油罐子说这些。黑女子这么做倒不是油罐子不让她回娘家走走看看,是黑女子怕因此伤了油罐子的面子。此前,黑女子的母亲为了阻止黑女子的第二次婚姻,说下了狠话,她母亲说,黑女子要是跟了油罐子,她就不许黑女子和油罐子踏进她家的门槛。黑女子的母亲把话说绝了。
几年后,黑女子厚着脸皮回了一趟娘家,母亲赶她,她不走,母亲板着脸不说什么了。可是,两家的关系始终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并未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黑女子偶尔去了娘家,母亲不再赶她走,但也不跟黑女子搭话,黑女子不尴不尬地坐一会儿,拉阵子闷牛的手,怕油罐子怀疑她的行踪,要走了,母亲也不挽留。在村里,除了油罐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人们认为,是黑女子的母亲做得过分了。可对这个老太太的态度,人们无可奈何,谁也改变不了她,只能听之任之。
黑女子第一次出嫁就是母亲做的主,她嫁到了母亲的娘家村子,那个村庄很远,黑女子的第一次婚姻,我很不了解,也不用了解,我只知道她的第一次婚姻很短,很不幸福。黑女子娘家的生活我了解,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原因在于,黑女子的养父,也就是那个人们叫他老吕的外地人,一直都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这是全生产队最肥的差事了,哪怕队长家里揭不开锅,老吕家里也能够保证,每天至少吃一顿细粮,这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对老吕这个生产队的“蛀虫”听之任之的原因是,他们普遍认为,无论谁做了保管员,都是有私心的,都会偷偷摸摸往自己家里拿一点。可有时候,人们又对老吕忿忿不平:凭啥让一个外地人占这么大的便宜?
背着油罐子,人们常常议论老吕,当着油罐子的面,人们从不议论。因为老吕是一个外地人,还因为老吕一家跟关系最亲的油罐子一家也没什么来往,队长才一直让老吕当生产队的保管员。老吕的保管员职务是队长任命的,队长当然可以撤他的职,不让老吕当。队长有这个权,但他从未打算那么做。队长心里想的是,老吕当保管员,生产队的损失,应该是最小的。这是队长的逻辑。
油罐子不明白队长的逻辑。他很不服气。油罐子不找队长摆事实讲道理,他想当着众人的面,让队长下不了台。
干活的间隙,大家猫在树下,歇气,乘凉,说些闲话,山坡上的小风吹得无比舒服,人们或躺或坐,无一不是放松的姿态。这时,油罐子突然站起来,对不远处的队长说,无比尊敬的生产队长同志,公社社员油罐子跟你提一个建议行不行?
队长太了解他这个弟弟了,他不耐烦地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油罐子说,那就不说话了,我还是放一个屁吧。
油罐子停了停才接着说,报告领导,我要放的屁是这样的,你能不能让老地主做生产队的保管员?你让老吕当保管员,我这个名义上的女婿,一点光都沾不上嘛,我好歹也是你的亲兄弟嘛。
队长白了油罐子一眼。
队长知道,油罐子不是为了沾光才这么说的。
队长不理油罐子的碴儿,他故作不知,说,是我沾了老吕的光了。
人们当然明白队长说的是气话。队长行为端正,并未从老吕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让老地主当保管员,队长不是没有想过。可是,这么做明显是不行的。
队长一本正经地教训油罐子说:你也不用你的尿罐子(脑袋)想想,老地主当保管员,大队支书答应吗?公社领导同意吗?生产队这个大家庭的总管家,能让一个地主来当吗?
油罐子的确不曾想得那么深远。他说不出什么来了,沉默了很久,油罐子才解嘲地说,看来,我这个屁是白放了?
队长也不客气,他挖苦油罐子说,你放的屁,臭都不臭!
油罐子说,我知道我放的是香屁,可也没人爱闻。
油罐子的提议,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油罐子认为自己还是有所收获的,起码他已明白,队长对老吕的行为,是了解的。油罐子这么做无非是让队长做一个明白官,他也不一定非得让老地主来当生产队的保管员。
老地主一个人独自过日子,已经有很多年了。他要是当保管员,生产队的损失应该是最小的,可惜的是,他不能当。
生活或日子,就这么不完美,谁也没办法。
保管员平常不参加集体劳动,油罐子的丈母娘是饲养员,她给生产队放牛,也不参加集体劳动。闷牛是个孩子,年龄稍大的孩子都会偶尔加加夜班,给家里挣两分工分,闷牛从不加夜班,因为老吕不需要那么多工分。
人们议论保管员没什么顾忌,方便得很。
小时候,我经常参加“抬大寨田”的集体劳动。那时候,“农业学大寨”搞得风风火火的。我清楚地记得,“抬大寨田”的地方,从前都是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一块块水田,它们是村里最好最高产的土地。“抬大寨田”就是把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整合成一大块一大块的长方形梯田,乡亲们把这些方方正正的土地叫“大寨田”,而把整合土地的过程,说成是“抬大寨田”。
“大寨田”整整齐齐的,很好看,很壮观,至今仍在村旁排列着。
“抬大寨田”不仅白天做,有月亮的晚上,也经常做,人们称之为加夜班。晚上又没有什么事情做,睡觉嫌早,不睡又会浪费煤油。加夜班干活只需两小时左右,却可以记半天工分,有了夜色的掩护,偷懒也比较方便,不算太累,是很划算的事情。
村里的人,无论老幼,都喜欢去加夜班“抬大寨田”。
“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时不时地,我也去加一个夜班,给家里挣一点工分。我们这些孩子能做的,通常是把小一些的石头捡起来,扔在架子车的车厢里,再让专门推车的人,把石头运到指定的地方去。刚从地下挖出来的较大的石头,我搬不动,只能留给身旁的大人,让他们把石头抱起来,搁在车厢里。捡满一车子石头,大人可以就地休息一分钟左右,孩子们还得帮忙推车子,回来接着捡石头,连喘一口气的时间也没有,比大人还辛苦。一车子石头是很重的,地也坑坑洼洼,很不平整,推架子车是最吃力的事情,推不了几趟车子,我就累得不想动了。
加夜班“抬大寨田”是很重的体力活,中途照例要休息一段时间,这时候,往往有人提议:谁来玩个仗?谁来玩个仗?在我们村,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玩仗”。
“玩仗”又叫“玩跤”,其实就是摔跤。一方将另一方摔倒在地,再压住他,让他彻底丧失反抗的能力,也不再有反抗的打算,就算赢了。那时候的人没什么娱乐,摔跤既可以比试力气,消耗过于旺盛的精力,又不能完全凭借力气,还得有一点技巧才行。在村里,无论男女老幼,大家普遍接受摔跤的玩耍方式,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玩仗”得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场地才行。一般在村里的打麦场或干活的田地里来进行,在田地里“玩仗”,还得是在土地空了的时候,不然会弄坏庄稼。被点名邀请的人除非自愿认输,一般都会出面应战,输了就输了,图得就是一乐,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不能不上阵就认输。
腼腆的女性,多半不会应战,会直接认输,男人往往不会,怎么也得比试比试。也有已经输了的,还要继续比试,他认为力气差不多,输得不服气。
这天加夜班,中途休息时,已有好几组人玩过跤了,队长觉得差不多了,正想招呼大家继续开工加夜班。冷不丁地,勤娥站了出来,邀请队长,她要跟队长玩一跤。这是很少见的事情。一般都是男的出面邀请女的,少见女的邀请男的。何况队长人高马大,力气也足,这不是自讨苦吃嘛。队长当然不能认输,他愉快地接受了勤娥的邀请。结果也跟人们预料的一样,用了不到一分钟,队长就将勤娥死死地压在身下了。人们大笑起来,都认为勤娥自不量力。即使村里的年轻男子也不敢轻易跟队长叫阵,勤娥凭啥这么胆大妄为呢?
勤娥在队长身下,很快就不挣扎了。队长以为勤娥认输了,就在他打算起身的时候,勤娥又挣扎起来,做出要反击的样子,队长只好继续用力压着她,过了一会儿,勤娥又不动了,队长又想起身,勤娥再一次挣扎起来。就这么,两人在冷冰冰的地上纠缠了很久。后来,到底还是勤娥心虚,怕人们看出端倪来,终于放弃了挣扎。
勤娥用这样的办法,要让队长熟悉她身上的沟沟坎坎。
队长是个木讷人,不知道勤娥的心思,油罐子却明白勤娥“玩仗”的真实意图了,勤娥的目的,无非是让队长在她身上压一阵子嘛,她还能图啥呢?
收工的时候,油罐子故意走到勤娥跟前,他小声地对勤娥说,你这个女子,也真是的。
勤娥左右环顾之后,才说,咋的?
油罐子说,队长是个闷子(不灵醒的人),我的心里可是亮清(明白)得很呢。
勤娥故作不知,说,你说的是玩仗吧?玩仗就是玩仗,打打闹闹的事儿,有啥亮清不亮清的?
勤娥这么做,的确是在人们的道德范围之内,无可指责,连油罐子也不好说什么了。
勤娥的做法,让油罐子深受启发。
当天夜里,油罐子回了家,立即对黑女子说,明天加夜班的时候,你跟老地主玩一次仗吧。
黑女子为了悄悄地去看一次母亲,谎称有病,这天晚上加夜班“抬大寨田”,她恰好没有参加。黑女子不明白油罐子的意图。黑女子说,老地主是个大男人,我不是他的对手。黑女子的意思是,她是不会邀请老地主,跟他玩仗的。黑女子的想法当然没有错,明明知道会丢人现眼,为什么还要自讨没趣呢?她是个女人,要面子,爱面子,更怕当众出丑。
油罐子突然生气了,他说,叫你玩仗你就玩仗,输了就能少块肉啊?
在黑女子面前,油罐子从未这么生气,她不明白油罐子为什么要她这么做。黑女子想,油罐子是不是发觉她并没有什么病,而是借故回了一次娘家,这才故意找茬儿,跟她斗气?黑女子觉得,油罐子或许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是真要她这么做。
黑女子不说什么了。
油罐子也不说什么了。
黑女子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黑女子想错了。
又过了一天,又到了加夜班休息的时间,油罐子带头起哄说,老地主咋从不玩仗呢?让他今天也玩一个!油罐子说完就把老地主向场地的中间推。大家都知道油罐子的脾气,以为他要跟老地主寻开心,都在齐声对老地主起哄。
老地主从不参加玩仗的游戏,他扮演的,一直都是躲在一旁观看的角色。即使偶尔有人邀请老地主,也是为了给自己壮一壮声色,他们都明白老地主不会应战。有了这样的机会,老地主只是不停地说,我不行,我不行,我是真的不行。当然,邀请老地主的,多半都是男人,偶尔有女性邀请他,老地主还是说,我不行,我不行。人们当然明白,老地主不是不行,而是不想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生产队开社员大会,老地主经常被批斗,他被关注怕了,他对面子,也已经无所谓了,一个经常被“揪”出来批斗的人,哪有什么面子呢。用油罐子的话来说,就是:甭说面子,他这个人,里子都没了!
躲无处躲,藏无处藏。老地主也怕得罪了众人,那样对他更为不利。
在大家的推推搡搡中,老地主到了场地中间。
可是,没有人出面邀请老地主。一旦跟老地主有了什么瓜葛,人们都怕将来会对自己不利。
大家也是搞不清油罐子,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油罐子说,没人敢来,那就我来!
油罐子走到场地中间,三两下就把老地主摔趴下了。老地主没有反抗的意愿,油罐子也很快起来了。
油罐子知道老地主不跟自己真心比试,但他故意对大家说,这个老地主,浑身软绵绵的,哪儿像个男人呀,他跟女人摔摔还差不多。
老地主也明白,油罐子用的,是激将法。
老地主不明白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油罐子回头招呼黑女子:黑女子,你来跟老地主比试比试。
今天这一出,油罐子是早已策划好了的,黑女子明白,不顺着油罐子,就看来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黑女子只是不明白,油罐子演的,到底是哪一出?
黑女子来到场地中间,靠近老地主,揪住他的袖子,说,要来就来吧。
老地主无处躲避,只能应战。
僵持了片刻,黑女子主动出击,老地主却纹丝不动,她难以用双手摔倒他,就想用腿扳倒老地主。黑女子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就在她想另打主意的时候,一不小心,老地主一别腿,将黑女子摔倒在地上。
黑女子被老地主压在身下,起不来了。
油罐子大声招呼黑女子:你是贫下中农,千万不能输给一个地主啊。
黑女子挣扎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放弃了。
黑女子不挣扎了,认输了,老地主也就松了手,站起来了。
黑女子回了家,立即生气地责问油罐子:你为啥非要让我跟老地主玩那个仗?你也不想想,我一个女人,是人家的对手吗?
油罐子平静地说,我晓得你会输。
哪你还让我跟老地主玩仗?
黑女子不依不饶。
油罐子说:让老地主也可以摸摸女人的身子,不行啊?
就这么一句,把黑女子说得,愣在了原地。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