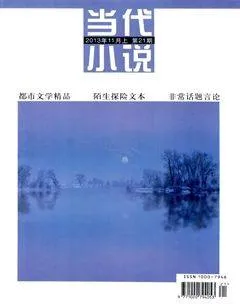全家福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赵小玫的婚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可是这件家庭大事里的主角儿,却像个局外人。媒人上门来,总要背着她和妈嘀咕,嘀咕得差不多了,妈就去跟爹说。爹呢,坐在那里弓着腰,双肘撑在大腿上,低着头吸着烟,听完了也不作个声。不作声就表示没意见,妈就像拿到了什么令牌似的,转过身来高声招呼道:玫儿,过来!
那个时候,在农村,在许多家庭,都还是媒人介绍,父母做主的,但在关键时候,也还要征求男女双方的意见。那多半是男女双方见了面,在介绍人,或者亲戚家里吃完了饭,媒人就把男的女的拉到一边:该介绍的介绍了,该看到的也看到了,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时候,赵小玫的脸就羞得发烫,红得真跟花儿一样。整个相亲的过程,她是又胆怯又害羞,不敢拿眼看也不敢动嘴问,坐在那里低着头,垂着颀长白皙的颈脖,不安地绞着肩头的一根乌黑的长辫。人儿呢,就跟喝了几碗醪糟样,晕晕乎乎的,别人的说,别人的笑,别人的在她低着头的身边过去过来的身影儿,就像梦境似的。媒人问了一遍,又问一遍,不知在想些什么的姑娘慌忙抬起了头,乌黑的两眼茫然而又惊恐;还没听完,一颗头早摇得拨浪鼓似的。
我的姑奶奶,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儿的?!
走在回家的田间小道上,妈是一脸不知拿她怎么办的怨。风儿吹着一田又一田青青的麦苗,也吹着那跟在妈的后面,像打了败仗一样的姑娘的脸。听了妈的这些话,沮丧的脸儿垂得更低了。望着脚下的田埂儿,田埂两旁的星星点点的花儿,赵小玫也委屈得直想哭。
要找个什么样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啊,只是见了那男人的面,想到要和这陌生的人一个屋里住,一个屋里吃,心就先慌了,害怕了,就要赶紧扯着妈的衣袖,躲到妈的后面;曾经无限憧憬的甜蜜的事儿,到头来竟是这样的为难。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浪一样在麦苗上翻卷,将那一排排绿浪,吹送远远的天边。
是的,她已经不小了,是个大姑娘了,和她同一个岁数的,早已抱着娃儿回娘家了。
强盗杂种的,看她找个什么样的!当个皇妃娘娘,也没生到那个命!
姑娘嫁不出去,当妈的最放不下心;时间一长,放不下的心事儿就变成了唠叨,爹听了也烦人,就隔了一间屋,坐在门外骂。在一家人的眼里,她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自不量力的人,成了大家的累赘。
我不嫁,我当尼姑去!使性子的姑娘扑倒在床,扯上被子,把脸,把耳朵都蒙上了,可不争气的泪水,一条一条地,像那让人伤心的话一样,又顺着脸颊爬进了耳朵。
话是这样说,可嫁还得嫁:总不能守着爹妈一辈子啊。又过了一年,媒人喜滋滋地来了,一进门就说,这下好了,为小玫找了一个好婆家,是个当老师的!一家人听了,相互一望,脸上都隐秘地笑了,像终于挖到了一个什么金元宝。
几次相亲不成,家人都以为是自家的姑娘性气儿高,看不上那些种田使力的。别人的姑娘绣个鞋垫儿,无非花儿朵儿的,图个鲜艳好看,可这小玫,绣也要绣个蝶儿成对,鸟儿成双。有时见她拿着针线,一怔半天,不知在想些什么名堂。一听说村里要放电影,这个闺女就像喜从天降,同样的电影百看不厌,这个村看完了跟到那个村去赶场,开口闭口的那些话儿,也尽是不着油盐。当妈的就叹了一口气,就私下里劝姑娘,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过日子就不是那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是七仙女与董永郎,什么情啊爱的,全是写书的骗人的,结婚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回你可要想好了,人家是拿工资的!媒人刚一出门,妈就说道。
听听这口气,就像在下最后通牒,好像她真是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
你们就是想赶我走!好,我同意!
赵小玫的泪水哗啦一下淌了出来:她转身跑进了自己的房屋,扑到床上,伤心地耸动着肩头。一个大姑娘了还在挑三拣四,村里已经起了风言风语;哥哥感到了背后的指指点点,嫂子干脆指桑骂槐。妈一提起来就在叹气,爹说不上两句就要破口大骂:她不仅成了家人急于摆脱的累赘,还危及到整个家庭的脸面。
跟进闺房来的妈,怕姑娘着凉了,拉开被子给她盖上,一边在床头坐下来,开导说,儿,你不说妈也知道,那个黄老师长得是与你不大般配,可是长得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只要时间一长,什么都看习惯了。当年我和你的爹——
赵小玫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也是这十乡八里的一朵花,只是因为成分不好,才嫁给瞎了一只眼的爹。赵小玫听着听着,一起身趴在了老妈的腿上,嘴里喊了一声妈,早哭成了泪人儿。
老妇人抚着女儿的头,像在安慰,又像自言自语:谁叫托生个女人呢——
就这样,赵小玫感到自己就像一朵被移栽的花儿,一根苗儿,被连根拔了起来,脱离了原来熟悉的环境,栽到了一个离娘家三十来里的小镇,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家庭,陌生的家人,公公,婆婆,两个姑子,还有一个全然陌生的睡到了一张床上的男人。男人黄大柱虽然是个教书的,但并不是自己想像的教书先生的斯文模样,又黑又矮又胖,倒像个卖烧饼的武大郎。人家武大郎心眼还细,还知道处处心疼自己的婆娘,可这个黄大郎倒好,一回家就像一个大老爷,跷着二郎腿,等你递给他吃,递给他穿,连洗脚水也端到他的面前。在他的眼里,老婆就是佣人,就是不花钱的长工。他是讨了家庭成份的好,才被推荐上的工农兵大学,上了大学就觉得高人一等,既不屑于那些没有文化的事,也不屑于没有文化的人,更不用说跟没有文化的老婆还交个什么流,掏个什么知心话。他在离家十多里的另一个乡镇中学教书,一个星期才回家一回。在这个陌生的家里,这个最有文化也最应该明理的最亲近的人是她, 很多事儿憋了好长时间,想回来跟他说,可他倒好,一回家就只知好吃好喝,尤其好那一口酒,一喝就醉,一醉就睡,呼噜打得床都在抖。
晚上说不成,白天里说吧,她搓好了一盆衣服,拿起棒槌,要他帮忙提到门前的河边码头去清洗。黄大柱低头瞟一眼花花绿绿的衣物,眉头一皱,这一篓衣服你也提不起?
他是怕别人的笑话,更不屑于女人家的家务活儿。
不愿意干家务活儿,怕损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脸面,那去挖田,去帮忙种种菜园也可以的吧,可是他照样没有时间,不是把每次回家都要挎回几件脏衣服的包儿一提,说要赶回学校去上课,就是摊开了本子说要备课,一脸备受打扰的苦瓜相。偌大的菜园里,到头来照样只有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低头劳动的身影。望着菜园上的鸟儿飞过天空,望着菜园里的蝶儿在花儿上翩跹,这不会说话的物件儿也成双成对呢,想起做姑娘时的种种憧憬,想起那些电影里引起她无限憧憬的美好画面,她举起锄头挖一下田,抹一下泪,突然她像使气似的,急促地挖起田来,挖得尘土四溅,挖得轰轰烈烈,仿佛要把那些结成了板的心事儿刨开,敲碎,埋进泥地里。
嗬,这大黄家的媳妇真能干!不知情的村人,在另一头的田园里见了,称赞着说。
她就只有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其实她也知道,哪家没个矛,没个盾呢,牙齿有时还咬着了舌头呢,她要的只是一个人说说话儿,倒倒心里的委屈。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了,剩下她和男人俩人了,委屈的话儿还没说两句,这个黄大柱就变了脸:怎么就都是我家里的人不对?
这个黄大柱,在他的眼里,自己竟还是个外人!
她像望着陌生人似的,望着这个蛮不讲理的男人,吃惊的表情就像吃饭时噎住了似的。算了,懒得跟他说了,越说话越多,越说心越烦;本不是什么大事儿,没有矛盾的,看他这个样子,倒真成了矛盾了,成了打小报告,闹不团结了。如此一回两回,她也就死了这份心,就只当自己是个寡妇,是个死了男人的!从此,什么委屈的事儿就都憋在心底,像那些叶儿茎儿,挖田时一锄头埋在土里,让它自己烂掉。
实在烂不掉的,就回趟娘家,回娘家去倒倒委屈,一进门,见了妈,一声妈还没有喊出来,泪水就先涌出来了,涌得汹汹涌涌,像不断线的屋檐水。妈慌了,这真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忙拉着姑娘的手,问是怎么了怎么了。可听去听来,都还是拈不上筷子舀不上调羹的琐碎事儿。
那黄大柱,他的工资,是不是每月交给你?
赵小玫愣了一下,接着擦下眼泪点点头。
这就行了!妈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转身去忙自己的事儿——只要他每月把工资都交给你就行!
本想找妈痛痛快快诉说一番的,想像中娘儿俩儿会来个抱头痛哭,到头来却是这个不咸不淡的结局。自己像一天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妈倒好,只当飞过一只蚊子的,巴掌都没舍得拍一下。她赌气地坐在那里,妈问什么也不理了。见姑娘突然没了声音,手头忙着的母亲一回头,见了姑娘嘟嘴生气的样儿,就笑了。
儿啊,你还真是个儿!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没有心思想这想那了——妈像是深有体会地说:妈都是打这路儿上过来的啊。
可是赵小玫,总感到是从这条路上走不过去了。她想,如果只有她一个,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期盼,再难走的路,她也会下定决心,奋力地几跳几蹦,那些沟儿坎儿,那些隐在河中的石凳儿,说不定就过去了;就是遍山的荆棘,也会跟当姑娘时样,提着篓子,眼都不会眨,一低头,钻过去了,哪怕刺破了手,划破了脸。可是现在,明明有个人可以伸手拉一把的,可那人就是袖着手,甚至连望也懒怠朝这方向望一眼,任她一个人蹦,一个人跳,不高兴了,还要批评她这不对那不行。现在,她想跳也跳不动了,因为她不再是单打单的一人,因为有了儿媳妇,嫂子,老婆,母亲的几重身分,就像背上了装满柴火、猪草的重沉的背篓,努力地伸着脖子,张着两只手,两条腿,吃力的乌龟一样只能慢慢地爬,慢慢地移。
并不像母亲说的那样,有了孩子矛盾就少了;的确,很多当姑娘时的想法。那些关于情,关于爱,关于生活的甜蜜梦想,有了孩子就像是一个梦,是人家的生活,是画中人的生活了,她不再幻想,不再望着那些蝶儿鸟儿,或者夜来那布满星宿的高天,光灿灿的一泻银河一怔半天,也不再为男人黄大柱的一句话气得流泪了。希望没有了,怨气也少了,但是新的矛盾也随着新的生活,随着增长的日月也发芽了。
与公婆,与姑子们在一起,当然也有矛盾。开始,她想分开过,可是公婆不同意,黄大柱更不同意,因为这个家庭只有黄大柱一个独子,别人分家是兄弟多,他分家算是哪一门?千万不要背上不孝的名声!回家跟妈一说,妈更是一千个不答应。于是她也学着跟妈一样,与公婆争是争,吵是吵,可过后低头的还是她这个当儿媳妇当晚辈的;有时吵闹后,一家人几天都不说话,平常天一亮就起床来忙家务的公婆,那几天日头照到了窗口也还不见动静,这时候,赵小玫就要认真检讨自己,就要做和好的准备。她早早地起床,劈柴,烧水,舀米做饭,公婆们做的家务她一人承担,本是知道米油放在哪儿的媳妇,这天也要装糊涂,站在公婆的房门口,朗声喊妈喊爹,问米问油放在什么地方。如果碰巧那一天是公公或者婆婆的生日,这媳妇就会头一天上街买来了油条,冲了两碗鸡蛋花儿,推开公婆的房门,端到公婆的床前。
谁叫自己是晚辈,是媳妇呢,她常这样安慰自己,也尽量多想两位老人的好处;对待姑子,她更是做出长嫂的样子,尽量宽宏大度,一想到她们也会跟自己一样,会嫁人,会跟自己一样去忍受当儿媳、当女人的很多磨难,本想跟她们大闹一场的心气就先散了;只是像不经意地说,大姑,这鸡蛋糕你来尝尝咸不咸,或者对二姑子说,二姑,你看这鞋垫是怎么锁的边儿——她只是想,把自己学到的、当女人当媳妇应该掌握的持家的本领,都一点儿不留地传给她们,让她们少受自己受过的欺辱和白眼。
对公婆,对姑子,对来自外人的一切的委屈,她怎么想都想得通,怎么忍都可以忍下去;毕竟,他们都不会跟自己过一生,可是,对来自丈夫的委屈,她却一点儿也吞不下。
仍是到了星期天才回来,回来就像领导,像是客;家里大小的事儿都不动手,田里的事儿更不用说,他是半边户,家里种了几亩田都不知道,到了农忙赶季节,不是说有事不能回来,就是回来也像个闲人。一请三五个栽秧割谷,这帮忙的都卷起裤腿下了田,他这个当主人的却穿得工工整整,蹲在堤上抽烟,跟人说笑,要不中午又喝多了酒,躺在堤上树阴里打呼噜。赵小玫一身泥地在田里栽秧,看看天色晚了,要他回去帮忙洗好菜,她回去弄饭省时间,可这个黄大柱睡了一觉醒来,坐在树阴下的石头上,正眉飞色舞地跟田里帮忙的人开着玩笑,听了老婆的吩咐,大煞风景似的,眉头一皱:我搞不好!
那时,孩子还小,晚上还要把几回尿,田里、家里忙乎完了,晚上还要带孩子。实在太疲倦了,听见了躺在一边的孩子发出哼哼的声音,知道要尿了。自己累得浑身一动就痛,眼也睁不开,就叫黄大柱。黄大柱一上床就打起了呼噜,喊了几声不见动静,就用脚去蹬。黄大柱用手抹着惺忪的醉眼,不耐烦地说:孩子屙尿也要我去?!
就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人事的。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赵小玫有了独自生活的打算。她一想到这个打算,想到无牵无挂,突然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不再像一只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乌龟了。当她高高兴兴地告诉妈时,妈吓了一跳:
你怎么,要离婚?!
在许多人的眼里,她的条件还是让人羡慕的,从乡下嫁到了集镇上,丈夫是拿工资吃皇粮的,公公婆婆身体也好,几个姑子相处也还融洽。可是过得好不好只有她自己知道。
是不是那黄大柱,外头有人了?
赵小玫摇了摇头。
那,你,心里有人了?妈审视地望着姑娘。
妈,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赵小玫一脸的苦笑;接着坚定地说,我不想再这样过了!
儿啊,自古说结发的夫妻好,后来的赶不上先头的;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要一竿子撑到头——
妈说了很多阻止她的理由,这些理由都像沟,像坎,像横在她面前的高山大川,但都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要获得,总是要付出,要前行,就会有障碍,就像她小时候挖黄姜,寻猪草,看见了那一蓬黄灯笼儿,看见了那一树猪草叶,是荆刺也得钻,不怕头破血流。可是妈最后说出的一个理由,顿时让那些障碍放大了十万倍,就像高天难于攀越。
孩子怎么办?
是啊,孩子怎么办?儿子刚上幼儿园,一见她,就像鸟儿张开了翅膀飞了过来。一想到孩子会是无爹无妈的凄苦样儿,想到小脸蛋儿上会挂着两行无助的泪珠儿,这个母亲就心如刀绞,泪水就涌了出来,心中如何坚硬的堤坝,如何坚决的打算都崩塌了。
她像害了心绞痛似的,抚着自己的胸口,强按着要冲出心胸的想法,离开了娘家。她顺着那条田间的羊肠小道走着,走得哀伤又缓慢。她望着前方的路,田野庄稼的绿浪淹没的小道,知道这已开始的生活再也没了回头路。她叹了一口气,望着前方的茫然的两眼露出坚定的目光,总有一天,她想,总有一天,孩子会长大,她会过上自由选择的生活。
然而,时光是无情的,在她咬牙等待的日子里,她那光鲜如一朵鲜花的脸庞不再年轻,乌黑的一条长辫也成了花白的短发:人们从喊小赵,喊小玫,到喊她赵妈妈,赵阿姨,赵奶奶了。在这漫长的等待里,她陪伴两个姑子先后出嫁,她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让她们的婚事办得大方又体面,那一行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送亲队伍,曾引得多少人羡慕指点,也让走在送亲队伍中的姑子风光满面;她侍候公公婆婆百年归山,她跪倒在公婆的灵牌下,她真诚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引得多少人抹泪擦眼。总之,她是一个称职的嫂子,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等着那一天的到来,自己再无任何的后悔不安。
终于有一天,她把自己埋在心底的想法跟儿子说了。儿子长大了,母亲那些已经消失的青春时光,仿佛都跑到了儿子身上。正当青春年少的儿子打扮时尚,穿着时髦,更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如果不是性别上的差别,就是活脱脱当年的赵小玫。儿子刚成了家,小两口双双在县城一家不错的单位工作。这当儿子的是怎么也没想到,逆来顺受、温和贤慧的母亲,竟还有比自己更前卫、更叛逆的思想。而且是忍受了几十年!他吃了一惊,望着头发花白的母亲。他懂事的时候就知道父母之间情感的冷淡,以为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所谓的恩恩爱爱,都只属于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他感到了惊慌,更感到不可理喻。这个头发花白的母亲,竟然曾经也有过和自己一样的青春。可是不管怎样,一个已经习惯了的舒适完整的家庭,突然说要分散,任何人都会感到来自内心深处的抵触。
爸爸什么意见?
只要你同意就行!
母亲平静地望着儿子,目光中只盼着他的决断:这个决定她已经等了好多年。儿子现在已经成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她已经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现在,她可以跳出那个束缚她的壳儿,想走哪条道儿就走哪条道了。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下,儿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有一阵儿喘不过气来的压抑。他沉吟了半晌,说出来的话突然像老成持重的过来人:以前,爸爸是在上班,您们一起生活得时间少,过一年,等爸爸退休回家了,再在一起过过看?母亲垂下了目光。她不得不让自己承认,儿子的话说得合情合理。以前,爹妈的话说得有情有理,现在,爹妈去世了,儿子的话她也不得不考虑。可是过后,她又后悔,怎么都是别人的话合情合理,自己的事情怎么老要别人做主?难道自己的一生就是在为别人的意愿活着?然而话已经说出口,也不好再更改。她又像多少年前一样,像害心绞痛似的,时时要捂着自己的胸口,像在压着要冒出胸口的心事。
黄大柱也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儿,也许是他的没有风吹日晒的职业,也许他的一身黑皮肤看不出年龄的太大区别,或者男人本身就比女人抗衰老,这个比赵小玫大得多的男人,现在看出去却比赵老太婆年轻,尤其是在喝了酒后的一脸醉颜酡酡,更显出一种生活的滋润来。
的确,他已经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操心的滋润的生活;他有着一份旱涝保收的体面的工作,也有一种不屑任何家庭琐事的优越,在家里,老婆就像学校的勤杂工;家里的事情,口头上说是不会,心底更多是不愿,不屑,他堂堂一个大学生,没能留在大城市,没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同学、同行当老婆,已经倒了八辈子的楣;上班的时候,从没有放松、开心地玩,退休以后,他迷上了镇上茶馆里的那些娱乐,一种叫上大人的纸牌,和新型的名叫“血流”的麻将,他要在这种欢乐刺激的日子里度完自己的夕阳红。
老黄,这日光灯不亮了,你看——
我又不是电工,我怎么知道?!
老黄,没有煤气了,你是不是——
你不知道打个电话,叫送煤气的来换?!
老黄还是那个老黄,腔调还是那个腔调,退休前退休后都还是一个样;他是出门欢喜进门愁;他的脸本身就黑,进了门更黑;吃饭的时候黑着的脸更是愁眉苦脸,一双筷子在碗里挑去拈来,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了就是软了。要说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不再是一分不少地把工资交给老伴儿,上无老了,也无负担了,儿子的工资比他还高,他总是抽一小半儿给老伴儿,剩下的,全送到了茶馆里,他在茶馆里呆的时间比在家都多。后来,他干脆连吃饭也在那里了。
有一回,赵老妇人病了,得了重感。她又烧又咳,头晕脑涨,脚一落地就像会晕倒。她躺了一整天,一整天没吃没喝。黄大柱从茶馆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见这个老太婆咳的声音一阵儿比一阵儿大,黄大柱起床夹起衣裤,一边往门外走,去睡客房,一边不满地埋怨:这还让人睡不睡?!
从来没得过大病的赵老妇人,那回是真的病了,她烧成了严重的肺炎,被回家的儿子发现,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挂吊针的那几天,黄大柱照样天天到茶馆打他的牌。赵老太太躺在病床上,望着那一根塑料管儿滴着的药水,泪水总是不干。儿子跟父亲说了母亲的病,黄大柱的眉头皱得十分难看:她又没得个保险——这个月工资算是打水漂了!
病好以后,赵老太再次提出与黄老头儿分开的想法。这一回,儿子没有阻拦。父亲对母亲的冷漠,让他看见了母亲心底的伤痕。儿子只是问,是住在镇上,还是愿意跟他们进城去住?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赵老太太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喜悦。她收拾着自己的衣服,准备跟儿子到县城去居住。她的眼前,展现着儿子媳妇给她描绘的美好的蓝图:宽广的马路,绿草如茵的花园,彩绸飘飘的休闲又精神饱满的老年秧歌队——儿媳妇动员她也参加县城的老年人的活动,还给她准备了一套花花绿绿的服装,一把太极剑。
收拾好正要出门,突然一阵急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这是黄老师的家吗?
见是和父亲常在一起玩的邻居,儿子忙问道:什么事儿?
快快快——你爸爸黄老师出事了!
长期嗜酒,终于引发了身体的疾病,坐在麻将桌上的黄大柱刚起了一把牌,一把好牌,就要笑,突然嘴一歪,瘫倒在麻将桌上。
小镇也在发展,也像县城一样建起了公园。不过这个新型的小镇公园似乎没有县城的规范,它一头连着集镇那参差不齐的房屋,一头连着还没有开发的农田。不过,那些不同于毫无修剪的花儿草儿的花圃草坪,还有那些打过蜡上过漆的石头,水泥凳,已经够新鲜了,休闲的时候,小镇里的人们也会来好奇地转一转。
在这公园的人群中,人们经常看见一个熟悉的场景,一位老妇人推着一辆轮椅车,轮椅车上坐着一个瘫痪的老头儿,有人认出,那是某中学退休的黄老师和他的老伴儿。今天,大约又是个什么节日吧,经常孤独地推着车的老太婆身边,热闹起来:身边有了一大家子人,儿子,媳妇,还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孙子。公园摆摊的、一个胸口挂着相机、戴瓜皮帽儿的小伙子,看准了这个生意,就热情地走过去,提议照个全家福。
妈,今天是您六十岁的生日,我们就照一个吧!儿媳妇说。
于是,那一家人,就站到了照相师选定的那一丛花草前。在闪光灯闪烁的那一刹那,站在中间,推着瘫痪丈夫的头发雪白的老妇人,脸上说不清是安详还是茫然,是高兴还是忧郁,她的目光,望着前方的田野、那一片尚在开发的荒芜的大地上、盛开的几丛野花。老黄的突然病倒,打乱了她的计划;她将陪伴这轮椅、这轮椅上的人度过一生。
来生,老妇人想,来生一定要自己做主,好好活一回……
茄子!老妇人旁边的小孙子,突然跳了起来。
接着咔嚓一声,闪光灯一闪,定格的又是一个美满家庭。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