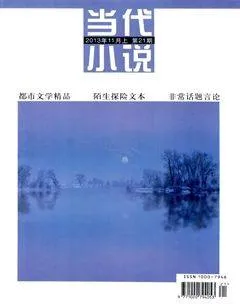蹉跎诗
按照儿子的眼光,我妈妈终生都没有获得讲故事的才能,但她在那些年,又确实讲过多少故事啊。谈起邬村的东家长西家短,她总是如数家珍,可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
我知道她是力图要使我们明白,她早就对这个世界失去了热情,即使在她比现在年轻三十岁的时候。作为她的长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三十五年了,如此说来,她的失望感几乎与我的生命同步。事情显然是这样的。很小的时候我就确信,在整个邬村都找不到像她那样的母亲了。她生我下来就是为了玩儿,那一年她才十九岁。一年后她还为我生了双胞胎弟弟。等我们大了一些的时候,她就一个人跑出去了。如果不是酒鬼父亲活着,我们差不多就成了孤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个父亲,因为他不仅揍我,而且一喝醉了酒就往家里带女人。我知道那些人都不是我的妈妈,但她们不这样认为。她们喜欢揪着我的耳朵让我这样叫她们。年长日久,连我都分不清真假了。父亲无所谓,他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时刻。
我妈妈还在家的那几年,他们常常打架。作为总是胜利的一方,我妈妈要父亲彻底交代他到底有过多少女人。如果父亲妥协,他会数出两三个名字,但等我妈妈去寻找时,那些女人不是刚刚搬走,就是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妈妈为此被吓得大叫。“你再敢说跟死鬼上床,我就让我的六个哥哥把你剁成肉酱。”但结果却是我的妈妈逃走了。
我父亲接连逍遥了六七年,直到我妈妈从外地回来。她像从来没有离开家那样径直走向我们,说:“都在家啊。”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父亲和两个双胞胎弟弟正在院子里劈柴,黝黑的肩膀上流下细密的汗珠。我刚在梨树下撒完尿,一抬头,就见我妈妈穿着几年前离家时的旧衣服站在了院子里。我一眼认出了妈妈。如果我记得不差,那一年她也就是三十四五岁。
大半个村的人都跑过来看稀奇。他们问起我妈妈这些年去了哪里,被我父亲和弟弟们阴沉着脸赶走了。我打定主意不再回家,虽然我也很想听听妈妈的故事。我猜测他们会在当天夜里打一架。可事实是,我想错了。我父亲那天除了喝令我不许出门外,连个屁也没再放。家里静得像坟墓一般。我真想点起一把火把那间柴房烧了。我希望那柴火的烈焰能驱走一切鬼魅。
关于我家里有鬼魅的说法,是我们的邻居告诉我的。他们说起许多年前的旧故事,像亲眼看见的一样。但我对于这些话,从来都是半信半疑。我妈妈曾经警告我要多长点脑子,她说爱撒谎的人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他们可能想吓死我,好趁机侵吞那三分之一的房子。他们窥伺这个大院子已经好久了。这些事,我刚从我娘肚子里掉下来的时候就知道。
我妈妈长得人高马大,别人都说她很漂亮。正因如此,所以有不少人说:“你妈妈在外面享福了。”还有人对我说:“你应该庆幸。”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数九寒天的时候,他们的妈妈都在家里的暖炕上坐着,而我妈妈只身在外。如果不是她离开了我们那么久,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她。
既然无处可去,我只好选择同妈妈呆在一起。我不能肯定她还会不会同以前一样,但有一句话我觉得非说不可。
“妈妈,我觉得他们都撒谎了。撒谎的人心地都是恶的。”
我妈妈伸过手来抚摩我的头。她说:“我的傻孩子,你怎么总也长不大呢?”
妈妈的手变得粗糙了,和我爷爷前几天刚刚砍倒 的老榆树的皮一样糙。
这次回来,妈妈在许多方面都变了。她甚至学会了抽烟。她抽烟的姿势和父亲和爷爷都不一样,但我感觉她比他们都熟练。妈妈抽着烟沉思的样子美极了。我想,怪不得有那么多人赞美她。
听说妈妈回来,我的五个舅舅很快来了一趟,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这次顺带把父亲也收拾了。仗着人多势众,他们甚至想抬起手来教训父亲,被我的两个弟弟拉住了。他们虽然比我小一点,但比我长得壮实。有那么几年,他们简直像奇迹一样地长大了。我父亲一向喜欢他们多一点,因为他们是他能靠得上的人。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太瘦小了。“都是因为我们穷,”在我妈妈离开之前,她常常带着歉疚之心对我回忆,“如果有几斤细粮你就至少能长得跟你弟弟们一样,可我们当时连半斤都拿不出来。妈妈怀着你的时候,吃了好几个月发了馊的玉米面。”说完话,她总是抱着我哭。哭完之后,她又傻呵呵地笑起来。
我不太喜欢妈妈哭泣和傻笑的样子,因为太难看了。她哭的时候和每一个邬村人都一样,把鼻涕和眼泪抹到了衣襟上。每逢这时,我就会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久而久之,她的眼泪就少了。临到她跑走的时候,我都不记得她哭过,或许做这件事的时候,她是背着我的。
我的大舅舅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那几年,我们在村子里是很孤立的。我的双胞胎弟弟就是在那几年里辍了学,还学会了跟人打架。他俩甚至联合起来对付我。或许因为我想念妈妈,而妈妈曾经也喜欢我。人都是有嫉妒之心的。
我读了十一年学,才终于把初中念完了。从小到大,我除了对作文课感兴趣,其他功课都学得一塌糊涂。我的毕业于地区师范的初中老师经常说:“我真不知道你这颗脑袋是怎么长的。”在她的鼓励下,我曾经写下许多奇思怪想。她甚至一度打算把它们推荐到报纸上发表。最后一次,她告诉我这件事就要成功了,可我等啊等,却等来了她终于调走的消息。她教完了我们这届毕业班,就跟着她的男朋友到县城去了。因为这件事,我失落了好些日子。
这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回来好几年了,她和父亲商量,准备供我读高中,如果有可能,再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生。她仍然觉得我太瘦弱了,如果跟弟弟们一样留在村里吃苦,估计连媳妇都娶不到。但我没有听她的话。快开学的前几天,我跑到最小的舅舅家住了下来。因为怕自己不受欢迎,我还给他们家的每个人都买了礼物。我的妗子连连夸我,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我在他们家住到第三天的时候,妈妈来了。她在舅舅家大闹一场,并且扬言从今以后再不来往了。因为是他们耽误了我的前途。而这个责任,即使作为舅舅,他也是承担不起的。
但我不得不让他们失望了。我只上了三天高中,就因为头疼病发作退了学。连老师们都说:“书可以不读,但命不可以不要。”他们早看出我不是块读书的料。
其实我的头疼病是装出来的。但他们都没有发现。在彻底告别校园的那一刻,我高兴坏了,因为我突然感觉,只要动点小脑筋,就可以欺骗全世界。妈妈说骗人者心地都是恶的,但我觉得没什么。我已经十八岁了。
妈妈大哭了一场,接连两天不吃不喝,到第三天一早,她就彻底想开了,在大街上与人乐呵呵地谈天说地。我觉得这才是她的本性,所以我从来没有为她担心过。
我父亲老了,他刚过四十岁,身体就奇特地衰败下去。他夜里长时间地咳嗽,白天下地干活,做不了两个钟头就累得头晕眼花。以前和他有过瓜葛的女人们,见了他就躲着走,更有那心肠恶毒的,还冲他吐唾沫,说他不但身体垮了,连脑子也出毛病了。我父亲憋着一口闷气躲在家里,不到一年时间,头发就全白了。他干脆把头发都剃光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他在镇子上找了一份看大门的活儿,躲得我们远远的。开始的时候我和妈妈去看过两回,后来看他不理不睬,干脆就不去招惹他了。只有两个弟弟三天两头给他送去吃的喝的,甚至给他找了一个中医调理。他在镇子上渐渐安定下来。
我结婚那年,父亲已经在镇子上住到第六个年头。经过我们轮番劝说,他终于辞了工,跟我们回了邬村。
我的两个弟弟先我两年成了家。我们家的院子被拆倒翻修了。作为长子,我住最东头的四间。我结婚以后,又把其中的一间加以改造,作为父母的住所。寂静的夜里,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打闹声了。他们像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母亲的相貌并未老去,但她却变得唠叨起来。我觉得她这样不太好,但她不以为然。她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我娶了媳妇这件事,后来还给她添了孙子。她说这都是她没有想到的。她没有想到的事情其实还多着呢。我难道可以对她吹牛说“这都没有什么,我可以跟弟弟们一样,再给你添两个孙子”吗?老实说,我确实这样想了。
我的妻子是个安静的女人。因为太安静了,有时我简直意识不到她的存在。有时我也想与她吵吵闹闹,使家里多一些生气。但没有一次成功。这次又有许多人奉承我,说:“你真是幸运。”这一回,我倒是懂了。但我没有理会他们。
与弟弟们相比,我的生活很快落败了。他们太能干了,不仅装饰了房子,而且都买了可以拉货的大卡车,出来进去,用上了手机,他们一个是司机,一个学会了建筑房子的手艺,在积累了一些钱后,他们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贷了款,在邬村的南边办了一个货运公司。他们两个,都不愧是父亲的好儿子,在他们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向母亲提议,应该让他们多为家里付出一些,比如把父母住的房子也装饰一下。因为当年经济紧张,这房子只是草草收拾了一下,两三年过去,已经显出破旧了。母亲注视着我的眼睛,像在努力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愿意与她对视,就推说自己生病,回屋去了。
但我的建议迟迟没有消息。妈妈却是隔三差五地过来。她说:“我养了三个儿子,到头来却是哪个都不济事。”我不同意她的说法。我觉得两个弟弟在村里也都算是富翁了。他们开始准备竞选村长。我把这件事也告诉了妈妈。她觉得他们的想法有些疯狂。她早被当村长这件事弄怕了。
她曾经有一个当过村长的爹,但在他退下来之后,那些在他任上被他得罪的人开始寻机报复。其中有一个本家亲属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姥爷下过重罚。他虽然如数上缴了二十块光洋的罚金,但本就贫瘠的家庭因此陷于困顿。这个人一直扬言要杀死姥爷。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始终不肯放手,情势一度一触即发。但姥爷最终没有死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八十八岁那年,躺在自家的暖炕上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他生前已经拥有了九个孙子。临终前,他嘱咐他们:“不许当村长。”
活着的时候他说:“一个人是杀不了另一个人的。”听起来这像是命运之神的口吻。然而杀人的事情年年发生。
我妈妈只有三个儿子,她不容许孩子们去冒这个风险。但冒险的事也是年年发生的。我的弟弟们义无返顾地步上了姥爷的后尘。一个为正,一个为副。他们尽可能地不得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我妈妈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忘记说了,这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表哥已经从村长的位置上全身而退。他既没有完全听从姥爷的遗命,又没有被小小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在卸任之后通过各种手段过活。现在,包括他,我表哥们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他们有时来看我妈妈,给我父亲送来几瓶好酒。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一个个变得越来越成熟。在我结婚那年,我最小的表哥已经移居到城市了。而他的堂兄们,在村子里开始大兴土木,他们各自的住宅占据了村庄的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角落,对整个村庄形成了包围之势。
我妈妈把这些故事讲得七零八落。从这一点上说,她老了和年轻时并没有区别。
她差不多每隔几天会讲到一个新故事,更多的还是交叉和重复。她讲起故事来完全没有次序,逻辑混乱不堪。比如她上个月讲到的某个人在五年前就死了,可到了三年前,这个人又突然复活,并且在邬村的地面上自由出没。当我提示她这一点时,她很恼火地说是我弄错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人。也许真是我听错了。但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一次她甚至矢口说道,她在外面还有一个女儿。
老实说,我对她的信口开河反感极了。每次她讲完故事,我都得用好长时间才能回过神来。最为可恨的是,我知道她的讲述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她所讲的我在外面也常常听到,只不过口吻变了,他们说的是“你们那”,而在我妈妈嘴里,却变成了“你们邬村”。她用确凿无比的语气来证明一个荒唐的真理:活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在成堆的故事面前,每一个人都可信可疑,可真可假。
而在这些故事中,她常常把自己置身事外,只有很少的几次,她无法回避,就用揶揄的语气说道:“都怨你那窝囊的父亲。”我力图使自己忘记那些话。
比如她说我爷爷是老狐狸变的,我奶奶是童养媳。在先前的岁月里,我们家与村里许多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比如她谈起那些令我们头疼的家族风气,似乎男女老少,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异族人的血液。这怎么可信呢?在那些星月高照的夜晚,我可不愿意听这些败坏人胃口的馊事。我常常想,如果我拒绝聆听,她会不会对我怀恨在心?这样的先例已经有了。我的两个弟弟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与她闹翻的。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祖上像一群宵小般充满了卑劣的企图,那意味着他们出身于微贱的血统。事情怎么会是那样?痴妄而无聊地在邬村生活过多年,然后像静止的植物般被埋葬到地里。每到春天,他们的坟墓上都该开满芬芳而纯洁的花儿。
我弟弟刚当上村长以后与妈妈的关系稍有缓和。但我很快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既然没有耐心坐在那里听她说完一个故事,那真正的谅解就无从谈起。有时他们又觉得母亲说得对,为求得某种帮助,他们会转而向我求助,我尽可能使他们满意。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一个长子的职责和自尊,否则,光是对他们的嫉妒就足以让我发了疯。我相信在许多时候,他们都没有我对妈妈的了解更深。
但我并不认为妈妈是个智者,因为她也常有浅薄无知的时刻。
我生活中惟一的难处就是生计。我的孩子在稍稍长大一些后开始对我提出种种要求。我竭尽全力也无法满足他的全部心愿,在生气的时候我就动手揍他。因为这事,静默的顽石也开口说了话,我安静多年的妻子终于学会了与我大吵大闹。而且我发现她有一种难以启齿的古怪心理,她竟然说我与妈妈的谈话比她都多。而这一点,恰恰是她最难以容忍的。我乍听到这话的时候心里一片漆黑。
后来她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听说了我妈妈离家出走的故事。她试着与我挑起这个话头,但被我毫不客气地阻止了。“别听他们的屁话,”我指着她的鼻子骂了几句,后来意识到这样不妥,才把手放下来。尽管这样,她已经受不了了。她把家里刚刚买好的几只碗都扔在地上,摔碎了。我人生中无边的苦役从此开了头,我不只要面临生计的难题,而且还得面对两个女人复杂的心计。这件事使我抓耳挠腮好长一段时日,但事情并无改观。我的一个弟弟来了。他告诉我有一个活儿可以使我脱离苦海。但一听说要离乡背井,我就摇头否决了。他说我是“烂泥糊不上墙”,我举起拳头揍他,但被他一把推开了。
“你不应该动武,”他轻蔑地看了看我,“你在我身上占不到便宜。”说罢扬长而去。
我到妈妈那里哭诉了弟弟对我的轻蔑态度。这是我们兄弟间发生冲突的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他们俩对我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不仅借口盖厨房把我出入的通道堵了半个月,而且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企图放火烧毁我家的柴房。这是邻居的说辞,我尽管不能完全相信,但也深知他们的居心。我很快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惟一能够说得上话的我的父亲对这些最新的变故置若罔闻。他每天喝二两小酒,但仍然装出一副酒鬼的样子,这是最让我痛心的。我趁他清醒的片刻和他谈话,但他用一句“和你妈说去”就把我打发了。我们的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窘境。
我妈妈慢慢地显出了老态。她的容颜终于被打上了时光的烙印。变化最大的是她的肤色,从前她的肌肤白皙,后来却越来越黑。当意识到这种变化之后,她对于人生原有的失望感占了上风。整个邬村的人都注意到她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的话也少了,有时竟然连续一个月都说不了几句话。她曾经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早已随风而逝,至于现在的邬村,又与她说不上有多深的关系。她偶尔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去寻找应该活下去的理由,通过观察侄子们的新生活来映照她自己的。可她终归还是茫然。她终于找到的一个新结论说到底也算不上是什么结论,因为在此之前她也说过类似的感慨生存之无意义之类的话。我觉得那是她精神的源头。
她眼睛里呈现的一切都离她渐远。她还能指望什么?
但她刚刚五十来岁。
有一天我外出散步时捡到了一本故事书,那上面登载的好几篇乡村故事在我看来都很熟悉。一开始我误以为是他们偷听了我妈妈的讲述,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他们写的比我听到的完整多了。我妈妈可没有完整地告诉我那些做坏事的人后来都受到了惩罚,而事实也是如此。现在那些人多半在邬村的地面上活得好好的,有时我迎面碰到一个人,会突然想起他在二十几年前所造的罪孽。比方他曾经将屎罐子里的秽物泼到一个犯了点小错的妇人头上,这妇人因为想不开寻死觅活了好几回,后来终于精神失常了。我妈妈还讲过恶婆婆虐待软弱媳妇的事。起因只是言语不和或者钱财上的一点小冲突,那婆婆便仗着自己有能耐的丈夫撑腰,把媳妇的衣服剥光,拖到众目睽睽之下撕扯她的私处。反过来的事情当然也有。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作恶的人扬眉吐气,被侮辱者忍气吞声。
我读完整本故事书后把它拿到了我从前的小学老师处,这位戴眼镜的退休先生告诉YVvZDhAZu1T623yUFReNkA==我:这是一本杂志。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就为这种杂志写稿。那个学生现在被人称为“作家”。
“作家”这个词我倒是听过,只不过原先觉得离我的生活很远。读完这本杂志,我的想法变了。
我猜测这是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留下来的。在我们邬村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在这里逗留,年代远些的下乡知青不说,光是近几年来,就有一拨一拨的异乡人来到我们邬村。先是因为村里引资办企业,那些邻县、邻省甚至南方人都来了,后来是县上派来支教的老师,再后来是大学生村官,他们在村子里待的时间都不长,但却把我们邬村不少漂亮姑娘的心带走了。我的一个不出五服的堂妹就是前几年跟着一个河南人跑掉的,几年后她回来,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也想写几篇那种杂志上的玩意儿试试。多年以前的学校生活残留在我身体里的那点儿梦想突然又燃烧起来,我很快被这种想法弄得浑身发抖。因为不知道这样做是好是坏,所以我跑到妈妈那里,想跟她仔细商量一下。但我口干舌燥地说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妈妈睁着迷茫的眼睛看我,后来还用手碰了碰我的额头。当她确定我不是在说昏话之后,就用干脆利落的语气打断了我:“别说了。以后我什么故事都不会讲了,你把那些事都忘了吧。”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下午之后,我的脑子里不时地浮现出那些已逝的场景,它们像盘根错节的树根一般,深深地扎进了我的生活。
关于我想当作家这件事,一直是很秘密地进行着。在我与妻子冷战的那些日子,我去镇子上买了两本厚厚的稿纸,然后搜索枯肠地把我所能记起来或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写了母亲相貌的变化,虚构了姥爷年轻时候的壮举,我甚至想象自己就是半导体里那煞有介事的说书人。当我的思维渐渐打开之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一无所有,但沉浸于妄想中的欢乐却足以让我内心富足。我还设计了好几个妄想能够夺人眼球的乱伦故事,有继父与养女的,有公公与儿媳的,在精心修改、誊抄好之后投寄出去,几个月后竟然收到一封杂志社的来信。但拆开信件一看,我就傻眼了,里面只空空地写了几个大字:“大作不忍卒读,建议另投他刊。”卒”字我不认识,查了字典后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后面还有几个被涂抹掉的文字,我辨认了半天,但没有认出来。估计不会是什么好话。
我在这件荒唐事上耗费了好多精力。我妈妈来看我几次,但被我及早发觉,偷偷地把稿纸藏起来了。至于妻子,自打学会了与我吵架,她对这个世界就无所畏惧了。她每天都跑到邻居家去谈天说地,家里脏得像猪圈似的。我和孩子的衣服也好久没有洗过了。每逢我出门去,总是拣人少的地方走。但还是有好多人议论我。他们看我的目光就像看一个疯子。如果我真的疯了,那也不能埋怨别人。是妈妈讲的那些故事把我弄疯了。
她说邬村这个地方,真是藏污纳垢之地,那些年,她就是由于受不了这里污浊的风气才跑出去的。那些说起来让她觉得丢人的事,直到现在都时不时地钻进她的梦境。
真要细说起来,我撰写的那些乡村故事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我坐在院子里仔细地重读了它们。我觉得那个给我退稿的编辑真是瞎了眼睛。
读完之后,我划了一根火柴,把那些故事都销毁了。当烟雾散尽之后,我离开了家。同时被我抛下的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当我走到村口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邬村。金黄色的阳光正四处倾泻,许多人家的屋顶上都晒着丰收后的庄稼。那些正在收拾玉米、大豆和谷子的人们扭过头来看我,我向他们挥手告别,祝愿他们在这里,继续过那种暖融融的、罪恶而快乐的生活。
有几只鸡慢腾腾地走到了乡村公路上,被扫马路的人用一把扫帚赶得到处乱飞。有几只鸟儿正从我的头顶飞过,漂亮的羽毛和温湿的鸟粪同时落在了我眼前的空地上。
我就这样步上了妈妈的老路,四处流浪,不知所终。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