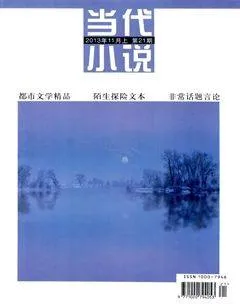奶奶的守望
一
我迷乱的视线里经常出现的是我爷爷。多年以来关于爷爷的形象我只能听凭别人的描摹,或者努力从父辈的相貌中寻找。在我的想象里,爷爷应该是一个英俊剽悍的男人,不像流传在瓦塘南街那些不着边际、捕风捉影的传说。在宁静的深夜,我常常独自地站在窗口,一次次看见他的漂泊,听见路途上的汤汤露水,起落的鸟声和弥漫的烟尘;他腰里的刀闪着寒光,眼角的长寿眉在风中舞动。这个孤独的人,长久以来已经找不到家的方向,像一只鸟儿茫无目的地飞翔。在瓦塘南街的记忆里,他当年的出走是替村里的一个大户去当了壮丁,为我们的家庭换来的是3亩薄地和2石粮食,而代价却是他一生的流浪。
果真如此,这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最亏本的一桩生意。
我常常无意中听到关于爷爷的传说。一个我最不愿相信的版本是爷爷当年的死亡:由于想家心切,当兵一个月后,爷爷趁一个月黑天跑出了山区的营房。爷爷躲过站岗的士兵,没入弯曲的山路,急切地想回到瓦塘南街,见到奶奶和他的三个儿子。可爷爷在大山里走了一夜,第二天太阳从山沟里爬出来时,他看见的竟然是逃出的军营。这也许就是命数,为杀一儆百,爷爷被下令活埋。
我似乎听见叮叮当当的镐声,在山谷里回响。我相信爷爷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幸运的可能,他就这样被埋进了一个山沟或者崎岖的路边。正如许多的影视镜头,在爷爷被推下坑里时,天上飞过了一群乌鸦或者其他饥饿的鸟类,在大山深处发出瘆人的叫声。问题是,爷爷被埋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就为奶奶以后的寻找埋下了艰难的伏笔,使她一生受尽寻找的煎熬。
因为特别好奇爷爷的身世,20岁那年我贿赂了一个叫张大化的老人,同时在看三叔寄来的家史,他单调的文字让我更加迷茫。那个夜晚,我决定去听一个老人的讲述。这个孤寡的老人和我索要了五个烧饼,两瓶廉价的白酒,外加一个花生豆和一个鱼肉罐头。在开始前他又敲敲眼前的破桌,做了个烟瘾上来的动作,我回到小铺又买了两盒纸烟。
你爷爷的出走是为了几石小麦。那几石小麦你爷爷一袋袋扛到了家里,村子里好多人都看到了你爷爷弯曲的身材,从家里出来时你爷爷手里拎着空出来的布袋。站在街头的几个人问,朱老二,还有几布袋才能扛完啊?你爷爷头上的汗扑扑嗒嗒地落到地上,喘着气,说,快了。他不说还有几布袋,只说快了,这就是你爷爷的狡猾,也是咱瓦塘南街说话的习惯。就这样,你爷爷把几石粮食一趟趟都扛到了家。扛到家后你爷爷长叹一口气,心里头开始不高兴了。一个人替人去当壮丁,背井离乡,那不是高兴的事。到处都在打仗,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枪子就把小命送了。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有钱人的命主贵,收钱的人就得撞运气了。你爷爷说,我要走了。你奶奶问你爷爷,粮食吃完你能回来不?你爷爷整理着囤里的粮食,说那可是不好说的事。你奶奶埋怨,你不能回来咱可就亏了。你爷爷说,我是想早一天回到家的,你和孩子们在家等我。你奶奶把三个孩子搂到你爷爷跟前,说,朱老二,你可记住,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临走前,你爷爷在麦田里一坐就是大半夜。到了最后一个夜晚,你爷爷彻夜地坐在地头,快天明时他跪下了,头抵着地,抓着几把黑土,狂喊几声,说,土地爷,我要走了,你好好地护着我们的庄稼,让他们娘儿几个有粮食吃,我会尽量地早点回来。
你奶奶在麦地里搭起了小棚,期待着你爷爷会回到他换来的麦地。那时候温煦的小南风吹得频繁起来,你奶奶守在小棚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你爷爷从麦地出走的情景,你爷爷在麦地里的匍匐叫喊,明年,明年又是一地好麦,好小麦啊。
张大化继续地对我叙述着:后来,你爷爷逃出又被就地惩罚的传闻已经传到了瓦塘南街,只有你奶奶还蒙在鼓里。没有一个人去为你爷爷的死因考证,你们家里的情况可能也不容出现一个去为爷爷考证的人,你爷爷的父亲和母亲已经不在了,你父亲弟兄三个里最大的你大伯才12岁,他和你奶奶肩并肩扛起家中的劳动,和你奶奶盼着你爷爷回来。在你奶奶每天晚上来守小棚后的第三天,你伯从河滩里砍来了一捆树枝,加固了棚子,用铁锹为小棚的脚边培了土,挑了几担水给棚子糊了泥巴,第四天又给小棚钉了一个小门,和你奶奶一样坐在麦地,望着麦田。麦子越长越高了,夜深时他扶你奶奶在小棚里睡,他独自坐在地头,听见地里有很多的声音,地沟里总是哗哗啦啦地响。你大伯一次在地里往远处走,走了十几里。他走迷了,走到了良乡坡,麦地中间晃着明晃晃的几沟水,直到天明,看清了路,才回到瓦塘南街。
麦梢转眼就黄了。这是庄稼人盼望的季节,头顶的太阳一天天毒起来,把麦秆也烤黄了。你爷爷没有回来,瞭望你爷爷的小棚拆了。你奶奶开始爬上你家土楼的楼顶,往远处望。你奶奶在楼顶骂你爷爷,朱老二,你好狠心。至今想起来,那骂声多么酸心。
多少年过去,谁也无法证实爷爷的死因和真实去处,对张大化的讲述我半信半疑。它能给我提供的或许仅仅是一个小说的注脚。
二
张大化在一个丘坡上刨树根。他挖了一个很大的榆树根,我走过去,帮他把最后一个大根拔出来,装到路边的架子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有了一辆架子车,但他的腰里还习惯地别着一条粗麻的绳子。回到丘坡,他燃了纸烟,抬起头,往前头指指,说,你家的麦地过去就在这儿。我想让他和我走过去,他不动,就坐在丘坡上,手不时地往丘坡下指。他说这地分了几次,私人的汇成了集体,集体的又分给了私人,还要隔几年重分一次。换了多少多少茬人家了,我们没事的时候还想多来看它几眼。你奶奶就别说了,她还在想你爷回来,想着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坐在地头,胡子拉碴的,头发和胡子全白完了,在自家的地里哭;要不一睁眼,眼前站一个弓腰眼花的老头儿。
你奶奶的心天天就这样操着,你奶奶天天站在土楼上,村里人都知道,还有她手里举着的那个铃铛。你家的麦场在地的东北角,离路近,扬场是个技术活儿,要说我对你们家有功,我每年都给你家扬场;秋天帮你们家犁地耩地。那一年麦子生了灾,你家麦子出得稀,你奶奶气汹汹地来找我的后账。我说,老嫂子,你没给我恁些种子,它们怎么会长出那些芽儿啊。再说扬场吧,小子,别小看它简单,不是谁都是好手艺。我们乡下人没什么主贵的东西,最主贵的就是人帮人,就是对自己的手艺不吝啬,乡下人的手艺都是和小时光紧连的,比如锔锅,锔盆,钉簸箕、拴杈、编席子。我这扬场不是什么手艺,庄稼人都会,可又说回来,有扬好的,有扬差的,那秕糠出来的程度不一样,同样的麦子扬出来干净的程度不一样。你奶奶老夸我扬得净,扬得快;我扬,她用一把扫帚扫糠。你奶奶和我配合得挺顺当的,用你们年轻的话叫什么默契。不是我干得好,是你奶奶一夸我,我更有力气干,我一个老光棍,一个独身女人夸,你想心里是啥滋味,高兴呗。我对你奶奶说,我一个光棍老男,你不怕说闲话啊?你奶奶说,说呗,没事不怕鬼叫门,你自己说你和我有过啥?我干笑笑,还真没有。我说,你一个老婆子太不容易,我帮就帮了,反正我一个大老爷儿们不怕谁捣我的脊梁骨。你奶奶说,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死是活,要是还能活着回来就好了。我说,这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啊。
小子,我对你家是有功的,吃你几个烧饼,喝两瓶白酒不亏吧!
不亏,不亏。
其实,我和你奶奶吧,还真算心有灵犀。你奶奶对我还真有过许诺。你奶奶搭棚住在野地里,不安全,我对她操心,那时候我常常就坐在这土岗上。有一天半夜,那是秋后,又一茬麦子长出来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都是小麦,你奶奶从村口走到了这土岗下,望着你家的小麦地,像一根树桩,迎着风,可怜。夜深了,我从土岗上下来,我说,回家吧,别再傻等了,小心谁把你的孩子从家里抢走。你奶奶摇摇头,木呆呆地对我说,老化,我要再去山里找他爹,找老朱,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不敢说你爷爷已经被埋了,人活在念想里还会有一点盼头。我劝你奶奶回家,扳着她往村里转身。她说,老化,我要进山,你敢和我去吗?我说,我怎么不敢啊。我就和你奶奶背着你最小的三叔进山了。
你奶奶脚小,上了路背你三叔的事儿就交给我了。那时候我想,背着的要是我儿子多好啊,要是能喊我一声爹就美死了。我开玩笑地和你奶奶这样说,你奶奶一歪头,恼了,说老化你要是不帮我你现在就把孩子放下回去,你要帮就把心放正,让我放心。你是好心人我才选你来的,我不怕别人说闲话,但不能让别人把话头说中了。那一次我和你奶奶在山里找了半个月,我们累了,找一户人家歇歇,找一个山洞钻进去;饿了,我们找点食物吃,我往树上爬,钩树上的半拉柿子、山楂。一直盘绕在大山里,你不知道你奶的喊有多瘆人。
张大化站在丘岗上,开始模仿我奶奶的喊声,孩子他爹,朱老二,我是许桂枝,你老婆,我来山里找你了,我找你好几回了,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回个话,托个梦也行;你死在哪个山洼里了告诉我,让我把你背回去,我好死心了。
你奶奶就那样嘶声地喊,有一天夜里把狼招来了。我和你奶奶坐在山头,看见绿莹莹的眼睛。我挡住你奶奶,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再喊。就是那晚上你奶奶蹴在我身边,说老化你帮我,如果真找到了他的尸体,确认他死了,我嫁给你。我知道你爷死了,可是不敢说,得把心里话压着,你可以对别人说,但不能对主人说。比如,我现在可以坦诚地对你说,说你爷爷的死因,你爷爷的故事,但不能对你奶奶说,也因为不能对你奶奶说,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帮你奶奶。扬场的事不算事,那是明明白白的,村里人来帮你奶奶扬场的不是我一个爷儿们,张守桐,村里最好的扬场手都来帮你奶奶。
我在张大化的叙述里看见奶奶蹒跚在崎岖的山路,张大化在奶奶的后头挑着担子,肩上扛着我三叔。也许该让三叔来论证张大化的叙述,他那一年大概三到五岁,不知道是否会有记忆。一天晚上,我拨通三叔的电话,我支吾着,终于说出张大化的名字。三叔沉默着,在我又重复一遍张大化的名字后,三叔说,你想说什么。我又支吾着终于说出了我的疑问,三叔在支吾后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还听张大化的叙述吗?
张大化说我可以画出你奶奶的行踪图,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女人的老化和失望。他把一个人的老去说成老化。那年头你奶奶找了很多地方,去过很多部队上找你爷爷,有一次我和你奶奶去一个部队上问,他们把我留下来,我在那个连队里干了半年多才跑回来。
是在哪里?
南阳!
南阳?
我和你奶奶从牧城的大山里出来往南走,不知不觉走到新密,去过新县,最后走到了南阳。我们看到了那支国民党军,山岗上挂着青天白日旗。你奶奶要去问,我说我去。我在去时心里头乱哄哄的,我折回头,对你奶奶说,你先坐一个地方等我,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不要找我,你就自己想法摸回去吧。我摸摸兜里,反正也没有钱,你自己一路走一路问回去。
我真的被抓在了那里,他们那个连队的伙夫前两天跑了,看我的样子可能像个伙夫,说,你,你就不要走了。我想跟他们解释,看那阵势没有说理的份儿,你不敢强走,强走,一个枪子就把你崩了。我又求他们,我说我和大嫂出来找人的,你们告诉我知不知一个叫朱老二的人,你们告诉我,我就留下。他们一个个都摇头,都没有听说过什么猪。我真是自投罗网,没得到消息,反而人也留下了。我又求他们,求他们给我一些路费给我的大嫂。终于说动了连长给我两块大洋,我被两个人押着跑回去,已经不见了你奶奶。
我着急从部队跑出来是不放心你奶奶,那个时候要像现在联系这么方便我可能会得到消息。我找机会跑出来,看到你奶奶,我一颗心才掉到肚里。那已经是半年之后。
随着和张大化的接触,我逐渐走进了他的内心,这个老人,如果不是我的奶奶,也许不至于这样孤独,张大化说,你奶奶把自己害苦了,如果不是等你爷爷她可以去城里生活。
他没有说可以嫁给他。
大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对爷爷的行踪充满了幻想……他在15岁那年,步上爷爷的后尘踏上流浪的旅途,按照奶奶曾经的讲述去寻找我爷爷行踪。他后来也成了一个壮丁,战争中几次被俘,最后在共产党的军队干到全国解放。他落脚的地方是大城市西都,当他回到瓦塘南街时已满头白霜。
我三叔一直上学,上到当时的县一中,从县一中考上绥化的工业学校,后来成为电气化的工程师。说我奶奶可以过上城市的生活,是大伯和三叔几次回家接我奶奶,奶奶都不肯到城里去,不愿意离开土楼、中断楼上的遥望,还满怀期待地等待一个人会有一天归来。
张大化说到了我的疑惑,父亲弟兄三个究竟是怎样拉扯大的,穷人的孩子好养,但总要吃饭。张大化说,好几宗买卖我都跟你奶奶出去,跟着她去彰德、开封、甚至邯郸。见我的人以为我已经是你爷爷了。你奶奶先是卖面,借了钱买了小麦,磨成面到彰德去卖。每一次我挑着面把你奶奶送到几里外的塔岗火车站,看你奶奶上了火车我才回头。后来你奶奶从彰德带回来棉花到县城卖,卖棉花不赚钱又卖布匹,用在彰德卖面的钱换成布回来,算着你奶奶回来的时间我去车站等她。可是你奶奶被人骗了,那时候布匹紧张,彰德的布匹不让往外带。一次你奶奶买好了布匹,遇到了一个三轮车夫,三轮车夫说他警察局有人,可以帮着带到城外。你奶奶就把布匹给了三轮车夫,然后按照约定的地点去城外等三轮车夫,却一直没有等到。你奶奶知道被人骗了,坐在地上哭,可哭有什么用呢?从此,你奶奶不再去那个伤心之地。
张大化说,太累了,喝酒。
我陪着他喝,想再一次在酒中挑起他的兴趣。可我失算了,他真是老了,不胜酒力,喝着喝着,呼呼地睡着了。
三
那一年,我一次次搀着母亲走向村外的豆地。我听到风在大地的流动,豆荚在阳光中蜷缩,豆叶刷拉刷拉地响。如果你蹲在豆棵间你会看见几乎在同一个间距的豆叶带动着豆枝齐刷刷地摆动,像一溜挥动的小手,豆棵间偶尔有掉下的黄豆,落在地里的干叶上,金灿灿像一粒落地的玛瑙。
母亲的孱弱让我心疼。我搀着母亲,不知道母亲能不能再看到明年的秋景。我和母亲坐在一处高埂上,整个秋景里更多的是一人多高的玉米,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之后,秋收后的大地又将坦坦荡荡,那时候又一个季节又会从大地上开始。就是在母亲艰难地一次次走近大豆地的那个季节,母亲告诉我奶奶收藏大豆的秘密,她交待我每年给奶奶留足大豆,她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了。事实上,母亲离开人世后,我奶奶又活了10年。
我终于看见了那些大豆,在一个黎明,我像一只老鼠,通过土楼的一个小门潜入了奶奶的二楼。我看见了陶罐和陶罐里的大豆:那些大豆,分别装在几十个缝制的荷包里,荷包上模糊地绣着年份,比如1942、1943、1944……1949……1994……1996……那天凌晨,我钻到了奶奶的楼上,搬掉陶罐上的石板我摸到了那些荷包。我感谢母亲临终前告诉我奶奶的这个秘密。我掏出最早的荷包,试图闻出发霉的气息,我很失望,我闻到的仍然是大豆正常的气味,带着微苦的馨香,特别干燥,陶罐里掉落的一粒大豆裂出很多细小的皱纹。借着熹微的晨光,我看到楼上除了陶罐,角落里有一个老柜和几件用旧的工具,上下楼门都锁得很紧。我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些大豆,眼前是一个老人用一粒粒大豆打发的光阴。
因为爷爷,奶奶一生有很多次的坐立不安,在预感她盼望的日子即将来临时她朝着墙头开始端详爷爷的照片,等待着照片上的人来到眼前,这个一走不回头的男人让奶奶一生受尽了煎熬。接着她开始打扫房子,安排床铺,在她的枕头旁又放一个枕头,多准备出一个人的食物,在夜色里焚香。她在预感非常强烈的时候爬上楼顶,向远方眺望,晃在手里的是一个又新绣的荷包。
我似乎看见爷爷曾经走回过瓦塘南街,一个黄昏,非常消瘦的爷爷像一个鬼魂回到了瓦塘南街。事实上爷爷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奶奶无数次把枕头拿出来又重新放回。在我发现陶罐的秘密后,开始同情一个老人的痴情。在她后来病重时,我每天都给她递过去几粒黄豆;阳光穿过天窗又穿过黄豆,她艰难地凝视,打颤的手使劲地捏着一粒大豆,手暖过后再搁进身边的小罐。每天十粒,在除夕的夜晚正好又绣好了一个荷包,把积攒下来的大豆从身边的小罐装进荷包。
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奶奶晒豆的情景,尤其在她攒积了越来越多的大豆之后,我想象楼顶上的那一层金黄一定汪汪地晃眼,像金色的玛瑙,滚圆金黄。一个老人在她70岁、80岁以至90岁左右晒黄豆的过程称之为工程毫不过分。奶奶从屋里上楼梯是12阶,从楼上上到楼顶是1Nyz3y4zOfZJCgoPiSJZwnj5Ov+tbTlaPAM+EDab7drY=3阶。奶奶要像走独木桥一样走过25阶的楼梯,她最后几年,每次把黄豆弄到楼顶都是一次艰难的长征。奶奶从来没有相信爷爷已经死亡,90岁还抱定爷爷一定会回到瓦塘南街的念想。
每年第一次晾晒大豆是在暮春,太阳最为明媚的季节,天气暖而少风雨,楼上的阳光无遮无拦。奶奶爬上楼顶首先要完成她每天一次的遥望,大多的时候她面向村西,目光里是村外的沧河和沧河桥。河水轻轻流淌,像已经流逝几十年的光阴,每一次遥望她都会有一种心疼,仿佛看见在河边饮水的牛羊,还有跳跃在河边卵石上的小鸟,从石缝里挤出的青草或者野蒿。那个叫朱老二的人那一年涉过沧河就再也没有回来。奶奶的目光透过树梢看见一条漫长的铁路,她无数次经过、无数次跨过、无数次失望的京广铁路,铁路如果是一个巨大的等号,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一个零。零,多么让人心疼。在铁路边有一个小站,十几年二十年前已经被闲置不用的塔岗车站现在已经是荒草丛生。她无数次地站在铁轨旁,无数次地被列车员拉出来,告诉她路过的列车已经过完。夜幕降临,她还固执地守着小站,像一棵路边的孤树。她不说话,她已经修炼得没有了说的欲望。我们家人和奶奶的交流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很少,奶奶和我们说话只用行动或者凝滞的目光。我看过奶奶的照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奶奶一表人材,是我们乡村的美女,她一米七五的身材在乡村属稀有动物。红颜薄命,几十年留给奶奶的只是无情和漫长的等待,是一个女人的守寡。
奶奶手握笤帚,细心地打扫房顶,黄豆是一种滚圆而又细小的颗粒,她不容许房顶上有任何能掺进豆粒的东西,她扫得很细,包括鸽子和麻雀之类的鸟粪,而后是繁琐的搬运,奶奶按顺序打开陶罐,把荷包分类搬上房顶,在打开每一个荷包时她先把鼻子闻上去,她很欣慰没有闻到异味。下一个步骤是把荷包里的豆粒轻轻地放在楼顶,这样的过程奶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她把荷包依次摆好,再用带到楼顶的铅笔画好白线,然后一个一个地打开,再一粒粒数荷包里的大豆。按我后来的了解,前10年,前15年奶奶每天只数一粒大豆放在身边一个小如酒壶的陶器里,这样一年下来是365粒大豆。每年的除夕,奶奶在上完除夕夜的整炷香时,虔诚地拿出已经绣完的最后一个荷包,她在往荷包里放的过程还有一个数数的过程,一粒粒捏得很细。她在数够365粒后把豆粒缝进这一年的荷包,荷包上缝着19××年,如果有任何疑问奶奶会不厌其烦地再数。这是一个细心又漫长的过程,漫长如逝去的光阴,几十年奶奶就是这样过来的。而在15年或者最多20年之后,这可能是1960年,或1970年,奶奶每天开始数10粒大豆放进身边的陶器,这样一年下来就是365天×每天10粒黄豆,一个荷包已经装不下去。荷包就是从这一年变大也增加了数量。奶奶在楼顶晒黄豆是一个漫长又细心的过程,在一包包打开时,她要验证那些荷包里的黄豆是否够数,摊开几十包黄豆时已经是日上正午,阳光更烈更强地照在楼上,那些黄豆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晃着奶奶的一双老眼。她戴着花镜守在楼顶,恹恹欲睡,整个一天她不会下楼,鸽子和麻雀从楼顶掠过,看见黄豆有尝尝的欲望都被奶奶谢绝。太阳差不多要开始滑下树尖,爬下了几级树枝,奶奶又开始卸黄豆的过程,比晾开还细。奶奶捏着荷包,又数着一粒粒黄豆,再把一个个荷包缝好。直到把几十个荷包装好,太阳留下的只是细微的余光,荷包全装进了陶罐,剩下的是最后一抹夕阳。
这样的晾晒每年还有一次,通常是在暑期之后。
有一件事让母亲甚觉惭愧,她竟然走在奶奶的前头。那年秋天,我一次次推着母亲往地里走,我们看见了大片的豆,我推着母亲,看见大豆从麦茬间长出来,又长成了秋天的大豆,大豆枝枝杈杈像一片树林。母亲暴满青筋的手握住车厢,细黄的头发在阳光中疲倦颤动,她使出所有的力气凝视,看见鸟儿翅膀一样的叶子,豆荚在天空下又一次镀金。我听见母亲说,站住!大地的坦荡让我激动,我没有听见母亲的战栗,不懂得母亲的灵魂正沿着一种她激动的方向开始逃逸。我仰起头,天蓝得水洗过样干净。每一次我都把母亲从车上扶起来,让她尽量接近豆的地方,她亲手种下的大豆正在那片土地里热切地等她。母亲的脚步开始轻盈而又虚弱,只有仔细谛听才能听见她的脚步和土地的触点,像蜻蜓点水。在母亲走过草地时发出噗噗的响声,大豆在阳光下蓬勃生长。这是农历的七月,是七月阳光的下午。在每天的下午,黄昏来临之前我都和母亲逗留在豆地旁,我们倾听着大豆的成长,阳光白银一样的光箭穿过稠密的豆棵,在豆地投下无数的碎影。我们每一次穿过瓦塘南街,然后穿过一条青纱筑成的长廊。这是母亲种植的最后一季大豆,这一年的大豆长得格外稠密,一派丰收景象。在小麦生长快要接近成熟的日子,母亲亲手把大豆点到了小麦的垄间,最后一垄即将点完时是一场密集的夏雨,母亲低着打湿的头颅,衣裳贴到了她瘦弱的身上。她勉强点完最后一粒大豆,她身体虚弱地扶住锹把,终于滑落在潮湿的草地。母亲不知道她种下的大豆她能不能收割,好像有一种预感,这是我们家历史上面积最大也是她最后点下的豆。一天黄昏前,我们看见了提前来到豆地的奶奶,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握着几枝还发青的大豆,她苍白的头发被阳光晒成一头雪白。奶奶像往常一样不说话,她远远地看着我们,在走过母亲身旁时她停下来,她终于讲了最多的话:你不该这样,你要活下去,你说好要和我做伴的。然后她飘过我们身旁。我听见母亲扭过头,母亲说,我会留下足够你用的大豆。
这就是母亲每年都要种豆的原因,是母亲那年为什么种下了比往年要多得多的大豆。母亲说,其实我是你奶奶的女儿。母亲说她最初认了奶奶干娘,母亲和奶奶算是萍水相逢,患难与共。母亲见到奶奶那年8岁,那年奶奶走在寻找爷爷的路上。母亲是在逃饭的路上和大舅大姨走散的,在一个凌晨奶奶从一个草垛里钻出来时看见双手露在外边的母亲,母亲的头发杂乱得干草一样,睡在草垛里的样子让人可怜。母亲就这样跟上了奶奶,拉着小脚的奶奶走在深山的角落,后来的一天黄昏,奶奶在一个破庙里让母亲行了跪拜的仪式,庄重地拉起母亲,说,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了,我来养你,你听我的话。母亲跟着奶奶继续走在大山里。奶奶在山崖上喊爷爷的名字,她让母亲喊爹,母亲摇头,说我爹和娘都不在了。母亲说你忘了你认了我做娘了吗?你喊干爹。母亲的喊声从此回荡在山里,那铜铃声招来了狼,狼看母亲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转身走了。这都是母亲在最后一次走向豆地时对我的叙述。母亲说在此后的几年,又跟着奶奶去过很多地方,总是失望而归。其实你爷爷可能早已经死了,你奶奶却不甘心。母亲说你奶奶在我20岁时让我嫁给了你爹,我越来越看出了你奶奶的心计,她在路上哪里是拾女儿,她是拾了个媳妇。后来我和你大舅大姨又见面了,他们也都去了另一个地方。你大姨你没见过,解放前已经不在了,你大舅在20年后才回到老塘。
母亲的叙述停下来,夜幕降临,我把她扶到床上。母亲的叙述还意犹未尽,她说到了村里的三个男人,张大化之外的三个男人。说他们也都对奶奶抱有幻想,称奶奶疯婆子,说奶奶的心比石头还硬。奶奶一次次抛开他们的目光,根本不理他们,最和他们接近的一次是奶奶声嘶力竭地大喊,我男人还在!
你男人早沤成渣了。
其中一个男人说。
奶奶首先淘汰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为自己说过的话后悔不迭。他跪在奶奶的楼下,请奶奶原谅,说我说错了,你男人还在,可能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把瓦塘南街忘了,他不是故意的,但失去了记忆,甘心情愿在另一个地方做别人的爹和别人的爷爷。所以你不要等了。
奶奶说,你胡说八道,他在什么地方做别人的爹做别人的爷爷?你把他找来,或者你带我过去,让我见证是真的他回不来了,他真的还在,甘心情愿地做别人的爹和做别人的爷,我可以跟你。
奶奶当然没有等到找到爷爷做别人爹做别人爷爷的地方,那个男人找不到爷爷,他理所当然做不了我的后爷。
我完全可以想象奶奶的这种传闻,像奶奶的人高马大在瓦塘南街不可能不招人产生欲望,即使奶奶真的再嫁我们也完全理解。奶奶不断地去塔岗车站,就是我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如今已经荒草丛生的地方。那个车站一次又一次出现过奶奶孤立的身影,她像一棵开在一片孤地上的野蒿,然后她总要走过沧河桥,有时候要涉水而过。瓦塘南街的第二个男人总是适时地出现在沧河桥上,漫过石桥的是哗哗的流水。一个雨天,那个男人弯下腰把高大的奶奶背过了河岸,对奶奶说,也许你找的人有一天也会涉过河流回来。又一个黄昏,这个人去了塔岗车站,告诉坐在铁轨旁的奶奶,时光不早了,该回了,在小站停的车已经过完。他把奶奶扶上一辆驴车,不断地拍打驴的屁股,一路上不说话,只是隔几日会来车站接一次奶奶。有一天奶奶长叹一口气,说,得不到他的消息我无法嫁你。那个人最终走在奶奶的前头:他在又一次赶驴车等在塔岗车站时,坐在一截生锈的道轨旁,先是打着呼噜,后来呼噜消失,奶奶摸他的下巴时,他嘴上的胡子已经冰凉。
奶奶说,又一个人被我等死了。
母亲说,曾经有几年,一个男人不断地往我们家送来粮食,帮父亲修补我们家的房顶,赶着牲口过来和父亲一起耙地,有时候躺在我家的牲口棚里过夜。他每年不声不响地坐在奶奶的身旁抽烟,奶奶的脸前飘满了烟气。这个男人有一年让奶奶坐上车去外边走了八天八夜,到处去查找爷爷的下落;让奶奶挂念的这个男人还在车上搁了一桶浆糊,带了一沓写好的寻人启事,八天时间他把启事贴遍了所有走过的地方。奶奶始终不声不响,奶奶每天晚上都把一粒大豆放进身边的罐里,豆粒掉进罐中当啷一声。传说这个人曾经死死地抱紧奶奶,猪一般嚎哭,求奶奶不再折磨他的等待。奶奶倚着一棵树,说,我死不见尸,活不见人,你怎么让我嫁你。这个男人疯狂地赶着车,几次要把奶奶从车上颠下,男人不坐车,在驴屁股后疯狂地奔跑,大把地流泪,几年后这个人忧郁而死。
奶奶还是那句老话,又一个男人让我等死了。
那一年,我们家的大豆给母亲做了葬礼。
母亲殡葬的那天,奶奶选择了又一次晾晒大豆。在楼顶上她说,我的又一个亲人走了!她面向遥远,念念有词,他爹,这一次你又熬走了一个,因为你村里已经走了三个男人,我都打消了他们的念头,这一次我们的干女儿,也是我们的儿媳走了。你如果再不回来,我可能等不及了。奶奶不知道她自己又活了10年还多,这10年里,她又熬走了村里几十个和她同龄的老人。
这一天,奶奶及早把大豆搬到楼顶,秋天的日光很亮地照着大豆,豆在楼顶倾听另一个院子传来的哭声和哭声间隙的唢呐,小麻雀掠过楼顶又掠过母亲的葬礼。我在悲痛之余朝向奶奶的楼顶,奶奶眼前是白色的挽幛,接下来在唢呐疯吹的午后会旋起一片白幡,在瓦塘的上空飘荡。无比悲痛的午后奶奶在楼顶无声地哭泣,她说她最孝顺的女儿——儿媳走了。后来她俯下身手摸着楼上的豆,几十个荷包分别压在楼顶的几个角落,奶奶抓着哗哗的豆,悲伤地诉说,这么多个日子,我的老头他还不回来,他真没良心,真要让我失望啊。后来奶奶数着数儿低头装她的大豆。我在葬完母亲后,在回来的路上想着母亲的嘱咐,她说,孩子,你一定要多留些大豆,每年都要把你奶奶外边的那个陶罐装满,那是你奶奶的寄托,让她数着豆多往前走走。
在离开家乡的第三年,有一天我忽然特别想见到家乡的大豆,我的眼前铺展起辽阔的豆地。我一次次想起我推着母亲去豆地的情景,奶奶艰难地去楼顶晒她的大豆。我疯狂地去了乌市的粮食市场,买回几斤大豆,回到住的地方我开始一粒粒数豆,数的结果是我又去街上买来一个陶罐,把豆子往陶罐里放,放着放着我哭了,我把脸埋在陶罐里哭,哭声非常豪放。我回了瓦塘南街,去看了奶奶,她雪白的头发更加雪白,想找到一丝黑发很难很难。我抓过她的手,她的手里正抓着几粒豆,她从床头摸出一个荷包,上边写着我的名字,她说,这是你的,你数一数你离开家有多少日子。
奶奶死于母亲离开人世的11年后。
奶奶在那个冬天留下了关于处理她大豆的遗言。奶奶说,把这些大豆给我全部陪葬。父亲睁大惊奇的眼睛,装满陶罐的大豆和几十个荷包亮在父亲眼前。奶奶说,有什么不舍,这是经过我的手温几十年保存下来,为什么不让它们跟我?父亲没有争辩,父亲从来不喜欢争辩,父亲已经计划好了,等奶奶真的命归黄土,刨一个大坑,或者再做一个匣子,装上几十包大豆,甚至父亲想象着那些大豆经过地下的水气,蓬勃而出,奶奶的墓地将会有一场壮观,几万粒大豆开出几十万棵豆苗蓬松成一棵豆树,如果都结出大豆,开出豆花将是瓦塘南街史无前例的风景。父亲曾经对周围的人说,看吧,等我老娘老了,会有一次壮观,你们就等着去我娘的墓地看吧!父亲甚至在一天午后坐在河堤上遥望我家祖坟,努力想象奶奶死后即将出现的一幕将是多么夺眼,绽放的豆花会多么绚烂。可是奶奶改变了计划,她在大限真的即将来临时告诉父亲,她不要那些黄豆陪伴。然后她掏出一个小包,里边装满鼓鼓囊囊的豆子。她说这是每年另外只有一袋的12粒豆子,一个月一粒,她只要这些陪葬。父亲听完奶奶的吩咐后有些沮丧,埋怨老娘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那年秋天,奶奶平静地走上楼顶。在生命的最后又一次晒了大豆,那些大豆包在荷包里,没来及卸下再装进陶罐。她斜倚在比她还老的楼墙上,再也站不起来,眼朝远方,完成了她平生最后的等待。
第二年夏天,父亲把那些大豆全种进了地里。那一年我在遥远的一个小镇打工。那年秋天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激动地叫喊,小马,你快回来,我们家的大豆好收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大豆,我每天都要坐在地头接待来参观的人,还有一拨拨飞来的喜鹊麻雀。小马,你一定回来,你回来帮我。父亲还在电话里喊,全村的庄稼都收了,我不舍得收咱家的豆,我想让它们长疯……
我紧握手机,听见了父亲的哽咽。父亲说,要是长生不老多好啊!可是,它们都要炸了。小马,你回来看看,它们长得多好。我握着手机,听见了炸豆声,砰砰啪啪,金子一样落地,在太阳下耀眼,整个瓦塘南街眼花缭乱。我握着手机,疯狂地往车站跑,对父亲喊,等我——等我——一定等我……
我在路上狂奔,眼泪豆一样落在小镇的大街。
四
在奶奶的葬礼上我看见了张大化。那几天,叙述的欲望冲撞着他的身体,他欲罢不能,苍白的胡须和杂乱的头发让我看到一个人的寻找和等待的结束。疯狂的唢呐手正满头大汗地调动情绪,吹奏一支哀歌。我们在哀乐中守着奶奶的灵柩长哭不止。
而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潜入了张大化的小屋。几年来,我已习惯了他的讲述。
我把一瓶白酒和从伙房弄来的几个小菜往他的桌上一撂,他夺过酒瓶咕咕嘟嘟一口气喝下了半瓶。他打了个酒嗝,一股浓重的酒气马上弥漫了小屋,他忽然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泪水顺着他粗糙的手指奔泻而出,像挤出山缝的岩浆,肩膀抽搐如一头濒临死亡的老牛。他抽泣着,朱小马,你本来该叫我爷爷,你奶奶许过我的,可她到死也没有让我如愿;她临死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让我去最后看她一眼,再和她说一句话,拉一拉她最后的老手。你们太无情无义了,你奶奶太无情无义,太心硬太霸道了。我跟她走过那么多的地方,还因为她,我当了半年的伙夫,差一点送了小命。如果她嫁给我我就是你的爷爷,你不用一瓶小酒一瓶小酒来逗我的话篓,你奶奶太心冷让我心寒。我该死了,我死了见到她也不会饶她,这个死老婆子,骗了我一辈子。
我在他的哭声中,知道奶奶越来越无法嫁给张大化,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她一直没有得到爷爷的确切消息,一直找不到爷爷的尸骨;她的儿孙们渐渐大了,奶奶她越来越无法嫁人。她只能一次次在心里企望:有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站到她的面前,对她说,孩他娘,这是咱的家吗?可是,没有,她最后留下的只是陶罐里的黄豆。对她有过念头的男人差不多都先她而去,只有张大化还苟延残喘地活着。
张大化说,我该死了。
我抓住他的手,任他沧桑的老手在我的手里一直颤抖。
第二年春天,村外又多了一座新坟,坟头上一个孤零零的花圈。张大化走了,无儿无女走得格外苍凉。那天夜里,我拎了一瓶白酒,在萧瑟的田野里,我一盅盅地倒给张大化。我说,张大化,我叫你一声爷吧。话音未落,一阵小风掠起,围着我旋转着。我在他的坟头一直坐到了天明,晨光中,我看见我拎去的那瓶白酒已经空了。
爷爷的死因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我最后要告诉你们的。我之前说过,三叔是我们家学问最高的人,上世纪50年代,考上绥化工业学校,他听从号召,辗转几个城市,一直当他的热气处理工程师。他文笔很好,除了做他的专业,另一个爱好就是旅游,或者叫做采风,在全国各地行走。三叔那年匆匆地回到瓦塘南街,拿出了一本县志和几张他在某县拍下的一个碑文时,我们才知道三叔所谓的爱好,实际上是他一直在寻找爷爷的下落。在奶奶的墓地,我们听到了三叔关于爷爷最后死因的描述,那段描述就摘自他带回的那本某县的县志:1943年9月,在苍峪山深处,发生了一场国民党军与游击队联合抗击日军的战斗,日军的偷袭是一个本来在逃走途中的壮丁朱老二发现的。最后,一小队的日军被全部消灭,游击队和国民党的一个连都伤亡惨重,朱老二等人在战斗中阵亡……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