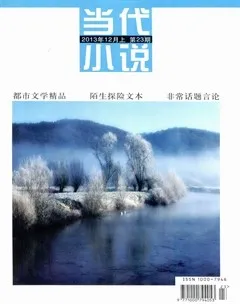你看见我看到的了吗(创作谈)
今年夏天,我和几位朋友沿着山东的海边走了一趟。对于水,对于海,我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欢,只要见到水,就莫名其妙地激动。我完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我的家乡鲁西平原,到处是连成片的田野,田野与水的关系是一种单方关系,能够被浇灌的被称作“水浇地”,旱地则打上机井,拼命用长长的管道与地下深水做着连接。对水喜欢的原因,我推测源自血液记忆,我的某位祖先或许与水有过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记忆至少要遥远到六百年以上,根据家谱记载,我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由北京锦衣卫迁至东阿县后范集,历经久远的时光,记忆仍然能够引起心灵的强烈感应,只能说这种隐秘的关系非同寻常。
第一站在日照,作家蓝强陪我们赶海,大家拍了照片发在微信上。不一会儿,同行的编剧朋友举着手机说,好友来了评论:0d58898b8e1b7c9c0494284e22a36438bb56cade59d4cd055ce79a8763e21b2d这是海吗,怎么看上去像黄河?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很奇怪,照片上的大海确实有点儿像黄河。紧接着,我的微信也有了动静,在澳大利亚度假的刘强老师直接发来一张照片,他说,老弟,看看我拍的大海。他拍的大海那叫一个蓝,那叫一个好看。不过,我并不服气,我并不在乎,因为所有的大海我都喜欢,只要是大海,我都喜欢。
第一次下海,时间是在晚上,真正进入大海之后,我们都很兴奋,孩子们尖叫起来,妻子游过来和我牵手,在海水里我感觉到了她手指轻微的颤动,朋友的孩子竟然和一对陌生父子开起了玩笑,一切都在美妙和幸福中进行。所有人都玩得太嗨了,浴场的灯光灭掉一部分的时候,大家越发贪婪起来,我有些不甘心,游到了远处,仰在水面上,闭上眼睛去体会大海。当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大海看不到头儿黑成一片,所有的灯光和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巨大的海和渺小的我,一种无法逃离的孤独感迅速攫取住了我,无边无际的海水让我彻底无助,绝望的心情比海还要深。当我重新回到沙滩上的时候,涨潮的海浪一层一层地翻滚而来,朋友们集体发出尖叫,我万分沮丧地坐在那里,我知道,一夜之间,关于大海的记忆已经被篡改,亲近大海变得那么一厢情愿,大海的凶险将替代“神秘的亲近”。
一种事物,会有两种或者多种面目,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我曾经发过感慨,有时候,一种事物就是一种事物,好像A就是A,这是事物最为基本的状态,还有的时候,一种事物可能是另外一种事物,A成了B,呈现完全对立的两面。
作为小说来说,虚构的可能,恰恰对应着现实的可能。
《太平》开始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圣安德里亚斯 断层》,小说中,母亲和父亲,周成舟和张映红,张映 红和于勒,六姑和校长,“五四青年”和张小琴,我和 小白,所有的爱情,和小说屡屡提到的冯内古特的爱情 遭遇一样,都隔着一条圣安德里亚斯断层。
其实在《太平》中,“断层”仅仅是一层,是爱的阻隔,是爱的困境,之后,它是孤独、绝望和悲凉,再之后,它是忍耐、慈悲和爱,这是一个从“爱”到“爱” 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此岸到爱的彼岸的故事。
小说当然不是靠数字般的堆砌成立的,最好的小说站在了反面,减少或者抽离反而是通往抽象世界最好的通道。就像叔本华所言,有一个和一个都没有之间,有无穷大的差别。如果说“更多”是“多”的敌人,那么“多”和“少”更是一对冤家。
我信服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主张,毁掉确切性,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在小说《太平》中,看起来是在抽丝剥茧地寻求真相,其实我干得是另一件活儿,一再地靠近模糊、复杂的生活“本相”。
我希望自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看见了你看到 的,你看见我看到的了吗?这话透着骄傲,又透着真诚!
我准备用这种骄傲和真诚对付平庸,不能再焦头烂额地给这个世界作答了,要主动对这个世界发问。很有可能,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平庸,惟一不平庸的是,我拒绝平庸的姿态。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