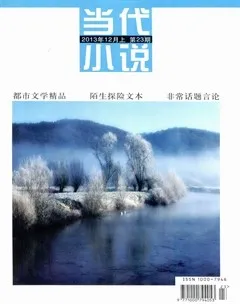陈州店铺
陈州鞋店
民国初年,陈州鞋店设在平湖街北侧,店面不大,老板姓白,叫白金全。开初只卖军装皮件、马缰绳、马鞭、箱包类大型皮件制品。后来才开始兼营皮鞋、皮靴,尤以男士线缝小方头皮鞋受到市场的热捧。小方头皮鞋是仿武汉大方头皮鞋,结合本地的皮鞋的鞋型创新设计的。采用方头夹圆头的角度形成一种扁平而带流线型的皮鞋头式,既没有大方头的笨相,又没有“小圆头”的娇相,别具一格,美观时尚,老、中、青穿着皆适应,很快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打进了开封和西安等大城市。生意好,赚钱就多。赚钱一多,就需要扩大生产。生产一扩大,就需要租赁或筹建厂房,增加人员。不料在这时候,老掌柜白金全患脑溢血身亡,其儿子白一凡年龄尚小,其妻是个小脚女人,眼见鞋店处于瘫痪之状,赶巧白老板的妹妹白冰花从北平回来,接替兄长担起了重任。
白冰花原在开封读书,毕业后嫁给了一位姓曹的军官,随夫进了北平。不想军阀混战,丈夫战死疆场,她只好回到娘家。
白冰花接任鞋店后,并不慌着扩建厂房。而是先抓皮鞋的质量。她说这叫以缩求伸,看似发展慢了,实则是快了。只要质量过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确保质量关,她很重视“做工”,对工人的操作技艺要求很严。规定个人所制成品均要通过其掌作师傅检验以及顾客的鉴定认可方算合格。小方头皮鞋的特点是:片帮薄厚均匀,叠帮棱角整齐,部位对称一致,车帮整洁牢固,采用双并线工艺,钳帮紧贴楦身,沿条宽窄适度,打蜡水线光亮夺目,花纹清晰,线条分明,轮廓清楚美观,包头硬扎平均,支跟坚挺舒适,不但能防潮,且包头部位脚踩也不致踩瘪,所以即使穿破了也不走样。从皮鞋的整体结构上看,前后部位匀称合度,具有外观美,质地牢,经久耐穿之优点。
除去重视做工外,在用料上也十分考究。无论面革、底革一律精选上等的原料。皮革则从汉口牛皮作坊进货,面革质量也不亚于进口的“西纹革”。就包括缝鞋的丝、麻线等材料也从不马虎。为更多地吸引顾客,白冰花还打出广告,可以画样订货,送货上门。由于皮鞋质地精良,服务周到,不但受到国人的喜欢,连外国人也前来订货。
当时社会上女老板极少,白冰花如此出色,很快就成了陈州名流。人这玩艺儿,无论你有权或是有钱,只要达到一定水准,就会引人注目。你有权了有钱人会巴结你,你有钱了有权的人自然就会找到你。就像现在的官员傍大款,旧世道也一个样。白冰花的鞋厂能赚钱,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就引起了官员们的注意。先是让其当了陈州商会副会长,然后又让其当了政府议员,各种重大活动皆请她参加。白冰花见过世面,善于应酬,自然也乐意参与这等活动。女人都有虚荣心,白冰花也不例外。每次出场,她均要精心打扮自己。有一天她一连赶了三个场子,连换了三套装束,成了陈州人的美谈。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白冰花如此招摇,自然会遭到妒嫉和眼红,尤其是陈州其他行业的老板,觉得白冰花抢了他们的风头,就想法生点攻击她。古今中外,攻击女人最好的手段是用桃色事件,于是就有人编排白冰花如何靠脸蛋当上了商会副会长,如何靠大腿之功攀上了某某政府官员,当上了参议员。而恰在这时候,陈州城新来了一位县长。县长姓田,叫田岱,年岁刚过而立,潇洒又倜傥。这田大人在未来陈州之前就听说陈州城里有个漂亮的女老板,可能是心仪已久,所以到任第三天就以拜见商会会长为由,拜访了白冰花。对于田岱的来访,白冰花颇感到意外和吃惊。因为过去与官员们见面,多是在县府或别的什么公开场所,像田县长如此屈尊还是头一次。又见新任父母官年轻潇洒,风度翩翩,白冰花就感到有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兴奋,当天中午特在陈州饭庄订下丰盛的酒席,用以回报县长大人的亲民之举。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接待,不想也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说白冰花真厉害,新县长刚上任就勾搭上了!不想田岱是个新派人物,去欧洲留过学,父亲为他订的婚约他不理茬儿,一心要找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子为伴,所以一直未婚。前天一见白冰花虽年过三十,但仍然朝气蓬勃,穿戴举止毫无陈腐之气,就起了爱慕之心。现在一听有人造谣中伤,非但不恼,反而很高兴。当下派人请来白冰花,问道:“有人在诽谤你我知道不?”白冰花笑道:“白玉无论如何被泼污,但终究仍是一块白玉!”田岱认真地说:“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以假当真你看如何?”白冰花一听年轻的县长如此向自己示爱,颇有些感动,她深情地望了田岱一眼,说道:“你要知道,我可是个寡妇!”田岱说:“什么寡妇不寡妇,在西方,人家从不在乎这个!”白冰花此时已经冷静下来,又望了田岱一眼,问道:“请问你是看中了我的人呢,还是看中了我的钱?请你直言相告!”田岱笑道:“自然是看中了人!若论钱,你钱再多,也比不得我手中的权!你信不信?”白冰花沉思片刻,点头称是后,又说:“我可是比你大几岁!”田岱说:“这个我早已知道了,你比我大三岁。西方称此为姐弟恋,在中国,称为女大三,抱金砖。所以说,这应该是好姻缘!”见年轻的县长把话说到这一步,白冰花甚感欣慰和激动,很真情地说:“真没敢想您能如此看重我!实言讲,鞋厂是我哥哥的,不幸兄长早逝,侄儿年少,我只好牺牲青春帮他们!首先请您原谅,婚后我不会跟你当专职太太。我还想再干几年,等侄儿长大成人,我们再在汴京或郑州开个分厂!”田岱见白冰花答应了婚事,很高兴,说:“有你对你兄长的这片真情,更证明我没看错人!请你放心,无论婚前婚后,一切全由你做主!”
不久,二人成婚。
因为是县长大人和商界名媛的婚礼,办得极其隆重,几乎轰动了整个陈州城。
二人婚后,相亲相爱。田岱当官,白冰花经营鞋店。一个掌权,一个挣钱,虽是夫唱妇不随,倒也相得益彰。田岱为官一任,由于受西方影响,他力革沉疴,锄恶霸,严法纪,办学校,抓教育,颇受陈州人爱戴。不久,由于政绩显著,被提升为副专员,刚上任不久,又被提任为省府教育厅厅长。这时候,白冰花的侄子已经长大成人,白冰花将鞋店交付给侄子后,也随夫君到了省城。他们在省府前街置买了一套宅院。乔迁新居时,田岱显得格外兴奋,对夫人夸耀道:“如此这般顺利,不出几年,我说不定能坐上省长宝座!”白冰花见夫君年轻得志,提醒他说:“别忘了,官场黑暗,尽量往坏处着想,往好处努力才是!”田岱说:“往坏处着想无外乎是下台不当官!可我怕什么,夫人早已替我铺好了后路,在省城办个鞋厂,当大老板就是!”白冰花一听这话,禁不住苦笑了一下,望了望丈夫,好一时才说:“只可惜,我已用办鞋厂的钱为你换成副专员和厅长的乌纱帽了!”
张三水饺
张三水饺是陈州名吃。
张家饺子的特点是:选料优良,制作精细,外形美观,皮薄馅大,鲜香味美,风味独特,脍炙人口。在陈州一带,提起张三饺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达到了以吃过张三饺子为荣的境界。
据传,张家原籍是河北河间房任丘县人,有一年河北遭荒年,张家上辈带着一家老小逃荒来到陈州城东湖边,为了谋生,搭了个窝棚,开始做水饺生意,维持生活。
开初,张家饺子为“元宝形”,包出的饺子个个像小元宝儿,为让食客讨吉利,挂牌就叫“元宝水饺”,生意还算混得下去。到了1870年,张家的独生子张三长大成人,并继承了父业。为维持经营,他想法提高水饺的质量,开始研究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人们的口味特点和饮食的变化规律。初春,他选韭菜做馅,味道鲜美,可是经过反复品尝琢磨,发现酱油和面酱用多了,影响韭菜的鲜味,于是多用食盐调味,韭菜鲜味丝毫不减。冬天,他用白菜制馅,发现馅儿颜色不美,就多放酱油和面酱让馅儿增色。经过反复实践,摸索出最佳配料方案,使张氏饺子总是保持鲜香可口。另外,他还认真研究外地饺子的特点,比如开封的蔡家饺子、哈尔滨的花家饺子、沈阳的老边饺子,发现这些名店多是两种馅儿,一是普通馅,二是炸馅。普通馅是用生肉和馅,加时令的蔬菜和调料。清末年间,陈州周围的饺子店基本全是普通做法,张三决定将炸馅引进中原。一开始,他用油炸馅,结果既不易消化又不出馅。张三对此苦心钻研,终于研究出汤饺馅。汤饺馅就是把肉用油炸之后,再放入骨汤爆煨二十分钟,使收缩的肉馅儿吸水恢复原样,这样既松散易吃,又易于消化,食后没有口渴之感。如此新品种一上市,很快就顾客盈门,名声大震。
生意越做越火,张氏饺子就扩大了门面,而且已由当初的“元宝饺子”发展到二十多个品种,并首开别有风味的“饺子宴”,使人大饱口福,又长见识。烙、煮、炸各种形状的饺子,满满一桌,盘盘饺馅各异,有银耳馅、香菇馅、虾仁馅、鱼肉馅、黄瓜馅、红果馅、山楂馅……最使人惊异的是“御龙锅煮水饺”,一盆蓝色的炭火,烘托着古色古香的御龙锅,一两面包成的二十五个小巧玲珑的元宝饺儿,在汤中上下翻滚,五龙搅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口。
清末光绪年间,袁世凯回项城葬母路过陈州,当地官员特请他吃了一回张三水饺。袁世凯品尝后,挥毫留下八个大字:张三水饺,天下第一。
只可惜,当时袁世凯是在县衙里写的这几个字,而且是回府奔丧,心情不是太好,写了也就写了,并没让人送到张三饺子馆。袁世凯走后,陈州知县望着那八个字,似望到了一堆元宝,决心要赚张三一把。他派人喊来张三,说:“你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应该请名人写幅匾额了!”张三不解其意,说:“我家店门上的匾额不就是请陈州名家段老先生写的吗?”那知县笑道:“段老先生只能在陈州一带算名人,出了陈州谁还知道他?我说的名人应该全国人都晓得!”张三从未想得这么高,瞪大了眼睛问:“那咱能请得动?”知县说:“只要舍得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这样吧,你拿一万块大洋,我请袁世凯袁大人给你写一块!”张三一听让袁世凯写匾,连连摇头说:“那我可请不起!一万大洋,那可得多少碗饺子呀!”言毕,忙起身告辞:“多谢大人为小民操心!”说完,就匆匆回店里忙生意去了。那知县万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大骂张三吝啬,但东西再主贵,人家不要也没办法。
这事儿本来已经算完,袁世凯吃过饺子,觉得饺子好,又是家乡人,即兴题了词。知县想借机敲张三几个钱,可张三对此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大人的题词也就没了什么意义。张三走后,那知县又拿起袁世凯的题词看了看,觉得已没什么用,只好先当做一幅名人书法收藏。他正欲收起拿回暖阁,不料被师爷看到了,问道:“大人,那张三怎么没要袁大人的题词?”知县生气地说:“一个守财奴,不识货!”师爷也姓张,叫张老五,为人聪明绝顶,一听那张三不要袁世凯的题词,很是吃惊,认为这张三真是土鳖,不知袁大人这句题词的含金量,便拿起那幅字,对知县说:“大人,袁大人的这幅字是专指,除去张三,别人收藏没什么意义。这样吧,我给您五百大洋,您将它送给我吧!”知县一听张师爷要买字,很奇怪地问:“你要它干什么?”张师爷笑了笑说:“大人,您别忘了,我也姓张啊!这袁大人是对我们张家的题词,若弃了岂不可惜!再说,我先用五百大洋买到手中,等哪一天那张三迷过来了,说不准还能卖到一千大洋哩!”一听张师爷说这话,知县就感到自己向张三要价太高了,但事已至此,又不便再和一个生意人讨价还价,若那样传到袁大人耳朵里,怎么了得?既然师爷如此巧妙地给自己台阶,赚一个是一个吧!于是,知县就答应了。
张师爷将袁世凯的题词拿回家后,到永昌斋让人制了一块匾额,将那八个大字镶在里面,藏了起来。几个月后,他又在与张三饺子馆对面的地方租了几间房,掏高价从张三水饺馆里聘了两名师傅,也办起了个饭馆,也专卖水饺。开张那天,请来不少陈州名流来捧场,敲锣打鼓放鞭炮,很是热闹。
由于张师爷请来的大师傅是从张三饺子馆里挖出来的,所以凡是张三那边有卖的,这边全有,而且味道相差无几,又加上张师爷在县衙里供职,各个部门都来捧场,请客待客,多在这里。于是,这边的生意就很快兴盛起来。一看时机成熟,张师爷便将袁世凯的题词挂了出来:张三水饺,天下第一。随即也将水饺馆命名为“张三水饺馆”。众人一看两边都是“张三水饺”,这方却有袁大人的题词,不知情者皆以为这方为正宗。尤其是外地人,更是信匾不信人。这样,很快就把那真张三盖了下去。
真张三自然很不满意,认为张师爷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将张师爷告到了县衙。那知县也没想到张师爷会有这一手,而且自己正想找真张三出恶气,是张师爷的这一手逼他自己找上了门。知县很佩服地望了望张师爷,对真张三说:“你姓张,人家也姓张。兴你叫张三,就不兴人家叫张老五?”张三说:“大人,如果他叫张五水饺馆,我没的说。为什么也专叫张三,而且在我生意兴隆之后?”张师爷笑道:“这店开初是我开的,后来让给了我家三哥。我叫张五,我三哥不叫张三叫什么?你说你叫张三之前,更是谬理,我比你还大一岁,我家三哥岁数更比你大,怎么会在你之后呢?”张三有理却被辩得没理,反被判作诬告,不多不少,知县一下罚了三万大洋,一家伙就让张三大伤了元气。
看斗不过假张三,真张三只好离开陈州,回河北老家去了。
真张三走后,假张三的生意更为红火。张师爷看时机成熟,就辞去了师爷的职务,专干起老板来了。
因为张师爷也不是笨人,当上老板后更加注意饭店的质量和管理,生意越做越大,最后连周口、汴京都开了连锁店。
这事除去张三外,最后悔的是那个知县。他看到张师爷的生意蒸蒸日上,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当初没看到这一步,只顾借权力想法生点捞别人的钱,却忘了自己去挣钱。
再后来,张老五财大气粗,不但自己当上了陈州商会会长,也为两个儿子买下了前程。大儿子进了省府,小儿子进了专署。每逢过年过节,地方官员都来拜望张师爷。那时候知县早已作为前清遗老遣回了原籍,据说很是穷困潦倒。好在张师爷不忘旧情,早晚还救济他一些。
郭家药号
郭家药号的老板叫郭心增,又名郭鸿义,出身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郭老板9岁时被其父送进私塾读书,跟着老师学《三字经》,老师不讲含义,只念句子,让他反复朗读。由于聪明,他很快就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受到老师赞扬,就教他全文含义,不久,他便心领神会。此后老师专给他开小灶,教他《千字文》《名贤集》《劝学》《忠言》等。接下来又让他攻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郭心增参加了科举考试,被录取为附生。光绪三十年,他赴开封赶考,被录取为禀生。在清末年间,禀生为秀才中的最高等级,每月可以从官府领取禀生膳米若干作为生活费。考取禀生后,他还参加过开封咨议局的竞选,获得成功,被授予官服。官服式样为蓝色长袍,咖啡色马褂,圆形黑圈的红缨帽,帽顶上装配有铜质葫芦型饰物。郭心增在任职期间,为官清廉,常为百姓着想,得罪了一些权贵。见清政府官场腐败,他毅然辞职。辞职后本想潜心苦读力争考举人当大一点儿的官惩治腐败,不想科举制度被废除。他只好作罢,便回到陈州,开了一家药号,走上了经商之道。
郭家药号,专经营白芍、菊花和蒲黄。陈州有万亩城湖,盛产蒲黄,每到蒲黄下来时节,郭家就张贴告示广收。要求纯、净、干,不达标决不收购。收白芍时,更讲究,必须个匀、粉足、条净、光泽好,加工时要两头见刀,不留一个虫口黑疤,装包分伏贡、方贡、伏顶、天奎、天斗、尾勺片、剁头片七个等级。对菊花也同样严格,采来后,无论数量多大,皆不惜花钱雇年轻的姑娘一朵一朵地挑拣。初拣出的菊花,再分拣成小箱菊花王、箱菊花两个档次,剩下的统称包菊,算等外品,以筒席另装成件,送往禹州、安国或亳州药材大市场。郭家的蒲黄、白芍和菊花的另一个特点是包顶包底一个样,绝无质量不一的现象。由于郭家药号的信誉好,所以生意很兴隆。
郭家药号在南湖街街口处,建筑是仿杭州胡庆余堂的式样,整个形状宛如一只仙鹤栖居在南湖岸边。店铺分两进,一进为厅堂,宽敞明亮,也是营业大厅,二进是帐房间。营业厅内金碧辉煌,陈设琳琅满目,厅两旁清一色黑漆木制大柜台,梁上边学胡余堂悬有“戒欺”、“真不二价”两块横匾,给人一种庄重、信义的感觉。柜台后边的“百眼橱”上,陈列着各种色泽殊异的瓷瓶和锡罐,与柜台上的乌木镇纸和铮铮发亮的铜药臼相映增辉,皆显示出郭家药店的气魄和威严。
药号大厅的一侧,有一大门,可进轿子和车子。其实,郭家药号与别家大药号一样,大宗生意多在后院交易。后院是方形的,有交易厅、药库和制药坊。交易厅里摆放着药材样品,可供药商们挑选。每到菊花和蒲黄下来的季节,也正是郭家药号最忙的时候。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郭鸿义已年过不惑,正值年富力强。由于经济基础雄厚,还被推选为陈州商会会长、陈州中草药务会会长、河南中草药研究会理事。为扩大经营,他还在安国、禹州、亳州等药材大市场安有分号,一举成为了药界名流。
因为是陈州商会会长,所以就常出席当地的重大活动。这样,就必须与陈州地方官员打交道。
民国十二年春,陈州调来一位新任县长,姓石,叫石宜金。石县长上任初始,就先来郭家药号拜见郭鸿义。因为郭鸿义平常爱看曾国藩的《冰鉴》,所以也养成了与生人见面先观其相的习惯。他见石县长门齿外露,一脸奸笑,就觉得此人不可深交。可是,若换上一般人,可以与其少打交道或不打交道,而这石宜金乃是一县之长,无论他如何奸猾凶诈,自己身为县商会会长,是少不得与其打交道的。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姓石的上任初始,就专来郭府拜访,无论是凶是吉,自己是决不能失礼的。
郭鸿义将石县长让到小客厅后,命下人们上了香茶,抱拳施礼道:“石大人上任伊始,就光临敝店,真让敝店蓬荜生辉呀!”
石宜金笑道:“哪里哪里,卑职未来陈州之前,家父就一再嘱咐,让我先来贵府拜访!”
郭鸿义一听这话,深感疑惑,先是怔了一下,最后还是禁不住问道:“据我所知,石大人府上是杞县,令尊大人怎会认识我郭某?”石宜金意味深长地看了郭鸿义一眼,说:“郭会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十多年前,你曾在汴京城咨议局任过要职,而那时候,家父也正在那里任个小官,只因多占了些银两,你就将其贬家为民了,还记得不?”郭鸿义想了想,仿佛还真有这码子事,因为他当时只顾与当地权贵斗,对石父等小人物记忆不是太清。可自己忘了,人家没忘,看这架势,人家还将自己当成了仇家,大有明目张胆的报复之意!石宜金看郭老板一直不言语,笑道:“虽然郭老板对家父处理过重,但家父对你还是挺佩服,常夸你官虽不大,但敢斗大人物!只不过,那些年你可苦了我们了,家父没了俸禄,我们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苦难的日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过也就因了那苦难,才促使我发奋读书,方有今日呀!”郭鸿义听了石宜金这段诉说,更是琢磨不透这石某到底想干什么了,只好应酬道:“石大人如此一说,可更让郭某担当不起了!当初黜退令尊,也决不是郭某一人能决策的。石大人已为官场中人,想必对这一点儿是清楚的!”石宜金笑道:“是呀是呀,这个我自然懂得!郭先生请放心,本县此次拜访,决无他意,只不过是替家父来叙叙旧而已!等我稳定下来,一定让家父来陈州与郭先生细叙,你看如何?”郭鸿义平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觉得好笑又好气,心想若是自己仍在台上,这石某岂敢如此放肆?说穿了,他是有意欺负人!郭鸿义本想发火,可又一想人家眼下是自己的父母官,又一片热情,不能僵持,更不能冷淡,只好借坡下驴道:“那样再好不过!郭某时刻恭候令尊大人的到来!”石宜金笑笑,拱手告辞,走到门口处又回首望了郭鸿义一眼,又笑笑,这才走了。
郭鸿义一下就陷入了恐慌与无奈之中。
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一连几个月过去了,不但没见到石宜金父亲来陈州,也很少见到石宜金了。有关新任县长的消息全是派专人打探来的,有消息说新上任的父母官很有魅力,自上任以来,几乎每天都下乡察看,扬言要根治几条河,以改变陈州灾区的面貌;有消息说这石县长是个清官,有人送礼被他拒收,还罢了那人的官;还有人说,石大人不畏强暴,城南颍河镇上的一家恶霸依仗其兄在省城做官,横行乡里,已被石大人将其押进了南监……当然,也有负面消息,说这石县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全烧的是假火;他下乡察看专访有钱人家,根治河流只是喊了喊,颍河镇那家恶霸是真的被收监,只不过那人的兄长被罢官,云云,云云,反馈回来的消息有好有坏,这更让郭鸿义摸不着头脑了!后来他仔细想想,觉得这石宜金无论是好官还是赖官,当初来府上谈往事很可能也没什么恶意,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有种探奇的意思。你想,是我郭某罢了他爹的官,恰巧他又来陈州做官,这里边肯定有种好奇的意思。反过来想,如果他想替父出口恶气或挟嫌报复,何必专来讲明,暗中使坏不就得了!人家是不是想以父为戒,在仕途上有更大的作为?如果真是那样,反倒是自己多心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决不是我郭某人的秉性……如此思来想去,郭鸿义就释然了不少。可令他想不到的是,那种“释然”只是暂时的,石宜金临走时的奸笑像是刻在了他的脑际间,挥不去,打不走,还时常在梦中出现,吓得他半夜惊醒大汗淋淋。为此,他常为自己的这种提心吊胆而苦恼,心想自己当了一回清官,本该坦坦荡荡,却料不到会碰到这种事情,反倒像做了贼一般!再想想自己当初在仕途中的受挫,更觉得“自清”是多么的不容易!自己早已退出了官场,本想清静为民,想不到仍摆脱不掉官场的阴影……这一下,郭鸿义不单单是陷入了恐慌和无奈,同时也被懊恼、苦闷、痛惜所包围,吃饭不香,睡眠不足,不久,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了。
闻听郭老板英年早逝,石县长大吃一惊。为表敬意,亲自到郭府吊唁。他悲痛地说家父过几日就要来陈州,原想让两位老朋友叙叙旧情,不想您老却提前走了,实乃悲哉!说着,泪水横流不止。
因为郭鸿义为陈州名流,又是商会会长,所以丧事很隆重。商界大贾,地方长官,远亲近朋,都来吊唁,很是热闹。
郭鸿义去世后,其长子郭增茂接管药号。这郭家大少爷虽然年轻,但对业务并不陌生,将药号生意做得井井有条。只是与郭鸿义不同的是,其性格比较随和,不像他父亲那般耿直,而且会走官路。他说经商不靠官,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小家子气。于是,他开始与石县长来往。很可能是同人之故,二人很谈得来。由于关系越来越亲密,郭增茂就让石宜金入了药号股份,而且是干股。石宜金欣然接受,每到年底,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当然,这些外人皆不知道。
有一天,石县长的老爷子来了,听说独生子与自家仇人的后代成了朋友,很是愤怒,大骂儿子不孝,说让你来报仇,你竟与仇人之子同流合污!石宜金先劝下老爹,然后说道:“冤冤相报,何时是了!现在我每年都拿着郭家药号的干股,若把他们整垮了,不等于白白朝外扔银子吗?再说,那郭鸿义已薨逝,这仇就已经烟消云散了!再弄下去,还有什么意思?”石父怒气未消地说:“我是想让你把他们整得家破人亡方解我心头之恨!可万万没想到,他竟早早地死了!”石宜金笑道:“如果说他是被我略施小计吓死的,你会信吗?”石父一听这话,方悟出儿子的心机比自己高明得多。他呆呆地望着儿子,许久没说出话来。石宜金见父亲呆了,这才说话:“你当初为何会栽在郭鸿义手中,就是不谙当官之道!为官者,要先落下好名声,然后再贪大不贪小!收点儿小礼小钱,收益不大,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贪大的捷径是贪商不贪农,官商勾结,才能捞钱。捞到钱才能去买更大的官!”
可令石宜金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已有人将他告下了。原来他不只收了郭家药号一家的干股,其他商号也均有股份。有人一串联,便将其告到了省府。尽管石宜金上有保护伞,可这么多陈州大贾联名上告,他们也只能丢卒保车,摘了石宜金的乌纱帽。
当然,这带头串联的人,就是陈州年轻的商会会长郭增茂。
石宜金被押走的那天,不少人来看热闹,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那个几年前“死”去的郭鸿义也在其中!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全是这个郭鸿义“死后”操作的。
郭鸿义对石宜金说:“我们自清的人,并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肯用而已!因为你来势汹汹,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石宜金长叹一声,说:“领教了!不过,这回你可要真死了!”
郭鸿义一听此言,怔了一下,不料正在他打怔的瞬间,只见他身后一老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后心!他痛苦地扭脸望了一眼凶手,只见那凶手拽掉假须,笑道:“郭大人,没想到吧!”
郭鸿义这才认清了,原来他竟是当初被他撸下去的石宜金的老爹!石父“哈哈”大笑着对石宜金说:“怎么样?我就猜他是假死!”然后又对即将咽气的郭鸿义说:“郭大人,我告诉你,你这清官永远难斗过贪官的!我再告诉你,我的长子虽然完了,但他早已为他的弟弟买通了官路,不久就会到一个县任县长了!”
陈州古旧书铺
民国初年,陈州北关有一专收古旧书的铺面,主人姓姚,名金堂。原籍汴梁人,上辈可能有人在陈州为官,后代便落户于陈州城。姚家过去也为世家,后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到姚金堂记事的时候,几乎已沦为引车卖浆者流了。
一开始,为生活计,姚金堂是走街串巷地收购古玩物。他挎着篮子,到城内的世家去串游,收买珍珠、玛瑙、翡翠、玉器、古玩、眼镜、家具等等。那时候他不收古旧书。有一次从汴京城来一位姓王的亲戚,说他在汴京开有旧书铺,如果能收到古旧书可转卖给他。姚金堂觉得有利可图,便开始收古旧书。碰到字画、碑帖也收。收了,就转送到汴京王氏旧书铺。这样过了几年,他从中就掌握了不少古旧书知识,能辨别出什么版本值钱,什么书是珍品。再加上他爱学习,每收到整洁的旧书,就自己先留下来细读,学问也大长了不少。后来,就自己开了铺面,专收古旧书籍。走街串巷的小贩见有人收古旧书,也开始经营这项业务,收到了,就去姚氏书铺去卖。姚老板买下后,挑拣整齐,然后去汴京、北平找销路,生意一下就活了。
凡卖古旧书之人,多有一个特点,即是不论好坏、新旧、整套或残缺,总愿悉数卖完为快。姚老板每得到信息,必亲自登门,见其中只要有少许有价值的古旧书,就全部买回,然后挑选、整理,残缺者逐渐配套,少页者,他还能缮抄补帖,作整套出售。
一般买古旧书的人,多是大学里的教授或有品位爱收藏的官员。陈州有省立师范学校,也有省立重点高中。汴京有河南大学、杞县有大同中学。这几个学校里的教师和教授皆成了他的购书对象。常与这些人接触,姚金堂从中得到不少有关古旧书的信息,什么书是孤本,什么人喜欢什么版本,他都要记录在册,一旦收到,立即送往,讨个好价。当时有一个省里的官员是登封人,很想得到同是登封人耿逸安著的《敬如堂文集》。不久,姚金堂在城北一世家买到,系清道光年间刻本,竹纸、十册。他急忙去开封送给那官员,喜得那官员如获至宝,赏给他了一个不菲的价钱。有一次他收到明弘治年间慎独斋刘弘毅刻的《十七史详节》,内有《南齐书》四本,白棉纸,系明仿宋制小字本,刻工甚精,知其珍贵,打开词簿,查出北平有一著名的学者要此书,便亲送京城,感动得那学者又掏高价又给他报路费,成了他日后许多年炫耀的例证。
再后来,他本钱大了一些,便不再亲自给人送书,改为邮寄。先发出广告信,寄给老客户们。信中列出他所出售的书籍名目,比如《李氏焚书》六卷,明李贽著,明闵齐伋刻,朱墨本,白纸,六册;《杂剧三编》,三十四卷,董康诵芬室刻本,美浓纸,八册;《翠屏集》,明张志道著,成化年间刻,黑口本,白棉纸,四厚册;《四圣悬解》五卷,清黄元御著,蓝格旧抄本,竹纸,二册;《池氏鸿史》,十七卷,高丽刊本,皮纸,十七册;《新定十二律昆腔谱》,十六卷,清王正祥撰,康熙停云室刊本,附《考证韵大全》,开花纸,六册,如此等等。得此信者,按其所需与上面的价格,先款后书,省了不少麻烦。
1938年,陈州沦陷后,有一天,伪河南省民政厅长赵筱三来陈州视察,得知姚金堂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便派人去购买。姚金堂当时确实藏有这部书,中华书局排印,三节版,连史纸印,一万卷,共八百册。姚金堂为搜齐这部巨书,已费了好几个年头。他跑项城去界首和周家口,还去过几次许昌和南阳,才收购五百余册,尚缺二百余册。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一部书,仅目录就有四十卷之巨。姚金堂如此精心搜集这部大书,是应京城一位大学校长之约,单等收齐后一同送到京城。不想赵筱三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非要不可,而且还舍得掏大价。论说,收旧书就是为赚些银钱。货是自己的,谁给价高就卖给谁。可姚金堂觉得开店铺不能光讲钱,还要讲信誉。如果没有北平大学校长之约,卖给谁都行。而既然应了约,就得守约,虽然没有签字画押,只是口头应允,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古训不能不守。于是,他思量再三,最后婉言回绝了来人。不料来人也是一汉奸,他对陈州人骂他是汉奸早已记恨在心,尤其这个姚金堂,别看只收个破书,却口口声声给他讲信誉讲节气,于是他就想借此机会杀一杀陈州人的气焰。回到驿馆,便添油加醋地向赵筱三汇报,说是那姓姚的认死不会将所藏卖给日本人的走狗!赵筱三一听此言,像被人揭了疮疤般羞怒。他原本只是派人前去探听一下,并不想巧取豪夺,不想此老儿竟如此放肆,不卖书还骂他是汉奸走狗!这种人不治一治可真咽不下这口气!但他毕竟是省里的官员,来陈州只是视察民情,并没权杀人搞报复。他虽然不亲自杀人,但却有能力借刀杀人,于是便把《古今图书集成》的重要性告知了驻陈州日军长官川原一弘,并有意将这套大书说成是中国之国宝,对大日本帝国极其有用。川原一弘虽不太懂收藏,但一听说是中国之国宝,便动了心,决定要夺过来。当下,他就派人去了姚氏古旧书铺。
川原一弘派去的人一到姚金堂的旧收铺,先用刺刀逼住姚金堂,然后让翻译上前说明目的。面对明晃晃的刺刀,姚金堂当然害怕,忙将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交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走后,姚金堂感到害怕又失落,像被人挖走了身上一大块肉,思前想后,就觉得这事太蹊跷!心想我是一个收古旧书的人,说白了跟拾荒收破烂儿差不多,怎会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而且他们进门就点名要那套还未收全的《古今图书集成》?当然,不用多想,一下就想到了赵筱三。因为两件事挨得太近,向日本人告密的必是他无疑!姚老板就觉得太可气,而且是越想越气!他说自己跟日寇无法讲理,找到赵筱三说说道理总是可以的!主意一定,他就直奔了赵筱三住的驿馆。
赵筱三身为省府大员,门前自然是岗哨林立。姚金堂到了驿馆门前,守门岗哨自然不让进。姚金堂心想,赵筱三既然派人去买书,肯定喜欢收藏。于是他就向哨兵说我是古旧书铺的老板,手中有两套孤本,请您请示赵厅长要不要?那岗哨是赵筱三的随从,自然知晓赵筱三的这一爱好,便打电话向赵筱三请示。赵筱三一听姚金堂亲自登门向自己售书,肯定是稀世孤本,便同意见见他。
姚金堂走进赵筱三的住所,赵筱三刚从洗手间出来。姚金堂问:“你就是赵厅长?”赵筱三点点头说:“是!”姚金堂又问:“是你将我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的消息告知了日本人?”赵筱三可能觉得这事儿没甚好隐瞒,便说:“不错!”姚金堂一听果真是这汉奸,就有些气冲牛斗。人这玩艺儿,气过火了就会失控,姚金堂此时就已经失控。他望着赵筱三,双目冒火,突然就抡起巴掌很响地打了赵筱三两个耳光,然后骂了一声“败类”,就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赵筱三一下被打蒙了,怔怔然竟好一时不知所措,等他清醒过来,看姚金堂已经走出了过道。他当然也气,想喊人抓住姚金堂,可嘴张了一下竟没喊出来!原因是那一刻他的脑际里一片空白,没找出抓住姚金堂的理由,又深怕自己挨了两个耳光传扬出去,最后竟傻呆呆地看着姚金堂走出了驿馆大门。
当然,等姚金堂冷静下来,也极后怕,当天就离开陈州去外地躲藏,两个月后才敢回来,只是令他颓丧的是,每当向别人炫耀此次壮举时,没人相信他,都说他是吹牛皮!
再后来,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