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意民营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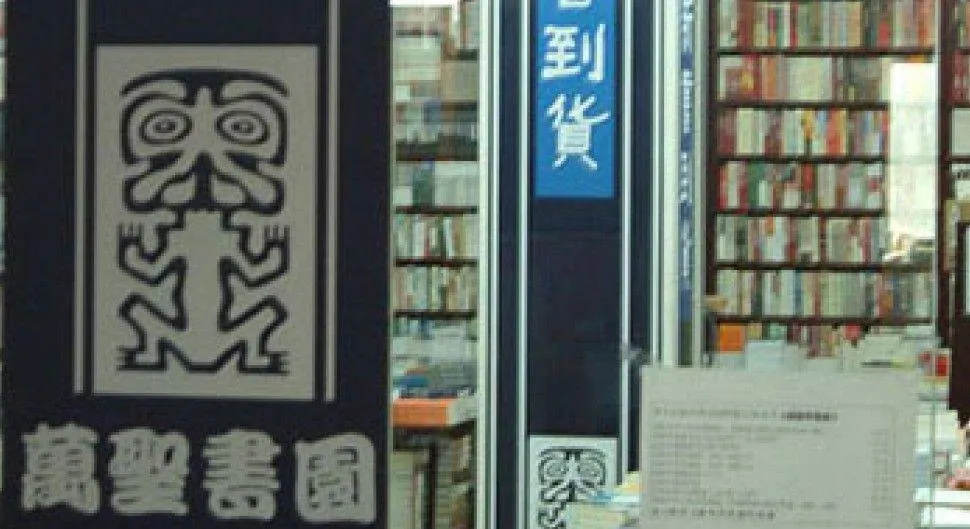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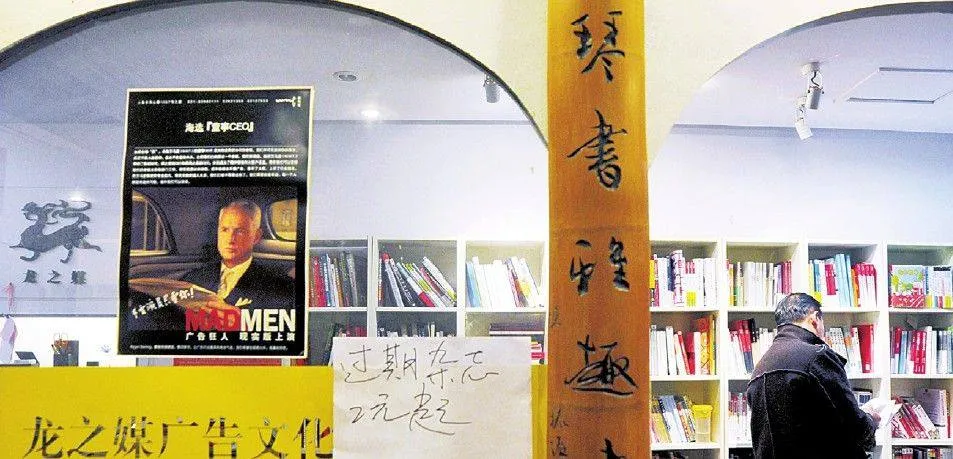




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都能找到一些文化遗迹。然而遗迹只是遗迹,没有文化内容的古迹只能称为废墟。书店,在培养市民的人文素养和展现城市的人文风景上,承担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独具特色的民营书店。
如今,在大型连锁书店和网络书店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书店,除了面对实体书店所共有的图书价格战和读者阅读习惯转向等问题,还挣扎在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中。当商业因素逐渐淡去,开书店变得越来越文艺范儿之后,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书店经营者们无不像坚守自己一方理想国度的斗士,展现出在残酷现实中继续耕耘人文土壤的决心。
如同拥有查令十字街84号的伦敦、莎士比亚书店的巴黎、城市之光的旧金山、惠文社的京都,每个爱书人心目中都有一份有关书店的城市人文地图。这些书店的存在,缩短了那些从未到过的城市与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它们存在或消失,都不会影响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美好印记。
千篇一律钢筋水泥的都市现代化建筑,消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只留下一副装扮过后重度相似的面容。如果某天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醒来,你怎样才能辨认出自己身处何地?还好,城市中还保留着独立书店这般个性的存在。它们或大或小,或远或近,或华丽或朴素,或活跃或沉静……作为读者,我们要坚信的一点就是:不管处境如何艰难,它们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回望2012年,我们为那些依然坚守在城市中的民营书店做个素描,不管未来它们的发展趋向何方,依旧是每个城市中最令人眷恋的风景。
(北京)万圣书园:坚守学术品位
对于北京的爱书人来说,万圣书园无疑是一处圣地,也是中国民营学术书店和学人办店的先驱。从1993年创立至今,二十年的时间里历经四次搬迁,这家书店一直专注于对学术、人文优秀书籍的推荐和传播。长期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万圣书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12年年底万圣书园迁入新址,新址由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将房屋签下后让万圣书园继续使用,并由他个人贴补房租的差额。另外,万圣的老读者新东方王强和房东北大资源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万圣书园在中国的民营书店里扮演了一个开启者的角色,它是最早一批构建链接“爱书人”和“爱书的书商”模式的书店。它的出现,打破了固有的新华书店模式,让人发现只卖那些原以为不容易赚钱的学术书籍,也能盈利,也能生存。后来,海淀片区与万圣定位相同的“三味书屋”“风入松”等书店相继出现,开设学术书店蔚然成风。
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如同其他很多的书店,万圣也做过不少尝试:开分店、建网站、卖咖啡。而如今除如何在书店中经营咖啡副业和文化沙龙的经验可供分享外,其他差不多都可以算作失败的尝试。所幸万圣一贯坚持“站在读者立场思考”的经营理念和专业的选书标准,核心业务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同类书店纷纷关闭的今天,仍然坚守并存活了下来。
(北京)龙之媒书店:因为专业,所以生存
在中国提及专业书店,名气最大且经营状况最为良好的当属龙之媒书店。龙之媒的前身为北京广告人书店,是中国首家广告专业书店,创办于1995年,两年后更名为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广告专业书店,龙之媒在卖书之余,还兼做图书出版,其策划的“龙媒广告选书”,迄今已出版了近百种,建立了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广告专业图书品牌,其中很多图书被高校广告专业列为教材。2008年,龙之媒书店获得了“中国广告30年历史贡献奖”。
与其他民营独立书店不同,龙之媒的店址通常设在二楼以上,最高开到了16楼。这样的选址方式是在香港开书店的普遍做法,因为香港寸土寸金,开书店选择二楼以上实属无奈,但龙之媒的选址却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房租压力那么简单。专业书店的消费者是数量有限的一群人,不能像一般书店那样等客上门。龙之媒有自己的客户数据库,同时也保持与广告业的密切联系,可以确保需要它的读者能够找到书店。专业书籍对专业人士有很大的必须性,他们通常能够承受较高的书价,也肯为买书付出更大的搜索成本,因此也对购书环境要求较高。这样的经营策略,让龙之媒的连锁经营不需要承担过大的资金压力,再加上近几年来大力发展自身的购书网站和及时调整图书售价策略,让这家书店保持较好的良性循环。
小环境、小圈子所展现出来的专业性,是龙之媒书店独特的经营之道,也是值得当前书店经营者们学习的经验。
(北京)老书虫书店:书店的复合空间
老书虫书店正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源于入选LP(Lonely Planet,全球最著名的旅行系列图书)最新出版的《2011孤独行星最佳目的地》一书中所列的“全球十佳书店”,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书店。LP给这家位于北京三里屯南街滚石院书店的入选理由是:比一个好书店该做的做得更多,它将人文之美、阅读之美、知性之美甚至美食佳饮之美融为一体。
老书虫是一个将书店、图书馆、酒吧、餐厅和人文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目前除北京外,还在苏州和成都开设有分店。老书虫书店是目前北京最活跃的外文书店,店内约有1万本原版英文书籍和各种英文杂志。除卖书外,书店还实行会员制,会员可以在这里借书或者直接在店内阅读。
与很多书店一样,老书虫书店的图书销售本身并不盈利,各种文化活动才是书店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每周定期的讲座、猜谜、鸡尾酒会、古典音乐欣赏等活动,这里还经常邀请一些作家来进行读者见面会或作品朗读会。固定在3月举行的“书虫国际图书节”是老书虫书店每年最盛大的活动,这项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共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0位作家,其中不乏享誉全球的知名人士。
(北京)蜜蜂书店:文人的梦想
于某个街角开家小书店,卖自己喜欢的书,放自己喜欢的音乐,交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在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多爱书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有关书店的梦。
蜜蜂书店就是这样一个梦境的产物。店主老张本来是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向往着能够自由出版自己喜欢的书,所以辞职,卖房后来到北京发展。他将店址选在远离闹市区的宋庄小堡村,有着自己独特的考量。宋庄这里聚居着约7000多名画家,作为这个艺术村落里唯一的人文书店,蜜蜂书店主营艺术类图书并提供各类艺术服务。与书店并行经营的蜜蜂出版,也依托宋庄艺术区的地域优势,主攻艺术出版类选题,出版图书所得的获利又贴补到书店的运营中,在不断打造“蜜蜂”品牌的同时,维持一种相对良性的循环。
出书与开店相互滋养的模式,使得蜜蜂书店有着与一般独立书店不同的独特风格,可惜的是,这样的特色并不具备广泛的可复制性,不是每一家书店都拥有做独立出版的策划能力。也许,这也是蜜蜂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打造出自己品牌的原因。
(上海)季风书园:捆绑一个城市的文化情结
纵观中国民营独立书店群落,季风不算最有特色的,也非经营最好的,但是,它用了仅仅16年的时间,将自己打造成上海的文化地标。去年季风三家门店的关闭引起了一场有关书店保卫战的大讨论,牵动了一个城市读者的神经。凭借那次风波,季风获得了地铁店铺租金的优惠价并被列入了上海市政府首批实体书店扶持名单。
带着浓郁文人开店的色彩,季风书园试图通过选书风格表述对现实世界思想维度的判断,并认为书店在社会中的担当不仅是提供好书,而且应该坚持“通过阅读改变我们生活”的文化立场。三七开的图书品种配置(30%的学术类图书+70%大众文化类图书),且并不回避市场畅销书的做法,让季风书园保持一种巧妙的生存态度,不清高也不媚俗,贴近群众。也许,这也是季风高峰时期能开10多家门店的原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众多的门店将季风书园打造成全国规模较大的民营书店之余,也埋下不小的隐患。当初将店址选在人流集中区域的季风书园,发展初期众人都羡慕其经营眼光,然而现今,面对合约期满纷纷大幅上涨的房租,并不擅长副业经营的季风门店只能选择黯然退出,如今剩下的5家门店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长时间。政府杯水车薪的补助和读者乡愁似的支持并不能成为季风脱困的助力,未来的发展还是得靠书店自身去寻找动力。
(上海)汉源书店:老上海的记忆
汉源书店坐落在上海原法租界内素有“出版一条街”美誉的绍兴路,幽静且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被许多读者认为是个非常适合精心看书的好地方。书店不算大,但主人却对它进行了精心装扮,店面空间被巧妙地分割成欧式古典和中国传统两种不同风格。在这里,你可以沉醉于巴洛克风格的柜子、欧式古典木圈椅、笨重的留声机、八毫米电影放映机、古朴的手摇电话,也可以欣赏到中式风格的供桌、雕花木椅、牌匾、瓷瓶、美人靠等物件。据说汉源的咖啡和西点味道也是一绝,汉源书店甚至因此荣登上海有线电视评选的十大上海特色咖啡馆之一。
从1994年开店至今,汉源书店可以说是上海文艺书店的鼻祖,媒体赞其为“上海人的文化客厅”。与欧洲很多独立书店一样,它代表了小书店的一种生存态度,不追求大型连锁,而是选择在人们生活的小区中扎根,与面包房、咖啡馆、水果店并存。有出版人将汉源的生活常态拍成MV,并拿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播放,让很多外国人了解高楼大厦之外的上海。
汉源书店与其讲是书店,不如说是书吧来得更为贴切。在这个满是老上海风情的空间里,独自一人或是约上三五好友,在此阅读、静思、休息、聊天,回去的时候再带上几本有关上海的书。只是不知道2013年1月份租约到期后,面对高昂的房租,汉源书店是走还是留。
(广州)方所:书店中的奢侈品
方所的奢侈,不仅仅是它开设在广州最高端的购物中心太古汇,与爱马仕、阿曼尼、普拉达等一批国际顶尖名品店毗邻,还在于打造它的团队集合了内地、香港顶级艺术设计人才和台湾诚品书店原班人马。在18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内,拥有500平方米的书店,400平方米的展销设计品的美学馆、余下的空间中还包括展览馆、服饰馆和咖啡馆。今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最高级别的零售业会议上,方所获得了全球年度最佳购物场所设计奖。
方所这样的复合空间,很难将之简单定义为书店,但是它又确实以书店作为其主业。方所的选书以艺术、设计、文学为核心,在整体书籍组合上以主题、知识体系、思想谱系为读者搜罗书市少见的书目,展现出专业选书的诚意,涵盖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最好的各类出版品。这样的高端定位也延伸到对员工的选择上,为了倡导“私人阅读顾问”的服务理念,方所书店所招聘的人员要求至少是名牌高校中文或外语系本科毕业生,喜爱阅读并具备一定的阅读量。与台湾诚品一样,方所也将书店定义为多元的、动态的文化事业6QOkiMGkDKD0pl5yfnqy4Q==,邀请内地和港台的知名文化人进行演讲、座谈、表演、展览等延伸阅读活动,创造与读者对话的各种可能。笔者撰稿时恰逢方所举办陈丹青的讲座,不收门票,吸引了2000名左右的读者前来,偌大的场所挤得水泄不通。
方所最奢侈之处,是它不考虑营业收入并且拒绝一切商业活动,这种根本不在乎赚不赚钱的态度,实在很奢侈。
(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隐士·小
早在很多年前,豆瓣上便流传着主题为“如何找到博尔赫斯书店”的帖子,内容由店主亲自操刀,风趣地表述读者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找到这家隐匿于城市不知名角落里的小书店。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这地方实在不太好找。传说博尔赫斯曾经搬过11次家,目前的栖身之所大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态势。想来也是,本就是家坚持小众风格的书店,不必非得将店址设在人流量大的地方。
除了难找,博尔赫斯还很小,曾荣获过中国民营书业评选中的“最佳小书店奖”。这里的“小”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店小,书店面积只有15平方米,店面一楼是它家的yes-no咖啡厅,通过逼仄的回旋楼梯才到二楼的书店,不大的二楼空间还隔出间会议室,所以留给陈列图书的地方实在太过有限;二是小众,博尔赫斯选书虽然与众多的民营书店一样走的是文艺路线,但是它家卖的书,大多数是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且是以本为单位,你想多买都不一定有货。
博尔赫斯信奉的是少量阅读精神,读书贵精,不贵多。正如店主陈侗讲的那样:你不必带着任何成见和负累——传统的、权威的、教育的、知识的——去选择,如同萨特小说《厌恶》中那个“自学者”要在图书馆里从A读到Z,我们只需从中挑出一本《厌恶》就够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博尔赫斯书店里面的书数量不多,上架排列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标准。
(杭州)枫林晚:繁华过后的沉静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有关枫林晚“不卖金庸”的段子。尽管金庸在浙大当文学院院长时,常常去逛枫林晚书店,但是却没有他的书卖。枫林晚甚至标榜,只要能数出来的畅销书,这里一概没有,如果你需要的是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本雅明、波伏娃、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倒是可以来这儿找找看。作为一家定位为高品位的学术书店,枫林晚在选书上有着顽固的坚持。这种坚持也树立了书店的品牌,凭借自身搭建的平台,枫林晚经常举行主题学术沙龙,盛名远播,杭州的文化人都以经常出入这里为荣。
学而优则仕,店而优则扩,枫林晚也没有逃脱这一民营书店经营的固有线路。全盛时期,它在杭州及周边区域共开设了12家分店,试图将自己“学术+沙龙+咖啡+会所”模式拓展开来,打造品牌连锁经营。庞大旗舰店“书立方”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到这时,朱升华才真正意识到小众书店并不适合走大众连锁扩张的路子。
阿里巴巴的马云及时向枫林晚伸出了援手,邀请它进入自己的工业园区,共同打造企业文化。在此之后,枫林晚开始了真正的转型,将书店定位于做企业图书馆,并试图进驻高端社区,做“社区文化管家”。
枫林晚能够存活下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它如今的发展,也为民营书店经营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只是,我想很多人,也许都会怀念文三路上曾经的那家枫林晚。
(杭州)晓风书屋:变色龙般的存在
杭州是座适合开书店的城市。无论是西湖边上的三联、现代、外文所组成的书店“金三角”,浙大周边的数十家知名书店,还是遍布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其他书店,杭州的民营书店曾经盛极一时。不过,随着整个实体书店行业趋于式微,书店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这样的大背景下,拥有11家门店的晓风书屋不仅能够维持正常运转,还在积极筹备新增一家门店的态势逆势增长,实在令人惊讶不已。16年的发展历程中,晓风在图书零售和批销上做得很不错,其自我定位介于大众书店与学术书店之间,选书也保持着一种“中端”态度,以人文社科为主,学术类、艺术类图书占一部分,不回避市场热门畅销书,还兼销相当部分的少儿类图书。要消化书店的经营成本,单靠卖书是远远不够的,晓风的副业经营也算合格。
晓风书屋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它的发展规模,而是让每一间零售店的风格都依据其地理位置、书店场地、合作单位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经营形态样貌:体育场店以综合性为主,美术店突出艺术气息,紫金港店主打人文社科,西溪店以古籍文史见长,小河山店则蕴含科技特色,工商店侧重财经题材,河坊店着重杭州本地人文,浙报店倡导建设公共阅读图书馆……虽然都是晓风,但是在特色经营下却各有各的面貌,如变色龙一般根据客观环境来不断调适自己。不过,这样的运营模式对书店人事结构有很大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协调这一问题,是对晓风书屋决策者的巨大考验。
(南京)先锋书店:大地上的异乡者
广西师大出版社在2005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先锋书店:大地上的异乡者》,那年恰逢先锋成立九周年。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一穷二白的钱小华如何赤手空拳,将最初只有17平方米的小书店发展成拥有三家连锁,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且国内有口皆碑的一流学术书店的全过程。这位爱书成痴的店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书店经营者的一个榜样——对书籍炙热的情感和对书店全心的投入。
豆瓣上有先锋的获奖履历介绍,如果用A4纸打印,可以弄出厚厚一沓,这还不包括港台及国外媒体的诸多报道。先锋在新浪微博上的活跃程度也是有目共睹,每天你都能在上面见到来自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的书迷对于先锋的溢美之词。被誉为“中国最美书店”的先锋五台山总店,如何从废弃的人防工事变身为极具美感书店的传奇故事一直被媒体和读者传唱。拥有庞大的空间又不用太过担心房租成本,先锋从此致力于打造“图书馆式独立书店”的梦想。
犹如双刃剑,成就先锋的“大”也是其发展的绊脚索。因为大,所以要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放满一本本都能让人感到满意的书很困难;也因为大,书店在空间安排上缺乏让人静心留足的角落,很容易感觉重复和疲倦,每本书所拥有的独特性,在一致延伸、打平到底的书架上,被消减,难以凸显。先锋未来的发展,估计重点是放在实体店空间的科学划分和更好利用,网店树立具有影响力的选书意见领袖地位和提高图书销量上面。
(南昌)青苑书店:沙漠中的绿洲
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国功去年曾为青苑书店写了篇文,在文中记述了他这名老读者与青苑携手走过的二十载岁月。漫长的20年,从青涩学生过渡到哀乐中年,与他一同成长的青苑,也成为民营书店中经营历史最长的书店。
这家靠发行起家的夫妻店,身上带有许多时代发展所遗留的印记,它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是其他后生晚辈书店们所不能理解的。作为江西省民营书店中的龙头老大,青苑书店一直在扶持一些二级城市、县城的样板书店,这些书店往往多是上世纪“教辅风”留下的产物,如今处境艰难。青苑书店通过自己的零售店作为示范,让它们学习如何建立书籍品种、图书陈列、店面装修、开展会员制销售等,引导其逐渐发展成为综合书店。在这一过程中,青苑也不断地培养下线客户,成为这些书店的供货商。
青苑每逢周末举行的书友活动,是这家书店的特色。获得台湾“云门舞集流浪基金”赞助来大陆考察民营书店的台湾“小小书房”店主刘虹风,在谈及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书店时就提到过南昌青苑。据她描述她拜访青苑的那天是周六下午,刚好有场书友会,主讲人是中国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主题是探讨中国当代的社会思潮。当天一位难求的讲座现场让她很是吃了一惊,也很佩服青苑的实力,因为在台湾已经没有哪家书店会举办这么硬的主题讲座,而在青苑,却是一个月2—3次的常态性举办,这样的人文生态环境让她很是羡慕。笔者撰稿时,青苑书店正在进行2012年第41场书友会“航向台湾的故事——太平轮一九四九”,演讲嘉宾是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报道文学奖得主张典婉,主持人是青苑书店的老朋友张国功。
(青岛)我们书店:书打折,文化不打折
很少有书店,从开张伊始就将自己定位成特价书店的,因为感觉很没品。独立书店基本都是追求文艺气质的,成为会员积分达到多少后才给你个8折以上的优惠,特价处理书多是堆在书店外面或是某个角落,虽然谈不上遮遮掩掩,但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所以,当青岛的我们书店挂出“以文史社科特价书为主,全场五至七折”的招牌时,顿时让人觉得很好,很强大。
我们书店所销售的图书,几乎清一色全是出版社的库存,其中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为主。从小说、诗歌到历史著作,从哲学、社会学到政治学,不一而足。在书架前溜达,感觉好像回到了学校图书馆。这些早年出版的书,却没有图书馆里的书千人翻万人摸留下的污垢,捧手翻来满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书纸味道,带着那个年代书籍装帧的浓郁特点,让人有种时光穿越的错觉。绝的是,店里居然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旧书。
这家书店的存在,让人意识到出版社仓库里那些堆放了N年的书,除了化纸浆外,还能有别的出路,但前提是它必须是“好书”。这也给如今的出版者们提了个醒,您做的书,几十年后还能像这般焕发第二春吗?
(贵阳)西西弗书店:推着巨石上山的黔驴
建城只有400年历史的贵阳,地处西南边陲,经济文化落后,地缘劣势明显。如果说这里有一家横跨西南三省市的出色书店,除非亲眼所见,否则很难相信。
西西弗的前身名叫“启明”,1993年在贵州小城遵义,十几个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凑万把块钱开设了“启明”书店。后来其中7人拆伙出来,另立山头开设了后来的“西西弗”。1995年,遵义的西西弗书社与贵阳花溪宽心草书店合并,正式更名为西西弗书店。这家书店的诞生,让面目模糊的贵阳人突然有了清晰的气质,让他们不再淹没在这个以麻将文明和阴冷躁动著称的城市表层之下。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西西弗终于实现了西南王的初步梦想,如今它在贵州省内、成都、重庆共开了14家连锁门店。
西西弗是家很有趣的书店。正如24字镇店标语写的那样:背包太沉,存吧;站着太累,坐吧;书太贵了,抄吧;您有意见,提吧。为了让顾客能舒服地坐着看书或者抄书,有限的书店空间内专门开辟区域给读者做抄书点。书店经营者清醒地认识到,物理空间只是书店的体验基础,而书友才是书店的未来核心价值。如今,西西弗的会员人数已经超过16万人。
2007年西西弗的新掌门人金伟竹设计出书店的新吉祥物——一只憨态可掬的大头驴子,名曰西西。西西身穿长衫马褂头戴小皮帽,一副孔乙己的神情。西西弗这家自嘲出身于第三世界城市的书店,努力向外界展示黔驴不技穷的形象。
(大连)香蕉鱼书店:80后的先锋实验
将香蕉鱼书店归类到大连,已经不太适当,因为在2012年6月的时候,这家书店就结束了大连实体店的经营,重新回归网络。
“香蕉鱼”来源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作品《逮香蕉鱼的好日子》,用这种只在脑中才存在的鱼借喻稀少、限量、唯美和珍贵的事物。作为目前中国大陆第一家独立出版书店,香蕉鱼书店一直致力于推广普及独立出版文化,并与一些艺术家、摄影师和诗人合作,出版他们的个人作品集。香蕉鱼通过网络销售的形式将自己的作品寄送到国外去,让更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能为世界所知。同时,它也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出版社及艺术家们自主出版的作品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展览、购买欣赏到国外的独立出版文化。独树一帜的香蕉鱼很快被国际艺术书展所注意,伦敦、纽约、东京、首尔、香港等书展都邀请它去参展。
80后的店主苏菲,在网上开了一个名叫“苏菲独立书店”的知名博客,博客中她将自己欧洲八国游历中所关注到的独立书店整理成集。对于未来书店的业务,苏菲将之划为三块:一是售卖(香蕉鱼网上书店),二是出版(香蕉鱼出版社,独立出版摄影、插画类图书),三是印刷(内地第一家Risograph专门印社)。在她的计划中,这三项业务是完整的一条龙服务,重点放在出版产品上,不分心于诸如沙龙、咖啡馆、书吧等其他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