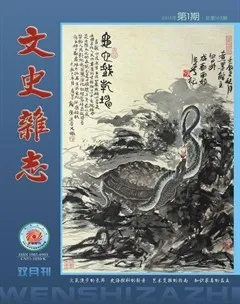屈原为何对鲧独怀深情
屈原是品德高洁,性情耿直,宁折不弯,爱憎分明,思维至宏的爱国诗人。每读屈赋,无不为赋中所表达的充沛感情所倾倒。但是通读屈赋,却能看出崇圣忠君爱国的屈原,最怀深情的不是圣君,而是被圣君尧、舜定为四凶之一并施以殛罪的鲧,并在赋中给以最多的笔墨为鲧鸣冤不平,以至对尧、舜有所指责,这是为什么呢?应该说,屈原对于以尧、舜、禹、汤为代表的圣君是怀着崇敬之情的,在他的赋中,就多次表达这种情感。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尊道而得路。”“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馋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黯而有瑕。何况一国之事兮,亦多端而胶加。”“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九辩》)
“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怀沙》)
但是,从《离骚》到《九辩》表明了屈原对于圣君尧、舜、禹、汤,却有着从尊崇到辩解及认为黯黯而有瑕的变化。而在《天问》中,更对圣君们发出质疑之声。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胡维嗜不同味,而快朝饱?”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汤谋易旅,何以厚之?……妹嬉何肆,汤何殛焉?……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在《离骚》等作中,屈原认为尧、舜都“尊道而得路”,是因谗人的嫉妒而有不慈之名。在《九辩》中,却改说“日月尚黯黯而有瑕,何况是一国之事呢?”不全是“尊道而得路”了。在《天问》中,却指问尧舜之非:“既然尧认为鲧不能胜任治水,但是大家为什么倒都推举鲧?英明的尧为什么对鲧不经常予以督查?” “舜已另有妻子登比氏在家里,怎么能说舜是鳏夫呢?(按闻一多《天问疏证》解‘闵’为妻,‘父’为夫)而尧为什么不通告舜的父亲就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舜也不事前通告父亲。那尧能说是尊道么?舜能算孝子么?”比较《庄子·盗跖》:“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吕氏春秋·忠廉》:“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对这些说法屈原原是认为出于谗人的忌妒,但在《天问》中却顺着谗人们的说法发出疑问了,不仅是“黯黯而有瑕”了。
对于禹,屈原还问得比较客气:“禹私通涂山女,为什么只图快个朝饱,三日后就离开了?”对于汤,那就是指汤靠耍阴谋灭夏,还将助汤有功的妹嬉处以殛刑。关于汤暗派伊尹入夏与妹嬉交以间夏的事,载于《国语·晋语一》《竹书纪年》《管子·轻重》《吕氏春秋·慎大》等书。妹嬉告诉伊尹让汤从西方进军将得胜(实是向汤泄漏桀西方后防空虚),“于是汤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方以进,未接刃而桀走。”妹嬉为报家仇氏恨,不惜与伊尹交充当汤的间谍而灭夏,其行与西施相类,但汤却翻脸不认人,一点也不“俨而祗敬”,故屈原指而问之。
屈原在《天问》中对尧、舜、禹、汤的问,实是倾向着《庄子》《吕氏春秋》的说法而提问,表明屈原对这四个圣君的看法有变了。如果屈原对圣君们的看法没有变化,他完全可以这样来提问:“佥曰何忧,何尧之能识鲧?”“帝命为大,何谓之不孝?”“胜心治水,胡为朝饱?”“何谋桀殛嬉,而黎服大悦?”那么,有没有屈原在其所作中态度始终如一的历史人物呢?是有的,这就是鲧。在屈赋中有三处深情地说到鲧: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离骚》)
“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惜诵》)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优,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天问》)
在《离骚》中,屈原述说其姊女媭出于关心而累累骂他,鲧以耿直亡身,你为什么偏偏以此夸耀这种节操呢?在《惜诵》中,屈原累说自己以忠诚事君却以忠获罪而遇罚,将鲧与晋太子申生相比。申生因纯孝而遭谗以致被逼自尽,鲧因耿忠而招怨未成治水大功,这与通常说的鲧因堵水之法不当或者“方命圮族”或“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大不一样。
鲧是因性格耿直而以忠心遭祸,诸子百家中都无此种说法。《吕氏春秋·行论》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韩非子·外储》:“尧欲以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这两则记载,说的却是鲧并不是因为治水无功而获罪,而是因为反对尧让天下于舜,这是鲧获罪的另一种说法。但它们所载的那个自负骄横,为争三公甚至举兵反对尧让天下于舜的鲧,虽然把话说得很耿直,却与屈原所说的“作忠而造怨”的鲧,是完全不一样的。屈原绝对不会把这种耿直以与之相比并给以深深的同情。那么在屈原心目中的鲧,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从如果鲧反对“尧以天下让舜”入手,二是从《海内经》所载的“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入手。
一、舜在传说中,是以孝而著名被四岳推荐给尧的。尧为什么要挑一个有孝行的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且迫不及待地连舜的父母也不通知就急急忙忙地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而以孝闻名的舜却将此大事不禀告自己的父母?如果仔细分析,尧实际上是将舜作为过门女婿而招赘入尧家的,所以舜才为此连父母都不事先通告就为尧婿了。舜是有虞氏人,居地在今河南东部,而舜都蒲坂,却在尧都临汾以南不远。为什么舜不在有虞氏居地建都呢?《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国语·晋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两者记载略有不同,但都可以看出有虞氏对尧是作为祖承来看待的,完全没有舜父瞽叟的地位。而《国语》中的“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郊鲧而宗禹”,也许更可以说明舜与尧的父子传承关系。尧与舜,鲧与禹都同样受到郊,宗的对待;而鲧为禹父,那么尧就应相当于舜父。尧与舜,虽然同禘黄帝,但尧为黄帝子玄嚣之后,而舜为黄帝子昌意之后,两者代差已过五服,这样舜才可能成为尧的女婿。如果不是舜是因入赘而承尧祀,那么有虞氏怎么能对尧致以宗、郊之祭呢?因为是入赘,所以尧才重视舜的孝道,而且不通知舜父,造成既成事实。舜既是入赘,那么尧之二女,与舜父就不存在那种翁媳亲密关系,故而屈原才会问:“尧不姚告,二女何亲?”了。这也可解释为什么舜与尧女婚后不回老家有虞氏居住,而是到尧所赐的成婚之地“历降二女于妫汭”(地在今山西省垣曲县历山镇)结婚成家。在舜将父、弟接来后,却与其父、弟分家而居,甚至连井也分用,独享尧所赐的丰厚财物,因此才会发生舜的父、弟欲谋杀舜并占有其财产的事。看来舜的孝是要打个折扣的,难怪后人会有舜不孝的疑问了。
舜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对父、弟也是时刻暗中防范着,因此才会在修仓廪时带上两个斗笠,在井下事先就挖个外出的通道。舜对尧也是藏而不露,即使尧安排二女对舜考查,安排九男予以监视,都没有看透舜。但是当尧禅位后,舜大权在握,便将尧的旧臣不用,改用尧不用的八元、八恺,启用新人禹、皋陶、契、稷等,并将都城从平阳(今临汾)迁到南面七百里的蒲坂,彻底摆脱尧的控制,将尧这个太上皇孤独地限居在尧都平阳直至老死,形同幽囚。因此,便有了“舜囚尧”之说。
也许鲧已经感觉到舜继尧位后,会对尧不利,但又无确切证据,便以舜是出身卑微的匹夫为由,对尧耿直进言。但是尧已为舜的表象所蒙蔽,认为这个累累抗命自行其事的鲧欲争位,而此时正好发生洪水冲垮鲧修建的堤防,便以“治水无功”、“擅盗息壤”、“反对禅舜”三大罪将鲧处以四凶中最重的殛刑了。
二、“盗息壤”说缘于《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之于羽郊。”古人对息壤的一般解释是:能够自身长高的土壤,称历代在各地多有发现。而一些学者却认为这段记载是个类似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帝那里为人类偷来天火的神话,没有什么历史意义。那么怎样来理解这段记载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呢?这种息壤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呢?顾颉刚先生在《息壤考》中认为它是一种遇水膨胀的黏性土。土工学上称这种土为膨胀土,其原因是土中富含蒙脱石等矿物,遇水极易膨胀,体积甚至增大一倍以上,多产于山与平原的交接带。那么鲧为什么要用息壤来堙洪水?因为要在河道两侧修建土堤防洪,而河道两侧多为沙土,那是不能用来建筑堤防堵水的。沙土渗透性强,遇水易渗漏崩解,因此修建堤防的土质必须以黏性土为主。鸱龟很可能是巫师名字,鲧也许是听了此巫的建议,以为用这种土来筑堤挡水,大堤便会随洪水位的增高而增高。但是鲧却不知,这样的堤坝虽然体积增大了,土却变松了,力学强度降低,遇水易崩解,反而挡不了水。息壤(膨胀土)也是植物易于生长的土,而山区与平原的交接带却是大量农耕居民区,远离河岸。因此,鲧取息壤必然要毁坏农田,还要远道运输,耗费大量人力。鲧是太急于治理好洪水为民造福了,以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尧的忠诚,造福于百姓。而治水现场距尧都平阳,往返需二十多日,为抢在洪水前,便不及向尧请示,自作主张挖田取土。这种能自行膨胀的土,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神土,是属于天帝所有。很可能有人向尧进谗言,说鲧竟然不向帝尧请示,不待帝命,不把天帝和帝尧放在眼中,可见其飞扬跋扈。鲧擅自挖神土息壤堙洪水,不仅得罪天帝,而且大量毁坏农田。因此天帝发怒,让筑堤的息壤崩塌,以致洪水冲决堤防,有负帝尧和四岳对他的重托。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鲧死时距屈原已有近两千年,口耳相传中必定有很多变形和失真,也许各类因素都有。儒家取其治水无功之罪,法家取其反舜之说;而屈原所了解的鲧,却是个忠而忘私,受谗获罪的形象,与儒、法两说大异。
屈原在《天问》中,于问天之后,便首问鲧事,鲧事占了《天问》十分之一的篇幅,表达了充沛的感情,与其他问的直言简语大不一样。屈原是在借问鲧事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将鲧事的问语写得十分感人。
“既然尧认为鲧不胜任,为什么却同意他治水?虽然大家都说不用疑虑,但尧为什么不对鲧的治水措施经过考查后再让他去施行?到鲧治水快要成功时,帝尧又为何对鲧加刑?已经把鲧处以殛刑永远地阻遏在羽山了,为什么三年后还不放过他?鲧被阻断了向西归家之路啊!那险阻的山崖,病中的鲧又如何能够翻越?耿直而不屈的鲧投入羽渊化为黄熊了,巫又为何要去将他救活呢?(以致鲧最后还落个被舜派来祝融用吴刀分尸的悲惨下场。)鲧与共工等都是因反尧禅舜而并投流放,为什么鲧却受到最沉重的处罚?”屈原把自己在流放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完全融入对鲧的命运同情中去了。结合鲧因反对尧传位舜而被殛羽山以及舜囚尧的传言,屈原与鲧的命运倒真有许多相似之处。
鲧—尧之宗室重臣—谏尧不禅舜—流放羽山—尧被舜囚—投入羽渊。
屈原—楚之宗室重臣—谏楚不亲秦—流放沅湘—怀王被秦囚—投入汨罗。
尧时的“殛刑”,一般多解为死刑。但从鲧当时并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羽山(在今江苏省东海县),很可能相当于现今的“死缓”,因而屈原有“何三年而不施”之问。
鲧化为黄熊投入羽渊的传说,见于《国语》和《左传》。人是不能化为黄熊的,疑古者多作为鲧是神话人物的证据。但是屈原却是充满着认同感情将鲧当成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待的。所谓鲧化为黄熊,或许是在流放地孤独无助病弱的鲧,以黄熊皮为衣呢!
被巫从羽渊中救活的鲧,最后还是被帝派来的祝融所杀死。这个帝,疑古者解为上帝,而古籍中的记载或为尧,或为舜。但是笔者还是相信《左传》《史记》的记载,应是舜。历史上任何明君,对反对派的处置,大都毫不留情。既然尧殛鲧三年后并没有对鲧执行死刑,那帝命祝融杀鲧就该是舜继尧位后的事。屈原在《天问》中没有提到鲧的死,也是对舜的回护吧!因为屈原对舜的行为即使有所置疑,但舜还是继尧之后治理天下的明君,屈原曾想:“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以吐心中的委曲,但是在写《怀沙》的最后日子里,就“重华不可遌兮,孰知余之从容”了,表示出对圣君们的最终幻灭,从容地选择走向与鲧相同的归宿了!
屈原在《天问》中对着苍天发出冲天之问:“天啊!为什么人世间会有那么多的丑恶事?为什么对忠直之士那么不公啊!”屈原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而呐喊吧?
作者单位: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