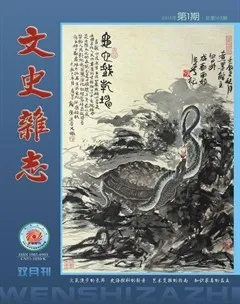余中英先生及其书法艺术略议
蜀中耆宿余中英先生是四川现代书法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新时期我省书法复兴繁荣的承前启后的奠基者之一。
先生于1899年生于郫县。其父以学为本,曾经商、吏生涯,有名于时;而中年尤致力书史研究,对先生之影响不言而喻。先生少时学军,正值上世纪初四川保路运动兴,辛亥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他自18岁任职川军始,历经军旅之苦,后来蜀中长期的军阀混战终致其35岁时决然离军。从军期间,他亦颇能体恤民生疾苦,并多倾心文翰,虚心请益时贤,曾深得赵熙先生称许。1932年,先生(34岁)即函请齐白石为受业弟子并幸得嘉许,次年醉心治印于战火之中。1933年至1934年间,先生负笈京华专心从白石老人学习篆刻书画,师生情笃,获白石师赠印、画若干。白石师赞其“三年一掷宦情轻”、“客居能自耐寥寥”、“蜀中不独官声美,篆刻犹堪后世名”。先生在京还结谊于徐悲鸿等名家;辞燕归蜀后,以书画印与四川诸名家多所过从,艺功日深。抗日战争兴,先生复从军参加抗战,历任军政数职。与此同时,其书法篆刻声名日盛,书迹流布甚夥。其任成都市市长期间还曾在抗战文化建设上致力,功载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余先生将所藏明、清、现代书画悉数捐献政府,为数甚丰,为成都市、四川省的博物馆建设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先生之为人,正直清明,刚毅儒雅,严谨精勤。他对书法艺术的研习则无一日懈怠,不论生活境况之顺逆,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敬畏和刻苦自励、虚心进取的学习精神;对后学则慈祥可亲,诲人不倦。我在“文革”时期曾经施孝长老师推荐往先生支机石住处请益多次,并获借怀素自叙长卷(赵蕴玉临本),又曾得先生之张迁碑临作一册。先生仅居一室,看书写字住宿狭容其中,自己烧饭即在窗外屋檐下置一蜂窝煤炉,生活之简陋清苦可想而知,但论书、挥毫却精神烁然!其景其情给人留下永难忘怀的深刻印象。
余老早年曾从著名书法家赵熙学书,又得齐白石先生指教,对北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他还转益多师,广泛地从秦篆、汉隶、晋唐楷书以及晋唐、宋、元、明多家的行草书中吸取营养,最终出之以隽拔峭劲、秾润雅练的鲜明个人风格。如果我们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北魏书及苏轼书那种横扁的取势,柳公权那种峻拔刚健的笔致,二王及米芾潇洒俊逸的气度,赵松雪那种研美儒雅的韵味——这多种养分,都化合到他的作品之中,成为他自己风格中的有机成分了;而其清刚缜密的人格特色则无疑是其书风的本质成因。
最能代表余老书风的是行草和小楷。行草书《杜甫诗·解闷》幅面不大,但全幅情感充沛,气势畅达。其结体以紧密稳健的横势为主,而破以洒落疏放的纵势,意态多变,相生相应;其章法密中见疏,擒纵对比,错落有致,虚实相映成趣;其用笔以铺毫方笔为主,辅以圆笔,振管直书,一气到底,在痛快豪健中见沉着含蓄,通篇体现出一种爽利超迈的气度,而用笔结字又透露着苏、米的神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老驾驭硬毫笔的精熟本领:使转灵活,中侧锋互用,藏露兼施,轻重递变,疾涩适度,铺得开收得拢,用侧锋取势而又力强气厚,显示出其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修养。同时,余老还把写隶、篆之所得融合到行草中,因而用笔能见到一种疾而涩、畅而厚、文而质的意味。对联“千章古木阴浓处,万卷藏书读尽时”苍劲遒润,气象朴茂,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更具新意,不愧是老年力作。
在余老的书艺中,小楷堪称精绝,尤为世所称道。他所书的《白居易诗八首》,通篇用意精密又不乏空灵,显得秀逸清健;用笔精到,笔划虽细如髭发,但势贯力到,笔笔不苟,意态完足;其结字章法在整齐精严中参差变化,略于典雅稳重的楷书中糅进流变的行书,和谐而又灵活。这样,使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意境的美。余老精于书法,也工于篆刻,能诗词,擅国画。他对传统书艺能突破一点,全面继承,综合运用。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作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